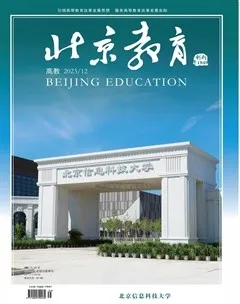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愛國主義教育的“反計算”策略探討
□ 文/劉 陽 劉永林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迭代更新,“計算宣傳”也成為人工智能時代的產物之一,并且作為“一種帶有明顯政治目的的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操控手段”[1]干擾著大學生的認知和行為。“計算宣傳”(Computational Propaganda)的概念最早由美國華盛頓大學學者塞繆爾·伍利(Samuel C.Woolley) 和英國牛津大學學者菲利普·霍華德(Philip N.Howard)提出,并將其描述為“以在社交媒體網絡上故意散布誤導信息為目的,使用算法、自動化和大數據分析等方式操縱公眾輿論的方式”[2]。吉利恩·博爾索弗(Gillian Bolsover)等學者也進一步認為“計算宣傳”是為達到特定目標而故意歪曲事實、逃避理性思維的傳播宣傳方式[3]。“從技術手段來看,計算宣傳基于算法運作機制,發展出制造利己趨勢、消除不利聲音和推薦垃圾信息等基本形式;從動機來看,計算宣傳以煽動公眾抗議、攻擊政治對手、破壞國家關系等為目的”[4]。
算法技術雖然能讓青年大學生充分享受人工智能時代的各種便利,但也更容易使他們迷失在人工智能的技術“陷阱”中。正處于“拔節育穗期”的大學生,思想觀念還不夠成熟,接受和化解不良信息的能力不均衡、不穩定,容易被“計算宣傳”的手段、技術、內容所迷惑,成為宣傳中“被計算”的主要對象。因此,高校愛國主義教育“要高度重視網絡作為各類風險的策源地、傳導器、放大器的負面效應”[5], 防范意圖破壞社會共識的人工智能技術手段,強化高校愛國主義教育實效。
“計算宣傳”對大學生愛國主義教育的影響
在人工智能背景下,“計算宣傳”蓄意動搖大學生愛國主義共識和愛國信念,惡意誘導大學生產生不良行為,嚴重干擾著高校愛國主義教育的育人效果。具體而言,涉及“知、情、意、行”四方面。
1.違逆教育主流方向,擾亂愛國認知。“計算宣傳”通過在社交媒體上組建大規模的機器人水軍、打造虛擬人設,頻頻推送、點贊、轉發不實言論,發起謾罵誹謗、線上騷擾等攻擊行為,不斷壓制愛國聲音,違逆主流思想,使大學生在雜亂的網絡信息中迷失愛國認知。例如:2022 年,自某地暴發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網上忽然曝出海量妖魔化的留言和推送,其中不乏“水軍”和“僵尸號”,它們通過制造虛假輿論,忽悠中國民眾向中國政府施壓,逼迫中國政府取消動態清零政策,營造民眾和政府對立態勢,而部分大學生受輿論蠱惑,在潛移默化中失去對社會共識的客觀認識和理性分析,產生了消極配合疫情防控措施的不良行為。
2.阻斷教育傳播鏈條,削弱愛國情懷。接受主流價值觀念的教育和滲透是大學生堅定政治認同、價值認同,樹立愛國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方式。然而,“計算宣傳”通過低質量的信息傳達和短時間的信息轟炸達到“劣幣驅逐良幣”的目的,不斷消解著大學生對愛國主義教育的價值需求和情感體驗。一方面,“計算宣傳”通過暗箱操作和技術手段過濾愛國主義教育訊息,降低主流價值信息在青年大學生中傳播的可能性和廣泛性,阻斷主流價值信息進入青年大學生視域,試圖在愈發堅固的“信息繭房”中隔斷大學生的愛國熱情;另一方面,借助搜索引擎、社交媒體平臺的信息抓捕和精準推送技術,以大量感官刺激、獵奇標題等噱頭性信息破壞愛國主義教育內容的吸引力,使青年大學生成為“吃瓜群眾”的主力,而對愛國主義的教育引導視而不見。
3.炮制不良教育內容,動搖愛國意志。“計算宣傳”以混淆真偽信息、安置誘導信息、制作虛假信息等作為內容“彈藥”,蓄意降低大學生對主流媒體和價值觀的信任度,動搖大學生的愛國意志。一方面,以一種“高級黑”“低級紅”的形式偽裝愛國主義教育內容,使得廣大青年放松對網絡信息的警惕性,在無形中挑唆其產生偏隘的言語和行動,動搖青年大學生的愛國意志;另一方面,部分不法分子通過“計算宣傳”對不良信息進行蓄意偽造、惡意拼湊,并借此挑起輿論事端,破壞大學生的社會信任譜系。例如:部分西方勢力建設僵尸網站和網絡部隊,精心炮制“實驗室泄漏病毒論”,將虛假新聞的傳播量級無限放大、相互論證,讓信息愈發難辨真假,挑戰大學生的愛國主義信念。
4.開展負向教育引導,培植對抗行為。愛國教育要求廣大青年自覺維護祖國的主權和獨立,能同一切阻礙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勢力進行斗爭。然而,“計算宣傳”嘗試通過發送各色各樣的騷擾、詐騙、非法廣告等垃圾信息,誘導青年大學生在信息化浪潮中迷失方向,產生不利于國家榮譽和利益的違法亂紀行為。例如:在公安部披露的大學生被策反案件中,不良組織借助計算手段廣泛撒網,以發布所謂的“兼職”廣告為慣用伎倆,對青年大學生進行思想滲透拉攏,誘騙大學生一步一步泄漏國家機密,產生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此外,部分不法分子借助“計算宣傳”開展意識形態“攻心戰”,促使青年大學生產生與愛國主義精神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對抗的社會行為。例如:部分西方主流媒體和網絡平臺藏著大批“僵尸機器人”,特別針對留學大學生推送和發表詆毀愛國主義的言論以洗腦他們,使其成為境外敵對組織人員,向境內倒灌“斗爭經驗”,產生直接的對抗行為。
高校愛國主義教育的“反計算”策略探討
如何提高“反計算”技術,凈化網絡生態,推動思想政治工作傳統優勢與信息技術深度融合,使互聯網成為引導學生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最大增量是高校開展網絡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落腳點。
1.以算法反制算法,削弱不良導向信息的錯誤干擾。高校愛國主義教育工作要善于運用網絡技術賦能意識形態安全教育,強化互聯網建設管理運用,加強對不良輿情的預警,最大程度地削弱“計算宣傳”等各類人工智能手段的負面影響。一方面,更新網絡技術手段,高效開展網絡輿情監控治理,如利用計算手段、網關技術、大數據處理技術、圖像和視頻處理技術、語義分析技術等及時限制和清除“僵尸號”“水軍號”,強化對學生網絡信息的跟蹤、篩查和分析,及時向公安網警反饋IP 地址、敏感網站等;另一方面,主動對學生常用互聯網平臺進行網絡輿情監控和風險監測,按聚集數量分類、分層、分流,通過人工智能手段對超過界限的網絡社群進行重點監控,對敏感詞匯和不良言論及時發出預警,并通過禁言、屏蔽、限流等果斷措施降低熱度,防止大規模的群體極化事件發生。
2.優化話語布局,堅守愛國主義教育文化陣地。調整內容布置、優化話語布局,是促進高校多途徑渠道吸引愛國主義教育受眾,增強教育感染力,實現觀念契合、價值共振的重要方式。高校要牢牢掌握教育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和話語權,善于通過算法和技術提升信息推送的均衡調控功能,將一定數量比的愛國主義教育內容分散在不同版塊內容的瀏覽信息中,橫縱遞進、反復強化,不斷暢通愛國主義精神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信息流。例如:通過話題置頂設置,將愛國主義教育融入主題宣傳、形勢宣傳、政策宣傳、成就宣傳中,引導大學生參與愛國主義教育議題和討論,鼓勵帶動學生主動打破“信息繭房”的束縛,積極開展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網絡文化陣地建設。
3.及時主動出擊,推進網絡愛國教育靶向到位。高校要及時抓取學生關注的熱門話題,有針對性地開展教育引導,及時防止各種錯誤意識形態在高校搶灘登陸。一方面,以輿情信息超前探測為支撐,了解學生關注的熱點話題,跟進學生的思想動態,對事關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則的誤導性信息和事件,要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以抽絲剝繭的方式及時分批次、分步驟提供有效信息,以層層跟進的方式對問題進行綜合性、深層次探討,幫助學生在輿論對壘中,明辨是非、凝聚共識;另一方面,高校要敢于亮劍,有理、有力、有節開展輿論斗爭,擊中“計算宣傳”中的虛假點、發酵點,對失實報道和輿論進行正面回擊,不避諱、不遮掩,突出重點、表述直接,切實提高大學生對事件本身認識的科學性、準確性。
4.提升算法素養,增強大學生規避“計算宣傳”的主體效能。在人工智能背景下,人機交互、AI 換臉、虛假音剪輯等深度偽造技術,擴增了人們“眼見為實”的盲區,使得“計算宣傳”的造假技術發揮得更加游刃有余。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線教師不僅要善于主動學習大數據等相關技術用以甄別網絡信息的真偽,從理論源頭和技術原理增強工作隊伍的數據能力[6],更要注重在日常愛國主義教育中幫助青年大學生掌握相關算法知識,了解算法背后的生產邏輯、目的意圖以及造成的認知偏差,最大程度上規避“計算”的負面影響。例如:2021 年8 月,上海交通大學面向高校大學生發起《提高“算法素養”倡議》,鼓勵大學生對“計算宣傳”的運算邏輯、慣用伎倆、功能特點有基本認識,時刻保持對“計算宣傳”的警惕性,時刻注重提升“反計算”能力。
5.注重以人為本,持續堅定大學生的愛國立場和行為。“計算宣傳”作為一種技術手段和方法,最終需要通過與人的交互作用實現信息的傳導、輸入與內化。因此,幫助大學生牢固確立愛國立場,堅定政治自覺意識是對抗一切意圖破壞愛國共識的重要舉措。一方面,高校愛國主義教育工作要立足當代大學生認知水平、思維方式、話語體系,教育引導大學生博學慎思、敏銳觀察,用清醒的頭腦思考問題,不信謠、不傳謠,堅持愛國主義信念不動搖;另一方面,高校要以真切互動的情感體驗、積極向上的引導性言論,時刻引導學生把愛國情、強國志、報國行融入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斗之中,[7]切實樹立起大學生愛國擔當的良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