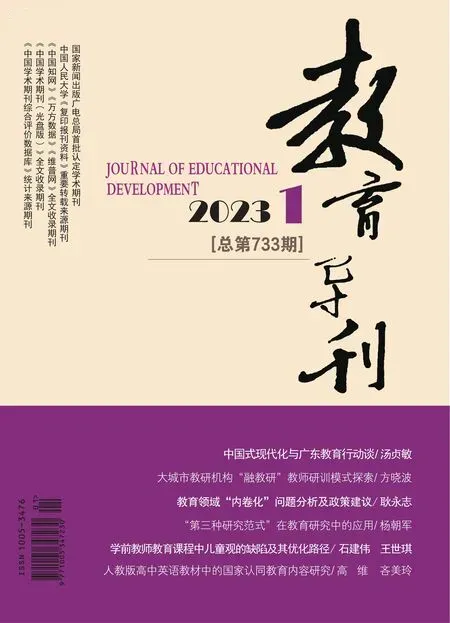“雙減”政策背景下智慧作業能否提升學生幸福感
——基于江西省78個縣(區)的調查數據分析
付衛東 馬沁雪 唐 旭
(1. 華中師范大學 人工智能教育學部,武漢 430079;2. 江西省教育技術與裝備發展中心,江西南昌 330046)
一、引言
著名教育學家烏申斯基說:“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學生獲得幸福。”〔1〕內爾·諾丁斯亦認為:“幸福與教育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幸福是教育的核心目的。”〔2〕站在以人為本的理念上,所有的教育都應當是幸福教育,是以培養能夠追求幸福、感受幸福的人為目的的教育〔3〕。而幸福感說到底是一種主觀感受和狀態,它主要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對自身生活滿意度的認知評價;另一部分是心理健康指標的情感反應,包括積極和消極的情緒〔4〕〔5〕。當前以“效益”為核心評價域的現代社會,引發了家長、教師與社會對學生過高的期望和要求,隨之而生的競爭化考試、題海戰術、課外“加餐”等使得學生的學業負擔逐日加重。已有研究發現,中小學生心理健康與生活事件間存在因果關系,學業負擔作為主要生活事件之一對心理健康起著重要的影響作用〔6〕〔7〕。同時,不同學生的學業負擔水平與生活滿意度上存在顯著差異,學業負擔水平低的學生生活滿意度顯著高于學業負擔水平高的學生〔8〕。總體而言,目前中小學生主觀幸福感情況不容樂觀,幸福感在不知不覺中悄然消逝成為當前教育事業中最大的問題〔9〕〔10〕。
2021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11〕(以下簡稱“雙減”政策),明確提出中小學生負擔太重,教育短視化、功利性等問題,要求減輕學生過重的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從而“提高教育教學質量和服務水平”“全面壓減作業總量和時長”“科學合理布置作業,提高作業設計質量”等,以期減輕學生學業負擔,提高學生主觀幸福感,實現以人為本的教育。為助推“雙減”政策落地落實,江西省教育廳組織研發面向全省中小學師生和家長的智慧作業平臺,在不改變傳統紙質作業書寫和批改習慣的同時,利用信息技術幫助教師優化作業設計、智能分析作業情況,并幫助學生智能生成錯題集、精準推送教學資源,實現個性化學習。當前江西省智慧作業已成功入選教育部落實“雙減”政策的典型案例,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12〕。誠然,智慧作業在提供優質教育資源、智能化作業管理等方面具有優勢,但其使用后能否有效提高中小學生主觀幸福感,推動教育生態良好發展更是我們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本研究擬通過對江西省11個市78個縣(區)的調查數據進行實證分析,了解智慧作業的使用能否有效提高中小學生主觀幸福感,進而為解決當前教育中幸福感缺失問題提供新的視角。
二、文獻綜述和研究假設
基于已有研究,主要有兩類指標被用來衡量主觀幸福感,即生活質量指標和心理健康指標〔13〕。生活質量指標指的是個人對生活滿意度的感知判斷,而心理健康指標指的是對積極和消極心理體驗的權衡〔14〕。一些研究者在感知層面上將主觀幸福感僅理解為生活滿意感,認為幸福感就是生活滿意感,是自身對生活質量的感知〔15〕。另一些研究者則在情感層面上將主觀幸福感等同于快樂感,認為幸福就是愉快的情感體驗〔16〕。然而,主觀幸福感并不是由單一因素構成的,而是以不同方式實現的這幾個要素的整合,應將它們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以便對主觀幸福感做出更全面的判斷。因此本研究對主觀幸福感的測量主要從三個因素出發,即生活滿意度、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
學術界的研究表明,主觀幸福感的發生機制是個體內在因素與外部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因此,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因素主要從內部和外部兩個視角出發進行探討。通過對已有研究的梳理,我們發現,性別、健康狀況、人格特征、自尊、自我提升、自我效能感和控制感等內部因素均與主觀幸福感呈一定程度的相關〔17-20〕;而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外部因素主要包含文化、地域、家庭環境、社會支持、收入水平等〔21-23〕。目前關于主觀幸福感的探討主要針對老人、心理疾病患者等成年特殊人群,多涉及一般生活領域,以影響因素和心理機制的研究為主,而有關青少年尤其是學生群體主觀幸福感的實證研究較少。已有研究表明,個體主觀幸福感狀態對其身心健康及其成長與發展有重大影響,主觀幸福感水平低的個體可能產生一系列消極后果,表現在學生個體上即可能出現成績不良、違紀違規、厭學退學等情況〔24〕。因此,為填補現有研究的空白,本研究強調主觀幸福感對學生群體的重要性,通過對青少年主觀幸福感的實證研究,豐富和深化主觀幸福感主題,以期促進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各方面素質的發展。
已有文獻指出,信息技術在教學中的應用可以使學生更有新鮮感,更能激發他們的學習主動性和興趣,同時也可以提高他們的注意力,使學習更加有效〔25〕。此外,基于互聯網的信息化教學還有利于克服學生的心理負擔。利用互聯網為學生提供自主學習和交流的空間,既有利于培養學生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還能夠幫助其克服學習過程中的膽怯心理及其他學習障礙,進而提高學生的學習自信心與學習成績〔26〕。作為利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輔助中小學作業的典型案例,江西省智慧作業平臺既有上述的教學優勢,又有自身的突出特點。智慧作業能夠滿足不同層次學生的學習需求,通過探索協商性作業分層設計避免了機械、重復、無效的作業練習,節省了作業時間,減輕了學生因作業太多無法有效完成作業的焦慮感〔27〕。智能化的作業分析、精準化的資源投送等也可以緩解學生在作業太難而無人幫助時的無力感。此外,智慧作業統計數據還顯示,長期使用智慧作業的學校,學生作業正確率和完成效率明顯提高,這極大地調動了學生作業的積極性,增強了學生的學習自信心〔28〕。因此,智慧作業的使用可能減輕學生學習焦慮,提高學習自信心。而生活滿意度又與自我效能感、心理壓力存在高度相關,所以智慧作業有可能會對生活滿意度存在積極的影響。鑒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1:智慧作業能減輕學生消極情緒,主要表現在學習焦慮、抑郁緩解。
假設H2:智慧作業能激發學生積極情緒,主要表現在自我效能感提升。
假設H3:智慧作業能提升學生生活滿意度。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所使用數據來源于華中師范大學研究團隊與江西省教育技術與裝備發展中心于2021年11月在江西省開展的“江西中小學智慧作業實施基本情況調查”,以中小學生及其家長、教師作為調查對象,問卷涉及江西省11個市78個縣(區)。對收集到的學生問卷進行專門數據清洗后,剩下28808份有效學生問卷。數據顯示,18379名學生(63.8%)使用“智慧作業”,而10429名學生(36.2%)沒有使用“智慧作業”。
(二)變量設定和描述
1. 關鍵自變量
本研究關注的問題為智慧作業的使用對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此研究的關鍵自變量為是否使用智慧作業。通過問卷中題項“你是否使用了智慧作業平臺?”進行測量,其中未使用取值為0,使用了取值為1。
2. 因變量
本研究涉及的因變量包括學習焦慮、抑郁、學習自我效能感、學校生活滿意度,分別對應四個量表,采用李克特4級或5級量表進行測量。而且,使用組合信度(CR)和克隆巴赫系數(Cronbach’s α)對研究工具進行信度檢驗,同時對聚合效度及區別效度進行了檢驗。
(1)學習焦慮量表改編自安東尼(2000)等編制的學習焦慮量表,共設置6道題目,經計算得到該量表的Cronbach’s α=0.891,CR=0.920,AVE=0.658,區別效度為0.811。
(2)抑郁量表源于中國教育追蹤調查(CEPS)2014-2015 學年調查八年級學生問卷,共設置10道題目,經計算得到該量表的Cronbach’s α=0.900,CR=0.909,AVE=0.528,區別效度為0.726。
(3)學習自我效能感量表改編自梁宇頌自編量表,共設置12道題目,經計算得到該量表的Cronbach’s α=0.944,CR=0.950,AVE=0.616,區別效度為0.785。
(4)學校生活滿意度量表源于中國教育追蹤調查(初中階段)2013-2014 學年調查七年級學生問卷,共設置12道題目,經計算得到該量表的Cronbach’s α=0.824,CR=0.933,AVE=0.544,區別效度為0.737。
可以看出:各組合信度 (CR) 和克隆巴赫系數均高于0.8,因此問卷信度良好;各構面的變量平均抽取方差 (AVE) 均高于0.5,表明構面聚合效度良好;各構面的AVE平方根均大于0.5,且均高于其余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表明各個變量之間具有良好的區別效度。整體來看,本研究所選用研究工具信效度較高。
3. 控制變量
研究前期,根據研究數據相關分析結果發現,年級、是否留守、家庭經濟條件及學生整體健康狀況會對學生的學習焦慮、抑郁及生活滿意度產生影響。同時,性別、年級、家庭經濟條件、整體健康狀況及自我教育期望也會對學生的學習自我效能感產生影響。因此,本研究將控制變量設置為:性別、年級段、是否留受、家庭經濟條件、整體健康狀況、自我教育期望。
(三)研究方法與思路分析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評估是否使用智慧作業對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即揭示是否使用智慧作業與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心理健康因素和生活質量因素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然而在實證研究中,內生性及樣本選擇偏差問題往往會對估計結果造成很大干擾。例如,在本研究中,最理想的方法是通過比較學生在使用智慧作業及不使用智慧作業時主觀幸福感上的差異,但現實中我們無法進行這樣的觀測,因為這種情況是一種“反事實”。因此,為解決上述問題,本研究使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簡稱PSM),通過構造“反事實”結果對變量之間實際因果關系進行檢驗。

表1 變量的名稱設定及說明

表2 主要變量的相關性分析結果
PSM的基本思想是構建一個未使用智慧作業組(即控制組),其與使用智慧作業組(即實驗組)在使用智慧作業之前的主要特征盡可能相似,然后將實驗組的學生與控制組的學生進行匹配,使匹配后的學生僅在是否使用智慧作業方面有區別,而其他方面相同或非常相似。由此,就可以用匹配后的控制組來最大限度地近似替代實驗組的“反事實”,最后再比較實驗組使用智慧作業后兩組學生在學習焦慮、抑郁、學習自我效能感及生活滿意度之間的差異,由此來確定是否使用智慧作業與學生主觀幸福感之間的因果關系。其中,我們將是否使用智慧作業對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因果影響表示為使用智慧作業的“凈效應”,即實驗組學生的平均處理效應(average effect of treatment on the treated, ATT),具體模型表示如下:
ATT=E{E[Y1i-Y0i|Di=1,p(Xi)]
=E{E[Y1i|Di=1,p(Xi)]-E[Y0i|Di=0,p(Xi)]
其中Y1i和Y0i為因變量,分別代表學生個體i在使用和未使用智慧作業兩種情況下主觀幸福感的得分情況;Di是關鍵自變量,意為個體是否使用智慧作業的虛擬變量,若參與則Di=1,未參與則Di=0;p(Xi)是傾向值,代表在控制性別、年級段、是否留受、家庭經濟條件、整體健康狀況、自我教育期望的情況下,個體i使用智慧作業的概率。
為了進一步分析是否使用智慧作業與學生主觀幸福感的關系,本研究基于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模型,實證分析是否使用智慧作業對影響學生主觀幸福感因素的作用機制。有研究表明,學習焦慮能夠顯著負向預測學習自我效能感,體現在自我效能感的形成受到情緒喚醒的影響,如強烈的厭惡、恐懼、焦慮等消極情緒往往會降低學生的學習自我效能感,使學生對自己的學習能力失去信心〔29〕。自我效能感又能正向預測作為主觀幸福感認知成分的生活滿意度〔30〕。如果使用智慧作業能夠降低學生的學習焦慮,提高學習自我效能感和生活滿意度,那么使用和未使用智慧作業的兩組在“學習焦慮→學習自我效能感”和“學習焦慮→生活滿意度”的關系上應該有所不同,使用智慧作業小組的學習焦慮對學習自我效能感和生活滿意度的影響應該比未使用小組更強。此外,如果使用智慧作業能夠同時增強學習自我效能感和生活滿意度,那么“學習自我效能感→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在使用和未使用智慧作業兩組上應該沒有差異。因此,我們構建了如圖1所示的理論模型,將生活滿意度作為因變量、學習焦慮作為自變量、學習自我效能感作為中介變量,是否使用智慧作業作為調節變量。

圖1 學習焦慮、學習自我效能感、是否使用智慧作業與生活滿意度的假設關系
四、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不同智慧作業使用狀態學生基本情況對比
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顯示,在消極情緒上,使用了智慧作業的學生其學習焦慮和抑郁程度顯著低于未使用智慧作業的學生;在積極情緒上,使用智慧作業的學生學習自我效能感強度顯著高于未使用智慧作業的學生;在生活滿意度上,使用智慧作業的學生生活滿意度得分顯著高于未使用智慧作業的學生(詳情見表3)。總體來看,使用智慧作業的學生學習焦慮和抑郁程度更輕,對生活的滿意度較高,同時在學習上的自我效能感也較高,這表明智慧作業可能是引起學生主觀幸福感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基于此,在“雙減”政策背景下研究智慧作能否提高學生主觀幸福感的確有必要。

表3 不同“智慧作業”使用狀態學生基本情況對比
此外,在實驗組與控制組中,學生在除性別外的其他變量間,如年級段、是否留受、家庭經濟條件、整體健康狀況、自我教育期望之間均存在顯著差異,這表明在分析中的確會造成內生性及樣本選擇偏差問題。為探尋是否使用智慧作業對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影響能否達到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水平,本研究使用智慧作業為因變量,將性別、年級段、是否留受、家庭經濟條件、整體健康狀況、自我教育期望作為自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其結果如表4所示。
(二)PSM模型
1. 預測傾向值
本研究首先采用Logit模型考察影響學生使用智慧作業和未使用智慧作業的因素,表4中數據結果表明學生的性別、年級段、整體健康情況與學生是否使用智慧作業影響不顯著。然而,是否留守、家庭經濟條件及自身教育期望對學生使用智慧作業均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具體來看,非留守兒童使用智慧作業的概率比留守兒童顯著高14.5%,家庭經濟條件越好的學生使用智慧作業的概率越高,自身教育期望越高的學生使用智慧作業的概率越高。因此,為避免樣本選擇偏差問題,有必要對這些協變量加以控制。

表4 以使用智慧作業為因變量的Logit回歸分析結果
2. 樣本匹配效果檢驗
由于最近鄰匹配法是最常用的匹配方法,具有最佳和最接近事實的匹配效果,所以本研究采用k近鄰匹配(k=4)后的Balancing檢驗結果〔31〕。通過表5的檢驗結果可以發現,匹配前除性別外,年級段、是否留守、家庭經濟條件、整體健康情況及自身教育期望均存在顯著差異,匹配后所有協變量實驗組和控制組兩者之間標準化的偏差大幅下降,%bias絕對值全部低于5%,消減在60%以上,表明匹配效果良好。

表5 匹配前后Balancing檢驗結果
從圖2可以看出,實驗組的大部分樣本都能與控制組的樣本相匹配,而且實驗組和控制組樣本的數據存在重疊,即存在共同取值區間,總的來說,樣本匹配情況良好。

圖2 匹配結果傾向得分分布圖
3. 使用智慧作業對主觀幸福感影響的估計結果
在本研究中,基于logit回歸計算傾向得分值,并進一步選擇k近鄰匹配法(k=4)來探討使用智慧作業對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凈影響,分別對假設1-3進行檢驗。
(1)對假設H1的檢驗結果。
從表6中可以看出:①無論是匹配前還是匹配后, 實驗組學生的學習焦慮和抑郁程度均小于控制組;②匹配前ATT的絕對值均大于匹配后ATT的絕對值,這說明利用PSM法匹配后的確消除了部分內生性問題,使得匹配后樣本間更具有可比性;③樣本匹配后,實驗組的ATT值分別為-0.033及-0.068,且均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

表6 是否使用智慧作業對消極情緒的影響匹配結果分析
以上分析表明,使用智慧作業的確能夠顯著降低學生的學習焦慮和抑郁程度,該統計結果與表3中的描述性分析結果相一致,由此假設H1成立。
(2)對假設H2的檢驗結果。
從表7的匹配結果中可以看出,在完成匹配后, 實驗組學生的學習自我效能感高于控制組,并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這與表3的描述性分析結果相一致,即使用“智慧作業”后學生學習自我效能感提升,由此假設H2成立。

表7 是否使用智慧作業對積極情緒的影響匹配結果分析
(3)對假設H3的檢驗結果。
表8結果顯示,在完成匹配后,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在生活滿意度上呈現出明顯差異,其平均處理效應(ATT)值在1%水平上顯著正影響,由此可見,使用智慧作業能夠提升學生生活滿意度,這與表3中的描述性分析結果一致,由此假設H3成立。

表8 是否使用智慧作業對生活滿意感的影響匹配結果分析
4. 模型穩健性檢驗。
為保證本研究結果的穩健性與可靠性,研究綜合采用半徑匹配法、卡尺最近鄰匹配法、核匹配法的方式對使用智慧作業的平均處理效應(ATT)進行穩健性檢驗。分析結果與k近鄰匹配法(k=4)所得結果基本一致,使用智慧作業對學習焦慮和抑郁有顯著負向影響,對學習自我效能感和生活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總體而言,使用智慧作業能夠有效提高學生主觀幸福感。

表9 穩健性檢驗結果
(三)使用智慧作業影響主觀幸福感的機制分析
本研究所構建的理論模型符合Hayes的第59號模型,使用SPSS26.0的Porcess插件對該模型進行檢驗。將學習焦慮設置為自變量,生活滿意度設置為因變量,學習自我效能感作為中介變量,是否使用智慧作業作為調節變量,bootstrap種子數設置為5000進行分析。首先,簡單中介效應檢驗結果是:Effect=-0.148,BootSe=0.002,BootLLCI=-0.153,BootULCI=-0.143,[BootLLCI,BootULCI]區間不包含0,學習自我效能感在學習焦慮和生活滿意度之間的中介效應顯著,說明學習焦慮能夠通過學習自我效能感對生活滿意度產生影響。在控制學習自我效能感這一中介變量后,學習焦慮對生活滿意度的直接效應依舊顯著(LLCI~ULCI為-0.137~-0.125,區間不包含0,具有顯著負向影響)。可見,一方面學習焦慮能夠直接對學生生活滿意度產生影響,另一方面學習自我效能感也能夠影響生活滿意度,且此結論與已有研究相契合。
如表10所示的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可以看出,是否使用智慧作業與學習焦慮的交互項對學習自我效能感的影響顯著(β=-0.031,p<0.05),說明使用智慧作業在學習焦慮對學習自我效能感的影響中起到調節作用。圖3的簡單斜率分析表明,對于未使用智慧作業的個體,學習焦慮對學習自我效能感的負向影響顯著(β=-0.393,95%CI=[-0.409,-0.377],p<0.05),而對于使用智慧作業的個體,學習焦慮對學習自我效能感的影響作用增強(β=-0.424,95%CI=[-0.436,-0.4122],p<0.05),這說明與未使用智慧作業的學生相比,使用智慧作業的學生學習焦慮對學習自我效能感的影響更加明顯。同時是否使用智慧作業與學習焦慮的交互項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顯著(β=-0.025,p<0.05),說明使用智慧作業在學習焦慮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中也起到調節作用。圖4的簡單斜率分析表明,與未使用智慧作業的學生相比,使用智慧作業的學生學習焦慮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更加明顯。然而,是否使用智慧作業負向調節了學習自我效能感對生活滿意度的正向影響(β=-0.013,p<0.05)。上述相關分析結果顯示,使用智慧作業的學生學習自我效能感更強,生活滿意度也更高。

表10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n=28808)

圖3 是否使用“智慧作業”調節效果圖1

圖4 是否使用“智慧作業”調節效果圖2
五、結論與對策建議
(一)結論
基于以上實證分析結果,本研究認為使用智慧作業能夠對學生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滿意感產生積極影響,能夠推進“雙減”政策落地,提升學生主觀幸福感,實現以人為本的教育目標。
第一,智慧作業的實施能夠減輕學生的消極情緒,幫助學生緩解學習焦慮和抑郁感。這點與關于江西省智慧作業實施的新聞報道觀點一致。《中國教育報》的報道《江西為落實“雙減”注入“智”動力——作業更智慧 學生不喊累》提及,通過分層作業和“舉一反三”練習,能夠實現個性化學習,幫助學生擺脫題海戰術,同時名師微課又能幫助學生解決學習中的難題,促進對知識的掌握〔32〕。因此,對使用智慧作業的學生而言,長時間海量刷題的枯燥感、作業過多無法完成的焦慮感、作業太難無人幫助的無力感等消極情緒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這與本研究結論相符。
第二,智慧作業的實施能夠激發學生的積極情緒,促進學習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同時調節效應顯示,使用智慧作業使得學習焦慮對學習自我效能感的負向作用得到強化,表明使用智慧作業一方面能夠降低學生學習焦慮和抑郁感,另一方面能夠使學生學習自我效能感增強,在一定程度上對學生的心理健康產生積極影響。該結論與智慧作業相關信息觀點一致。例如,《江西日報》的報道《江西省推行“智慧作業”落實“雙減”》言及,通過大數據統計和調查問卷回訪,使用了智慧作業的學校,學生作業正確率提升了3%至5%〔33〕,增強了學生對自身學習能力的信心,提升了學習自我效能感。李章科的研究認為,使用智慧作業一方面能夠促進學生對知識的掌握,提升學習效果;另一方面有助于培養學生良好的自學能力和學習習慣,有利于學習能力和心理調控等多方面的發展〔34〕。通過提高學習能力和學習效果,使學生處于積極的身心狀態,從而使他們體驗到更多的成功,對自己的學習更有信心,有更高的學習自我效能感。
第三,智慧作業的實施能夠提高學生生活滿意度。調查顯示,使用智慧作業的學生生活滿意度顯著高于未使用智慧作業學生。中介效應顯示,學習焦慮能夠通過學習自我效能感對生活滿意度起到負向作用,在此基礎上的調節作用顯示,使用智慧作業的個體,學習焦慮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作用更強。此外,學生問卷中關于智慧作業實施情況的調查顯示,在使用智慧作業后71.2%的學生表示作業量減輕,72.8%的學生表示學習壓力減輕,72.6%的學生表示學習興趣提升,這也能從側面反映出學生生活滿意度有所提高。
(二)對策建議
基于以上結論,為充分發揮智慧作業在提高學生主觀幸福感上的作用,特此提出如下對策建議。
1.加強智慧作業推廣力度,落實智慧作業常態應用
智慧作業的實施在提高學生主觀幸福感上成效顯著,為使智慧作業惠及更多更廣的學生,加強智慧作業推廣力度勢在必行。目前,江西省已在全省范圍內探索推廣智慧作業平臺,已使用學校達7359所、使用的師生數達479萬人〔35〕。下一步應繼續擴大智慧作業應用范圍,以期實現智慧作業全省全覆蓋。同時,智慧作業平臺常態化應用問題也不容忽視。從已開展的智慧作業推廣工作中可以看出,雖然智慧作業平臺具有諸多優勢,但是學生和教師多年來養成的學習和教學習慣并非能輕易改變。因此,從推廣智慧作業的應用到常態化應用間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未來,政府在擴大智慧作業平臺覆蓋面的同時,還需加強開展面向學校師生的平臺應用培訓,進一步挖掘平臺應用典型案例、推廣應用典型經驗,監督學校智慧作業使用率,進而落實智慧作業平臺的常態化應用。
2. 精準定位學生學情,重點優化作業設計
作業量過大會導致大腦疲勞、精神狀態不佳,是產生學習焦慮的外在影響因素;因做題效果不理想而產生的自卑、否定等不良心理可能是產生學習焦慮的內在因素。然而,簡單粗暴地減少作業量和作業難度,并不能有效緩解學生的學習焦慮,反而可能增加學生和家長的焦慮。因此,根據學生不同的學習情況設計分層或個性化作業至關重要。研究結果表明,江西省智慧作業平臺運用新興信息技術,通過分層作業和“舉一反三”練習,實現了減輕作業量、提升學習效果的目標,緩解了學生的學習焦慮。但是調查結果顯示,仍有28.8%的學生表示作業量沒有減輕,58%的學生表示沒有設置分層作業,84.6%的學生表示會將分層作業全部完成。為改變此現狀,應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信息技術,使智慧作業能夠更加精準定位學生的學習情況,并根據學生學情設置更適合學生的分層作業,通過嚴格控制作業量并實時調整作業難度,實現緩解學生學習焦慮,提升學習自我效能感,提高學習效率的目標。
3. 共建共享名師微課,創新實施翻轉課堂
智慧作業中的名師微課既能解決學生在家無人指導作業的難題,還能幫助學生鍛煉自主學習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能夠有效提高學生的學習自信心和學習效率。雖然目前智慧作業已經建設了52.8萬多個微課,涵蓋了江西省教育廳教輔目錄中所有練習冊的作業題目〔36〕,但微課資源還需要不斷豐富和動態更新。同時,還需要不斷加強對微課質量的審查,進一步完善優質名師微課資源建設。此外,目前智慧作業中的名師微課主要針對練習冊的作業題目,未來還可以拓寬微課范圍,變革現有教學模式,實施基于微課的翻轉課堂教學。學生通過提前觀看微課對即將學習的內容進行預習,然后在課堂中對預習過程中存在的疑點和問題進行討論,最終實現知識的深度內化。基于微課的翻轉課堂教學模式能夠提高學習效率,增強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和學習信心,這對提高學生主觀幸福感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本研究針對江西省智慧作業對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豐富了主觀幸福感的研究主題,對落實“雙減”政策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之處:其一,對主觀幸福感的測量從“消極情感”“積極情感”“生活滿意度”三個因素出發,但所選取的相關變量較少,后續還可加入學習興趣、自尊和自卑等變量,分析使用智慧作業對上述變量的影響;其二,以實證調查為主,缺乏質性研究,調查數據無法完全反映學生真實情況,后續應著重走訪各中小學,更深入了解使用智慧作業對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