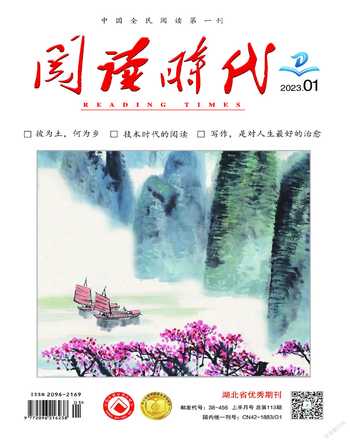藏在火鍋背后的逸聞趣事
王寧

在諸多美食中,火鍋可謂一個奇特的存在。它以水為介質,聚齊了中華美食的關鍵——湯羹、調味、面點、時鮮與葷食,它并不依賴廚師,卻集烹飪與品味于一處,鮮綠紅白皆可調涮。
中國人愛吃火鍋。這一份熱愛,并非今人的專屬情結,自古以來就有不少名人雅士成為火鍋的擁躉,對其品評與揮毫。甚至不少流傳至今的美味火鍋配方就出自他們之手。
每一餐火鍋都能有一段故事,火鍋不但滿足了人們的口腹之欲,也見證了歷史的翻滾沉浮,更彰顯了傳統飲食文化的魅力所在。
海昏侯墓中的“火鍋宴”
2016年10月,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墓發掘結束。在眾多出土文物中,有一件“三足”青銅器比較引人注目,當時根據使用功能被命名為“銅火鍋”。后經多位考古學家再三論證,更名為“溫鼎”。
“溫鼎”一詞見于諸多古籍,其歷史可追溯于商周時期。冬日天氣寒冷,盛出的飯菜很容易變涼,在沒有家用電器的時代,古人用溫鼎來作保溫鍋,通過內置炭火,以保證鼎內食物溫熱不冷。而到了西漢時期,溫鼎的功能被進一步擴展。海昏侯墓出土的這件器物,上端是一個肚大口小的容器,便于蓋上蓋子,下端連接著一個炭盤,之間并沒有連通,儼然是個實用型火鍋。
考古人員發現,溫鼎有被用過的痕跡。如炭盤里有燒過炭的跡象,鍋內也有使用過的痕跡,甚至還有板栗等殘留物。由此判斷,這尊銅火鍋很有可能是海昏侯劉賀生前使用過的物品,而作為陪葬品入葬,說明他十分喜歡吃火鍋。
不僅如此,在海昏侯墓中還出土了一件染爐,似乎更能說明問題。
染爐是西漢時期常見的飲食器具,底下有托盤,托盤之上是個炭爐,上面有銅耳杯,是成套使用的器具。當時人們使用分餐制,一人一案,宴飲時一人一套,隨吃隨用。食材從溫鼎中取出,再通過染爐蘸取調料、醬汁后食用,現代人享用火鍋的方式已初見雛形。
可以想象,在2100多年前的西漢海昏侯國,當精美的食案食具井然有序地擺置好,一場華麗風雅的火鍋筵席開始了。侍者捧食進饌,仕女翩翩起舞,劉賀與賓客們正襟危坐,吃著涮肉,欣賞著歌舞,把酒言歡,好不熱鬧。
有歷史學家曾表示,漢代的火鍋品種其實有很多,并不是人們想象中的那么少,不僅種類多,式樣也多。除了銅火鍋外,還出土過陶火鍋、鐵火鍋等器物。
江都王與他的“鴛鴦鍋”
漢代火鍋宴飲之風從海昏侯墓中可見一斑,而喜歡火鍋的王公貴族絕非劉賀一人。在江蘇盱眙大云山漢墓中,曾出土過一件“分格鼎”,直接證明墓主人、西漢江都王劉非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火鍋“吃貨”,而且還考證出他喜歡吃類似“九宮格”的火鍋。
劉非是漢景帝劉啟第五子。在當初爆發的吳楚七國之亂中,年僅15歲的劉非率軍擊破吳軍,戰功顯赫,受封江都王。在位期間,劉非廣招賢才,其中就包括一代大儒董仲舒。
閑暇之時,劉非也專注于“舌尖上的生活”。他不但愛吃火鍋,還會吃火鍋,專門有一套火鍋炊具供其使用,而這件分格鼎便是其中之一。劉非平時用它來涮涮肉、燙燙菜,日子過得頗為愜意,成為少有的幾位善終的諸侯王。
分格鼎也叫“五格儒鼎”,做工特別,也格外精致。將蓋子打開之后,可以看到在鼎中分布著5個小格子,中間為圓格,可將狗、羊、豬等肉品放在不同格中,從而能吃到不同風味的火鍋。而且不同的燒煮空間,還能將不同的味道分隔開來,從而避免串味,方便不同飲食習慣的食客食用。分格鼎可以說是“鴛鴦鍋”和“九宮格”的前身了。
《三國志·魏書·鐘繇傳》里也提到過“分格鼎”這一多功能鍋,取名為“五熟釜”。里面的故事記載,魏文帝曹丕賜給相國鐘繇一個“五熟釜”。為了表示對鐘繇的重視,曹丕還在鼎上鐫刻了銘文。所以不難推測,分格鼎其實是宮廷貴族才可以享用的一種炊具。
說不盡的菊花暖鍋
每逢“家家菊盡黃,梁國獨如霜”的季節,若采下清香宜人的白菊花入饌,則有“菊花暖鍋”。席間食客將主料在撒有菊花的沸湯中涮透蘸食,吃完主料后,原湯中放面條,帶湯而食,情趣盎然。
說到菊花,我國食菊的習俗歷史悠久,戰國時期屈原在《離騷》中就說:“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這無疑是指吃菊花。除了屈原之外,漢代《西京雜記》里說:“漢人采菊花并莖葉,釀之以黍米,至來年九月九日,熟而就飲,謂之菊花酒。”西晉傅玄在《菊賦》中寫道:“服之者長壽,食之者通神。”
要說把菊花吃到一定境界的,非東晉大詩人陶淵明莫屬。“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眾所周知,陶淵明愛菊、食菊,那究竟偏愛到何種地步呢?南梁蕭統《陶淵明傳》記載道:“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據說,陶淵明不但發明了菊花酒還創出了菊花火鍋。有一日,五柳先生突發奇想:若將菊瓣撒入鍋中,會是怎樣滋味?于是,他將庭園中盛開的白菊花剪下來,掰瓣洗凈,投入鍋中,味道果然令人叫絕。從此,每逢菊花盛開的時節,陶淵明都以菊花火鍋招待他的好友。
在歸隱田園的日子里,陪伴陶淵明的,只有詩、酒、菊和火鍋。很顯然,這四者可以有效結合,將火鍋吃出一種意境來:吃火鍋時,在火鍋中放上幾朵菊花,這樣一來,舉杯飲酒,低頭有花,腹中有肉,何愁作不出好詩?
這種新鮮的吃法在唐代受到了追求意境享受的文人騷客熱力追捧,被時人稱為“菊花暖鍋”。
到了清代,菊花暖鍋被慈禧太后列入冬令的御膳之中。每至深秋初冬,御膳房每日都會采摘鮮白菊數朵,清水洗凈,然后讓慈禧太后用暖鍋雞湯涮而食之。
據德齡《御香縹緲錄》記載,為慈禧太后制作菊花暖鍋,需先采下一種名喚“雪球”的白菊花。雪球的花瓣短而密,且非常潔凈,特別宜于煮食,每次總是隨采隨吃。
開餐前,內侍先從御膳房端出一具銀質的小暖鍋來,里面已盛著大半鍋原汁雞湯或肉湯。暖鍋的蓋子做得非常合縫,易于保溫。此時,慈禧太后座前已放好一張比茶幾略大的小餐桌,桌子的中央有一個圓洞,恰好可以把暖鍋安安穩穩地架在中間。和暖鍋一起端出來的是幾個淺淺的小碟子,里面盛著已去掉皮骨、切得很薄的生魚片或生雞片,外加少許醬醋。
負責掌管膳食的太監把暖鍋蓋子揭起來,擎在手里候著,慈禧太后便親自揀起幾許魚片或肉片投入湯內,太監忙將鍋蓋重復蓋上。五六分鐘后,又將蓋子揭起,慈禧太后自己將菊花瓣抓一把投下去,接著仍把鍋蓋蓋上,再等候五分鐘便煮成了。
每次揭鍋蓋投菊花的時候,慈禧太后總是不住口地指揮著。魚片在雞湯里燙熟后的滋味已經鮮美可口,再加上菊花所透出來的清香,更是人間美味。
在江蘇揚州的傳統美食中,也有一道“菊花暖鍋”。不同的是,這個暖鍋里并不含菊花,只有“四葷四素一雞湯”。四葷指的是生雞片、精肉片、腰片和魚片;四素指的是黃花菜心或青菜心、粉絲、麻油馓子、金剛臍;雞湯即湯底,是用冬筍、雪菜配合排骨、豬蹄以及雞湯熬制而成的。
既然菜中沒有一項包含菊花,何來“菊花”之名?原來,以前的家庭都要準備一只紫銅鍋,當地俗稱“暖鍋子”,在爐腔里加足點燃的火炭,出來的火焰就像一朵綻放的菊花。最重要的是,所涮的菜品無論是葷菜還是素菜,在揚州大廚的精心加工下,要做到“刀下生花”,裝盤的形狀都如菊花,十分精致。吃火鍋講究一個“燙”字,菜品放進雞湯里涮兩下就要熟。所以,菊花暖鍋里的生雞片、精肉片、腰片、魚片都是由廚師一刀一刀劈出的細薄片,極其考驗刀工。
名詩佳句贊火鍋
唐代時,更多的達官貴人開始迷上了小火鍋。白居易的《問劉十九》一詩就惟妙惟肖地描述了當時食火鍋的情景:“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有綠映襯著紅,把酒圍坐在火鍋邊,白樂天等待著劉十九的到來。雖然詩文沒有寫后來的情景,卻讓人極易聯想到最后盛情難卻,對坐而飲,說些新聞舊識。天色暗下,外面大雪紛飛,室內火光搖曳,鍋中冒出的蒸汽氤氳繚繞……如今讀來仍有一番暖意涌上心頭。
宋代詩人陳藻,終生不仕,授徒不足自給,課妻子耕織以為生。深秋的時候,他去訪問老朋友,人家用新釀制的美酒與火鍋款待他,陳藻吃罷贊不絕口,留下一首七絕:“白秫新收釀得紅,洗鍋吹火煮油蔥。莫嫌傾出清和濁,勝是嘗來辣且濃。”
明代大才子楊慎小時候隨其父楊廷和赴明孝宗在御花園設的酒宴。宴上有涮羊肉的火鍋,火里燒著木炭,皇帝借此得一上聯“炭黑火紅灰似雪”,要眾臣對出下聯。大臣們頓時個個面面相覷。這時楊慎不緊不慢地答道:“谷黃米白飯如霜。”眾人皆驚,為這么小的孩子有如此才智而稱贊。這個對聯也是對得既工整又巧妙,因為火鍋一直都需要炭火加熱,木炭原本顏色是黑的,燒得旺的時候才變得通紅,燃燒殆盡就只剩下白色的灰燼,所以這句對聯,暗藏邏輯,并不好對。但楊慎雖然只有十歲,卻能在皇帝面前勇敢發言。下聯也是用了層層遞進的關系,從稻谷變成米再到飯,不光顏色對應,邏輯關系也對應,因此當下讓所有人都刮目相看。
清代進士嚴辰吟善于吟句對聯,他為火鍋撰聯甚多。“圍爐聚炊歡呼處,百味消融小釜中”,這是表達對火鍋的無限熱愛與向往;“熊熊烈火燒出天下美味,滾滾沸水煮盡人間佳肴”,這又道出了火鍋的真諦;“各取腹所需,各吃口所長”,這是火鍋愛好者們最典型的神態。
(源自《中國食品報》,有刪節)責編: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