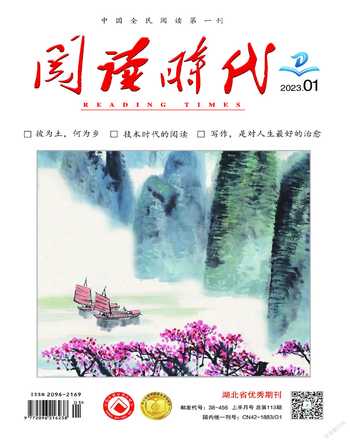尋找中國文化的源頭活水
甘武進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三江源地區注定是刀戟搏擊、戰爭高發的邊防要沖,“更在青海湖以西”的地理環境,自古以來,極大影響著中原官員、文人士子們對此地的環境認知與文化表達,也加深著內陸士人對蠻荒邊塞的恐懼與逃避。這里沒有連綿的農田,嚴寒干燥,滿目荒涼,在富庶而溫文的中原人士眼中,這里當然不是實現社會生命價值的理想處所,更不可能成為他們魂牽夢繞的精神家園。
多年來,人們對三江源自然和地理環境的認知,始終局限于“亞洲水塔”之類的概念,以及來自官方和旅游者的新聞報道、旅游攻略;但我們一直忽略了,作為一種空間文化現象的三江源:那是一個動態的、原初的、高古的、變易不居而令人悲欣交集的文化空間地帶。在《江河之上:三江源的歷史與地理》這本書中,作者劉東黎從歷史、地理、人文的角度,進行鉤沉梳理、深入探尋,尋找中國文化的源頭。
劉東黎,文化學者,近年來致力人文地理和自然文學創作。三江源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腹地,也是孕育中華民族、中南半島悠久文明歷史的長江、黃河和瀾滄江的源頭匯水區。它對影響中國數千年歷史的河西走廊、青藏高原、蒙古高原、黃土高原,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作者對三江源牧區、河流、自然環境進行了深入觀察,引領讀者奔走于懸崖荒野,撿拾失落的文明;同時微觀呈現漢藏民族的歷史記憶、生活史、風物志,與三江源遼闊的知識場域和文化地理空間相得益彰。
對“源”的探尋,就是對民族文化的尋根。作者描繪了中國古人對江河之源探索的史詩。黃河上源一帶的地理狀況,漢以前為戎羌諸族所占據。隨著人們對河源的追尋,漢朝在黃河的“源頭”設立了“西域都護府”。西晉博物學家張華指出了黃河相對具體的發源地:“河源出星宿,初出甚清,帶赤色,后以諸羌水注之而濁。”至隋代,世人認識到黃河河源在青藏高原。到了唐代,“河源”常出現在詩文之中,如“簫聲去日遠,萬里望河源”“鄉關萬里無因見,西戍河源早晚休”等,表現了當時詩人對河源的情感與態度。
作者實地考察了三江源的歷史地理與人文風物,為讀者呈現出立體狀、多層次的當地社會風貌,以豐富的故事與豐沛的情感打通古今,講述三江源地區所承載的愛恨悲歡。玉樹,那里是三江源的核心區域,海拔5000多米以上的山峰多達2000多座,境內東西昆侖山及其支脈巴顏喀拉山屹立于北,可可西里山、祖爾肯山屏障在西,唐古拉山綿延于境南。這里是“名山之宗、牦牛之地、歌舞之鄉”,也是大山之源、冰雪之源、江河之源,是一片“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土地。
20世紀80年代開始,三江源地區的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幾十年間,三江源地區4000多個湖泊中半數以上枯竭,冰川干涸,這對青藏高原乃至整個亞洲的氣候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于是,政府啟動了三江源生態保護與建設工程。原本已經變成沙土的草原重新綠了起來,野生動物開始頻繁出現。這一切,都有著三江源移民無聲的付出。不過,無論發展經濟還是保護環境,地方政府并沒有通過移民將三江源地區的民族文化邊緣化,三江源移民與這片土地,依然唇齒相依,難以分離。
每一個人都像一條潺潺的溪流,渴望看到大海、融入大海,盡管很多探求最終沉入沙土,無聲無息。然而,江河標記了一個人故鄉的所在。作者說:我看著遠山遠河的起伏,用文字記錄人與河流容與共的畫面,感受時代浮沉,經受洗禮。或許這種想象性的書寫只是一種幻象或徒勞,但同時似乎又具備著某種未知的吸引——江河與根系中涌動的源頭活水,會把兩樣東西永留于世,那就是精神的翅膀與文化的根。
(作者系本刊特約撰稿人)責編: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