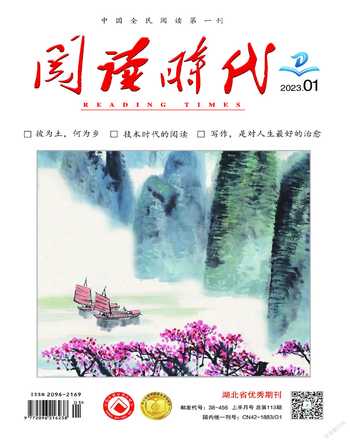讀書為何
黎戈
出門接孩子放學(xué),把看到一半的西西老師的新書《欽天監(jiān)》反扣在桌面上。回家后,我媽對(duì)我說她也翻了兩頁,很喜歡作者的表達(dá)方式,我說是啊,她一開口,無論說什么,我都很愿意聽。
她是寫長(zhǎng)篇小說的人,必須克制沉著。她的行文速度、緩緩道來的耐心,宛如春風(fēng)拂面,不是那種高壓輸出觀點(diǎn),氣勢(shì)洶洶、挾帶一股凌人的寒氣,讓我有一種被尊重的感覺。
我繼續(xù)說:“包括在網(wǎng)絡(luò)上,每個(gè)熱點(diǎn)新聞出現(xiàn)時(shí),我都特別希望有優(yōu)秀的一線記者能去實(shí)地做個(gè)翔實(shí)的訪談,多展現(xiàn)一些真實(shí)的人事視角,或者是長(zhǎng)期關(guān)注該領(lǐng)域的專業(yè)人士能提供一些精確資料,而不是一些蹭熱點(diǎn)的網(wǎng)紅在那里發(fā)言賺流量。”
“基本的分析能力大家都有,缺的是可供分析的事實(shí),而基于錯(cuò)誤、片面信息的分析討論,又有什么意義呢?包括辯論,即使以氣勢(shì)壓人,用辯論技巧讓人口服,也不是心服。如果對(duì)方能發(fā)自內(nèi)心地認(rèn)同你,多半是因?yàn)樗泻湍阃雀叨鹊捏w驗(yàn)。而隨著人生體驗(yàn)的豐厚,本來持異見的人最終也會(huì)被說服,他是被體驗(yàn)說服的。”
所以,為什么要多讀書呢?因?yàn)椋喿x便是增加體驗(yàn)維度的一個(gè)路徑——我說的不是快餐式新聞,而是書(包括電子形式的)。就是必須拉長(zhǎng)快感反射弧,慢慢去體味和理解的精神載體。
比如小說,它是最接近生活的文體,包括它呈現(xiàn)事情的流速、裹挾很多生活碎片的包容度、多人物切入的視角。最重要的是,它傳達(dá)觀點(diǎn)、知識(shí)的那種方式和生活教化人的方式一模一樣。你想搞明白一些道理,看一本濃齁的格言語錄集,遠(yuǎn)不如看小說的效果好,就是因?yàn)樵谛≌f里,你可以代入另外一個(gè)人,觀望他的內(nèi)心風(fēng)景,走一遍他的心路,預(yù)演一次他的歷程,這樣,很多道理不言自明。也就是,體驗(yàn)是最好的學(xué)習(xí)和說服。
但是,文本分類不是絕對(duì)的。前陣子看英國(guó)作家亞當(dāng)·尼爾科森的《海鳥的哭泣》,這書可以說是科普讀物,也可以當(dāng)小說看,如果人類放下萬物之尊的倨傲,像導(dǎo)盲犬那樣學(xué)會(huì)以他者的立場(chǎng)來思考(它必須以盲人的角度判斷障礙物,狗能通過的矮門人未必能),就會(huì)發(fā)現(xiàn)海陸空三棲的海鳥,其生活很有情節(jié)感,這樣說來,這本書就有了小說的質(zhì)感;它也可以當(dāng)哲學(xué)書來看,里面有很多對(duì)生命的反思;還可以當(dāng)科學(xué)史看,知道早年沒有全球定位系統(tǒng)、跟蹤儀、航拍這些現(xiàn)代設(shè)備的科學(xué)家,是怎么風(fēng)餐露宿,蜷縮在酷寒的海風(fēng)中記錄鳥類活動(dòng)的,感佩他們對(duì)生物研究所作的貢獻(xiàn)。
包括手頭這本西西的新書。我小時(shí)候讀李方的《天涯獵戶星》,里面有很多關(guān)于星星的小故事,我特別喜歡這本書,把書都翻卷角了。我很好奇里面那種觀星的工作,真浪漫啊,上班就是夜觀星象,“漫步在頭頂?shù)男侨褐小保€可以用心愛之人的名字命名新發(fā)現(xiàn)的星星。
受此書影響,長(zhǎng)大以后,我買房都買在江蘇南京紫金山天文臺(tái)腳下了。沒想到啊,幾十年之后,我的“女神”還真寫了本關(guān)于這個(gè)工作的小說,年前得知這個(gè)出版信息,我嘴巴半天都沒合攏,太吃驚了。整個(gè)年假,我都在靜靜地等著這本書,像守著藏在口袋里的一顆糖。這本書是小說,但也可以當(dāng)天文史看,也可以當(dāng)歷史書看,且可以當(dāng)服裝、建筑史看:龍袍紋樣、故宮古建群在書中都介紹了,甚至可以當(dāng)作宗教傳播史看:清代欽天監(jiān)的監(jiān)正和監(jiān)副都是洋人,最早是來中國(guó)傳教的。
又比如這幾天讀的黃永川的書,黃是明式文人花藝研究者——生活美學(xué)是近年出版大熱門,《瓶史》之類的古籍也被注析過多次,這本是黃永川注本。

插花不是一門孤立的學(xué)問,它是綜合學(xué)養(yǎng)的產(chǎn)物。黃對(duì)古詩畫皆有研究,常以詩意畫境作為插花靈感,而且熟悉民俗,有年三月他的插花作品是以豆花、油菜花為花材,這是緬懷宋代春來時(shí)的“挑菜節(jié)”。有些人不是專業(yè)文人,但是文筆甚是清麗怡情,比如做名物研究的揚(yáng)之水,還有研究中式插花的黃永川,他的插花史和古典插花研究書,我都是當(dāng)散文集來讀的。
還有手邊的一本敦煌圖案集,其中談及的裝飾圖案內(nèi)容實(shí)在精深,要通曉佛教、美術(shù)史、文學(xué)等諸多領(lǐng)域的知識(shí),又需要知曉當(dāng)時(shí)的歷史。比如談及莫高窟第158窟時(shí),書里說因?yàn)轭伭显颍藭r(shí)石綠色使用減少,而轉(zhuǎn)向了灰綠。我仔細(xì)看了下,這是一幅北朝的工筆畫,我想應(yīng)該是當(dāng)時(shí)戰(zhàn)亂頻頻,西去帕米爾高原的路被阻斷了,所以產(chǎn)于阿富汗境內(nèi)的青金石無法獲取,而群青顏料是拿它磨制出來的。還有很多圖案的創(chuàng)造,必須要有幾何知識(shí),它們是靠方程式推算出來的,比方說六邊形圖案就是個(gè)√3結(jié)構(gòu),水晶花圖案里面有個(gè)八次對(duì)稱公式,等等。
林林總總,手邊的書里就有數(shù)不盡的例子可舉。
多讀書,就知道世界的多元和豐富,而其中又有微妙的牽系,就不會(huì)急于判斷,而是津津有味地觀察。在視野里,讓一個(gè)個(gè)具體而不是概念化的“人”呈現(xiàn),就沒有那么淺薄狹隘、非黑即白的是非心和占領(lǐng)道德及智力制高點(diǎn)的急迫輕狂。多讀書,就是為了活在一種開放式的學(xué)習(xí)狀態(tài)中,不斷打破自己的認(rèn)知桎梏,這樣,靈魂從視野狹小的底層爬到了高層,人就慢慢走向了開闊的高處。“小我”謙卑收斂,繼而獲取“無我”的力量感。
(源自《心的事情》,余娟薦稿)責(zé)編: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