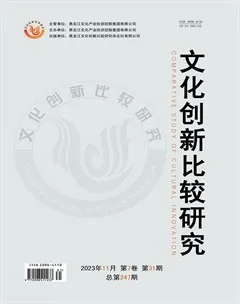生態(tài)翻譯學(xué)視角下《盈虛》漢譯研究
——以李默默、梁玥、六花、林非譯本為例
鄭仕宇,鄧亞曄
(1.景德鎮(zhèn)藝術(shù)職業(yè)大學(xué),江西景德鎮(zhèn) 333000;2.江西科技師范大學(xué),江西南昌 330038)
隨著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日益興盛、日本文學(xué)在中國譯介的不斷發(fā)展,日本作家中島敦(1909—1942 年) 的中短篇小說也愈加受到中國讀者的關(guān)注。現(xiàn)如今,學(xué)術(shù)界關(guān)于其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學(xué)價值、人物特征、小說結(jié)構(gòu)、敘事手法等方面,漢譯研究學(xué)術(shù)成果較少,且多集中于代表作《山月記》[1-2]和《李陵》[3]。
近年來,翻譯理論指導(dǎo)下的多譯本比較研究逐漸成為翻譯研究中的熱點。生態(tài)翻譯學(xué)是一種新型翻譯研究 “生態(tài)范式”,具有獨立自主的理論體系框架。本文試從生態(tài)翻譯學(xué)視角出發(fā),以短篇小說《盈虛》[4]為原文本,以2020—2022 年內(nèi)出版的李默默[5]、梁玥[6]、六花[7]、林非[8]等4 個中譯本為研究對象,在“多維度適應(yīng)與適應(yīng)性選擇” 原則的指導(dǎo)之下,采用多譯本比較研究的方式,考察各譯本的適應(yīng)性選擇過程及其在各維度下 “整合適應(yīng)選擇度” 的高低。
1 生態(tài)翻譯學(xué)概述
在 “翻譯適應(yīng)選擇論” 基礎(chǔ)之上發(fā)展而來的生態(tài)翻譯學(xué)是由胡庚申教授提出的中國本土翻譯理論[9],是一個以新生態(tài)主義為理論主導(dǎo),以生態(tài)翻譯的喻指和實指為研究取向,以翻譯文本生態(tài)、翻譯群落生態(tài)、翻譯環(huán)境生態(tài)為研究對象,以平衡和諧原則、多維整合原則、多元共生原則、譯者責(zé)任原則為倫理規(guī)范,以 “翻譯即文本移植、翻譯即適應(yīng)選擇、翻譯即生態(tài)平衡” 為核心理念的生態(tài)范式,致力于求解 “何為譯、誰在譯、如何譯、為何譯” 等根本性問題,旨在以生態(tài)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統(tǒng)領(lǐng)和觀照翻譯行為和翻譯研究,是一種從新生態(tài)主義理論視角綜觀和描述翻譯的研究范式[10]。
生態(tài)翻譯學(xué)起步探索于2001 年,立論奠基于2003 年,倡學(xué)整合于2006 年,全面拓展于2009 年。作為翻譯學(xué)和生態(tài)學(xué)相互融合的產(chǎn)物[11],帶有跨學(xué)科屬性的生態(tài)翻譯學(xué)立足于翻譯生態(tài)和自然生態(tài)的同構(gòu)隱喻,并以生態(tài)整體主義為理念、以東方生態(tài)智慧為依歸、以 “適應(yīng)/選擇” 理論為基石,具備深刻的理論內(nèi)涵和豐富的研究價值。現(xiàn)如今,富有生命力的生態(tài)翻譯學(xué)已經(jīng)成為廣為人知的翻譯研究范式,廣泛見于各類翻譯研究成果中。
2 《盈虛》和四個中譯本簡介
具備深厚漢學(xué)造詣的昭和初期小說家中島敦于1942 年創(chuàng)作《盈虛》一文,原與《牛人》一同以 “古俗”為題,發(fā)表于《政界往來》昭和十七年(1942 年)七月號之上。該作品取材自編年體史書《左傳》中 “定公十四年” 至 “哀公十七年” 有關(guān)衛(wèi)莊公的事跡記載[12],描寫了春秋時期衛(wèi)國太子蒯聵跌宕起伏、波瀾壯闊的一生。從身為太子倉皇出逃、流離失所,到回歸故國即位為君,再到最終橫死于己氏之手,讀來令人唏噓不已。《盈虛》涉及故事角色眾多,刻畫人物鮮活生動,故事情節(jié)精彩,作品構(gòu)思巧妙,語言表達優(yōu)美典雅,是日本近代文學(xué)中不可多得的佳作之一,具備較高的研究價值。
隨著中國讀者對于日本文學(xué)關(guān)注的日益加深,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譯者選擇重譯小說集《山月記》(《盈虛》收錄其中),推出一個個優(yōu)秀的中譯本,以饗讀者。本文選取2020—2022 年出版的4 個各具特色的中譯本作為研究對象,分別為李默默譯本(以下簡稱 “李譯”)、梁玥譯本(以下簡稱 “梁譯”)、六花譯本(以下簡稱 “六譯”)、林非譯本(以下簡稱 “林譯”)。
選取這4 個譯本的原因在于:(1)4 譯本發(fā)行渠道廣、發(fā)行量大,且在淘寶、京東、拼多多等國內(nèi)知名電商平臺均有發(fā)售,擁有深厚的群眾閱讀基礎(chǔ);(2)4譯本成書時間較新、均在近年來出版,它們是在新時代中日文學(xué)交流日益繁盛的物質(zhì)表現(xiàn);(3)4 譯本均為新生代優(yōu)秀譯者所譯,能體現(xiàn)新一代日本文學(xué)翻譯者的翻譯理念和翻譯思想。
3 “三維轉(zhuǎn)換” 視角下的多譯本比較研究
生態(tài)翻譯學(xué)認為,翻譯活動應(yīng)以譯者為主導(dǎo)、以文本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轉(zhuǎn)換為宗旨,翻譯是譯者適應(yīng)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而對文本進行移植的選擇活動。這里,譯者 “適應(yīng)” 的是原文、原語和譯語所呈現(xiàn)的“世界”(即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譯者 “選擇” 的是對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適應(yīng)度和對譯本最終的行文[13]。
在 “多維度適應(yīng)與適應(yīng)性選擇” 原則指導(dǎo)下,譯者應(yīng)當(dāng)合理運用三維轉(zhuǎn)換法,即在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完成譯文的適應(yīng)性選擇轉(zhuǎn)換,構(gòu)建出譯語的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使得譯本具備較高的 “整合適應(yīng)選擇度”(即譯者產(chǎn)生譯文時,在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等多個維度的 “選擇性適應(yīng)” 和繼而依此照顧到其他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因素的 “適應(yīng)性選擇” 程度的總和),并且自然地融入譯語生態(tài)之中。
下文基于 “三維轉(zhuǎn)換” 視角,采用多譯本比較研究的方式,考察各譯本在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的適應(yīng)性選擇轉(zhuǎn)換過程,探討 “語言生態(tài)”“文化生態(tài)”和 “交際生態(tài)” 在原語和譯語之間的轉(zhuǎn)換方法與不同譯者構(gòu)建譯語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方式。
3.1 語言維
語言維聚焦于文本的語言表達,側(cè)重點在于翻譯過程中語言層面的轉(zhuǎn)換,要求譯者應(yīng)當(dāng)從詞匯、語法、修辭方式等不同層面完成適應(yīng)性選擇轉(zhuǎn)換,不僅要盡可能地忠實原文,還務(wù)須使得譯文通順流暢、具備較高可讀性。
例1:父·霊公の夫人(といっても太子の母ではない)南子は宋の國から來ている。容色よりも寧ろ其の才気で以てすっかり霊公をまるめ込んでいるのだが、……
李譯:父親衛(wèi)靈公的夫人南子,并不是太子的生母,她是從宋國來的。比起容姿來,南子更是憑借其卓越的才干,將靈公玩弄于股掌之間。
梁譯:他父親衛(wèi)靈公的夫人(并非太子的生母)南子出身于宋國。她不以色事人,而是憑著出眾的才華將衛(wèi)靈公完全玩弄于股掌之間。
六譯:父親靈公的夫人(并非太子的母親)南子來自宋國,她憑借出眾姿色及過人才氣,徹底籠絡(luò)住了靈公的心。
林譯:父親靈公的夫人(此人并非太子生母)南子是從宋國來的,不僅姿色出眾,而且才智過人,哄得靈公對她言聽計從。
這段話介紹了南子的基本情況,為后面蒯聵伙同家臣戲陽速預(yù)謀刺殺南子交代了故事背景。原文中用到了「~よりも寧ろ~」這一句型,表達 “前后兩者對比,后者更為恰當(dāng)” 之意,直譯為 “與其……莫不如……”“與其……寧可……”,重點在于突出強調(diào)后者的作用、功效等。
李譯采用直譯的翻譯方法,選用 “比起……更是……” 的句法結(jié)構(gòu),較為忠實原文。梁譯采用了 “不是……而是……” 的句法結(jié)構(gòu),突出強調(diào)南子的出眾才華,但否定了她美麗的姿色對靈公產(chǎn)生的作用。六譯譯作 “她憑借出眾姿色及過人才氣”,將 “出眾姿色” 和 “過人才氣” 并列在一起,表達這兩者都對靈公產(chǎn)生作用。根據(jù)《現(xiàn)代漢語詞典(第7 版)》的描述,“及” 可用作連接并列的名詞性詞語,例如:圖書、儀器、標(biāo)本及其他等。但在使用時,連接的成分多存在意義之上的主次之分,主要的成分放在 “及” 的前面。因此,六譯在此重點強調(diào)南子的 “出眾姿色”。林譯選用 “不僅……,而且……” 的句法結(jié)構(gòu),表達遞進關(guān)系,重點強調(diào)南子才智過人,在忠實原文的基礎(chǔ)上保證了行文的通順流暢。
綜上所述,針對例1,4 位譯者雖然強調(diào)的重點各有不同,但都傳遞出了原文蘊含的信息,實現(xiàn)了語言維的適應(yīng)性選擇轉(zhuǎn)換。梁譯重點強調(diào)南子的 “出眾才華”,六譯重點強調(diào)南子的 “出眾姿色”,而李譯和林譯則采用了與原文相對應(yīng)的句法結(jié)構(gòu)并傳遞出了其中的遞進關(guān)系,較好地完成了語言維的適應(yīng)性選擇轉(zhuǎn)換。
例2:此の態(tài)を見た太子は、いきなり良夫に躍りかかり、胸倉を摑んで引摺り出すと、白刃を其の鼻先に突きつけて詰った。君寵を恃んで無禮を働くにも程があるぞ。君に代って此の場で汝を誅するのだ。
李譯:太子見狀,一躍而起,一把揪住他衣服前襟將其拖了出來。太子把明晃晃的刀子抵在他的鼻尖上,質(zhì)問道:“就算仗著君寵狂妄無禮,也該有個限度! 今日我便替主君殺了你! ”
梁譯:太子疾見此情景,冷不防猛撲向渾良夫,揪住其脖領(lǐng)將其拖到眾人面前,又將白刃架在他脖子上發(fā)難道:“你恃寵而驕也要有個限度吧! 今日我便要替父君了結(jié)了你! ”
六譯:太子疾見狀,突然跑到渾良夫面前,一把揪住他的前襟,硬生生將他拽到外邊,還將刀抵上他的鼻尖,責(zé)問道:“恃寵而驕也該有個限度!我今天就要替國君殺了你。”
林譯:太子見狀,一下沖到他的座前,一把將他揪住,用長劍指著他的鼻尖,呵斥他恃寵而驕、不講禮數(shù)、無法無天,還說要替莊公殺了他!
例2 講的是此前渾良夫曾與莊公密謀召回前任衛(wèi)候太子,此事被太子疾耳聞,太子疾便有誅殺渾良夫之心。在莊公即位后的第二年春日,莊公召開盛大的宴會宴請衛(wèi)國名流,太子疾和渾良夫都參加了此次宴會。會上渾良夫觸犯禮法,太子疾覓得良機,挺身而出,將渾良夫斃于宴會之上。
原文「白刃」表 “脫鞘的刀” 之意。李譯、六譯均將「白刃」譯作 “刀(子)”,梁譯按照日本漢字直譯為 “白刃”(鋒利的刀),而林譯則譯作 “長劍”,與原文詞義不符。「引(き)摺り出す」表 “強行拽出去、拉出去” 之意,李譯、梁譯和六譯分別譯作 “將其拖了出來”“拖到眾人面前”“硬生生將他拽到外邊”,而林譯則漏譯了該詞,在譯文中未出現(xiàn)太子疾拖拽渾良夫的動作。「鼻先」表 “鼻子尖兒” 之意,后引申出 “眼前” 之意。梁譯將「白刃を其の鼻先に突きつけて詰った」這句話譯作 “(太子疾)又將白刃架在他脖子上……”,將「鼻先」誤譯為 “脖子”,與原文語義不符。「突きつけて詰った」由「突き付ける」和「詰まる」組合而成,「突き付ける」表 “(將兇器等物)擺在對方面前” 之意,而「詰まる」則表 “沒有任何空隙,充滿、擠滿” 之意。李譯與六譯均譯為 “抵”,即用刀觸碰著渾良夫的鼻子,較為生動形象地傳遞出了太子疾在會場之上對于渾良夫的威懾和壓迫。林譯則譯為 “指著”,這僅表明刀的指向,即將「突き付ける」的詞義翻譯到位,而未能翻譯出「詰まる」的詞義,未能展現(xiàn)出刀與渾良夫的鼻子毫無間隙,太子疾的威懾力也未能較好地體現(xiàn)于譯文中。梁譯將動詞譯為 “架”,表 “以一物加在另外一物之上” 之意,雖將詞義翻譯到位,但因前置動詞對象翻譯有誤,仍與原文語義不符。
由此可見,例2 中,林譯和梁譯出現(xiàn)了明顯的誤譯和漏譯問題,李譯和六譯則保證了原文語詞的準(zhǔn)確翻譯,在忠實的基礎(chǔ)上賦予了譯文流暢性,完成了語言維的適應(yīng)性選擇轉(zhuǎn)換過程,使其具備較高的 “整合適應(yīng)選擇度”。
3.2 文化維
文化維關(guān)注于翻譯的語境效果,兩種語言背后文化內(nèi)涵的傳遞和闡釋是譯者應(yīng)當(dāng)著重考慮的要點。通過文化維的適應(yīng)性選擇轉(zhuǎn)換,譯者務(wù)須完成文化意象和文化內(nèi)涵的轉(zhuǎn)換,將原語 “文化生態(tài)” 轉(zhuǎn)換至譯語“文化生態(tài)”,構(gòu)建出優(yōu)質(zhì)的譯語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
例3:丸坊主にされて帰って來た妻を見ると、夫の己氏は直ぐに被衣を妻にかずかせ、まだ城樓の上に立っている衛(wèi)侯の姿を睨んだ。
李譯:看到被放回來的妻子被剃光了頭發(fā),丈夫己氏立刻給她罩上一件斗篷,他狠狠盯著站在城樓上的衛(wèi)侯,……
梁譯:丈夫己氏看到自己的妻子回來時被剃光了頭發(fā),立刻將衣物披在妻子頭上,并對仍站在城樓上的衛(wèi)莊公怒目而視。
六譯:己氏見妻子回來時被剃成了光頭,立即幫她遮蓋住頭部,怒視仍然站在城樓上的衛(wèi)侯的身影,……
林譯:己氏見到被剃光頭發(fā)的妻子,趕忙拿出斗篷蒙在她的頭上,橫眉怒目地看向高高站在城樓上的衛(wèi)侯。
例3 講的是莊公在城樓上驅(qū)逐西方戎人部落時,無意間看到了戎人己氏的妻子,并將其秀發(fā)連根剃除,為后宮寵妃制作假發(fā)。己氏由此與莊公結(jié)下了深仇大恨,為文末莊公之死埋下了伏筆。
《左傳》 中并未記述己氏遮蓋妻子頭部一事,而中島敦在改編過程中則創(chuàng)造性地使用「被衣」一詞,將日本傳統(tǒng)文化要素融入其中。在漢譯過程中,譯者應(yīng)當(dāng)考慮到中國春秋時期的故事背景,基于兩國文化的差異性,選擇合適的語匯將之譯出,實現(xiàn)文化維的適應(yīng)性選擇轉(zhuǎn)換。
在此不妨選用春秋時期常見服飾,如續(xù)衽、長衫,體現(xiàn)譯者主體性的同時亦能彰顯出中國服飾文化深厚的底蘊和內(nèi)涵。中國古人認為 “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遭受剃發(fā)是對人極大的羞辱。此例己氏為了遮掩愛妻的光頭,用「被衣」為其遮掩。「被衣」(かずき)同「衣被」(きぬかずき),直譯可譯為 “蒙頭外衣”,是日本古代傳統(tǒng)服飾,從頭部覆蓋而下,用于遮掩頭部和面部以避人眼目,一般為女性所穿著使用,其歷史最早可追溯至平安時代。
李譯和林譯都將其譯為 “斗篷”,根據(jù)《現(xiàn)代漢語詞典(第7 版)》的解釋,“斗篷” 意為 “披在肩上的沒有袖子的外衣”,這與日本服飾「被衣」相差甚遠。「被衣」有袖,主要用于覆蓋頭部和面部,使用對象為女性,主要用于遮掩自己的面容不被外人看見;而 “中式斗篷” 是清代的產(chǎn)物,不連帽、無袖,主要覆蓋在肩上,往往搭配風(fēng)帽、風(fēng)兜共同使用,使用對象不限男女,只在冬季為防寒而用。兩者之間衣著形態(tài)、使用對象、使用場景、功能用途都大相徑庭。六譯譯為“(己氏)立即幫她遮蓋住頭部,……”,省略了己氏為妻子遮掩頭部的方式,有可能會使讀者誤解為 “己氏用自己的身體為妻子遮掩頭部”。梁譯譯為 “衣物”,選取了「被衣」的上位概念,擴大了詞義范圍,基本符合原文情節(jié)中的場景描述,但未能體現(xiàn)出春秋時期的服飾文化,在文化維的適應(yīng)性選擇轉(zhuǎn)換程度略顯不足。綜上所述,4 位譯者在文化維方面均有欠缺,未能選取合適的語匯進行替換,文化維的適應(yīng)性選擇轉(zhuǎn)換完成度仍有所缺失,原語中的 “文化生態(tài)” 未能轉(zhuǎn)換至譯語的 “文化生態(tài)”。
例4:公は改めて卜した。その卦兆の辭を見るに「魚の疲れ病み、赤尾を曳きて流に橫たわり、水辺を迷うが如し。大國これを滅ぼし、將に亡びんとす。城門と水門とを閉じ、乃ち後より踰えん」とある。
李譯:莊公再度占卜,這一次,卦辭中說:“如魚赪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后逾。”(注)
注:卦辭意為:如疲病之魚擺動著紅色的尾巴,為急流所阻,徘徊于水畔。在大國旁邊,將為大國所滅。閉城門和水門,而越過后墻逃走。
梁譯:隨后衛(wèi)莊公又重新卜了一卦,一看卦兆這樣說道:“魚疲病,拖赤尾臥于水中,如同在岸邊迷路。大國滅之,瀕臨消亡。閉城門,閉水門,爾后則逾。”
六譯:莊公后來又卜了一卦,卦辭如此寫道——“魚兒疲病,搖曳紅尾橫在水中,仿佛不知哪是水邊。大國來襲,滅亡在即。關(guān)閉城門水門,從后邊逃遁。”
林譯:后來,莊公又卜了一卦。卦辭顯示:“如魚赪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后踰。”(注)
注:大意是,像一條淺色紅尾魚,穿越激流的時候彷徨不決。與大國為鄰,消滅它,將要滅亡。關(guān)好門堵住洞,翻越后墻。
例4 講的是莊公即位的第二年秋天,他夢見了渾良夫向他伸冤叫屈,醒來后看見紅月亮從曠野升起,心下不安,召來筮師為他解卦,但筮師卻謊言相告、獲得賞賜后便逃往國外。由此,莊公進行了第二次占卜。本次占卜的卦辭象征著莊公日后悲慘的命運,為后面莊公緊閉城門、棄城而逃作了鋪墊。
作為中華傳統(tǒng)文化要素之一的卦辭,相傳為周文王囚禁之時所作。卦辭是對所占卦象的總體評價,涉及內(nèi)容廣泛、語言表達精簡凝練,微言大義。莊公在此通過占卜求卦預(yù)測今后兇吉禍福。原文卦辭采用日語文言體書寫,在進行翻譯時必須符合中國古代卦辭的表達特點并體現(xiàn)出其中蘊含的文化特質(zhì),以此實現(xiàn)文化維的適應(yīng)性選擇轉(zhuǎn)換。
《左傳·哀公十七年》 中曾出現(xiàn)該則卦辭,原文為:“衛(wèi)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后逾。’”[14]。
4 譯本中,李譯和林譯均采用直接引用《左傳》原文的形式翻譯卦辭,并在卦辭旁附加現(xiàn)代漢語腳注,輔助讀者理解。梁譯采用文白夾雜的文體自譯,而六譯則采用白話文文體進行翻譯。作為四書五經(jīng)之一的《左傳》是儒家經(jīng)典,其中對于卦辭的描述較為符合卦辭的語言表達特點,能夠體現(xiàn)出中華傳統(tǒng)文化特質(zhì)。李譯和林譯均通過引用原文文言體的方式,較好地構(gòu)建出譯語的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使得譯文語言表達不僅與卦辭的語言表達相一致,還附帶上中國文化色彩、添加上中國文化要素。此外,李譯和林譯還通過附加現(xiàn)代漢語腳注的形式進一步解釋說明卦辭大意和內(nèi)涵,有助于加深讀者對于中國文化的理解,由此實現(xiàn)了文化維的適應(yīng)性選擇轉(zhuǎn)換。
而梁譯和六譯雖然都復(fù)現(xiàn)了原文語義,但因譯文文體與傳統(tǒng)卦辭的語言表達有所偏差,且較為冗長,與卦辭微言大義的語言特點相悖,因此譯文未能展現(xiàn)出卦辭所附帶的中國文化內(nèi)涵,譯語的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仍未構(gòu)建齊全。
3.3 交際維
交際維重點關(guān)注于 “諸者” 的交際意圖。其中交際主體和交際對象范疇極為廣泛,既包括故事人物,也包括譯者、作者、譯文讀者、譯品評論者、譯事審查者、譯著出版者、營銷者、譯事贊助者……譯者在進行交際維的適應(yīng)性選擇轉(zhuǎn)換時,應(yīng)當(dāng)盡可能體察到“諸者” 的交際意圖,并將之充分展現(xiàn)于譯文中,維護和保持好原語和譯語間的 “交際生態(tài)”。
3.3.1 譯者的交際意圖
在翻譯過程中統(tǒng)籌各方、在翻譯行為中發(fā)揮著核心作用的譯者,其自身的交際意圖無疑至關(guān)重要[15]。如何將譯者自身的翻譯理念和思想體現(xiàn)并貫穿在譯文之中,實現(xiàn)譯者自身交際意圖的傳遞,并且將 “原語交際生態(tài)” 轉(zhuǎn)換為 “譯語交際生態(tài)”,這一點關(guān)乎交際維適應(yīng)性選擇轉(zhuǎn)換程度的高低。
例5:荘公は城門を悉く閉じ、自ら城樓に登って叛軍に呼び掛け、和議の條件を種々提示したが石圃は頑として応じない。
李譯:莊公將城門悉數(shù)關(guān)閉(注1),親自登上城樓向叛軍交涉,提出了種種和議的條件,然而石圃十分頑固,不肯接受。
注1:此處呼應(yīng)卦辭 “闔門塞竇”。
梁譯:衛(wèi)莊公關(guān)閉了所有的城門,親自登上城樓向叛軍喊話,提出了一條條議和的條款,但石圃絲毫沒有退讓。
六譯:莊公下令關(guān)閉所有城門,登上城樓召集叛軍,提出種種議和條件,然而石圃態(tài)度堅決,不肯妥協(xié)。
林譯:莊公下令緊閉城門,親自登上城樓向叛軍喊話,做出種種議和承諾。但石圃態(tài)度堅決,根本不為所動。
例6:月の出ぬ間の暗さに乗じて逃れねばならぬ。諸公子·侍臣等の少數(shù)を従え、例の高冠昂尾の愛鶏を自ら抱いて公は後門を踰える。
李譯:必須趕在月亮出來之前趁著昏暗的夜色逃走。莊公帶著諸公子和侍臣等少數(shù)幾人,照例親自抱著那只高冠翹尾的愛雞,從王宮后門翻了出去(注2)。
注2:此處呼應(yīng)卦辭 “乃自后逾”。
梁譯:衛(wèi)莊公想著必須得趁月亮還沒升起時于漆黑的夜色中逃走,于是便攜少數(shù)幾名公子、侍臣從后門翻了出去,手中還抱著他那只心愛的、高冠昂尾的雄雞。
六譯:莊公知道只有趁著月亮尚未升起的傍晚時分才能逃走,于是他帶著公子、侍臣等少數(shù)幾人,又親自抱著那只高冠昂尾的雄雞,翻墻出了后門。
林譯:莊公很清楚,唯有趁著月亮升起前的黑暗才有可能逃走。因此,他帶著諸位公子和少數(shù)隨從,抱著那只雞冠高聳、雞尾昂揚的雄雞,從宮城后門翻墻而出。
例5 和例6 講的是莊公即位的第二年秋天,他曾占過卜,卦辭顯示出莊公前途暗淡、時日無多,衛(wèi)國將為晉國所亡,但卦辭中具體的含義,如 “闔門塞竇”“乃自后逾” 卻不甚明了。同年冬天,晉國與大夫石圃合謀入侵衛(wèi)國,莊公關(guān)閉城門、親自向叛軍交涉,但最終和談失敗。莊公無法抵擋,只得倉皇從后門出逃。這兩件事正呼應(yīng)著卦辭中 “闔門塞竇” 和 “乃自后逾”。
生態(tài)翻譯學(xué)認為,翻譯過程中的交際對象范圍十分廣泛,包括作者和譯者、作者和讀者、譯者和讀者……因此,交際意圖的傳遞不僅局限于作者,譯者自身的交際意圖也應(yīng)當(dāng)包含在內(nèi)。4 譯本中,僅李譯添加上了譯者注,解釋說明前文卦辭在后文中與現(xiàn)實相互呼應(yīng)。通過添加注1 和注2,使讀者能夠更加深刻地理解卦辭的內(nèi)涵,并領(lǐng)悟出作品所蘊含的 “宿命論” 和 “因果報應(yīng)” 的思想內(nèi)核。李在《譯后記》中曾表示:“我希望這個譯本能夠淡化翻譯的痕跡,使讀者盡可能直接地、面對面地與作品和作者碰撞出火花。為此,我雖如履薄冰,但亦全力以赴。” 如其所說,李譯通過加注的形式,使得譯文更加歸化、易于為現(xiàn)代中國讀者所理解和接受,并將譯者自身的交際意圖較好地傳遞給讀者,由此實現(xiàn)了交際維的適應(yīng)性選擇轉(zhuǎn)換。
3.3.2 故事人物的交際意圖
在翻譯文學(xué)作品時,譯者除了需要傳遞出作者、譯文讀者、譯品評論者等諸方的交際意圖外,還需要盡可能地貼近故事人物,融入于情節(jié)之中,設(shè)身處地地從人物自身的立場出發(fā)考慮問題,豐滿人物形象、傳遞出人物的交際意圖。
例7:其の聲に驚いて霊公が出て來る。夫人の手を執(zhí)って落著けようとするが、夫人は唯狂気のように「太子が妾を殺します。太子が妾を殺します」と繰返すばかりである。
李譯:靈公被這聲音驚動,走了出來,他握著夫人的手想要她冷靜下來,夫人卻只是像瘋了一樣一遍又一遍地喊道:“太子要殺臣妾! 太子要殺臣妾! ”
梁譯:她的呼喊聲驚動了衛(wèi)靈公,他出來握住夫人的手想安撫夫人,但夫人只是像瘋了一般重復(fù)著一句話:“太子欲殺臣妾! 太子欲殺臣妾! ”
六譯:靈公聞聲大驚,他出來握住夫人的手,安撫著她的情緒,而南子卻像瘋了一般,只顧反復(fù)呼喊著 “太子要殺我,太子要殺我”。
林譯:靈公聽到動靜趕了來,握著南子的手不停地安撫。南子仍舊花容失色地大喊道:“蒯聵想殺我! ”
例7 講的是衛(wèi)太子蒯聵途經(jīng)宋國時聽聞鄉(xiāng)間歌謠,暗諷衛(wèi)靈公夫人南子與宋國公子朝有染,歸國后便與家臣戲陽速商議,意圖刺殺南子。但因戲陽速別有二心導(dǎo)致事情敗露,刺客的存在為南子所察知。此時,情緒激動的南子沖進內(nèi)室,尋求靈公的幫助。
在文學(xué)作品中,每一個故事人物都是獨立的交際個體,都具備各自的交際意圖。因此,譯者在進行交際維的適應(yīng)性選擇轉(zhuǎn)換時,必須重視故事人物交際意圖的傳遞。只有站在故事人物的立場之上,思人物之所思、想人物之所想,才能在譯文中充分展現(xiàn)出故事人物所要傳達出的交際意圖。
面對蒯聵的脅迫,南子逃進內(nèi)室、希望靈公保自身周全。原文通過反復(fù)的修辭手法將南子的話重復(fù)了兩遍,展現(xiàn)出其內(nèi)心的驚慌失措。李譯、梁譯和六譯均沿用原文句式,在譯文中同樣使用反復(fù)的修辭手法,體現(xiàn)出南子的驚恐無助。而林譯則對南子的話加以省略,未能很好地體現(xiàn)出人物的交際意圖。
原文中,南子將蒯聵稱為“太子”,而自稱為“妾”。一方面,在春秋時期,太子是儲君、是諸侯的法定繼承人,地位僅次于君,君主的妾室不能直呼其名,只能尊稱之為 “太子”;另一方面,身為妾室的南子意在尋求靈公的庇護,自稱為 “妾” 符合所處的身份立場,體現(xiàn)出除靈公施以援手外,本人的孤立無助。李譯、梁譯和六譯均將「太子」直譯為 “太子”,這一稱謂與南子的立場較為符合,而林譯則改譯為 “蒯聵”,直呼太子之名極為失禮,體現(xiàn)出了南子的莽撞和不懂禮法,其與原本的交際意圖相悖。李譯和梁譯將「妾」翻譯為 “臣妾”,該譯法確認了南子的說話對象為靈公,體現(xiàn)出了古代 “妾室” 的從屬關(guān)系,較好地站在南子的立場上傳遞出人物的交際意圖,完成了交際維的適應(yīng)性選擇轉(zhuǎn)換。六譯和林譯則將「妾」翻譯為第一人稱代詞 “我”,“我” 的使用對象不限性別、男女皆可,在此無法凸顯出南子作為 “妾室” 的身份和地位,未能傳遞出南子的交際意圖。
綜上所述,李譯和梁譯從人物自身立場出發(fā),通過 “太子” 和 “臣妾” 這兩個人稱的譯文,構(gòu)建出了南子的人物形象,體現(xiàn)出南子此刻的驚慌失措和弱小無助,重點突出了故事人物的交際意圖,由此實現(xiàn)了交際維的適應(yīng)性選擇轉(zhuǎn)換。而林譯和六譯則無法傳遞出南子本人此時的交際意圖,在交際維的適應(yīng)性選擇轉(zhuǎn)換完成度方面有所缺失,譯文總體的 “整合適應(yīng)選擇度” 大打折扣。
4 結(jié)束語
本文立足于生態(tài)翻譯學(xué),遵照 “多維度適應(yīng)與適應(yīng)性選擇” 指導(dǎo)原則,以短篇小說《盈虛》的李默默、梁玥、六花、林非等4 個中譯本為研究對象,基于 “三維轉(zhuǎn)換” 視角,考察各譯本的適應(yīng)性選擇轉(zhuǎn)換過程及其 “整合適應(yīng)選擇度” 的高低。
研究發(fā)現(xiàn),4 譯本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翻譯選擇不適配問題。總體上看,梁譯存在明顯的誤譯和漏譯問題,六譯在故事人物交際意圖的傳遞上有所不足,林譯則兼具上述兩種問題,而李譯的 “整合適應(yīng)選擇度” 和適應(yīng)性選擇轉(zhuǎn)換過程的完成度較高,在語言維和交際維均完成了譯文的適應(yīng)性選擇轉(zhuǎn)換過程,構(gòu)建出優(yōu)質(zhì)的譯語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但由于原語的 “文化生態(tài)” 與譯語的 “文化生態(tài)” 并不對應(yīng),造成了各譯本在文化維適應(yīng)性選擇轉(zhuǎn)換過程的完成度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與此同時,整體的 “整合適應(yīng)選擇度” 也受到了一定影響。
本文探討了《盈虛》4 個譯本的適應(yīng)性選擇轉(zhuǎn)換過程,集中考察了各譯本 “整合適應(yīng)選擇度” 的高低,以期為中島敦作品的翻譯實踐與研究提供些許借鑒,促進該領(lǐng)域譯介和研究工作的深入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