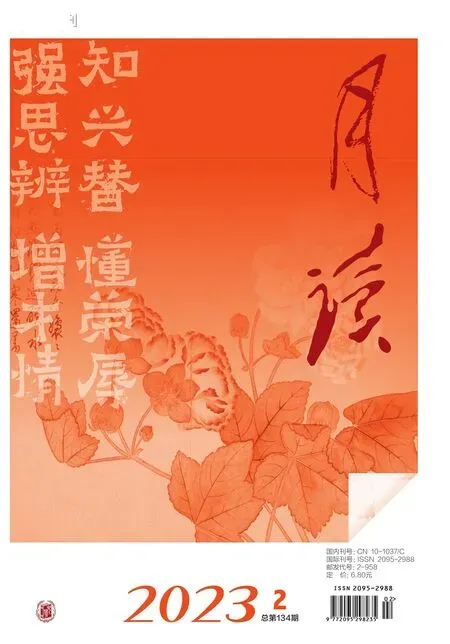文徵明:山靜日長 茶韻悠悠
◎ 楊多杰

絹封陽羨月,瓦缶惠山泉。
至味心難忘,閑情手自煎。
地爐殘雪后,禪榻晚風前。
為問貧陶谷,何如病玉川。
——〔明〕文徵明《煮茶》
明朝建立之初,中國茶界發生了一件大事。
據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記載:
國初四方貢茶,以建寧、陽羨茶品為上,時猶仍宋制,所進者俱碾而揉之,為大小龍團。
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采茶芽以進。……按茶加香物,搗為細餅,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開千古茗飲之宗。
以上這段史料,簡而言之就是四個字:廢團改散。不管是唐代的煎茶法,還是宋代的點茶法,基礎都是蒸青團餅茶。這種茶不僅制作繁瑣,喝起來也很麻煩。陸羽《茶經》中記載的茶器,有大大小小二十余種。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撬茶、碾茶、篩茶的器具。宋代點茶的程序,與煎茶法相比就更為復雜了。如今日本的抹茶道,根源便是我國南宋時的飲茶方法。窺一斑見全豹,您就知道宋人喝茶有多費事了。
適當的儀式感,有利于茶文化的登堂入室。
過分的儀式感,有礙于茶文化的廣泛普及。
由團餅茶改為散茶,不僅是茶葉形態的改變,中國人的飲茶方式也相應得以簡化。明代人常用的“撮泡法”,與今人的泡茶方法一般無二。可以說,我們當下的飲茶架構,并非直接承接自唐宋,而是來源于明代。因此明代茶詩讀起來,也覺得多了幾分親切感。
在明代眾多愛茶人當中,吳門畫派值得格外關注。所謂吳門畫派,是以蘇州為中心,形成的筆墨含蓄、文雅謙恭、富于書卷氣息的書畫流派。這個派別的代表人物有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中國美術史上,四人合稱為“吳門四家”。值得注意的是,“吳門四家”人人愛茶。他們不僅繪制茶畫,同時寫作茶詩。畫中有詩意,詩中含畫韻。茶詩與茶畫相輔相成,構建起明代獨特的文人茶風。這里賞析的《煮茶》一詩,就出自吳門四家之一的文徵明之手。老規矩,咱們還是從作者講起。
文徵明,字徵仲,號衡山。在《明史》本傳中,說他是文天祥的后代。據王世貞《文先生傳》中說,文徵明的先祖文俊卿在元朝曾做過配金虎符鎮守武昌的都元帥。文徵明的父親文林,曾做過溫州太守。說文徵明出身于官宦世家,大抵是不錯的。
在吳門四家當中,數文徵明的茶學造詣最為出眾。作為一位丹青高手,文徵明一生創作了許多茶畫,傳世的就有《惠山茶會圖》《品茗圖》《玉川圖》《煮茗圖》《林榭煎茶圖》《茶事圖》《茶具十詠圖》等。其中以《惠山茶會圖》最為有名,此畫現收藏于故宮博物院。與此同時,文徵明也稱得上是茶學研究者。他不僅著有《龍井茶考》,還對宋代蔡襄《茶錄》進行過系統的論述。他這樣一位愛茶又懂茶的藝術家,所寫的茶詩就自然別有一番滋味了。

惠山茶會圖
講完了作者,我們來看正文。
開篇兩句:“絹封陽羨月,瓦缶惠山泉。”寫的是態度。
陽羨,是今天江蘇宜興的舊稱。那里出現的茗茶,在唐代最為流行。由于那時還是圓圓的團餅茶,所謂便雅稱其為“陽羨月”了。文徵明身處的明代中期,廢團興散已有多年。人們的飲茶習慣,也早就棄“點茶法”而改“撮茶法”。因此這里其實是一種虛寫,“陽羨月”直接視作名茶的雅稱便可。
后一句提到的惠山,位于今天的江蘇無錫,以天下第二泉而聞名于世。為難得的佳茗,配上一缶好水,這是一個飲茶人對好茶的基本尊重了。現如今很多人舍得花大價錢購買好茶,回來后卻直接用自來水或是過濾水沖泡,茶湯風味自然要大打折扣。我們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現代人,用新鮮泉水泡茶自然不現實。那咱們泡茶時怎么也得準備一瓶礦泉水吧,這也算是不辜負了這份好茶。切記,切記!
資料卡片
中國茶的雅稱別名還有很多。一個字的如茗、槚、蔎、荈,兩個字的如甘露、酪奴、綠華、葉嘉等,三個字的如晚甘侯、瑞草魁、滌煩子、不夜侯、苦口師等。掌握了雅化名稱,分清了動靜虛實,也更便于我們解讀茶詩的幽美之情。
三四兩句:“至味心難忘,閑情手自煎。”道出了真情。
中國人講話,十分的生動形象。我們要求一個人認真對待工作時,常常要他遇事都得“過腦子”。但當我們碰到了自己的愛人時,辦事光“過腦子”就不行了,而一定要“走心”才可以。怪不得,喜歡的人要叫“心上人”呢。
“走心”比起“過腦子”,就更深入了一層。或者這樣說,“過腦子”是理性,“走心”是感性。所以真的碰到“至味”好茶,一定是要“心難忘”才對。就沖這一句話,我相信文徵明老先生是真正的愛茶之人。
那讓人心難忘的茶中至味,又是如何得來的呢?后半句給出了答案:一要心有閑,二要手自煎。同樣的一杯茶,忙時只能是喝,閑時才能算品。心亂如麻時喝茶,只是囫圇吞棗。氣定神閑時品茗,才解個中至味。正如同六祖惠能在廣州法性寺所講,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而是心動。
至于自己動手沖泡,則又另有一番樂趣。從備茶到擇器,從燒水到沖泡,紛亂復雜的思緒會因專注于茶事而歸于平靜。現如今科技昌明,出現了一種速溶茶。這類產品打出的廣告口號便是:讓喝茶變得簡單快捷。殊不知,飲茶的樂趣,不止來源于茶,那更是水之美、器之美、茶之美、景之美、情之美與人之美的綜合呈現。文徵明筆下“閑情手自煎”的樂趣,絕不是速溶茶可以替代的了。
五六兩句:“地爐殘雪后,禪榻晚風前。”講的是理想的生活。
地爐與禪榻,既是一種場景的描述,也是一種超脫的符號。這些物件的出現,證明詩人的生活不是鐘鳴鼎食,而是樸實無華。進一步而言,詩人向往的不是功名利祿,而是本真生活。
這種生活具體是什么樣呢?我們用文徵明特別喜歡的四個字回答:山靜日長。所謂“山靜日長”,是南宋羅大經《鶴林玉露》里的一篇文章,其中詳細地描述了羅氏罷官歸鄉的閑適生活,現將其原文抄錄如下: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麝犢共偃息于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前,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跡、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粳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晌。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入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于聲利之場者,但見袞袞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如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這位羅大經何許人也?他可是文徵明的偶像,我們不妨多聊兩句。羅大經,字景綸,號儒林,又號鶴林,吉州吉水(今屬江西)人。羅大經原也是走傳統路線的文人。他于南宋理宗寶慶二年(1226)進士及第,后歷任容州法曹、辰州判官、撫州推官。羅大經在撫州任上遭彈劾而罷官,從此絕意仕途,過上了閉門讀書的日子,書茶相伴。
正如上文所寫的那樣,羅大經“午睡初足”后,“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可見,他的山居生活,總有茶相伴。羅大經愛茶,也懂茶,他還寫過一首《茶聲》:“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后,一甌春雪勝醍醐。”敘述煮茶的過程,把一樁日常小事寫得情趣盎然,讀此詩,如聞茶聲,如嗅茶香,如見茶乳。
文徵明的一生,非常推崇羅大經“山靜日長”式的生活。明嘉靖八年(1529),六十歲的文徵明畫過一幅《山靜日長圖卷》。二十多年后,文徵明以八十五歲的高齡又再次通篇書寫了《山靜日長》這篇美文。這首《煮茶》中的金句,都可視作“山靜日長”式生活的縮影。
結尾的兩句詩文:“為問貧陶谷,何如病玉川。”引出了兩位愛茶之人。
其中的“病玉川”,指的就是唐代詩人盧仝。他因一首茶詩《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而揚名于世。宋代蘇軾詩中“明月來投玉川子”一句,提及的便是盧仝。相較起來,“貧陶谷”的名氣就要稍遜一籌了,我們不妨多聊兩句。
陶谷,字秀實,邠州新平(今陜西彬縣)人。歷仕后晉、后漢、后周,入宋后累官兵部、吏部侍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轉禮部尚書,翰林承旨,乾德二年(964)判吏部銓兼知貢舉,累加刑部、戶部尚書。《宋史》卷二六九有傳,其中寫到他:
強記嗜學,博通經史,諸子佛老,咸所總覽,多蓄法書名畫,善隸書。為人雋辨宏博,然奔競務進。
在文徵明眼中,陶谷不僅是一位博聞強記的官員,同時也是一位精于茶事的愛茶人。相傳陶谷寫了一本《清異錄》,共六卷,內分三十七門,其中“茗荈”章節專寫茶事。現如今學界對于《清異錄》是否為陶谷所著,存在爭議。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中認為,書中所載多為陶谷身后之事,因而推斷應是后人假托陶谷之名的偽書。復旦大學陳尚君教授《宋元筆記述要》中認為,也可能陶谷生前確實寫了一部分書稿,身后又有人摻入了一部分新內容,進而拼湊出了如今的《清異錄》。但不管怎么說,《清異錄·茗荈》中的內容并非人云亦云,而是收錄陸羽《茶經》時代之后的大量飲茶習俗逸事,具有補白茶史之功。陶谷愛茶懂茶的形象,也因《清異錄》而深入人心。
盧仝與陶谷皆可算愛茶之人,但二人命運卻又大相徑庭。陶谷一生身處朝堂,而盧仝則以隱士自居。陶谷入世,盧仝出世,截然不同。文徵明詩中提及這二位茶人,似乎也是在思考自己該何去何從。
歷史上的文徵明,對于出世為官一直沒有興趣。起初寧王朱宸濠派人送來書信和金銀,聘請文徵明入王府作幕僚,被其婉言謝絕。后來明嘉靖初,文徵明曾進京做翰林院待詔,參加編寫《武宗實錄》。但他在三年間卻三次辭官,最終好不容易被準回鄉,卻又因冰凍運河而滯留在了北通州。這時朝廷借機再次挽留文徵明,卻被他堅定謝絕,留在通州潞河不肯再回北京。一直到了來年春至河開,他便急急忙忙放船南歸蘇州了。
他的后半生,既沒有像陶谷一樣入世,也沒有如盧仝一般出世,而是醉心于山靜日長式的生活當中。
文徵明生于明成化六年(1470)十一月六日,卒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二月二十日,享年九十歲。在人活七十古來稀的明代,文徵明卻能以近百歲高齡辭世,絕對算得上是活神仙了。
看起來,真正愛茶之人,最懂得生活。懂得生活之人,又總能頤養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