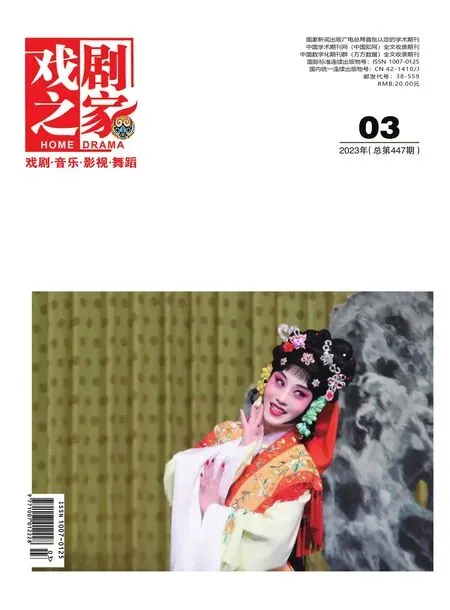中外早期舞劇藝術的比較研究
——以《王后的喜芭蕾》和《九歌》為例
李思晗
(北京舞蹈學院 北京 100081)
文學臺本的細致記錄與闡釋,以及宮廷畫師對演出場景的動態再現,使得《王后的喜芭蕾》在西方宮廷席間舞蹈的點點星光之后,成為第一顆在西方芭蕾史上始終閃耀的藝術明珠。與之相對的中國古代樂舞藝術明珠《九歌》,基于《九歌》的文字作品,其文化精髓得以傳世。兩部早期舞劇藝術的臺本呈現出舞蹈演出的重要史實,對于舞蹈形態、舞臺布置、人物形象、情節設置和主題立意等方面都有詳細的記載和闡釋。對兩者臺本的摘取和對比研究,可得出中外早期舞劇藝術的共性與個性,進一步挖掘早期舞劇形式背后的藝術自律性與藝術他律性。
一、創作舞蹈的生活藝術空間
早期舞劇藝術的發展是舞蹈藝術在生活空間和創作領域的相互滲透。《九歌》基于民間歌舞、祭祀歌舞的采集與創作而產生,其藝術創作來源于生活又再創了新的藝術形式,更側重于生活舞蹈藝術化。而西方的《王后的喜芭蕾》則是對已有藝術舞蹈與日常生活建立更深層次的鏈接,將舞劇藝術帶入日常生活之中,更側重于舞蹈藝術的生活化。無論是宮廷樂師博若耶,還是中國詩人屈原,都是中西方早期舞蹈藝術向舞劇最高形式轉變的推進者。一方面創作意識提升,將生活舞蹈藝術化;另一方面將創作歌舞融入日常生活,使舞蹈藝術生活化。
(一)西方早期舞劇藝術的舞蹈藝術生活化
《王后的喜芭蕾》在誕生之初,已經有席間芭蕾的藝術形式作為鋪墊。貴族對舞蹈藝術的喜愛是其推動力,深化舞蹈藝術與日常生活的關聯。1581 年,博若耶受到法蘭西亨利三世的王后路易斯的委托,為妹妹瑪格麗特與耶瑟公爵大婚慶典創作了《王后的喜芭蕾》,將舞蹈藝術的最高級形式——舞劇,同社會個人的婚慶宴會相聯系。
“博若耶接著描述了,他在波旁廳作出的特定的安排。在一頭,他建造了一個矮臺,供國王、王后、王子和公主端坐。在講臺的兩邊都是屬于大使和貴族夫人的區域。其他人坐在圍繞大廳四周的兩條走廊上。國王的右邊是潘和德萊德森林女神的小樹林。正對面是一個鍍金的穹頂,被叫做“黃金屋”,那里演奏著音樂。”[1]《王后的喜芭蕾》臺本有著大量對于舞劇表演空間、觀眾欣賞模式、華美的舞臺布景以及人物的描繪,精細流暢而華麗詩意地表現出第一部舞劇在藝術主張上的“窮奢極欲、盡善盡美”。不同于民間藝術舞蹈在集會表演中“舞蹈佐宴”的隨機性與自娛性,《王后的喜芭蕾》是帶有強烈創作意圖和審美指向性的統治階級屬性的生活藝術。早期舞劇藝術是眾人齊聚一堂、酒足飯飽后融于貴族生活的精神食糧。
(二)中國早期舞劇藝術的生活舞蹈藝術化
《九歌》是創作者屈原,經歷實地考察、民間歌舞采風后,根據江南民間祭祀的樂歌加工創作的系統完備的樂舞作品,襲用古題,但帶有藝術家極強的主觀創作意圖。《九歌》經過改編與加工,書寫成格調高雅的詩歌集,其文字一定程度上還原了樂舞的實況。王逸《楚辭章句》云:“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托之以諷諫。”[2]屈原改良了原本粗俗的文字語言部分,將清新婉麗的民間舞蹈風格加入神祠歌舞之中,形成凄美神秘的藝術風格。實現民間歌舞與創作樂舞的勾連,也是生活舞蹈藝術化的成果。
二、樂舞一體的綜合表演形式
詩、樂、舞一體的綜合表演形式廣泛存在于中西方藝術早期實踐之中,包括西方藝術文化之源的古希臘舞蹈也為綜合性表演形式。《九歌》與《王后的喜芭蕾》跨越時間、地域和民族因素的共性藝術特征,皆屬于“詩樂舞一體”的綜合表演形式,但是又有各自不同的創作目的。
(一)“詩樂舞一體”的娛人目的
《王后的喜芭蕾》中出現的綜合表意形式,其根本目的是以更加豐富的藝術形象和藝術感染力完成對于王權角色的塑造及整體的敘事性表達。為貴族婚慶獻禮和致敬王權的創作意圖,呈現并貫穿于其表演形式及表演內涵當中。《王后的喜芭蕾》臺本中記錄,“在‘第一部芭蕾舞’中,舞蹈只是幾個重要元素之一:器樂音樂、歌曲、詩朗誦、服裝和布景效果都受到了重視。用音樂使詩歌更多元;用音樂使詩歌交織,并且經常將兩者完美融合。就像古人從不離開音樂吟詩,而俄耳甫斯只伴隨詩歌來表演一樣。因此,我使芭蕾活躍起來,讓它說話,讓喜劇唱歌和表演,而且加上一些罕見且精心制作的布景和裝飾。”[3]從晚上到凌晨的5 個小時演出,兼有音樂、舞蹈、詩歌和雜耍,結合華麗舞美設計,形成具有敘事性和啞劇特色的歌舞戲劇樣式,創作同時滿足了視覺審美、聽覺審美和敘事理解的藝術體驗。“詩樂舞一體”其根本目的在于表演的娛樂屬性,通過啞劇特色的歌舞戲劇樣式突出敘事重心。其舞蹈語言所不能涵蓋的敘事性表達成分,配以詩歌和啞劇,加入具有獵奇性和沖擊性的藝術表現手段,能夠最大限度地表現出舞臺視覺的華麗感。
(二)“詩樂舞一體”的娛神旨歸
“詩樂舞一體”是我國古代樂舞的傳統表現形式,兼具表演性和敘事性。《九歌》的“詩樂舞一體”綜合表演形式是為了更好地呈現出神鬼形象及其民間傳說故事。《九歌》原文中寫道,“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九歌》有包括樂器、歌舞、戲劇、服飾和布景在內的綜合演出形式,以準確而豐滿的藝術形象和藝術形式,完成對于神話故事的再現,達到娛神目的。通過重要故事情節和形象塑造的呈現,達到模擬巫術與神靈溝通的目的。以表現神靈的方式娛樂神靈,以娛樂神靈的方式寄托崇敬與祈求。
三、神話素材的“人化”敘事改編
《王后的喜芭蕾》以及《九歌》都選用已有的神話傳說作為舞劇戲劇結構的素材。《王后的喜芭蕾》直接加入“人”的角色,《九歌》加入的是“人”的情感。《王后的喜芭蕾》更多呈現個人主義的藝術觀念,其國王角色的權威性體現出凌駕于神權的王權。而《九歌》當中對于神鬼形象的塑造以及接近人間情愛的情節呈現,則拉近了人神之間的距離,傳遞天人合一的君權神授的觀念,完成人神之間的精神溝通。
(一)凌駕神權的個人崇拜思維
《王后的喜芭蕾》與《九歌》,都是對于鬼神形象的藝術表現,都依托已經存在的神話鬼神角色進行藝術化的個性處理。《王后的喜芭蕾》中舞蹈性與敘事性是最為主要的兩大藝術特性。《王后的喜芭蕾》文本改編自古希臘神話女巫喀耳刻的故事,與原本結局不同之處流露出創作者的創作意圖與創作目的。
《王后的喜芭蕾》的臺本描繪道,“當所有的神靈攻擊了西爾斯的宮殿時,朱庇特用一個霹靂擊中了女巫,并把她帶到國王面前。”[4]將國王的社會性個人角色加入原本的神話傳說,是《王后的喜芭蕾》關鍵性的藝術處理。對于神鬼傳說的故事再現和人物塑造,都是為最后臣服于王權的個人崇拜思維做鋪墊。整個故事的走向和結局,都奔向對于王權的絕對擁護和對個人的極度崇拜。此時,神權低于王權,藝術創作當中的神性已然低于王室的統治階級地位,傳遞出至高無上的個人主義精神,也與中國傳統藝術觀念形成強烈對此。《王后的喜芭蕾》傳遞對國王與王后的尊敬與無限贊美。王力勝過神力,凌駕于神權之上的個人主義藝術氣息嶄露頭角。
(二)天人合一的君權神授觀念
中國傳統的王權觀念當中,具有天人合一的君權神授觀念。因此,在具有神性的藝術作品創作當中,經常出現神權與王權的統一與關聯,借用神權來提升王權的地位與權威。而對于神鬼形象的藝術創作常常通過人世間的情感與故事實現代入和投射,即通過神性與人性的結合來完成對于神鬼形象的藝術塑造和神鬼傳說的文本表達。凄美的愛情故事和悲情的生死別離引發民眾的共鳴,調動民眾的生命體驗,產生人性與神性之間的共情與共鳴。拉近神鬼形象與民眾之間的距離,實現藝術創作的表達與民眾欣賞之間的交流關系。
夏啟的《九歌》體現君王上天入地的超人神力,體現天人合一的君權神授思維。真龍天子依托神靈的絕對壓制,從而維護和加固統治力量的意圖毋庸置疑。而屈原的《九歌》是以娛神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藝術形象,表面上是超越人間的神,實質上是現實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畫和環境氣氛的描述上,既活潑優美,又莊重典雅,充滿著濃厚的生活氣息。《九歌》共有十一個篇章:《東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和《禮魂》。其中,《九歌》中存在大量的男女相悅之詞,在宗教儀式、人神關系的紗幕下,表演著人世間的鮮活生命。
四、統治階級的繁復審美導向
中外早期舞劇藝術呈現出統治階級在審美上的共性特征,即對于盛大場面的喜愛和繁復華麗的審美取向。正是華麗驚艷的藝術創作審美導向,使得統治階級集國家之力,集民族之力進行藝術創作。選用最精美的舞蹈道具和最華麗的表演場面,最大程度體現最高的藝術水準和極強的藝術影響力。由此也體現統治階級在中外的早期樂舞藝術發展當中,均作為藝術生產重要的推動力。只有在統治階級的生存環境當中,才能夠將早期的藝術推向最精致、最復雜的表現形式。他們所積累的財富和資本,才足以讓他們進行最具難度和最具復雜性的藝術創作實驗。正是基于這一得天獨厚的條件,才使得早期舞劇藝術在社會中得以產生和發展。
(一)奢侈華麗中彰顯財力
財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會影響力的重要體現。《王后的喜芭蕾》這部舞劇制作和創演當中花費的大量財力,象征著國家整體的經濟水平和統治者對于社會資源的絕對占有。大量的經濟投入,并不完全出于對藝術創作和藝術表現力的單純需求,更多的是為彰顯財力和政權實力。王后對于這部芭蕾舞劇的預設是壯觀的,華麗的。博若耶對于華麗的場景描述為:“噴泉里面有三個水池,上面裝飾著海豚、美人魚的雕塑。這些雕塑是由拋光的金銀制成的。芳香的水從最上面的池子緩緩流入第三個最寬廣的水池。”[5]舞劇裝飾都由金銀制作,水池由香水灌滿。演員們身著珠寶制成的衣服,使用真金白銀的精致道具。舞劇在奢華而精致的藝術品搭建的舞臺上表演。王后不惜用600 萬法郎巨資,精心策劃了這場富麗堂皇的演出,用簡單直接的形式彰顯權力與國力。
(二)宏大場面下體現神力
與窮奢極欲的西方早期舞劇藝術的表現手段相比,中國的早期舞劇藝術更側重于“以眾為美、以巨為觀”的場面打造。宏大的場面烘托出神鬼力量的巨大與神圣。宏大場面烘托出鬼神人物形象的疏離感和權力感。整體的樂舞氛圍清新雅致,但是通過盛大歌舞場面的眾多參與者和壯觀的表演,呈現出歌舞娛神時的敬仰之姿和虔誠心態。夏商以來,中國審美形成“以眾為美,以巨為觀。窮奢極欲、極盡奢侈。”的基本風向,《九歌》依舊保留對于宏大歌舞場面的喜好,延續歌舞娛神的藝術功能追求,誕生了壯美繁復而詩意浪漫的審美觀念。
五、結語
中國夏商周三代舞蹈的女樂作品,特別是神祠歌舞《九歌》宣告中國古代舞蹈由原始生命活動走向部分人的藝術活動。西方芭蕾第一部舞劇《王后的喜芭蕾》標志著芭蕾藝術初具雛形。兩者在不同的時代環境下,呈現出一定程度的藝術共通性與差異性。中外早期舞劇藝術是藝術自律性與他律性相互作用的結果,呈現出的共性藝術規律實際上是舞蹈藝術自律性所決定的。而共性特點之下的中西方區別,實際上是藝術他律性的具體體現。中西方早期舞劇藝術的對比研究,是在兩者對比基礎上的更深的自我認知和藝術特色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