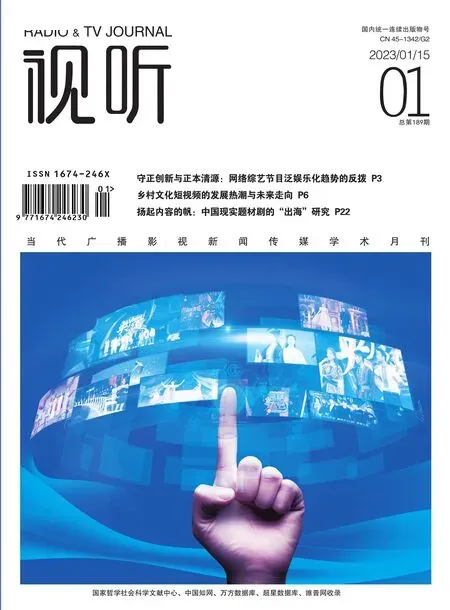守正創新與正本清源:網絡綜藝節目泛娛樂化趨勢的反撥
◎于柳
所謂“泛娛樂化”,可以用尼爾·波茲曼提出的“娛樂至死”概念來理解。“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①這種現象在綜藝節目尤其是網絡綜藝節目中呈現得尤為明顯,必須引起高度重視。應從正面進行疏導,創作更多優質的網絡綜藝節目,借助新媒體的傳播來擴大影響,實現對網絡綜藝節目業態的凈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希望廣大文藝工作者堅持守正創新,用跟上時代的精品力作開拓文藝新境界。”②對此,中央廣播電視總臺(下文簡稱“總臺”)等主流媒體責無旁貸。以《央young之夏》為代表的節目為網絡綜藝節目樹立了標桿,也證明了總臺的實力和擔當。
一、傳播優先:借力“流量主持”打造年輕態嘉年華
新媒體時代,在“傳播優先”的客觀要求下,引流是做好網絡綜藝節目的重要前提之一。然而,也正是因為意識到了引流的重要性,整個互聯網世界充斥著很多低俗化、庸俗化的引流方式。除了需要相關部門加強監管外,亟須進行相應的“撥亂反正”和正面引導。總臺匯聚了全國高層次的主播人才,這些主播自身的業務素質毋庸置疑,再加上近幾年總臺融媒體戰略的推動,很多主播在年輕人中的關注度和話題度都很高,他們因此成為總臺節目制作過程中的重要引流資源。基于此,《央young之夏》選取了在互聯網平臺上很有影響力的“央視boys”(康輝、撒貝寧、朱廣權、尼格買提)和“國民初戀臉”王冰冰、“暖瑩瑩”莊曉瑩、“體壇女神主播”馬凡舒等一眾流量主播來給節目增加熱度,在最短時間內營造話題,在年輕觀眾中打開市場。
二、模式創新:以主持人為主體的“團綜化”試驗
利用流量實現引流僅是做好一檔網絡綜藝節目的“萬里長征第一步”,觀眾通過這些流量主播開始關注節目。但如果節目本身的形式不足以吸引他們,或者說形式和其他網絡綜藝節目趨同,自然也無法提升觀眾黏性,勢必會陷入“流量為先、節目注水”的怪圈。《央young之夏》借助主播群體和團綜形式實現了模式上的創新,走出了網絡綜藝節目模式革新之路。
(一)以主持人為核心敘事主體
不同于市面上的綜藝節目類型,《央young之夏》另辟蹊徑,以總臺優質主播資源為主角,策劃了國內首檔垂直于主持人角色的原創綜藝節目。一般意義上的主持人主要起到串聯節目的作用,是襯托嘉賓這些“紅花”的“綠葉”。《央young之夏》中,這些“綠葉”站到了舞臺中心。整個節目從先導片開始,到備戰排練、探班直播,再到最后的節目公演環節,都完全圍繞主播這一核心要素推進。不同于總臺之前打造的《主持人大賽》,《央young之夏》的策劃重點不再是展示主持人精湛的職業技能,而是更加符合綜藝節目的套路,通過展示主播的才藝才華、性格特點等,營造傳統觀念中關于總臺主播角色的反差感,最大限度利用觀眾內心的情感認同,以“養成系主播”的方式給予受眾更加接地氣的親切性觀感和參與性體驗,確保了節目的收視率和關注度。
(二)“團綜模式”的創新實踐
自2018年以來,團體綜藝成為十分流行的綜藝節目類型之一。傳統團體綜藝的主要受眾是偶像團體的粉絲,由此也造成這些節目往往只能在粉絲之間傳播,很難吸引相關的潛在觀眾,無法實現“破圈”效應。況且,隨著國家對選秀類節目的嚴控,加之這些節目本身內容的趨同性、共情的虛假性等原因,“團綜模式”發展空間不斷變小。《央young之夏》在傳統的“團綜模式”上實現了再創新,參加節目的主播大多是“熟人面孔”,橫跨老中青三代,他們都有較為廣泛的群眾基礎和深厚的觀眾緣。整個節目賽制不再是單打獨斗、爭奪“C位”,而是采用“隊長+隊長助理”模式自行招募隊員,繼而用排練和公演的團體競技方式向前推動節目。但是節目本身的競技性不強,這樣在組隊的過程中就能給予這些主持人更多的選擇。不同風格主播之間的搭配也會產生更多的可能性,生產出更多“名場面”,創造更多意想不到的綜藝效果,賦予了“團綜模式”更豐富的時代內涵。
三、內容為王:增加節目的品位和厚度
即使在新媒體時代,模式也只是個外殼,如果沒有高質量的內容作為支撐,再好的形式也只是個“空架子”。現階段,很多網絡綜藝節目在泛娛樂化的影響下存在“重形式、輕內容”的問題。但是,《央young之夏》沒有停留在模式層面,而是在節目內容上搞創意、花心思,通過增加節目的青春感、豐富度和延續性,提升節目內容的整體品位,打破了不同觀眾群體之間的圈層壁壘,實現了真正的“雅俗共賞”。
(一)內容的青春感
從《央young之夏》的名字來看,“young”(青春)代表著總臺擁抱新媒體、擁抱年輕人的決心,這是節目的立意之一。在節目的公演環節,這種內容渲染得尤為明顯。節目中,總臺的40多位優秀主播褪去先前在主持臺上的職業裝扮,用更加年輕化的表達方式和表演內容,將青春的主題貫穿其中。比如,王冰冰跳女團舞、倪萍講脫口秀、康輝和朱廣權表演說唱等,這些都是時下年輕人最喜歡的節目類型。“冰皮月餅隊”表演的《娃娃臉》《“爺童回”》等節目更是勾起了青年觀眾的兒時記憶,喚起強烈的情感認同。
(二)內容的豐富度
《央young之夏》以長短視頻結合的方式來呈現節目內容,主要由成團的先導片、40多位主持人排練短視頻、公演前的發布會,以及5個多小時的公演直播等組成。這樣的編排方式按照時間順序涵蓋了臺前幕后,滿足了不同受眾的觀看需求。比如,在最受關注的公演環節,節目內容是傳統與當代、中國與西方、古典與流行各種元素的集合,最大限度地擴大節目的受眾面和影響力。在四大戰隊的成團直播和相關排練視頻中,節目又把這些平時臺前端莊典雅的主播的幕后生活場景呈現在觀眾面前,展示主持人更加多元、真誠和可愛的一面,用真人秀的方式滿足受眾的好奇心,這也符合新媒體時代網絡綜藝節目內容的制作要求。
(三)內容的延續性
優質的網絡綜藝節目往往會形成優質IP。制作方要不斷開發這些優質IP的價值,拓展資源生態體系,實現內容上的延續性。總臺通過《央young之夏》,扶持了更多主持人“出圈”,從而形成品牌和熱度。節目公演結束后,總臺依然在積極運營“young”品牌,從IP開發到品牌轉換,體現內容延續性。2021年年末,總臺開播了網絡綜藝節目《冬日暖央young》,繼續利用自己的主播IP,以才藝展示和冰雪運動的內容助力2022年北京冬奧會,取得了良好的傳播效果。2022年,總臺相繼開發出《開工喜央young》《這young的夏天》《這young的世界杯》等一系列“young”品牌的網絡綜藝節目,為其在新媒體平臺開發網絡綜藝內容奠定了堅實基礎。
四、全網覆蓋:借助新媒體實現傳播“破圈”
“媒體融合的實質是打破媒介形態的藩籬,突破邊界。”③像網絡綜藝這類依托移動互聯網存在的節目更是需要實現多樣態融合、全平臺覆蓋,方能取得良好的傳播效果。《央young之夏》作為主流媒體推出的網絡綜藝節目,更是將全網覆蓋做到了極致,成功實現了節目的“破圈”效應。
(一)立足“央視頻”,實現臺網聯動
總臺不僅是國家電視臺,也是國家級的融媒體傳播平臺,不包括第三方平臺賬號,光是自有的移動端App就有17個。其中,“央視頻”作為我國首個國家級5G新媒體平臺,自然成為《央young之夏》新媒體宣傳的主陣地。在“移動優先”的思維下,“央視頻”App上的《央young之夏》被作為宣傳和推介的重點,其視頻號擁有粉絲16萬人,在公演之夜獲得超2300萬的播放量。在直播當天,“央視頻”App還專門開設了專場互動抽獎環節,并開通了線上投票功能和在線購物專場,以此提升觀眾的參與度。同時,借助總臺傳統的宣傳資源,如通過《新聞聯播》報道、公演當夜同步在央視綜藝頻道直播等“臺網聯動”方式,實現優質節目從小屏到大屏的內容反哺,這種反哺激發了更為廣闊的傳播效應。
(二)打造全媒體宣傳矩陣,實現全網覆蓋
除了“央視頻”,總臺還將《央young之夏》的節目片段分發到抖音、快手、B站、微博等新媒體平臺,做到了全網覆蓋。在分發的過程中,總臺并不是不加區分、平均用力,而是做到了依據不同平臺的用戶群體,設計不同類型的視頻,進行精準投放和文案宣傳。比如,針對快手平臺用戶年齡層次跨度較大的特點,總臺設置的相關視頻話題更為直截了當、通俗易懂。針對年輕人的集聚地——抖音,《央young之夏》使用“我的心是冰冰的”等更具有網感和時代特色的宣傳文案,順應年輕人的觀看心理。節目相關視頻在抖音累計播放量達到6.2億次。“央視頻”在微博更加注重話題設置,利用微博的社交媒體屬性引發公眾討論,僅#央young之夏#這一話題就有8.2億的閱讀量,引發了超18萬次討論,足見其熱度之高。
五、正本清源:以主流價值紓解“算法焦慮”
泛娛樂化的背后掩映著一場娛樂盛行年代的價值虛無危機④,這也是網絡綜藝節目最令人詬病之處。在算法價值觀的驅使下,部分網絡綜藝節目的價值導向挑戰著公眾底線。“總臺作為黨媒,始終承擔著傳遞社會正能量與主流價值觀的職責。”⑤《央young之夏》是網絡綜藝節目市場中的一股清泉,在綜藝節目的包裝下更好地傳播了主流價值,承擔起傳播正面文化、樹立正面導向的任務。
(一)重新定義偶像內涵
偶像對個人起到重要的引導作用。特別是對青少年來講,正面的偶像可以幫助青少年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但是近幾年,娛樂圈的所謂“偶像”被局限定義在高顏值、好身材、有財富等表面特征上,在道德素質和才華能力方面則要求變低,甚至頻繁曝出負面新聞和“塌房”事件。如果這一亂象持續存在,結果堪憂。在這種情況下,《央young之夏》的主播們通過自己的硬實力和正形象,向社會樹立了有德有才的正能量榜樣。參演節目的40多位主播都經過總臺精心挑選,他們在節目中面對排練和公演都兢兢業業、認真負責,在節目外保持著謙遜真誠的姿態,被眾多網友點贊和崇拜。許多網友稱:“這才是真正意義的偶像!”這讓我們對于偶像的內涵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和理解。
(二)積極向上的價值引導
在“流量至上”的利益驅使下,很多網絡綜藝節目為了所謂的播放量和曝光度,通過劇本演繹、惡意剪輯等方式刻意營造嘉賓之間的矛盾沖突,渲染人物內心的陰暗部分來炒作節目熱度。這樣一來,雖然節目的關注度提高了,但是損害了互聯網環境,帶壞了社會風氣,也對主流價值觀的傳播產生了消極影響。《央young之夏》秉承著“綜藝也要有主流價值觀”的制作原則,摒棄當下網絡綜藝節目市場存在的“糟粕”,專注于通過優質內容輸出達到正能量引導的效果。雖然《央young之夏》力圖拉近與年輕觀眾的距離,但不一味地逢迎市場,而是選取青春中所包含的積極、成長、奮斗的理念,幫助青少年建立起“定義青春奮斗,書寫華彩人生”的積極向上的價值取向,這才是《央young之夏》節目的內核。
(三)彰顯文化自信
網絡綜藝節目必須承擔起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的責任。《央young之夏》節目有效破除了部分網絡綜藝節目過度娛樂化的弊端,讓優秀傳統文化以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實現了潛移默化的滲透,幫助受眾建構起文化自信。《央young之夏》公演中的很多節目彰顯出了文化自信。比如,融合了漢服文化、古典詩詞的《央young衣裳》,糅合了傳統樂器和古典舞蹈的《左手指月》,集合京劇、越劇等傳統戲曲的《拜壽》,主持人演唱的《竹石》《萬疆》等歌曲所包含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自豪感,都被主播們通過符合時代潮流的多樣方式展現出來,在文化傳播中增強了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六、結語
從某種意義上說,以《央young之夏》為代表的節目探索是主流媒體應對網絡綜藝節目泛娛樂化趨勢的一項反撥實驗,成功展示了新媒體時代網絡綜藝節目在相對寬松的創作環境下應該有的良好文藝生態,值得網絡綜藝節目制作者學習借鑒。同時,此類節目也為互聯網平臺的內容建設和價值引導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在正本清源的基礎上,重新定義偶像,引導主流價值觀,彰顯文化自信自強。
注釋:
①[美]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M].章艷,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4.
②田沁鑫.用精品力作開拓文藝新境界(堅持“兩創”書寫史詩)[N].人民日報,2022-04-08(020).
③曾白凌.論傳統媒體融合的邊界、偏向與在場[J].現代出版,2020(02):32-38.
④郝娜,黃明理.“泛娛樂化”現象:現代性語境下崇高精神的虛無困境[J].思想教育研究,2020(01):68-73.
⑤梁慧.主流媒體網絡綜藝的品牌定位與傳播策略探析——以《央young之夏》為例[J].視聽,2022(08):6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