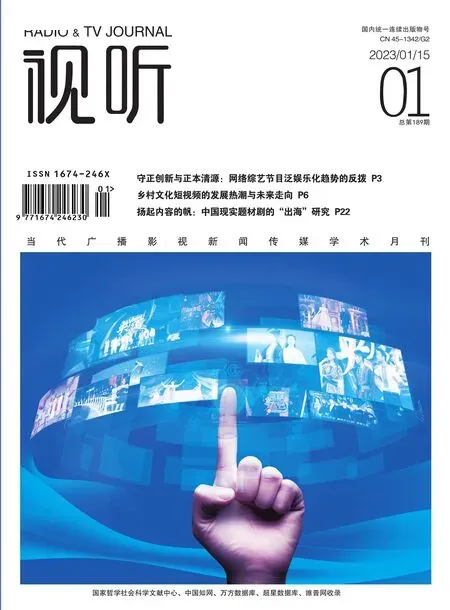虛擬偶像驅動消費行為的內在機理研究
◎宋鈺
2021年,虛擬數字技術被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意味著虛擬數字技術成為我國實現經濟社會創新發展的重要戰略資源。與虛擬數字技術相伴而生的虛擬數字人也獲得了數以億計的流量關注。其中,虛擬偶像成為虛擬數字人在文娛產業的重要應用。虛擬偶像,即非真實偶像,是依托建模、動捕、渲染等技術,并結合二次元文化建構起來的,在虛擬場景中進行大眾演藝事業的虛擬形象。隨著互聯網的發展,虛擬偶像逐漸成為Z世代群體青睞的文化消費品,其代言、演唱會、周邊產品、專輯等都能以各種商業形式盈利。艾媒咨詢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虛擬偶像核心產業規模為34.6億元,周邊市場規模為645.6億元,這兩項數字預計在2022年將分別達到205.2億元和3334.7億元。然而,虛擬偶像畢竟是一種技術打造的幻象,并非真實存在。這種技術營造的“非真實形象”為何能夠刺激粉絲的消費欲望,滿足粉絲需求?這一問題成為虛擬偶像消費的研究重點。本文試圖從虛擬偶像的技術設計、身體消費、情感維系三個維度,分析虛擬偶像以何種機制吸引粉絲的注意力、刺激粉絲的消費欲望,并創造出消費神話。
一、技術設計:智能化人格塑造與沉浸體驗的生成
虛擬偶像的生成是數字技術和青年亞文化、體驗性虛擬文化共同作用的結果。①它的產生和發展與數字技術的進步緊密相關,并展現出技術造星的文化表征。3D建模、計算機圖形技術使虛擬偶像的形象更加立體生動,語音合成技術使虛擬歌姬的歌聲與真人無異,人工智能技術使虛擬偶像具備人格化特點,虛擬現實、增強現實、全息投影技術賦予虛擬偶像身體展現。對偶像工業而言,如何吸引粉絲的注意力并將其轉化為消費行為,是其商業運作的核心訴求。對粉絲而言,為虛擬偶像打造人格化特征、實現傳統偶像無法賦予的陪伴功能,建構虛實共融的傳播場景并能夠與虛擬偶像進行沉浸式交互,則是提升對虛擬偶像認同感、刺激消費欲望的重要途徑。從技術角度出發,認同感與消費欲望的生成來自以下兩個層面。
(一)以技術為基礎:智能化人格打造
偶像人格化的缺失容易使粉絲產生負面的情緒反應,粉絲往往會為更具個性和人性的偶像買單付費。與虛擬偶像相比,真人偶像所具有的真實故事、個性人性等人格化特征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虛擬偶像內部人格的先天性缺失卻可以通過技術的外部建構來彌補。以人工智能為技術基礎的虛擬偶像從虛擬歌姬發展到虛擬網紅、虛擬主播,變得越來越親民、有個性、生活化,逐步體現出近乎完美的人格化特質,給人們帶來全新的技術文化體驗。例如,通過數字科技與傳統文化結合生成的虛擬偶像“翎”,不僅在節目《上線吧!華彩少年》中出演梅派京劇《天女散花》,以致敬梅蘭芳先生,還登上各大雜志封面,成為品牌代言人,在社交媒體與粉絲互動,展現出與真人偶像無異的人物形象和人格化特征。伴隨著人工智能、虛擬現實、5G等技術的發展,虛擬偶像人格魅力的展現舞臺或可從賽博空間延伸至現實世界,全面嵌入人類的現實生活。虛擬偶像還能在開展演藝事業的同時,充當粉絲的陪伴式角色。與真人偶像相比,虛擬偶像的技術特性使其可以更加精準地獲得用戶反饋,成為趨于完美的、更加符合用戶期待的智能化人格偶像,實現保羅·霍金森所描述的“模糊人與技術、真實與人造、現實與表征之間的界限”的跳躍。②
(二)以技術為中介:沉浸式體驗塑造
鮑德里亞認為擬像具有三個層次:仿造、擬像、仿真。這是一個描述復制物與原型之間差異存在、差異消失、擬像成為超真實的過程。③沉浸感正是一種“模型與真實的界限消失,模型成為幻象,成為真實世界并且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已經無法分辨何為幻象何為真實”的體驗。虛擬現實技術帶來了擬像的第三個層次——仿真。當模型成為幻象,超真實的世界就誕生了,人們更易被技術控制,沉浸在虛擬現實技術營造的仿真世界中。以虛擬偶像的舞臺為例,作為一個并無實體存在的虛擬人物,全息投影、虛擬現實技術在其舞臺表演中的應用為粉絲和觀眾帶來了一種沉浸式體驗。沉浸感形塑的重點在于對身體在場的感知。全息投影技術對虛擬偶像身體、表情、動作等進行了擬真化展現,在為觀眾打造一場夢幻般的視聽盛宴的同時,還可以與臺下觀眾產生互動,從而營造出對真實肉身的在場感。這種在場感使得粉絲模糊了虛擬和真實的邊界,產生與虛擬世界的融合感,保證粉絲可以充分沉浸其中,并通過提升粉絲的注意力和專注度來激發其產生心流體驗。在2017年舉辦的“洛天依2017全息演唱會”上,粉絲們對著舞臺上的虛擬偶像洛天依大呼“老婆”“寶貝”,并伴隨著洛天依的歌唱節奏吶喊、互動、歡呼,集體陷入一種無知覺的“沉浸”狀態。此外,以網絡平臺為中介的虛擬偶像傳播也能為粉絲營造出沉浸式體驗,技術平臺的實時彈幕、評論、點贊等功能會帶給粉絲一種集體圍觀的錯覺,使粉絲在觀看時沉浸其中,并不自覺地產生消費沖動。
二、身體消費:身體與消費欲望的創造
身體消費是將“身體”作為消費對象,即身體的商品化過程。在現代社會,技術的更新迭代、媒體的潛移默化、信息個性化推送、數據的精準反饋,每一個因素都使身體成為經濟資本,成為消費社會的主要消費方式。偶像工業中,“以貌取人”是一種常態。偶像的體格、面孔、身體是其吸引粉絲和觀眾最基礎、最原始的視覺表象,對偶像身體的消費已經成為一種時代表征或文化癥候。虛擬偶像與真人偶像的差異在于,其身體并非客觀實在,而是一種“虛擬身體”。但與真人偶像一樣,虛擬偶像也是一種重要的消費資源,其背后的娛樂資本在追求利益的原則下,依靠虛擬偶像身體的呈現與展演,實現粉絲群體消費欲望的創造。具體而言,虛擬偶像的身體消費主要有以下兩種形式。
(一)身體的符號化:審美迎合
居伊·德波提出“景觀社會”這一概念,認為整個社會生活都顯示為一種巨大景觀的積聚。鮑德里亞在“景觀社會”的基礎上提出消費以符號為中介。④其中,符號以視像化的表征滲透于大眾文化的方方面面。從這一層面出發,視覺化的虛擬偶像身體正是符號消費的重要資源,是一種技術創造的虛擬符號景觀。以技術呈現為基礎的虛擬偶像,通過各種策劃、組織和技術處理將身體變為視覺文化的主角,身體的審美得以進入視覺消費的話語場域。在虛擬偶像的消費初始階段,娛樂資本會對虛擬偶像的身體進行修飾和潤色,制作方通過運用CG、動畫、繪畫、動作捕捉等技術,為其打造出理想審美的身體景觀:無瑕的肌膚、精致的妝容、時髦的裝扮、完美的身材等。形象設計之外,虛擬偶像的性格、動作、表情、聲音、才藝都使其雖無生命與情感,但呈現出人格化的視覺形象特征。在這個技術建構的虛擬世界中,身體成了虛擬偶像的重要資本。真實與否已經不再是粉絲的關注焦點,對虛擬偶像身體的符號消費才是最終目的。虛擬偶像正是以這種迎合二次元審美的“符號化身體”的打造和編碼,滿足粉絲群體的視覺觀感與享受,刺激粉絲的消費欲望,造就一種全新的身體美學。
(二)身體的媒介化:身體展演
虛擬偶像的“身體媒介化”是指虛擬偶像的身體成為信息傳播的媒介。虛擬偶像不僅通過迎合社會審美進行身體形象塑造,還通過展演形式刺激粉絲消費。在展演過程中,虛擬偶像的身體成為其虛擬形態中的經濟資本。杜威認為,身體是我們能夠思考、交流、體驗之所有的最初視角;梅洛-龐蒂賦予身體主體地位,認為身體既是可以被感知的實體存在,也是感知世界的媒介物。⑤虛擬偶像正是以這種技術化的虛擬身體來感知世界和把握世界,但它所有的身體展演形式(唱跳、表演等)都是基于技術作為中介而產生的。同樣,粉絲對虛擬偶像的消費也是以虛擬的身體展演為載體。在展演過程中,虛擬偶像和粉絲之間會基于虛擬身體產生一定的聯系,通過觀看虛擬偶像的身體展演完成消費體驗。2020年12月,B站在上海舉行了BML全息投影演唱會,邀請了來自中日兩國的十幾位虛擬偶像同臺演唱。當晚,不僅演唱會現場座無虛席,B站在線直播觀看人氣也高達1000萬,在同時段排名第二位,人氣完全不亞于真人明星演唱會。虛擬偶像利用身體資本進行展演,推動了身體的媒介化進程,以其物化形態促使粉絲消費購買。
三、情感體驗:粉絲情感的生產與收編
在傳統社會,人們的情感交流主要通過人際交往來實現。現代社會,社會關系弱化,社會交往碎片化,人際關系淡漠,使人們的情感滿足方式發生了變化。尤其對于Z世代的年輕群體而言,通過傳統的情感獲取機制已經不再能夠完全滿足其自身的情感需求,情感體驗傾向于虛擬化、符號化。威廉·雷迪認為,人們為了避免情感痛苦,會通過情感表達來感受情感自由,但若達不到理想的情感狀態,人們便會努力尋找能夠自由表達情感的場所、機構或儀式,他稱之為“情感避難所”。⑥作為一種二次元文化,虛擬偶像之所以能夠“圈定”諸多年輕群體,創造出不容小覷的消費神話,正是由于其迎合了網絡環境下Z世代年輕人的情感需求,給予了他們真實的情感體驗,成為了“情感避難所”。本文認為,虛擬偶像主要通過以下方式生產并收編粉絲情感,驅動消費行為產生。
(一)參與生產:親密感的生成
長期以來,粉絲一直被視作是無生產性的,直到費斯克與德賽都的研究發生轉向。費斯克認為粉絲是具備創造力的群體,德賽都則用“盜獵”和“游牧”描述粉絲的積極、流動與變化。在技術賦權下,虛擬偶像粉絲又發生了角色轉變,由“游牧者”“盜獵者”轉變為更具意義的“強生產者”。⑦正如亨利·詹金斯所言,隨著傳播媒介發展,當代人對偶像的情感需求已經從對偶像作品的被動消費轉變為參與偶像文本創作的積極生產。粉絲的這種強生產者特性與虛擬偶像的獨特性密切相關。與真人偶像不同,虛擬偶像屬于一種開放性文本,崇尚UGC(用戶生成內容)文化。例如,洛天依、初音未來等虛擬偶像在出廠之時都較為簡單且留有空白,僅有簡單的人設與形象設計,這就給粉絲和創作者留下了很大的創作空間,從而可以親身參與偶像的內容生產過程。例如,洛天依的經典傳唱歌曲《普通DISCO》《達拉崩吧》等都是其粉絲創作,這兩首歌曲甚至在各大晚會上多次被真人偶像翻唱。在音樂之外,許多具備剪輯、寫作、設計技能的粉絲也會自發參與虛擬偶像的視頻、同人文學、平面設計等文本的創作和生產。如在《達拉崩吧》發行之后,大量粉絲在B站創作了《達拉崩吧》的“天津快板版”“古箏版”“理發版”等各種再生性文本。在這一過程中,粉絲將自己的情感釋放于虛擬偶像身上,兩者的情感關系變得更親密自主。
(二)自我投射:認同感的形塑
雅克·康拉提出“鏡像理論”,指人在嬰兒時期對“鏡中我”的滿足。將這一理論置于粉絲偶像崇拜的語境下,可以發現,偶像實際上是粉絲自我心理投射的載體。對粉絲而言,偶像是他們自我信仰和理想的終極體現,是粉絲理想自我投射出的一種“鏡像”。從偶像角度出發,偶像多樣化的特質、標簽正好為不同性格特征、年齡階段、社會階層、興趣愛好的粉絲提供了多樣化的理想模型,體現著人們在世俗社會中對美好的追求。對真人偶像來說,為了能夠更快地獲得流量和商業利益,其背后的經紀公司往往會為其打造人設,粉絲也樂于為自己的偶像加上各種濾鏡標簽。殊不知,完美的背后,偶像不過是一個平常人。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曝光率的增加,真人偶像的言行與其在粉絲心中的理想形象難免會產生一定的偏差,甚至發生“塌房”事件,粉絲由此陷入情感損耗與認同危機中。相比之下,完全依靠技術生成的虛擬偶像顯得更加安全。虛擬偶像的開放性為粉絲的自我投射提供了完美的容器,粉絲可以將自身的理想形象投射到虛擬偶像的創造中,將抽象的理想自我轉化為具象的形象。此外,粉絲還可以將自身的故事、情感投射到虛擬偶像的衍生內容創作中,如歌曲、同人文、舞蹈等。在自我投射過程中,粉絲不僅得到了情感滿足,還塑造了理想自我,形塑了自我認同,認同感的形塑反過來又驅動消費行為的產生。因此,虛擬偶像的意義已經不局限于娛樂、消費,它更是承載無數人情感與夢想的載體。
(三)社群鞏固:歸屬感的產生
“社交媒體平臺的發展為粉絲之間的情感聯結和互動提供了便利,形成粉絲社群。作為網絡社群的代表,粉絲社群一向具有自組織性、高忠誠度、高凝聚力等特征。”⑧虛擬偶像粉絲群體主要聚集于B站。在B站中,粉絲群體以趣緣為紐帶,共享著一套特定的闡釋規則、審美原則和符號體系。首先,粉絲進入社群具備高門檻性,必須成功回答出與偶像相關的問題才能獲得社群的準入資格,進入社群也必須嚴格遵守群體內部的規則。其次,粉絲群體內部成員各司其職。再次,粉絲群體內部有著一套共享的符碼,他們通過傳遞與偶像相關的符碼,達成相互之間的理解與共識。最后,消費成為粉絲認同表達的重要途徑。粉絲通過將自己購買的偶像的專輯、周邊產品等分享到粉絲群體內部或社交賬號來證明自己的粉絲身份。在這一層面上,消費成為布爾迪厄口中的一種產生社會權利和社會區隔的資本。粉絲們以虛擬偶像為中心,通過以上社群鞏固行為,營造健康豐富的趣緣聚集社群生態,強化粉絲的集體歸屬感,驅動粉絲消費。
四、總結
技術發展將原本處于分散狀態的粉絲集結成網絡社群,使偶像工業形成了一種高度依賴粉絲的商業增值模式。從真人偶像到虛擬偶像,粉絲群體的消費欲望和能力更是被有效激活,創造出虛擬偶像消費神話。從技術設計來看,人工智能技術為虛擬偶像打造的人格化特質,給受眾帶來全新的技術文化體驗。虛擬現實和全息投影技術使虛擬偶像成為“超真實”,為粉絲營造一種真實肉身的在場感與沉浸體驗,促進消費沖動形成。從虛擬偶像身體視角來看,虛擬偶像的身體成為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既是一種視覺符號,也是媒介本身,充當信息傳播的載體。虛擬偶像通過迎合異次元審美的身體形象塑造和以技術為中介的身體展演,實現粉絲消費欲望的創造與生產。從粉絲情感的生產與收編來看,虛擬偶像通過粉絲的參與、投射、鞏固,成為粉絲的“情感避難所”,情感成為虛擬偶像消費的驅動力之一。
注釋:
①付茜茜.技術神話與符號升級:文化消費視域下的人工智能虛擬偶像[J].天府新論,2021(02):150-159.
②Paul Hodkinson.Media,Culture and Society[M].London:Sage,2011.
③孔明安.物·象征·仿真——鮑德里亞哲學思想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95.
④[法]居伊·德波.景觀社會[M].王昭風,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16.
⑤於春.傳播中的離身與具身:人工智能新聞主播的認知交互[J].國際新聞界,2020(05):35-50.
⑥孫一萍.情感表達:情感史的主要研究面向[J].史學月刊,2018(04):20-24.
⑦宋雷雨.虛擬偶像粉絲參與式文化的特征與意義[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9(12):26-29.
⑧顧楚丹.社會網絡視角下社交平臺社群的互動儀式鏈研究——以粉絲社群為例[J].中國青年研究,2022(02):37-4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