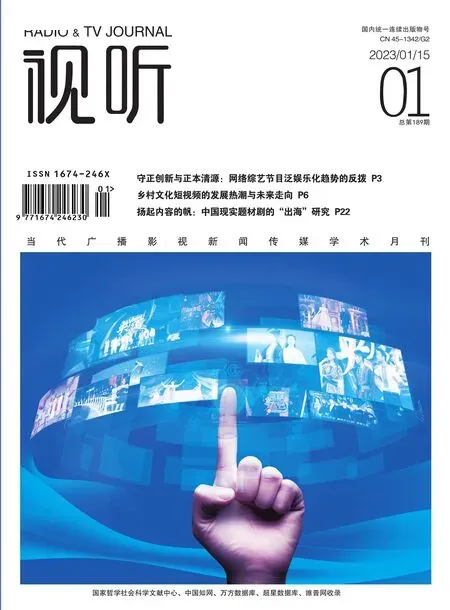新力量導演的作者性研究
◎史斐煜
新力量導演是在互聯網語境下應運而生的群體,有著與此前導演群體不同的特點,他們的創作既滿足了觀眾對影片的期待,也促進了中國電影工業的發展。新力量導演在商業上取得巨大成功,成為構筑中國電影產業的中流砥柱,受到業界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注意到這一群體的創作。
一、新力量導演的產生
中國電影進入新千年以來,電影創作者的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僅有與第五代導演、第六代導演一樣的學院派,還有演而優則導的演員導演、小說作者轉型的導演、其他行業的跨界導演以及在電影節嶄露頭角被挖掘的導演等,這些導演構筑了新千年以來中國電影產業百花齊放的創作格局。很明顯,不能用簡單的代際對當前的導演群體進行劃分。這些導演雖然構成復雜、風格多樣,但在個性中又有某些共性,特別是這批導演均產生于互聯網蓬勃發展、國家文化產業不斷繁榮的時代背景下。無論是在2014年中國電影新力量推介盛典閃亮登場的陳思誠、韓寒、路陽,還是憑借作品在國外屢獲大獎的畢贛、馬凱、張濤,抑或是在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中闖出重圍的曹保平、文牧野,都在作品中呈現出強烈的作者性風格,但他們又與第五代導演的“尋根”和第六代導演的“精英”相區別,成功地游走在個人性與市場性的二元對立之中。
二、新力量導演的作者性呈現
(一)地域書寫:多元載體的巧妙運用
縱觀新力量導演的創作不難發現,在他們的作品中出現了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即地域文化的呈現。與第五代導演的民俗奇觀不同的是,他們用一種更加在地化的方式對地域文化進行呈現,使作品具備了強烈的現實主義風格。
方言是影片中極力凸顯的一個載體。方言是一個區域最為顯著的標志,可以直觀地反映地域的審美特色,表現真實的風土人情和生活現狀,同時其作為一個標識,也能吸引同地域的觀眾選擇這部電影,擴大電影的受眾群體。邵藝輝導演在處女作《愛情神話》中,就選擇把上海話作為全片的人物對白。她說,在選擇非職業演員時,把會說滬語作為一個重要因素。因此,老白、李小姐、老烏、格洛瑞亞等人物在上海方言的襯托下顯得生動有趣,他們仿佛是現實中的人物一般,觀眾在觀影時也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自己代入這些人物的生活中,與他們一起歡笑、落淚。《火鍋英雄》則使用重慶方言作為影片的主要語言,影片中的人物都是小人物,方言的使用更加符合小人物的生活環境,使片中人物充滿了生命張力。同時,重慶方言的使用也讓影片蒙上了一層黑色幽默的面紗,例如于曉東在搶劫銀行時說的“膽大騎龍騎虎,膽小騎個老母雞”這句重慶歇后語,把當時人物的情緒渲染到極致,在緊張中透露出一絲輕松,放慢了影片的節奏,也讓觀影者得到情緒的舒緩。畢贛憑借作品《路邊野餐》斬獲國外數項大獎,該片成為當年豆瓣評分最高的華語電影,他后來執導的《地球最后的夜晚》還亮相第71屆戛納國際電影節。盡管畢贛的作品不多,但已經具有了非常強烈的個人風格,尤其是對貴州方言的使用,使影片中的人物更加立體生動。例如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中,萬綺雯站在臺上拿著話筒時,貴州方言的旁白便出現,營造出人物如夢如幻的內心世界,從而表現出萬綺雯內心的孤獨與迷茫,塑造了一個在外流浪的漂泊者形象。中國地大物博、城市眾多,不同的城市人物性格脾性也是大相徑庭的,而方言的獨特魅力可以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同時也能完善影片的鏡語體系,使主題的表達更加直觀完整。
此外,地域的書寫離不開城市景觀的呈現。電影是一種時空藝術,既需要時間的表現,也需要空間的塑造,從而滿足觀眾對電影的認同。而對空間的塑造,既是影片人物所處環境的描述,也是作者創造出來的世界,以此來完成內涵的傳遞與表達。
重慶因其地理位置的詭譎一直深受電影創作者喜愛,無論是大后方時期的電影,還是“十七年”的英雄電影創作,抑或是新時期以來涌現出的眾多電影,重慶這一3D立體的城市都頻繁地成為導演們的選擇。例如,在影片《火鍋英雄》中出現的輕軌、巷子、階梯等具有鮮明指向性的重慶標志,對影片黑色風格的塑造起到了巨大作用。劉波和劉小慧的多次相遇就是在輕軌這一空間內完成的,軌道線的錯綜復雜與不斷交織也暗示著兩位主人公命運的盤綜錯雜,兩人通過輕軌完成了舊相識的重逢,既符合現實,又暗示了人物走向。此外,火鍋作為重慶最著名的文化標志,成為影片的片名,讓觀眾在看到影片名稱時就聯想到重慶,從而引發重慶本地人的強烈認同。
陳思誠的《唐人街探案》系列無疑是近些年系列電影的代表作,其因詼諧幽默的風格深受大眾喜愛。其中,異域敘事也為影片增色不少。每部影片都會選擇一個城市,《唐人街探案1》中的泰國,《唐人街探案2》中的紐約,《唐人街探案3》中的東京,這些異域文化滿足了受眾的獵奇心理。同時,異域空間也對影片敘事起到了推動作用,異域的風俗文化也輔助了影片類型的塑造。在《唐人街探案3》中,推動故事發展的是日本的本格推理和黑幫文化,使故事環環相扣、跌宕起伏。
《小時代》系列拍攝地選取的是中國最繁華的城市——上海,這一城市的選擇無疑為劇中的人物塑造起到了關鍵作用。無論是顧里的豪華別墅,還是宮銘的豪華大樓,在上海這一環境下都顯得真實合理。與《小時代》塑造的燈紅酒綠、奢靡浮華的上海不同,《愛情神話》回歸生活化場景,其空間選擇包括老白購買打折商品的超市、李女士居住的逼仄的房屋、修鞋匠的小門面等。影片中,上海不再是符號化的摩天大樓、豪華公寓,而是讓觀眾觸及了人物真實,將重心集中在一個個人物中,而不是城市景觀之上。
地域空間經由人類社會產生,又反作用于人類社會,而電影作為一種敘事手段,既需要地域空間的支撐,又重新建構著地域空間。作為接受主體,觀眾在觀看中對電影生產出的地域空間產生認同,又因主體的差異性而產生了多維的解讀。同時,電影也向接受主體展現異域風情,激發其向往之情,呈現人們“未曾接觸”的空間,幫助人們認識地域和解讀地域。新生代導演也因此成為推動地域文化研究的中堅力量。
(二)微觀敘事:以小見大的主題呈現
電影是一門敘事藝術,既包括敘事人物的塑造,也包括敘事主題的表達。因成長環境的緣由,“文革”成為第五代導演人生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以此對民族文化進行反思與批判。第六代導演在出世時就被排擠在主流之外,于是紛紛將鏡頭對準不被社會注意的小人物或社會的邊緣人,如小偷、流氓、搖滾樂手等。新生代導演雖然也以塑造小人物為主,但與第六代導演不同,他們并不是為了自我的表達,而是利用小人物平易近人的特點,拉近觀眾的距離。
在敘事人物的選擇上,最為明顯的就是小人物的塑造。將視角從宏觀的英雄敘事轉向對小人物的描述,成為近些年眾多新生代導演創作的選擇。他們將鏡頭對準普通人,用從容平實的鏡語體系書寫小人物之間的悲歡離合或生活瑣事,在平緩的節奏中傳遞自身的價值觀。用貼近現實的人物作為主人公,不僅拉近了與觀眾的距離,也使得劇情真實可信,引發觀眾認同。
文牧野導演透過對社會問題的敏銳洞察,展現了他對邊緣人物的關懷。《我不是藥神》讓名不見經傳的文牧野一炮而紅,電影也憑借幾十億元的票房高居中國電影票房排行榜前十,而影片中最為人稱道的是由徐崢飾演的主人公程勇的轉變。在前期,程勇整日渾渾噩噩不求上進,經營著一家瀕臨倒閉的印度神油店,家暴前妻,拖欠房租,無法贍養年邁的父親。他是家庭生活中的失敗者,社會中的小透明,他人眼中扶不起的阿斗。黑暗的生活非但沒有燃起他的斗志,反而加重了他的頹廢落魄。自我放逐、自我否定的態度不僅使他在物質世界被邊緣化,更使他在心理上成了弱勢群體。當偶然得知走私格列寧賺錢的門路時,在巨大金錢誘惑的驅動下,程勇翻倍賣藥賺取巨額差價,在欲望的影響下做出種種快意人生的行為,儼然一副暴發戶的形象。日益膨脹的物質欲望,必然引發人們精神世界的巨變。物質的享受導致人們精神世界的坍塌,不斷迷亂著人們的生活。在程勇身上,物質世界在一天天地強大,感官的享受也一天天飽滿,但虛無的精神世界則處于不斷破碎與重構中。在實體世界得到滿足之時,他便不愿意往前走,所以當受人威脅時,他選擇全身而退,將代理權轉賣給毫無道德底線、販賣假藥的張長林。演員將人物的懦弱、自私、市儈的形象演繹得淋漓盡致,塑造了一個貪圖利益、俗不可耐的小市民形象。而后,呂受益和黃毛的離世促使程勇開始了痛苦的思想斗爭和心理掙扎,他潛在的善良和責任感被激發。他不僅看到了自己的苦難,更是看到了普通大眾的苦難,在生命痛苦中領會到了生命力量的伸張,喚醒了內心的良知和對生命的敬畏,決定冒著牢獄之災的風險重新為病人代購藥物。程勇褪去市井小販的形象開始重建自我,從欲望化、商品化的誘惑中突出重圍,擺脫了物質崇拜和精神危機,使自己的人生境界得到了升華。他從唯利是圖的藥販蛻變成犧牲自我的“藥神”,把外在的世界連續到自身的世界,進而實現了人性的回歸、自我的復歸,完成了在現代人性危機下的自我救贖,實現了自身價值,彰顯出地位卑微的小人物身上的人性力量。
文牧野導演的第二部影片《奇跡·笨小孩》延續了前作《我不是藥神》小人物的塑造,以景浩救妹妹為主線,講述了激勵人心的溫情故事。為了給妹妹籌集醫藥費,景浩孤注一擲,召集了一群并肩奮斗的伙伴,組成了奇跡小分隊。無論面對何種困難,這些小人物都沒有輕言放棄,在艱難的困境中散發出人性的光輝。小人物的逆襲盡管有一層浪漫主義的色彩,但是對于現實中的觀眾來說,無疑是一種情感的投射,點燃了觀眾對自我的定位思考和對社會問題的反思,并透過影片實現了對社會的再認知。①
小人物的塑造同樣是為了服務主題。在當下的社會中,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會感受到生活帶給自己的痛苦與希望,影片通過普通人的人生遭遇將觀影者的真實生活進行了投射,觀眾與影片中的人物共情。與此同時,影片還通過小人物來展現大時代,表現出當下被大時代裹挾的小人物的艱難生活。②在影片《無名之輩》中,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線索,通過環環相扣的敘事方式將人物與人物進行連接。仔細解讀該片不難發現,這些人物的行動元其實都來源于一個詞——尊嚴,同時尊嚴也是影片的主題。馬嘉旗被車禍奪走了雙腿,但是面對闖入家門的劫匪,依舊不卑不亢,而自己小便失禁與劫匪的拉扯更是讓人動容。想要尊嚴的她并不希望被陌生人看到自己的不堪。而馬嘉旗的哥哥馬先勇也是一個為了尊嚴而不斷奔波的人,他希望可以找到槍來實現自己的價值。作為劫匪的眼鏡和大頭也有著自己的英雄夢,可是卻在電視中看到自己搶劫的手機都是模型機,他們一直想要維護的尊嚴在現實面前顯得不堪一擊。影片中的人物都是“無名之輩”。但是在影片后半段,馬嘉旗在燦爛的煙花下醒來,看到劫匪留給她的話,她又重新堅定了活下去的信念,而其他無名之輩也在故事的推進中找到了生命的意義。正如影片結尾的臺詞一樣,“我們都生活在陰溝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這也正是導演想要給觀眾傳遞的主題。
(三)工業美學:藝術商業的二元平衡
陳旭光教授在梳理近些年新生代導演的創作時提出了一個新的觀念,即電影工業美學。他認為,在互聯網時代涌現出的這一批電影人,在創作中很好地遵循了電影工業美學原則:秉承電影產業觀念與類型生產原則,在電影生產中弱化感性、私人、自我的體驗,代之理性、標準化、規范化的工作方式,游走于電影工業生產的體制之內,服膺于“制片人中心制”但又兼顧電影創作藝術追求,最大程度地平衡電影藝術性與商業性、體制性與作者性的關系,追求電影美學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③,成為“體制中的作者”。
在電影類型創作上,新生代導演遵循傳統電影類型的創作原則,同時又將多個類型進行雜糅,使影片既符合國外電影人的審美,又滿足國內觀眾的期待。在國外屢獲大獎的電影《白日焰火》,不僅讓導演刁亦男走進大眾視野,還讓演員廖凡成為內地第一位柏林影帝。影片遵循了犯罪片的類型框架,又加入了懸疑、愛情、黑色、警匪等類型元素,大大增強了影片的商業性。與此同時,刁亦男也沒有讓藝術性讓位于商業性,在影片中也表現出強烈的個人風格。影片中多次出現破舊的工廠、雜亂的房間等環境,以及張自力因受傷而調崗、吳志貞命運的悲哀等,勾勒出在時代滾滾向前的過程中普通人悲劇命運的生活圖景。《刺殺小說家》是路陽繼《繡春刀》系列后的又一力作,該片緊跟數字化的時代潮流,將科幻、魔幻、武俠等元素雜糅,塑造了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為觀眾帶來了一場極致的視聽盛宴,使影片具備了強烈的想象力消費的特質。同時,影片從傳統文化中取材,融入宗教文化,為影片蒙上了一層東方奇幻色彩。影片用新的創意促使中國的視效公司創新思路,推動了中國電影工業結構的完善。
除去在類型美學上的創新,在影片宣發上,新生代導演非常善于利用互聯網,借用大數據的優勢,使影片得到最大程度的宣傳推廣,同時也善于利用不同的媒介,實現跨媒介傳播與互動。畢贛執導的《地球最后的夜晚》便是成功利用互聯網進行宣傳的一個典型,影片以“跨年之吻”為噱頭,吸引了無數情侶。盡管影片因為冗長晦澀而飽受詬病,但是數億元的票房已是藝術電影的票房奇跡。與《地球最后的夜晚》票房口碑相悖現象不同的是作品《你好,李煥英》的出現。作為賈玲的處女作,《你好,李煥英》憑借54億元的票房使賈玲成為中國最高票房女導演。《你好,李煥英》的成功,自然也離不開主創團隊對互聯網的利用。在點映后,影片借助抖音的裂變式傳播,用“看電影哭用完了一包紙”等主題吸引了眾多觀眾的好奇心,同時還在抖音平臺上傳了電影海報的同款濾鏡,各路UGC紛紛打卡,也促進了影片的迅速傳播。而影片溫暖感人的結局契合了春節檔觀眾喜歡合家歡影片的心理。可以說,《你好,李煥英》的成功正是對電影工業美學的一次完美踐行。動畫電影《哪吒之魔童降世》50億元的票房填補了國產動畫電影的空白,成為近年來的一匹黑馬。探析其背后的成因可以發現,影片在宣發上也是借力了互聯網。在電影的創制階段,針對哪吒這一人物形象的選擇,創作團隊就在微博上進行征集,引發網友的激烈討論,使影片未播先熱。在影片上映后,“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臺詞在網絡流行,為電影進行了引流。之后,導演餃子及其創作團隊的拍攝故事被各大媒體爭相報道。
不得不承認的是,當前,電影創作更強調全流程的產業化和工業化,不僅需要創作者具備技術創作能力,更需要他們具備技術創作思維,并像一根紅線,貫穿在影視制作的全流程中。與代際導演不同的是,新力量導演伴隨著互聯網產生,他們天然就對互聯網等技術有著親近性,在技術掌握方面游刃有余,而且他們接受了更高級、更先進的教育。不少新力量導演有著理工科的教育背景,或者擁有一些技術經驗,因而他們更能適應當下的生存環境,即技術化生存。他們憑借自己的技術思維,以及對當前觀眾觀影需求的了解,獲得了商業上的成功。而他們在技術方面的實踐,也在反推中國電影工業的發展。例如,在《路邊野餐》中,畢贛使用了大量的長鏡頭,還將2D和3D結合,而郭帆的《流浪地球》更是直接開啟了國產科幻電影元年,里面大量的特效全是由中國團隊制作,場景全是實景搭建,歷經數月完工。整個制作工期較長,既需要對團隊進行強有力的把控,也需要資金和技術的大力支持,這對于中國電影的技術發展無疑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餃子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也是中國自制,從人物形象、人物動作到故事環境等,每個鏡頭都源自主創團隊的精心制作。當然,電影工業不僅僅是高科技、大場面、炫酷特效,這些新力量導演的創作無疑為中國電影工業的發展起到了助推作用。概言之,對新力量導演踐行電影工業美學的研究,有助于構建中國電影學派,推動中國電影工業的完善。
三、結語
新力量導演并不完全是成功的、優秀的,也有一些影片成績慘淡,飽受爭議,但是更多的導演創作是不容忽視的。他們在商業和藝術之間游刃有余,并沒有一味地表達自我,也沒有讓藝術讓位于商業,他們用小視角來窺探大時代,關心時代浪潮中的普通人,同時對電影類型進行反芻,創作出許多新的且獨屬于中國自己的電影類型,對中國的喜劇片、青春片、懸疑片等類型進行了開拓和延展。與此同時,作為在互聯網環境下成長的一代,新力量導演具備了技術思維、媒介思維、電影思維、游戲思維,對電影創作的全流程進行了革新,有效推動了中國電影工業的完善,對中國電影從電影大國向電影強國的邁進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研究新力量導演作者性的創作思維,有助于深化對中國電影產業、電影美學等方面的研究。當然,新力量導演的發展還道阻且長,他們將以更多優秀之作推動中國電影再創輝煌。
注釋:
①邱麗.生存困境與空間隱喻:《奇跡·笨小孩》的小人物敘事研究[J].視聽,2022(06):101-103.
②李超然,于文夫.《無名之輩》:書寫小人物的敘事策略和藝術特征[J].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20(06):167-170.
③陳旭光.新時代新力量新美學——當下“新力量”導演群體及其“工業美學”建構[J].當代電影,2018(01):3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