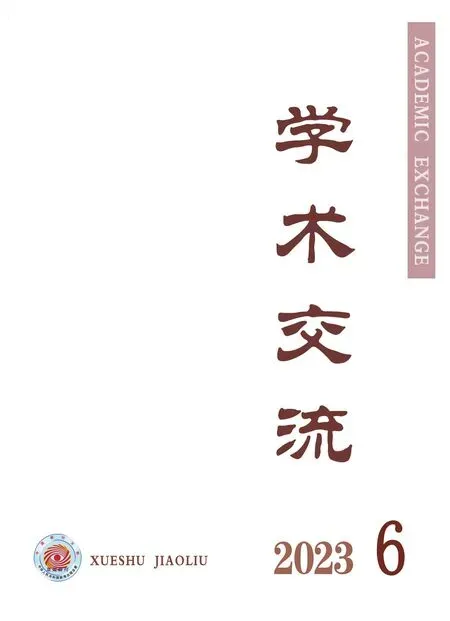馬克思主義視域下的高爾基小說空間敘事意蘊
高建華,仲維琪
(1.三亞學院 人文與傳播學院, 海南 三亞 572022;2.大慶市教師發展學院, 黑龍江 大慶 163000)
法國哲學家、社會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從知識和權力的角度來分析空間問題,在其著作《規訓與懲罰》中討論了空間與權力的關系。在現代法國思想大師列斐伏爾看來,空間具有物質和精神兩種形式,二者可以共同出現,并提出了著名的“空間三一論”,即空間表征、表征空間和空間實踐。此外,他在空間與性別、空間與政治之間的關系上具有獨特的認識和見解。諸多空間理論的不斷引入和發展為我們分析和闡釋文學文本提供了良好的切入點。高爾基作為成長于兩個世紀之交的俄國作家,見證了俄國底層社會人民的生活窘況,切身體驗過下層民眾的苦難,目睹了封閉昏暗的生活環境摧殘著人的身心,不平等的性別關系加重了女性被奴役被支配的從屬地位,專制制度禁錮著人們的思想意識和精神意志,因此,高爾基的文學創作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底層人民的無情剝削和壓榨,體現了深厚的人道主義思想。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作為西方現代社會思潮之一的馬克思主義對處于世紀之交的俄國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高爾基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接受和社會實踐活動的經歷使得他成為把馬克思主義思想融入文學創作的踐行者。自1888年起,他曾兩次到俄國各地漫游,在歷經人間心酸的同時也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思潮,并參加了具有先進思想的工人和知識分子組成的秘密小組。高爾基是列寧與勞動解放社共同創辦的第一家全俄馬克思主義政治機關報《火星報》的忠實讀者,在《火星報》進步思想的教育和影響下,高爾基又進一步比較系統地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高爾基借由文學作品表達了對底層人的同情,抨擊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對人的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毒害。高爾基在其著作《俄國文學史》中說道:“文學是社會諸階級和集團的意識形態之形象化的表現,是階級關系最敏感并最忠實的反映……”[1]1這表明,他是把階級論作為文學指導思想的,并將尖銳的階級矛盾通過文學創作體現出來,呼吁人的精神解放和自由意志的實現,其中蘊含著豐富而又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
一、生活空間:歷史唯物論與人道主義思想
從20世紀后期開始,批評理論出現了“空間轉向”,眾多批評家關注到空間批評的重要性。陸揚在《空間批評的譜系》中闡釋道:“空間不復是沒有生命的容器,而成為人類意識的居所。”[2]82空間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活動場所,二者相互影響形成了獨屬于人類個體的“人化空間”。在從自然空間轉化到“人化空間”的過程中,這一概念被作家賦予了審美價值和人文內涵。在高爾基的小說中,封閉簡陋的日常生活空間是底層貧苦民眾的悲慘境遇的縮影,反映沙皇專制制度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這是高爾基小說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及人道主義精神的繼承。
歷史唯物主義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思想。歷史唯物主義強調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存在指社會的物質生活過程,其基礎及決定力量是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違反人類個體發展的物質生活條件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人的意識的奴性發展,究其根源,是資本私有制肆虐的結果。非人化的生活空間成為奴役底層民眾的場所,這與馬克思主義強調的人道主義相背離。歷史唯物主義不僅關注物質基礎,也重視人的精神需求;既談事物及歷史發展的規律,也談人的自由意志;既重視階級分析,也關注人類個體的全面發展。高爾基小說空間敘事呈現出自由意志被消磨、個性被壓抑、奴性被強化,并且階級屬性十分鮮明的逆行發展方向。高爾基在其小說中以物質性的實體空間彰顯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精神內核。
《二十六個和一個》是高爾基早期現實主義作品之一,反映了社會底層人民生活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狀態。文本以“我們”的視角展開敘事,借由工人的生活空間再現了俄國底層民眾的苦難。他們從早到晚被關在陰暗潮濕的地窖里做工,密不透風的窗戶切斷了他們與外部世界的唯一聯系,箱子本是四周密閉、內部黑暗的儲物之所,可是工人們卻整日生活在位于三層樓之下的石頭“箱子”中。石頭“箱子”沉悶擁擠,摧殘著人們的身體和意識。“我們二十六人在這巨大的石屋的地窖里就是這么生活的,我們的生活是那么沉重,仿佛整個這座三層樓的石頭建筑就直接蓋在我們肩膀似的……”[3]318地窖與三層石頭閣樓構成了垂直方向上的上下壓制關系,象征著人與人之間無法忽視的等級秩序。“我們”每天像活機器一樣機械地重復著同樣的工作,身體早已形成肌肉記憶,精神也因此變得麻木不堪。艱苦的勞動條件和嚴酷的生活環境使這里的“奴隸們”已經失去了自己的自由意志,更無從談起人的個體發展。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現實的人無非是一定社會關系的人格化,他們所有的性質和活動始終取決于自己所處的物質生活條件。對于劣性物質生活條件的展現意味著被奴役者所具備的非人屬性,工作的地窖成為老板監禁工人的“石牢房”,二樓金繡作坊女工順其自然地把“我們”稱作“囚犯”,極其準確地說明了作坊工人真實的生存境況。福柯曾在《規訓與懲罰》中通過監獄這一特殊場所表明權力在空間中是如何運作的,其中所使用的“規訓”一詞明確了權力主體對被支配對象在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控制。在肉體上,通過限制被規訓者的活動范圍和行為動作實現權力在空間中對肉體的支配。工人們不停地“用手搓著有彈性的發面,還要搖晃著不讓它變硬;同時另一些人用水和著面粉”[3]317。在作坊中由資本家與工人形成的固定等級秩序作為無形的“紀律”在意識層面控制和奴役著人們,使他們漸漸習慣順從和忍耐的生存狀態,進而接受自己的奴隸身份。
歷史唯物主義從總體上來把握人類社會的全部生活,把人類的社會生活看作一個統一的有機整體。空間作為社會生活的言說場所,承載著底層人民的苦難與艱辛。《面包房里》涉及的諸多空間場景大多是黑暗隱蔽的,反映出19世紀俄國社會的丑惡現實。文本開頭便描寫了華西里制作面包的工場的位置和環境,“在地下室里,每扇窗子外面都張上密密的鐵絲網……室內是半明半暗的”[4]6。這一生活空間的設置具有多層面的隱喻內涵。地下室是一種人類生存的物質空間和精神空間的隱喻,它有著上與下的間隔、內與外的區分。這種空間性的區隔與19世紀俄羅斯的階級壁壘和社會現狀密切相關。而這一維度的區隔在高爾基這里變得更為簡單化了,具有極強的政治性,將此作為底層民眾與上層權貴的社會階級分隔的空間隱喻。地下室里常常籠罩著蒸汽和劣質煙草的霧氣,灰塵和粉屑充斥在各個角落。陰暗潮濕的地下室在方位中處于“在下面”的位置,是垂直方向的向下一極,因而總是受到來自上層空間的壓制和威脅。在面包工場里,華西里老板是權力的持有者,其他人都要服從于他的權威,受他支配。比如懲罰“我”去喂豬、隨意打罵為他工作的工人、干涉“我”的思想,甚至對“我”強行灌輸他所認為的那套“人生哲學”,這是現實生活中底層人從物質到精神自由都被剝削壓榨的真實寫照。
加斯東·巴什拉曾在《空間的詩學》中將人類詩意地棲居之地化為想象的空間,其中所提及的空間形象承載了人類的精神意識。高爾基在作品中所描繪的隱蔽性的角落空間,對于其筆下的底層民眾來說,是一個“避難所”式的存在。正如巴什拉所言:“靈魂的每一次退隱都有著避難的形象。角落這個最骯臟的避難所值得我們作一番考察。”[5]174角落相對于寬敞明亮的大空間而言,處在一個不被注意的狹窄空間,而處于社會邊緣的俄羅斯民眾,他們常常在角落里縮成一團,尋求屬于自己的歸宿。對于長期生活在底層的工人們來說,身體蝸居于隱秘黑暗的角落,實則是內心世界尋求庇護的一種表現,以此肯定自己作為人的存在;另外,外部空間的邊緣化折射出他們內心的怯懦卑微,揭示出長期受制于權威之下的人們螻蟻般的生存狀態。
歷史唯物主義中的社會意識指社會的精神生活過程,廣義指社會的一切意識要素和觀念形態,包括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形式。《母親》這一文本涉及的生活空間主要是工廠和家宅兩部分,即工人每天工作的工廠和工作結束后居住休息的灰色小屋子。人的精神意識被奴役與心靈的歸屬通過工廠和家宅兩個帶有不同色彩的空間得以顯明,而人們的精神生活在以往全然由掌握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左右。處于世紀之交的俄國社會剛剛擺脫了農奴制的壓迫,新興資本主義便快速進入生產中并日漸占有統治地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剝削和奴役著工人們的身心,他們每天被工廠的汽笛聲吵醒,機器和蒸汽的隆隆聲充斥在工人生活的各個角落,冒著黑煙的煙囪高高聳立在工廠上空,顯得陰沉而威嚴。生活在工廠附近的工人們無時無刻不籠罩在壓抑和沉悶的空氣中。工廠里的機器使人們成為資產階級私有制的賺錢工具。機器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象征,剝削和奴役著人的肉體和心靈,造成了人的自身完整性的分裂和喪失。枯燥乏味的機器生產把工人異化成了沒有正常情感的工具。工廠的機器聲和汽笛聲震耳欲聾,煤煙和油臭熏染著人們的面龐。工人們整天與機器為伴,等待被榨干身體里的能量。沉重枯燥的勞作使人的心中積郁著煩躁和痛苦,從父輩繼承下來的仇恨潛藏于人的內心,與肉體上無法消除的辛勞融為一體,由來已久。酗酒和打架早已成為年輕人生活的一部分,他們甚至習慣忍受生活對他們始終如一的壓迫,害怕打破這種無聊枯燥的生活常規,認為一切變化只會讓生活變得比現在更加糟糕,從而使自己受到變本加厲的壓迫和奴役。通過勞動創造了一切的工人反而被自己所創造的機器所制約,日復一日的工作使他們淪為資本家獲取利益的工具,失去了做人的尊嚴,換來的只有貧困、饑餓和疾病。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重視人的健全發展,其理論核心就是人的發展和人的自由,重視普通人的基本權益以及人性的全面發展。在高爾基的小說中,由官府和資本家所組成的支配性的資本主義空間,作為一種權力工具剝削和支配著工人階級。金錢至上的工廠主暴露出貪婪丑惡的嘴臉和作為資產者剝削的本質,以及在其身上所潛藏的資產階級的偽善性和欺詐性。高爾基借助文學文本揭露出資產階級剝削者的丑惡行徑,暴露了專制制度的黑暗統治,其中隱含著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的批判,以及對馬克思主義人道理論的繼承與探索。
二、性別空間:異化理論視域下的兩性關系
亞里士多德曾經直言:“女性是不完全的男性,女性的身體就像是孩子的身體一樣是不完整的……男人表現為命令,女人表現為服從。”[6]55這一觀點將男女兩性劃分為彼此對立的空間,而性別的差異直接造成二者生存空間的不同,以及他們在空間中身份、地位和權力的不同。性別空間并不能被簡單地理解為男性或女性生活和存在的地理環境或物理場景,而是在深受社會觀念影響下由男女兩性共同構建的復雜關系場。高爾基在俄國世紀之交關注到被異化的男女兩性關系,在創作中揭示了現實生活中被異化的現象和扭曲的人性。
異化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馬克思主義異化理論的認同、繼承和探索,同樣構成了白銀時代宗教哲學家視野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內核。[7]9高爾基小說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殘酷的社會環境下被奴役和異化的人。《二十六個和一個》這一文本反映了俄國世紀之交處于社會底層之人的生活狀況。小說中人物的思想意識尚未覺醒,在工作上他們是勤懇的勞動工人,在兩性關系上女性是男性的附庸。新來的面包工人“大兵”剛來到老板開設的作坊,便高談闊論自己如何游刃有余地周旋在姑娘們之中。與金繡作坊的女工廝混成為他樂此不疲的消遣,甚至將兩個姑娘為他爭風吃醋打架的事作為夸耀的資本。由于空間的封閉壓抑,工人們渴望與外界交流,他們將內心的渴望寄托在一個金繡作坊的女工妲尼亞身上,甚至將她神化,把她當作生活中的太陽。他們幫她開酒窖沉重的門,替她劈木柴,把她當作圣物一樣崇拜,不容他人褻瀆。就是這樣一位被“我們”奉為偶像的女子最終也難逃男性的魔爪,臣服于“大兵”的誘惑之下。奴性意識和愚昧的狀態使底層女性沉淪為男性的“物品”,作為一場工人們博弈中的籌碼和工具而存在。高爾基由此揭示出生活底層女性心靈的愚昧無知,同時也映射出對立失衡的男女兩性關系。當工人得知她被“大兵”征服之后,便開始對她展開侮辱和咒罵,這是心目中的“偶像”轟然崩塌之后的一種非理性行為。妲尼亞在“我們”眼里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我們”身處昏暗的社會底層,將一切理想和希望寄寓他人,并將其奉為女神。而當神壇倒塌時,人們心中的那份信仰和希望也隨之消亡。
在諸多影響下由男女兩性所構建的性別空間這一場域中,空間被賦予了性別化的特殊意義。在《面包房里》中,老板娘總是作為一個膽小無知的跟隨者出現在華西里和愛果爾旁邊,或蜷縮在無人問津的角落,在生存空間上表現出強烈的依附性和邊緣感。女性與廚房、臥室等家庭空間聯系起來,而象征著男性權威的華西里則常常出沒于工場、酒館等公共空間,彰顯其男性力量。社會性別的二元對立直接導致社會空間的等級配置,男性與女性將社會空間一分為二,生產的、支配性的空間屬于享有社會特權的男性,而生育的、從屬性的空間則歸于處于權力劣勢的女性。在華西里成為新一任的面包店老板之后,老板娘失去了利用價值,她在華西里的打罵中變得麻木,習慣了忍耐和順從,逐漸失去自我。在這里,女性只是作為男性發家致富攫取利益的跳板,隨后便淪為無用的“他者”,因此,她只好低頭跟在華西里的后面,眼含淚水度日。高爾基小說中的女性通常伴隨著男性活動的空間而出現,并且她們大多受男性統治者的控制與約束而無任何話語權,集中體現了底層女性的奴性意識與從屬地位。在《面包房里》中,華西里在談到女人時總是帶著一種探索和沉思的神情,對于她們,不談外貌,只關注胸部、臀部、足部等私密部位,言語中帶著輕浮和淫穢之意。他的情婦因能夠滿足于其肉體和精神上的需要而依附在他身邊,并分管他所開設的面包鋪子。由此可見,女性活動的空間始終附屬于男性權威之下,受他們支配,沒有個人尊嚴與自我選擇的權利,女性主體也被異化成非人的狀態。
《母親》中的女主人公尼洛夫娜與弗拉索夫的結合同樣充滿了諸多不幸,二人成為夫妻始于弗拉索夫粗魯鄙俗的求婚,這也體現了男女兩性關系上的不平等。女性在屈辱和壓迫之下被強行占有,毫無表達自我意志的權利。女性的自我主體性在男性的侵占下早已解體和喪失。在日常生活中,弗拉索夫是家中唯一的經濟來源,尼洛夫娜則依附于他、依靠著丈夫賺來的薪水維持生計。經濟上的依附使她受制于丈夫,為他服務,受他支配,照料著他的生活起居,還要時常忍受他以暴力手段宣泄心中的痛苦與不快。弗拉索夫常用“混蛋”呼喚妻子,完全不把她當人看。尼洛夫娜在丈夫在世時總是沉默不語,她是一個沒有話語權的失語者,在屈辱中度日,默默忍受生活的沉重枷鎖。身處家庭中的女性在以丈夫為中心的男性權威之下變得膽小懦弱,而沙皇政府的專制統治使本就地位低下的女性沒有任何政治權利,只能一味地順從和屈服,甚至被冠以“非人”的地位也從不反抗。“別人把她看作牲口,而她長期以來也毫無怨言地默認自己是牲口。”[7]185生活上的痛苦使得尼洛夫娜將希望寄托于上帝,在虛無縹緲的信仰中尋求精神的寄托。這是底層婦女在不公平的性別空間里精神被異化的生動寫照。恩格斯曾在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對當時社會背景下的婚姻關系作出詮釋。他指出,個體婚姻制度并非推動了男女之間的和解,而是“作為一性的被別一性所奴役,作為史前時代從未有過的兩性對抗底宣布而出現的”[8]62。由此揭露了男性權力支配下的女性地位。歸根結底,男女兩性的不平等關系是以經濟條件為基礎的私有制發展的結果。
在《經濟學手稿(1857—1858)》和《資本論》等著作中,馬克思以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基礎進一步闡明了異化的本質,在這些著作中,他明確地揭示了異化問題的實質,并依此理論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具體的、實證的、深刻的分析與批判。[9]9在《母親》中,由男女兩性構成的性別空間發生了質的轉變。從弗拉索夫與尼洛夫娜形成的支配與被支配的不平等關系,慢慢在母親與巴維爾之間發生變化,從而構成引領者與跟隨者的良性互動,并且在這一過程中促進了女性社會地位的轉變和自我意識的覺醒。高爾基在《論羅曼·羅蘭》中寫道:“這種女性了解到自己肩負著文化鼓舞者的作用,她要作為這個世界最合法的女主人,作為她們創造出來的、并在她面前對自己的事業負責的男子們的母親,威嚴地和完全平權地走進世界。”[10]216性別空間正被賦予新的內涵和意義,以往的兩性關系正面臨解構和重構。女性能夠走出家庭的束縛,進而在革命中找到生活的意義、實現自己的價值,母親逃離家庭束縛、尋求自我發展的成長歷程印證了馬克思主義在教育人、改造人方面的巨大作用。
三、政治空間:階級力量的博弈與自由意志的成長
列斐伏爾認為:“空間并不是某種與意識形態和政治保持著遙遠距離的科學對象,相反,它永遠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11]62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強調空間與社會的相互影響,政治空間是社會關系的產物,一定程度上反映社會中的階級關系。階級霸權通過空間霸權得以實現,而空間霸權又以固化的空間位置和空間活動為符號標志。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矛盾不可調和,資本家在現實空間中施行階級霸權以獲得既得利益,工人則在變態的權力空間中淪為犧牲品。階級力量的博弈透過空間顯現,體現著從未平等的階級關系,不平等的空間差異是社會關系失衡的反映。
《二十六個和一個》這一文本中,在作坊里工作的二十六個工人每天要從早晨工作到晚上十點鐘,即使在工作強度如此大的情況下,基本生活也無法保障。伙食里只有一些發臭的雜碎飽腹。苦役般的勞動使工人們變得像遲鈍的牲口,他們疾病纏身,生活苦不堪言。老板為了不讓工人把他們的食物施舍給忍饑挨餓的乞丐和失業伙伴而把地窖的窗戶釘死,反映出資產階級商人的冷漠自私和利益至上的剝削本質。此外,文本中不僅表現了資產階級商人與工人階級之間的對立,還揭示出工人與工人之間的矛盾,此時的他們并未團結起來,而是更為注重個體之間的懸殊和差異。面包作坊與花卷作坊只有一墻之隔,卻體現出工人之間鮮明的等級秩序。個體在空間中受到的權力控制與等級秩序息息相關,處于何種等級權力的支配是由個體在社會中的相對位置決定的,位置關系著“個人的權力狀況,也直接關系到個人的社會地位”[12]315。作為資產階級商人的華西里則將其階級特權通過面包工場這一空間顯現出來,老板與伙計的等級關系明確了二者之間的從屬地位,進而演變為潛在的觀念注入日常活動的空間之中,影響著處于這一空間的人物活動。只要華西里一到工場來巡視,各種閑談唱歌的聲音就會相繼消失,每人手里的工作速度也變得更快起來,到處充斥著服從權威的壓抑和苦悶。位于空間中的物品和基礎設施如食物、居住條件等,可以被看作構建空間的物質元素,從而作為一種符號代替空間成為某一特定階級的表征。在食物供應上,工人們日常只有加了菜油的黍米粥和青豆,偶爾有一些菜湯和咸肉,而老板的“屋子里彌漫著伏特加酒、熏魚之類的濃濃的氣息”[4]26。華西里可以舒服愜意地躺在床上享受,辛苦勞動的工人們卻只能在烘房的角落或面粉箱旁席地睡去。空間中基本物品的分配情況反映了人物階級地位的高低,隱含著不平等的階級關系。空間的位置關系反映著人物的階級身份,華西里總是突然出現在工場與面包房之間的石頭拱門里,而面包房的地板比工場高出三級,給人一種居高臨下的壓迫感,用以區分“上層”與“底層”在階級層面的壁壘。而無論是從剝削與被剝削的利益關系還是支配與服從的階級關系上來講,處于“上層”空間的老板總是試圖對“下層”的伙計們進行規訓和勸誡。福柯在探討權力的運作機制時曾提出:“空間是任何權力運作的基礎。”[13]13也就是說,空間作為權力運作的標記,記錄著不同等級和地位的群體之間支配與被支配的過程,掌握權力的領導者常常對處于低一級的弱勢一方進行約束和控制。
在《面包房里》中,相對于角落、地下室這種封閉性較強的空間來說,窗子這一特殊物象的出現將人類的精神世界引向另一個維度。“窗”的封閉性把底層民眾置于與外界隔絕的環境之下,是向外逃離的障礙。冬天的寒冷加劇了工作的痛苦,粘著生面團和泥污的窗玻璃使每個人的內心蒙上了一層看不清的霧,腐臭的氣味和污穢的言語侵蝕著人們的心靈。而其構造的特殊性又決定了它將成為聯結內心世界與外部環境的中介,透過窗戶人們可以看到來自外部世界的美好景象,從而給予人生活的希望和熱情。春天的來臨使陽光透過窗子照射到陰暗潮濕的工場里,“古老的、呈現出彩虹顏色的窗玻璃變得美麗而明朗了”[4]74。工場里重新煥發出生機,歌聲變得和諧起來,蘊含著春天的氣息和新生的希望。窗子將工人們作為人的自由意志被喚醒,成為其反抗奴役、渴望自由的內心外化載體,同時也預示著無產階級力量的崛起和自由意志的成長。
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俄國資本主義迅猛發展的階段,資本家對工人的殘酷剝削無異于野蠻的農奴制時代,社會罪惡深重。底層人在由農村走向城市的空間轉換中折射出底層與上層兩種階級之間無法逾越的鴻溝。西方工業化的迅猛發展如洪水猛獸般沖擊著俄國舊有的經濟基礎,城市中快速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無情地剝削和壓迫著底層民眾。他們每天被超負荷的勞動壓制,卻得不到相應的生活保障;政府的腐敗和專制制度的黑暗使底層民眾找不到出路;二十五盧布就可以讓遍地都是油蟑螂的面包工場照常運轉,而勞動者的處境卻越來越悲慘。在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高爾基逐漸認識到勞動人民只有團結起來,才能實現人類自身的真正解放,重獲人的尊嚴和價值。工人團結起來共同抗爭強權的壓制將彰顯底層民眾作為人的價值和意義。文本結尾處華西里工場的破產、工人的離去、“平民住宅”的崛起,都預示著曾經獨屬于資產階級的權力空間的坍塌與毀滅,無產階級力量在權力空間中逐漸成長起來。
馬克思認為,“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14]10。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俄國正處于復雜的社會階級斗爭中,高爾基作為出身于社會底層的知識分子在思想上受到階級斗爭理論的影響,反映在其創作的文本中,主要體現在《母親》這部小說所構建的政治空間形式中。在列斐伏爾看來,資本主義社會中主要的關系即剝削與統治的關系是通過空間這個工具得以維持的。換句話說,空間已經成為統治階級運用權力、控制工人階級和管理整個社會的工具,所以圍繞空間所進行的斗爭越來越激烈。[15]21資產階級借由權力機構實現自己對廣大勞動工人的統治,包括暗探、警察和憲兵隊等作為專制制度的執行工具出現在工人的對立面。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將宣揚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巴維爾及其同伴抓進監獄、審判、判處苦役,最終將其流放到偏遠寒冷之地。而在聚集大量工人階級的工廠中,同樣隱含著權力斗爭。“沼地戈比”事件引發的工人罷工最終被代表統治階級的工廠主壓制,他以老練的統治者的姿態出現在人群中,再三警告并以罰款威脅處于弱勢的工人,被剝削的貧苦工人只好屈從于強權的支配,放棄爭取個人意志的權利,始終陷入資本主義權力空間中受到資產階級商人的奴役和壓迫。
馬克思主義哲學觀關注人類個體的發展與人的自由意志的健全。在馬克思關于人的發展的理論中,人的自由發展占據核心地位。弗拉索夫一家居住在工人區的盡頭,附近是不高的陡坡和一片沼澤地,居住環境可見一斑。空間所處的位置和家中物品的陳列暗含著社會關系的層級劃分,工人長期居于社會底層,日常活動均在工廠附近的工人區。然而,就是這間小小的屋子成為巴維爾及其同伴思想滋生的發源地,在這里產生了帶領工人走向未來的革命思想。“每次集會都像一個坡度不大的長梯子上的一個階梯,這梯子慢慢把人們引向高處,通向一個遙遠的地方。”[7]31“梯子”被虛化為隱藏在人們思想長河中的抽象空間,與家宅相生相伴,工人們團結一致的親密感情在此融為一體。巴什拉曾在《空間的詩學》中強調“家宅”所蘊含的意義,認為它是承載著人類靈魂深處的內心空間,即使它的外表破爛不堪,但還是表達著無可替代的精神意義。“家宅是一種強大的融合力量,把人的思想、回憶和夢想融合在一起。”[5]5家宅是巴什拉最初為人類尋找的居住空間,一切真正有人居住的空間都應該具備家宅的性質。在充滿母性的溫暖家宅里,巴維爾褪去了粗野鄙俗之氣,母親找到了自己作為主體的存在價值,幸福的氣息彌漫在這個庇護所中。在這個生存空間中,人們遨游于真理所構筑的想象世界,主體的自由意志由此開始萌芽并逐漸走向成熟。
在《母親》中,丈夫死后,兒子巴維爾成為母親的全部精神寄托。起初,尼洛夫娜用母愛感動和勸慰兒子改掉從父輩承襲而來的不良習氣,此時的母親是男性的守護者。漸漸地,在巴維爾的影響下,尼洛夫娜從一個膽小怯懦、逆來順受的底層女性成長為一個勇于為社會主義事業獻身的進步女性。兒子讓作為女性的母親第一次認識到了自己的價值,使得一直以來處于邊緣地位的女性受到關注。母親在巴維爾入獄期間,利用去工廠送飯的機會偷偷地將印有知識和真理的小冊子帶入工廠,宣傳革命真理,進而參與到解放人民群眾的活動中去。而這也使她的精神世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華和洗禮。在這里,女性的從屬地位得到改變,她在男性的影響下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義。盡管此時母親的諸多舉動是源于對兒子的愛,并非出于自覺,但在解放思想和尋求自我的層面上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和非凡的意義。“五一”游行示威的活動和巴維爾在法庭審判時的演講使母親的思想境界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她開始主動自覺地加入革命斗爭中,成長為一名勇敢堅定、不畏犧牲的革命女性。
斗爭的關鍵在于擺脫資本家所構筑的私有空間,發展為由工人階級人民群眾建立的公共空間。父親弗拉索夫和兒子巴維爾都是處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人物。弗拉索夫是資產階級壓迫下的勞動者,而巴維爾則是志在反抗勞動工人受奴役地位、宣揚自由意志和思想的革命者,他是“工人階級新的一代,是勞動人民與專制制度、資本主義剝削斗爭的組織者、領導者之一”[16]61。“沼地的戈比”“五一節游行”和“法庭斗爭”是體現巴維爾革命斗爭思想的主要事件,也是階級矛盾最為激烈的時刻。他在演講中控訴了私有制的虛偽和貪婪,這種制度把人當作發家致富的工具,是奴役人的肉體和精神的罪惡之源。因此,巴維爾身負階級解放的重任,在他身上彰顯著工人階級領導人民群眾爭取自由的光輝。而諸多革命思想都是在工人區盡頭的那間小屋子里滋長出來的,這使得狹窄破舊的生活空間升華為產生和匯集進步思想的政治空間。最終在巴維爾這樣的先進思想者的引領下,越來越多的工人走上了無產階級爭取自由平等的革命道路。此外,以雷賓為代表的農民階級勇于加入革命斗爭的行動也體現著俄國底層民眾的覺醒,展示了馬克思主義與無產階級工農運動相結合的過程,印證了資產階級走向沒落、無產階級終將勝利的歷史必然。
四、結語
空間是承載人類活動的容器和場所,它從普遍意義上的物理空間不斷向外延伸,與社會中的性別關系、階級關系聯系起來,形成與社會相互作用的產物。高爾基以資產階級商人控制下的手工作坊或工廠為中心,通過構建具有不同特點的生活空間展示了俄羅斯人民的生存境遇,蘊藏了作家濃厚的人道主義情懷和對底層勞動人民自我價值的肯定。除此之外,在性別空間的關系場域中不僅折射出世紀之交社會背景下底層女性的受奴役和被異化的處境,而且對于女性革命力量的覺醒給予了真切的謳歌和頌揚,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對于男女兩性不平等關系問題的關注。而基于意識形態之上反映階級差異和矛盾的政治性空間表現出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無情批判,強調了人的精神內涵與價值,同時作家意識到人民群眾身上的精神力量,以及資產階級必然滅亡、無產階級必然勝利的歷史必然,體現了作家豐富而又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