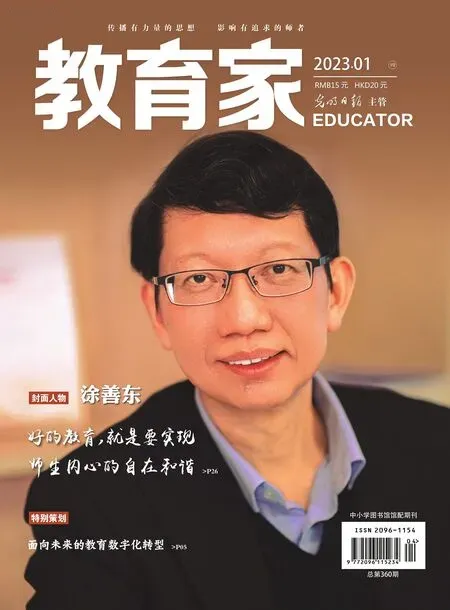陳桂芳:把知識化為學生的“底氣”
文 | 鄧曉婷
回想在小學數學課上把老師“懟”得啞口無言的場景,陳桂芳一臉羞澀。也正是由于這種愛追問的個性,讓她自小就留意到自己在理科方面的天賦——善邏輯、擅思考,這些素質,同樣也與做一名化學老師應秉持的求證精神環環相扣。在建平縣昌隆鎮九年一貫制學校任教26年,陳桂芳將興趣變成了事業,那些閃耀在化學課上的求知欲和愉悅感,不僅抵消著日復一日的職業倦怠,亦是她教學生涯里最為珍視的成果。
“陳教授來了”
高中時期,陳桂芳在同學甚或是老師們中間,也是小有名氣的。那時生物老師一共帶兩個平行班,另一個班里有入學考試年級第一的同學。“一次,生物老師提出一道題,他們班沒有一個學生能答出來。去我們班講課時,老師說,這道題誰會做,我就管誰叫老師。”年少氣盛的陳桂芳站起來,像打擂臺般自信篤定地說出了正確答案。
“陳老師請坐!”當著全班的面,生物老師略顯尷尬地兌現了自己的“承諾”。同學們也開始起哄,每每看到陳桂芳進門,就鼓掌說“陳教授來了”。“我們生物老師是本科畢業,而我一不小心變成了本科生的‘老師’,所以大家開玩笑叫我教授。”這讓正值青春期的陳桂芳很苦惱,她害怕成為焦點,于是生物考試時她故意留幾道選擇題或填空題不寫,但成績一出,她還是班級第一。一周以后,“陳教授”的熱度終于降下來,但這次事件也帶來了好的影響,自那以后,同學們每次遇到不懂的知識點都會請教陳桂芳。
在理科方面,陳桂芳的高光時刻確實不少,但灰心的階段她也經歷過。高一剛入學時,她的化學成績一落千丈,59分給她帶來不小打擊。“初中我的化學一直都是90多分,所以當時我特別傷心。”好在化學老師留意到陳桂芳的情緒,經常主動和她交流課堂習題中出現的問題。
陳桂芳記得,那時老師勸慰她:“女孩子一定要自立。考上大學和沒考上大學是有很大區別的。”話雖粗糙了些,但陳桂芳卻因此振作起來,慢慢從及格線到后來基本不丟分,高考時物理、化學和生物都接近滿分。

陳桂芳 遼寧省朝陽市建平縣昌隆鎮九年一貫制學校教師
陳桂芳說,她喜歡做實驗,喜歡那些奇妙的化學反應在手中慢慢升騰出的成就感。師專畢業后,陳桂芳自然而然地將這份愉悅延伸到了職業生涯中,也將這份誠摯的熱情存續在了更多年輕人的生命里。
化學是一種“底氣”
“老師,我覺得自己的化學底子和葉柏壽街里的學生基本沒差多少,甚至有些他們不會的,我還會一點。雖然我是您眾多學生中平平無奇的一個,但我會永遠記得您。”“芳姐在不在,我想問問應該怎么提高化學成績?”“老師,你知道嗎?我老問你問題,但我化學還考成這樣,我覺得你會很失望。”
在陳桂芳的微信里,這些真實、鮮活的聊天記錄大多來自她的畢業生。他們從初中升入高中,一直念念不忘陳桂芳的教育和師心,遇到不會做的化學題他們首先想到的是她,考試成績不理想時會忍不住找她傾訴,因能比其他同學多懂得一些知識點而沾沾自喜時,又不自禁地向她“炫耀”……也許因為自己曾在初高中銜接時遇到了不小的挫折,陳桂芳常常在課堂上適當地給學生拓展一些高中化學知識,以致能讓學生多些底氣,少走彎路。
但有時,又需要根據學生的學習階段和理解能力巧妙地保留一部分。在一次省里的公開課上,陳桂芳正好講到了高錳酸鉀制取氧氣的知識點。“這個知識點的其中一個環節是要每個學生準備一根帶火星的木條,如果將木條伸入集氣瓶口能復燃,則說明該瓶內的氣體是氧氣。其中有一組同學的木條沒有復燃,我一眼就看出來,是準備的木條太粗了。”課堂即將進入尾聲,陳桂芳說,考慮到學生的理解能力,在有限的時間下,最好的方法不是直接告訴學生木條太粗,因為它涉及后期要學到的“燃燒點”的知識,繼續深入下去會給學生帶來困擾,也不益于他們把握該堂課的重點知識。于是陳桂芳側面提醒同學們,木條不能復燃很可能是由于集氣瓶內的氧氣不純,以此來強化學生對課堂重點內容的理解。公開課結束后,陳桂芳還得到了省教研員的表揚。
看到學生們對化學產生濃厚興趣,陳桂芳自然是欣慰的。但在農村地區,受各種因素影響,總有一些孩子不愿學習甚至早早輟學。陳桂芳常常提醒他們:“課堂上能學就多學點,生活中處處有化學,化學知識對你們一生都是有用的。”陳桂芳說,很多孩子離開學校后還是會回歸家庭從事農業生產,做農活、下田種菜,蔬菜生病了要打農藥,農藥的溶液要怎么配制?種植要施肥,化肥怎么合理施用?每每在課堂上講到這些知識點,即使再不樂意學習的孩子,都會積極配合。
教學之外,要關注學生的存在感
“我雖然教化學,但也當了好些年的班主任,對孩子們的感情非常深厚。”這份感情讓陳桂芳放棄了去城里教書的機會,她覺得只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教好學生,在哪兒都無愧于心。多年來,她也漸漸體會到了一名鄉村老師的責任遠比教學本身更為重大。
初中是情竇初開的時期,陳桂芳的兩名化學課代表經常到她辦公室一起領任務,久而久之互相產生了好感。班主任“下令”讓他們“分開”,但陳桂芳不這么想,青春期的孩子在情感認知上原本就更易叛逆,與其強行灌輸分開的思想,不如把這種單純而美好的情愫轉化成學習的動力。
陳桂芳找來兩名學生,對他們說:“你倆化學成績最近可不對勁,成績都下滑了,作為我的課代表,我感到很沒面子。”看兩個孩子能聽進去她說的話,陳桂芳繼續說:“既然你們彼此都有好感,就應該互相促進,越來越優秀才對。上網課的時間,你倆是不是沒有好好監督?”
接著陳桂芳又給他們打了一劑強心針:“現在想學習以外的事太早,你倆應該在學習上較個勁,讓其他同學看看,自己的成績不會受任何事情影響。”陳桂芳幾番話語,讓兩個孩子感觸良多。中考結束后,女孩取得了全校第二名的好成績,她發微信告訴陳桂芳:“我又‘殺’回來了!我都激動得哭了。”
“我當班主任期間,學生小劉在初一初二時很優秀,初三之后成績下滑非常嚴重,我觀察很久發現他結交了四五個朋友,這些孩子不僅調皮搗蛋,還有抽煙的習慣,他們之間誰犯事了還會互相包庇。”陳桂芳見勢頭不妙,每天抽時間給小劉做思想工作,除了化學學科外,她還經常翻看小劉各科的家庭作業本,關注其完成情況,有時候還會抽幾道歷史或是政治題讓他答一答。
“一著不慎,學生就會跌入不學習的旋渦里,我們做老師的,哪怕多抽一些時間出來跟他們嘮嘮嗑也是好的,他們需要被關注,我們要用身心去感受和正視他們的存在。多督促,他們就能多學點。”陳桂芳說,日后待他們成人,會懂得自己不厭其煩的用心。后來小劉考上了山東一所不錯的大學,放假期間還經常和陳桂芳提及:“老師那時多虧你了,要不是你,現在我都到不了這個狀態。”
相比學科成績本身,令陳桂芳更為牽掛的是班級里生活比較困難的孩子,當班主任期間有名叫小兵的孩子很愛學習,但由于家里只有老父親和他相依為命,小兵的個人衛生情況相當糟糕,陳桂芳經常去他家幫忙洗衣服,后期老父親生病無法自理沒有收入來源,陳桂芳每個星期都會給小兵一點零花錢,“錢不多,但吃飯沒問題”。后來她和學校協商,讓他免費在食堂吃飯。雖然只資助了小兵一個學年,但陳桂芳心里是踏實的。
回看自己把興趣變成事業的心路歷程,陳桂芳心里也曾犯難。真正到工作崗位后,甚至有一段時間她覺得選擇化學不是一件理智的事,“因為每節課幾乎都要準備實驗,化學器具損耗性很大,而且課堂上實驗還不一定能做成功,需要課下反復驗證。我教書26年了,在課堂上偶爾還會出現失誤。”陳桂芳比喻,教化學就像吃飯,得把酒和菜都擺齊了人才能上桌。
但最初的手忙腳亂也好,日復一日地操持也好,和看到孩子們因實驗成功而收獲的喜悅,以及和自己教授的知識變成他們成長的底氣相比,這些困難和倦怠便顯得微不足道。“我們這個年齡的人,基本是不會混日子的。我相信無論什么工作,簡單的、困難的,只要努力細致地做下去,別害怕重復,慢慢就成專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