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zhàn)時(shí)期美國《太平洋事務(wù)》視域中的中國共產(chǎn)黨形象
陳奕濤
(華東師范大學(xué) 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上海 200241)
政黨形象是政黨屬性、政黨符號、黨員隊(duì)伍及政治參與能力給黨內(nèi)外公眾留下的相對穩(wěn)定的綜合感知和整體印象(1)孫景峰、陳倩琳:《政黨形象:概念、意義與建設(shè)路徑》,《探索》2013年第3期。。作為百年大黨,中國共產(chǎn)黨形象不僅是一個(gè)現(xiàn)實(shí)議題,也是一個(gè)重要的歷史問題。抗戰(zhàn)時(shí)期是中國共產(chǎn)黨迅速發(fā)展的關(guān)鍵時(shí)期,該時(shí)期的中國共產(chǎn)黨形象是其革命與抗戰(zhàn)的綜合呈現(xiàn),在中國共產(chǎn)黨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關(guān)于該時(shí)間段中國共產(chǎn)黨形象的歷史資料頗為豐富,既有中國共產(chǎn)黨自己的留存,亦有社會各界的記錄,這些資料皆有不可否認(rèn)的價(jià)值。習(xí)近平總書記指出,“關(guān)于抗戰(zhàn)關(guān)鍵問題的研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資料、圖書報(bào)刊、日記信件、實(shí)物等”(2)習(xí)近平:《讓歷史說話 用史實(shí)發(fā)言 深入開展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研究》,《人民日報(bào)》2015年8月1日。。因此,在利用自我留存史料的基礎(chǔ)上,立足全球史視野,借助“他者鏡像”對這一議題進(jìn)行反觀和思考成為一個(gè)重要課題(3)李金錚:《尋覓“他者”鏡像下的中共革命史》,《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11期。。在此方面,學(xué)界近年來也涌現(xiàn)出諸多成果(4)有代表性的如,李金錚: 《知行合一: 外國記者的革命敘事與中共形象》,《河北學(xué)刊》2016 年第2期;朱瀟瀟、徐宇:《美國主流媒體視域下的中國共產(chǎn)黨形象研究(1930—1937)——以〈華盛頓郵報(bào)〉〈紐約時(shí)報(bào)〉為對象》,《蘇區(qū)研究》2020年第2期;張雪梅:《國外關(guān)于中國共產(chǎn)黨形象認(rèn)知的演變過程與特點(diǎn)》,《人民論壇》2021年第14期。,這些成果充分利用了海外報(bào)刊、檔案和紀(jì)實(shí)作品,對中國共產(chǎn)黨形象研究的推進(jìn)以及中國共產(chǎn)黨抗戰(zhàn)中流砥柱作用的印證具有重要價(jià)值。然而,這類研究所呈現(xiàn)的中國共產(chǎn)黨形象要么是單向度的積極形象,要么是正面與負(fù)面的二元對立形象,亦或是二分式的形象轉(zhuǎn)變過程,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中國共產(chǎn)黨國際形象轉(zhuǎn)變的漸進(jìn)性與過程性,且對于形象的階段性變化背后的動(dòng)因也缺乏深入探究。對海外學(xué)術(shù)雜志中關(guān)于中國共產(chǎn)黨形象的觀察和研究,既有助于形成海外中國共產(chǎn)黨形象的變遷和理解,也是一個(gè)重要的學(xué)術(shù)研究方法。筆者以太平洋國際學(xué)會所主辦的國際知名刊物《太平洋事務(wù)》(5)太平洋國際學(xué)會是由美國國際主義者所組織的國際性民間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對20世紀(jì)20—40年代的亞太國際關(guān)系和美國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響。1928年,太平洋國際學(xué)會創(chuàng)辦《太平洋事務(wù)》。在三四十年代,該期刊是最為重要的關(guān)于遠(yuǎn)東地區(qū)經(jīng)濟(jì)、社會和政治問題的英文信息來源之一,對戰(zhàn)時(shí)和戰(zhàn)后美國有著重要影響。作為研究對象,探討抗戰(zhàn)時(shí)期該期刊中中共形象表征及漸進(jìn)性變化,力求通過分析文本背后的歷史語境呈現(xiàn)形象變化的動(dòng)力因素,以期從“他者”視角充實(shí)中共黨史與抗戰(zhàn)史研究。
一、從負(fù)面形象到中性形象:局部抗戰(zhàn)時(shí)期的中國共產(chǎn)黨
建黨初期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于國際社會而言一直都是模糊、缺失或被誤讀的狀態(tài)。哥倫比亞大學(xué)教授納撒尼爾·裴斐指出,“我們實(shí)際上對中國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dòng)的內(nèi)容一無所知,關(guān)于它的一切報(bào)道都是宣傳、詭辯、猜測或者道聽途說”(6)Nathaniel Peffer, “ Reviewed Work(s): The Chinese Soviets. by Victor A. Yakhontoff: China’s Red Army Marches. by Agnes Smedley: Fundamental Laws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Pacific Affairs, Vol. 8, No. 2, 1935, pp.223-226.。這一時(shí)期,《太平洋事務(wù)》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報(bào)道亦有著模糊不清、籠統(tǒng)概括的特征,但深入分析發(fā)現(xiàn),在局部抗戰(zhàn)時(shí)期,該期刊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報(bào)道由起初無事實(shí)依據(jù)的概括和惡意揣測,逐漸轉(zhuǎn)變?yōu)閷W(xué)理性探討與判斷。同時(shí),其視域下的中國共產(chǎn)黨形象呈現(xiàn)由負(fù)面到中性的變化。
(一)“紅色威脅”:局部抗戰(zhàn)初期的負(fù)面形象(1931—1934)
20世紀(jì)30年代初期,由于國民黨的封鎖和歪曲宣傳,中國共產(chǎn)黨在美國社會公眾中的知曉度并不高,且多以負(fù)面形象出現(xiàn)。美國歷史學(xué)家肯尼思·休梅克曾指出,“國外關(guān)于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報(bào)道大都來自第二手材料,而且充滿了敵意”(7)[美]肯尼斯·休梅克:《美國人與中國共產(chǎn)黨人》,鄭志寧等譯,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9頁。。與之相對應(yīng),1931—1934年《太平洋事務(wù)》中的中國共產(chǎn)黨呈現(xiàn)一種“紅色威脅”形象。該期刊不僅從悲觀主義視角出發(fā),把中國共產(chǎn)黨描述為“既有政權(quán)的威脅者”,還站在帝國主義的立場之上,視其為美國在華利益的威脅者。
1.悲觀主義視角:否定中國共產(chǎn)黨的進(jìn)步性。《太平洋事務(wù)》中的刊文在缺乏一手資料的情況下,以悲觀主義視角看待中國共產(chǎn)黨,并將其污名化為國民政府和民眾安全的“威脅者”。1931年,該期刊編輯伊麗莎白·格林指出,共產(chǎn)黨的活動(dòng)擾亂了中國國內(nèi)的局勢(8)“Pacific Items”, Pacific Affairs, Vol. 4, No. 6 , 1931, pp.523-526.。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后,她表示,“共產(chǎn)黨的活動(dòng)日益頻繁,其打算利用危機(jī)時(shí)期對政府和促進(jìn)中國政治統(tǒng)一的力量進(jìn)行打擊”(9)Elizabeth Green, “Progress of the Manchurian Disease: As Viewed from Peiping and Tokyo”, Pacific Affairs , Vol. 5, No. 1 , 1932, pp. 42-65.。在她的描述下,中國共產(chǎn)黨似乎成了苦難大地上的“暴動(dòng)者”。而夏威夷大學(xué)教授李紹昌則將中國共產(chǎn)黨污蔑為“強(qiáng)盜”,并認(rèn)為鎮(zhèn)壓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dòng)是國民政府所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10)Su-Lee Chang, “China at the Threshold of 1932”, Pacific Affairs, Vol. 5, No. 3 ,1932, pp.233-239.。在美國歷史學(xué)家貝德士看來,與蔣介石所引領(lǐng)的國家發(fā)展方向相比,共產(chǎn)主義最終所導(dǎo)向的是一種無政府狀態(tài)(11)M. S. Bates,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Politics: 1931-1932”, Pacific Affairs, Vol. 5, No. 3,1932, pp.218-232.。甚至還有學(xué)者認(rèn)為,農(nóng)民們深受共產(chǎn)主義“蹂躪”(12)C. K. Y, “The Second Chinese National Financial Conference”, Pacific Affairs, Vol. 7, No. 3,1934, pp.335-337.。這類認(rèn)知反映了這些作者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惡意猜測與偏見,他們?nèi)粺o視近代以來使中國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的帝國主義罪惡,無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歷史和人民對中國共產(chǎn)黨作為先進(jìn)的政治領(lǐng)導(dǎo)者的選擇,更沒有看到中國共產(chǎn)黨追求人民解放和民族獨(dú)立的使命和革命實(shí)踐,他們在缺乏事實(shí)基礎(chǔ)的情況下,站在既有當(dāng)局一方,視中國共產(chǎn)黨為國家穩(wěn)定與統(tǒng)一的“阻礙者”與“威脅者”。
悲觀主義態(tài)度及其所構(gòu)造出的負(fù)面形象主要受兩種因素影響。一方面,國民黨的信息封鎖和中國共產(chǎn)黨活動(dòng)的秘密性導(dǎo)致了這些作者獲取中國共產(chǎn)黨信息的渠道十分有限,而國民黨的歪曲宣傳則加劇了他們所接收信息的扭曲性與非真實(shí)性。肯尼思·休梅克就曾指出,該期刊此時(shí)的報(bào)道主要是“根據(jù)中國官方通訊機(jī)構(gòu)發(fā)布的消息做出的,他們對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描述恰恰反映了其消息來源的不足”(13)[美]肯尼斯·休梅克:《美國人與中國共產(chǎn)黨人》,鄭志寧等譯,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9頁。。另一方面,意識形態(tài)影響文本生產(chǎn)方式。美國學(xué)者追求個(gè)體主義自由和私有財(cái)產(chǎn)神圣的資產(chǎn)階級國家形態(tài),他們將追隨這一體制的中國當(dāng)局視為同類,而將中國共產(chǎn)黨視為其對立面。在他們看來,中國共產(chǎn)黨不僅和反對上帝、反對財(cái)產(chǎn)私有、反對有組織的政府相聯(lián)系,而且還與蘇聯(lián)有著密切聯(lián)系。在這一認(rèn)知之下,他們對新生的、無法接觸的中國共產(chǎn)黨有著先驗(yàn)的仇視,他們不理解中國共產(chǎn)黨為何會產(chǎn)生,更無從知曉中國共產(chǎn)黨的初心與使命。
2.帝國主義視角:敵視作為民族解放引領(lǐng)者的中國共產(chǎn)黨。《太平洋事務(wù)》的作者們在自我國家利益的主導(dǎo)之下,將中國共產(chǎn)黨視為激進(jìn)的民族主義者,認(rèn)為其破壞與威脅著美國的在華利益。美國記者E.H.安斯蒂斯將中國學(xué)生的愛國主義行為視為是受到共產(chǎn)主義影響的激進(jìn)行為,認(rèn)為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宣傳之下,中國的學(xué)生們認(rèn)識到他們的敵人是外國人”(14)E.H.Anstice,“China’s Student Politicians”,Pacific Affairs,Vol.5,No.8,1932,pp.689-694.。此外,他還將工人接受馬克思主義洗禮進(jìn)而成為愛國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中堅(jiān)力量的現(xiàn)象,污蔑為一種“消極”,即“大多數(shù)工人沒有受過教育,很容易被共產(chǎn)主義者引入歧途,成為反對外國人的一種武器”(15)E.H.Anstice,“Youthful Radicalism in the Far East”,Pacific Affairs,Vol.6,No.7,1933,pp.387-393.。這類話語表達(dá)的背后,是該刊部分作者忽視其國家給中國民眾帶來的深重災(zāi)難,完全站在帝國主義國家立場之上敵視中國共產(chǎn)黨,對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中國民眾覺醒、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爭取民族獨(dú)立和解放的愛國主義正義事業(yè)充滿偏見和反動(dòng)。
(二)“紅色力量”:局部抗戰(zhàn)后期的中性形象(1935—1937)
歷史的發(fā)展表明,正是這樣一群不被國際社會看好的政治力量,在蔣介石的反革命圍剿中,從城市走向農(nóng)村后逐步壯大。對“反圍剿”和長征勝利的疑惑,使外界觀察家們開始逐漸打破他們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刻板印象。同時(shí),《太平洋事務(wù)》自1934年后逐漸轉(zhuǎn)變了辦刊風(fēng)格,主張引入有爭議的現(xiàn)實(shí)政治問題,展開自由的學(xué)術(shù)討論,并開始越來越多地關(guān)注中國共產(chǎn)黨。
1. 肯定中國共產(chǎn)黨的生命力與影響力。《太平洋事務(wù)》此時(shí)注意到中國共產(chǎn)黨所具有的內(nèi)在生命力與外在影響力。美國漢學(xué)家戴德華著眼于民族抵抗角度,認(rèn)為中國共產(chǎn)黨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積極有力的力量(16)George E. Taylor,“ The Powers and the Unity of China”,Pacific Affairs,Vol.9,No.4,1936,pp.532-543.。1935年,盡管此時(shí)中國的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dòng)處于低潮時(shí)期、黨員人數(shù)急劇下降,但拉鐵摩爾認(rèn)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力量大小并不來源于人數(shù),而在于領(lǐng)導(dǎo)者的素質(zhì)以及他們在其領(lǐng)導(dǎo)土地上贏得支持的能力,中國共產(chǎn)黨重新崛起并實(shí)現(xiàn)力量的增強(qiáng)是完全可能的。他還指出,中國共產(chǎn)黨正在由西部向內(nèi)地轉(zhuǎn)移,在不久的將來很有可能主導(dǎo)政治關(guān)系(17)Owen Lattimore ,“ The Inland Gates of China”,Pacific Affairs ,Vol.8,No.4,1935, pp.468-473.。與其相似,芝加哥大學(xué)駱傳華也認(rèn)為,中國共產(chǎn)黨在當(dāng)今中國具有強(qiáng)大影響力,它所具有的力量優(yōu)勢超越了其數(shù)量(18)C. Pone,“Reviewed Work(s): Facing Labor Issues in China. by Lowe Chuan-hua”,Pacific Affairs,Vol.9,No.4,1936,pp.597-599.。
在此基礎(chǔ)上,該刊探討了中國共產(chǎn)黨在中國的出現(xiàn)與發(fā)展的生命力問題。戴德華認(rèn)為,共產(chǎn)黨必定無法被消除,原因在于當(dāng)局無法解決中國真正的問題——使數(shù)千人維持生活的農(nóng)業(yè)問題(19)G. E. Taylor, “ Reconstruction After Revolution: Kiangsi Province and the Chinese Nation”, Pacific Affairs, Vol.8, No.3,1935,pp.302-311.。拉鐵摩爾則直截了當(dāng)指出,中國的土地問題是亟待解決的問題,中國共產(chǎn)黨的訴求與主張便是土地的重新分配,很明顯,共產(chǎn)黨力量的增強(qiáng)是完全可能的(20)Owen Lattimore , “ The Inland Gates of China”,Pacific Affairs, Vol.8, No.4, 1935,pp.468-473.。因此,中國共產(chǎn)黨的社會經(jīng)濟(jì)思想對大眾來說具有強(qiáng)烈吸引力的觀點(diǎn),便成為駱傳華等人的詮釋核心,他認(rèn)為,“(中國共產(chǎn)黨)能否成為全中國的主人,取決于領(lǐng)導(dǎo)層能在多大程度上滿足普通民眾的需要,以及能否在公正和平等的基礎(chǔ)上重建現(xiàn)有社會秩序”(21)C. Pone,“Reviewed Work(s): Facing Labor Issues in China. by Lowe Chuan-hua”,Pacific Affairs, Vol.9, No.4 , 1936, pp.597-599.。可見,該刊開始認(rèn)識到,中國共產(chǎn)黨與中國特殊的政治經(jīng)濟(jì)土壤相適應(yīng),并致力于解決廣大貧苦民眾的生存問題,這類觀點(diǎn)可以說駁斥了當(dāng)時(shí)西方世界流行的“共產(chǎn)主義不適于農(nóng)業(yè)中國”的假設(shè)。
2.關(guān)于中國共產(chǎn)黨階級屬性之爭。《太平洋事務(wù)》在關(guān)注中國共產(chǎn)黨所具有的力量的同時(shí),非常關(guān)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階級屬性,并出現(xiàn)了兩類截然不同的認(rèn)識。美國學(xué)者哈羅德·伊羅生認(rèn)為,中國共產(chǎn)黨名義上是無產(chǎn)階級政黨,實(shí)際上是農(nóng)民階級政黨(22)Harold R. Isaacs,“Perspective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Marxist View”, Pacific Affairs, Vol.8, No.3 , 1935, pp.269-283.。對此,中共地下黨員冀朝鼎做出了針鋒相對的反駁,他指出,哈羅德·伊羅生不了解中國社會的性質(zhì)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他沒有看到無產(chǎn)階級的統(tǒng)治地位已經(jīng)得到保障,且實(shí)現(xiàn)并保持著對紅軍的領(lǐng)導(dǎo)。中國共產(chǎn)黨始終是無產(chǎn)階級政黨(23)Kathleen Barnes, “Another Perspective”, Pacific Affairs , Vol.8, No.4 ,1935, pp.477-481.。戴德華也進(jìn)一步闡明,中國的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dòng)不是農(nóng)民起義,也不是土匪活動(dòng),中國共產(chǎn)黨代表著沒有政治權(quán)利的階級——工人和農(nóng)民,該黨的骨干仍然是工人和學(xué)生,盡管農(nóng)民發(fā)揮著很大的作用,但卻是從屬作用(24)George E. Taylor, “The Powers and the Unity of China” , Pacific Affairs , Vol.9, No.4 , 1936, pp.532-543.。
從相關(guān)表述可以看到,該期刊此時(shí)傾向于對中國共產(chǎn)黨進(jìn)行學(xué)理性探討與判斷。在此過程中,作者們逐漸認(rèn)識到,中國共產(chǎn)黨并不是假借共產(chǎn)主義口號、劫掠和迷惑群眾的匪徒,而是力求為工農(nóng)群眾謀利益的政黨,他們所描繪的中國共產(chǎn)黨也呈現(xiàn)一種中性的“紅色力量”形象。但由于一手資料的欠缺,這一形象依舊較為模糊,且部分作者對中國共產(chǎn)黨也存在誤解。但無論如何,該刊關(guān)于中國共產(chǎn)黨的探討對促進(jìn)美國民眾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了解具有重要意義。
二、“璀璨的紅星”:全面抗戰(zhàn)時(shí)期的中國共產(chǎn)黨
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沖破國民黨的封鎖來到了延安,為探求中國共產(chǎn)黨的真實(shí)形象掀開了一角厚幕。1937年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美國的媒體界更加關(guān)注中國共產(chǎn)黨。為此,他們沖破重重阻礙來到了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下的抗日根據(jù)地。基于實(shí)地的了解,他們發(fā)現(xiàn),國民黨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宣傳空洞而缺乏說服力,“每個(gè)去過延安的人都可以證實(shí),延安從遠(yuǎn)處照耀四方”(25)John K.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Row, 1982,p.266.。梳理《太平洋事務(wù)》發(fā)現(xiàn),這一時(shí)期作者筆下所呈現(xiàn)的中國共產(chǎn)黨積極、清晰,“璀璨的紅星”是這一時(shí)期中國共產(chǎn)黨形象的概括,并體現(xiàn)在領(lǐng)導(dǎo)人、軍隊(duì)和邊區(qū)政府三個(gè)維度。
(一)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人:富有智慧的人民領(lǐng)導(dǎo)者
領(lǐng)導(dǎo)人是黨員隊(duì)伍的核心,是政黨的形象代言人。抗戰(zhàn)時(shí)期,《太平洋事務(wù)》的作者們認(rèn)識到,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人是樸實(shí)親民、富有智慧的人民領(lǐng)導(dǎo)者。拉鐵摩爾在與毛澤東等人交談后寫道:“毛澤東是一位屬于人民的人,一個(gè)智力超群但顯然具有農(nóng)民傳統(tǒng)的人”,他還轉(zhuǎn)述了這樣一個(gè)觀點(diǎn):“在延安,我第一次看到能夠領(lǐng)導(dǎo)中國的人”(26)[日]磯野富士子整理:《蔣介石的美國顧問——?dú)W文·拉鐵摩爾回憶錄》,吳心伯譯,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96年,第53、56頁。。對于周恩來,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認(rèn)為其是一個(gè)沉著、冷靜、有說服力的人(27)Chen Han-sen, “ Reviewed Work(s): First Act in China: The Story of the Sian Mutiny. by James M. Bertram”,Pacific Affairs, Vol.11,No.1,1938, pp.114-117.。由于朱德的突出戰(zhàn)績,斯諾將其稱為“中國的拿破侖”。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人的群體印象也開始初步產(chǎn)生,在愛德華·卡特看來,紅色中國的領(lǐng)導(dǎo)人代表著簡樸、勇敢和戰(zhàn)略獨(dú)創(chuàng)性,他們使民眾相信,終于有了不會把其出賣給地主和高利貸者的政治領(lǐng)導(dǎo)者(28)Edward C. Carter, “Red Star Over China. by Edgar Snow”, Pacific Affairs, Vol.11, No.1, 1938, pp.110-113.;在美聯(lián)社特約記者霍爾多·漢森看來,他們的特征是“對最終目標(biāo)的堅(jiān)定不移、方法的靈活性、對工作的自我批評態(tài)度以及完全沒有個(gè)人私心”(29)Haldore Hanson, “ The People Behind the Chinese Guerillas”,Pacific Affairs,Vol.11,No.3 , 938, pp.285-298.。還有觀察者認(rèn)為,邊區(qū)政府能夠取得成功,不僅是因?yàn)檐姽儆兄欠驳恼晤^腦,而且是因?yàn)槲墓儆熊娙祟^腦,年輕、進(jìn)步(30)A British observer,“ The Future Foreshadowed: China’s New Democracy”,Pacific Affairs, Vol.11,No.4,1938, pp.454-464.。對于敵后抗日運(yùn)動(dòng)阻滯日軍征服占領(lǐng)華北地區(qū)的原因,沃德·珀金斯將之歸結(jié)于經(jīng)驗(yàn)豐富、能力超群的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者(31)Ward Perkins,“ The Failure of Civil Control in Occupied China”,Pacific Affairs,Vol.12,No.2, 1939,pp.149-156.。對于中國共產(chǎn)黨這一反法西斯同盟軍,美國外交官謝偉思極力贊賞道:中共領(lǐng)導(dǎo)人忘我地獻(xiàn)身于崇高的原則,他們有著杰出的才干和堅(jiān)毅的領(lǐng)導(dǎo)素質(zhì)(32)[美]約瑟夫·W·埃謝里克編:《在中國失掉的機(jī)會》,羅清、趙仲強(qiáng)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1989 年,第 202頁。。
(二)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軍隊(duì):捍衛(wèi)人民利益的新型軍隊(duì)
《太平洋事務(wù)》的作者們經(jīng)常把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下的軍隊(duì)與以往的軍隊(duì)進(jìn)行對比,認(rèn)為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軍隊(duì)是把人民利益置于最高位置的新型人民軍隊(duì)。無論是美國東亞研究專家勞倫斯·羅辛格,還是美國記者斯特朗和美國社會學(xué)家蘭格都認(rèn)為,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軍隊(duì)“所有人都被訓(xùn)練去高度尊重人民的權(quán)利”(33)Lawrence K Rosinger, “Politics and Strategy of China’s Mobile War”, Pacific Affairs, Vol.12, No. 3, 1939, pp.263-277.,其始終堅(jiān)持“人民高于軍隊(duì)”的原則(34)Anna Louise Strong, “Eighth Route Regions in North China” , Pacific Affairs,Vol.14,No.2 , 1941, pp.154-165.,甚至原來把軍隊(duì)視為“蝗災(zāi)”的農(nóng)民,現(xiàn)在也相信八路軍是把他們的福祉放在心上的軍隊(duì),“八路軍現(xiàn)在與人民形成了新型關(guān)系,士兵已經(jīng)贏得了尊重和榮譽(yù)”。總之,在《太平洋事務(wù)》看來,與以往軍閥以及國民黨軍隊(duì)的貪污腐敗、掠奪百姓相反,中共領(lǐng)導(dǎo)下的軍隊(duì)是一支新型人民軍隊(duì),堅(jiān)決捍衛(wèi)著人民群眾的利益,“他的出現(xiàn)與存在表明,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之路已經(jīng)找到”(35)Olga Lang, “The Good Iron of the New Chinese Army” , Pacific Affairs , Vol.12, No.1,1939,pp.20-33.。
《太平洋事務(wù)》還贊賞了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軍隊(duì)的作戰(zhàn)能力和奉獻(xiàn)精神。拉鐵摩爾認(rèn)為,當(dāng)前戰(zhàn)線上唯一沒有退讓的是八路軍陣地,盡管日本多次對其發(fā)起猛烈進(jìn)攻,但都沒有取得勝利(36)O.L,“Reviewed Work(s): Inside Red China. by Nym Wales”,Pacific Affairs,Vol.12, No.3,1939,pp.344-346.。德國醫(yī)生亞提斯則認(rèn)為,八路軍的高戰(zhàn)斗能力、勇敢精神、巨大的機(jī)動(dòng)性以及領(lǐng)導(dǎo)人的戰(zhàn)略技能,被他們的敵人所證實(shí)(37)Asiaticus, “ China’s Advance From Defeat to Strength”, Pacific Affairs , Vol.11, No.1, 1938, pp.21-34.。蘭格發(fā)現(xiàn),許多人在抗擊侵華日軍的過程中受傷,但沒有人因?yàn)閼?zhàn)爭或受傷而抱怨,也沒有人因?yàn)楹ε聭?zhàn)爭而想逃跑,許多人渴望被醫(yī)治,以重新投入戰(zhàn)斗。可見,“人民就是軍隊(duì),軍隊(duì)就是人民”,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下的軍隊(duì)是經(jīng)得起戰(zhàn)爭考驗(yàn)的人民軍隊(duì),他們切實(shí)履行著保衛(wèi)祖國和人民、敢于斗爭、不怕犧牲的堅(jiān)定諾言,這一歷史事實(shí)同樣被該期刊所記錄。
(三)邊區(qū)政府:民主的范例
抗戰(zhàn)時(shí)期,中國共產(chǎn)黨堅(jiān)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學(xué)說同中國革命實(shí)際相結(jié)合,切實(shí)加強(qiáng)了邊區(qū)建設(shè),從而既保證了人民當(dāng)家做主的權(quán)利,又為抗戰(zhàn)勝利提供了動(dòng)力。《太平洋事務(wù)》認(rèn)為,“邊區(qū)政府始終把民主視為最高原則,他所實(shí)行的民主模式很有可能在全國范圍內(nèi)發(fā)展,呈現(xiàn)日本所不能應(yīng)付的抗戰(zhàn)局面,并使將來真正民主的中國成為可能”(38)④⑦ A British observe, “ The Future Foreshadowed: China’s New Democracy”, Pacific Affairs , Vol.11, No.4 , 1938, pp.454-464.。
《太平洋事務(wù)》發(fā)現(xiàn),中國共產(chǎn)黨積極推進(jìn)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并實(shí)施了“三三制”政權(quán)建設(shè)原則。統(tǒng)一戰(zhàn)線原則被該刊學(xué)者注意到,他們或者認(rèn)為,為保衛(wèi)中國領(lǐng)土,中國共產(chǎn)黨從日本侵華開始就提出同國民黨聯(lián)合作戰(zhàn)的口號(39)O. L, “ Reviewed Work(s): The North China Problem. by Shuhsi Hsu”, Pacific Affairs, Vol.10, No.4 , 1937, pp.457-459.,或者認(rèn)為,中國共產(chǎn)黨盡全力支持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在執(zhí)行統(tǒng)一戰(zhàn)線計(jì)劃上的誠意無可指責(zé)(40)Wei Meng-Pu, “The Kuomintang in China: Its Fabric and Future”, Pacific Affairs,Vol.13,No.1,1940,pp.30-44.。在“三三制”原則提出之前,一位英國的觀察者就發(fā)現(xiàn),邊區(qū)政府是一個(gè)聯(lián)合戰(zhàn)線的政府,既有共產(chǎn)黨,又有國民黨和無黨派人士④。“三三制”原則正式提出后,斯特朗在晉察冀邊區(qū)了解到,中國共產(chǎn)黨人始終遵守毛澤東先前作出的承諾,不接受任何聯(lián)合陣線政府中超過三分之一的民選席位(41)⑨ Anna Louise Strong,“Eighth Route Regions in North China”,Pacific Affairs,Vol.14,No.2,1941,pp.154-165.。
《太平洋事務(wù)》描述了邊區(qū)政府的精兵簡政和官員的清廉、高效。漢森發(fā)現(xiàn),以前政府中的數(shù)百名官員被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少數(shù)年輕人,“最高官員的工資只有1美元,官員們對百姓的壓榨可能被處以死刑”(42)⑩ Haldore Hanson , “ The People Behind the Chinese Guerillas”,Pacific Affairs,Vol.11,No.3,1938,pp.285-298.。一位觀察者記錄道,“他們帶著遠(yuǎn)大的理想、良好的教育和堅(jiān)定的目標(biāo)來完成他們的任務(wù)。他們吃著不太好的食物,領(lǐng)著象征性的薪水,放棄女性的陪伴,擁有的東西只比他們穿的衣服多一點(diǎn)”⑦。這些記錄反映出了邊區(qū)政府及其公職人員清廉為民、務(wù)實(shí)高效的政治品格。對此,斯諾還曾稱贊邊區(qū)政府真正當(dāng)?shù)闷鹎辶姆Q號(43)埃德加·斯諾等:《國際觀察家對中國政治的評論》,北京:新知識書店,1946年,第5頁。。
此外,《太平洋事務(wù)》還發(fā)現(xiàn)邊區(qū)政府通過民主選舉、削減稅收、普及教育等多項(xiàng)舉措滿足民眾的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訴求。斯特朗在談到晉察冀邊區(qū)的選舉時(shí)指出,人人都享有民主權(quán)利。“縣官”在群眾運(yùn)動(dòng)中當(dāng)選,被選出的縣政府包括所有階級⑨。在漢森的記錄中,土地問題得到解決,政府削減了稅率,稅收主要由富人承擔(dān)⑩。有觀察者還發(fā)現(xiàn),每個(gè)孩子都獲得了免費(fèi)接受教育的機(jī)會,同時(shí),所有教師都有一門關(guān)于國防主題的課程,為強(qiáng)調(diào)抗日,教科書也進(jìn)行了修訂。這些舉措不僅使邊區(qū)政府的群眾基礎(chǔ)得到了鞏固,更進(jìn)一步調(diào)動(dòng)了民眾保家衛(wèi)國、投身抗戰(zhàn)的積極性。
三、《太平洋事務(wù)》視域下中國共產(chǎn)黨形象變遷的影響因素
《太平洋事務(wù)》視域下的中國共產(chǎn)黨經(jīng)歷了從“紅色威脅”到“紅色力量”,再到“璀璨紅星”的形象變遷。為何會發(fā)生這一變化?分析發(fā)現(xiàn),中國共產(chǎn)黨英勇斗爭和卓越業(yè)績是基本原因,而該期刊學(xué)者群體的實(shí)地考察與立場轉(zhuǎn)變,以及中國共產(chǎn)黨的積極對外宣傳是直接動(dòng)因。
(一)實(shí)地考察:作者群體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深入了解
梳理文獻(xiàn)及作者群體的人生經(jīng)歷發(fā)現(xiàn),《太平洋事務(wù)》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認(rèn)知與其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實(shí)地了解程度呈正相關(guān)。局部抗戰(zhàn)初期,國民黨的封鎖和歪曲宣傳以及中國共產(chǎn)黨活動(dòng)的秘密性,導(dǎo)致了國際社會有關(guān)中國共產(chǎn)黨訊息的非真實(shí)性與誤導(dǎo)性。在此情況下,《太平洋事務(wù)》視域中的中國共產(chǎn)黨幾乎是在作者沒有接觸中國共產(chǎn)黨的情況下遠(yuǎn)距離猜測與構(gòu)建的。至局部抗戰(zhàn)后期,拉鐵摩爾的接任使該期刊開始以相對開放的態(tài)度介紹與討論中國共產(chǎn)黨,并基于少數(shù)作者的實(shí)地考察呈現(xiàn)相對中性的中國共產(chǎn)黨形象,但由于一手資料的缺乏,其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認(rèn)知依舊較為模糊。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隨著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形成,國民黨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封鎖有所減弱,同時(shí),由于中美關(guān)系的加強(qiáng),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來華。在此背景之下,太平洋國際學(xué)會積極組織其成員或與其有密切關(guān)系的人士到根據(jù)地進(jìn)行考察,以了解在中國被長期封鎖的中國共產(chǎn)黨(44)李曄:《太平洋學(xué)會與西方學(xué)界的中國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dòng)研究》,《理論學(xué)刊》2010年第11期。。這些來華成員包括拉鐵摩爾、畢森、斯諾、斯特朗、蘭格等多位知名學(xué)者,他們力求“搞清楚正在發(fā)生什么事,了解人們正在做什么”(45)[日]磯野富士子整理:《蔣介石的美國顧問——?dú)W文· 拉鐵摩爾回憶錄》,吳心伯譯,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96年,第51頁。。正是通過實(shí)地了解,學(xué)會成員們改變了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刻板印象與誤解,切實(shí)感受到中國共產(chǎn)黨是有力的抗日力量,該政黨友愛平等、政治成熟,積極投身于人民生活的改善中,與腐敗墮落和專制集權(quán)的國民黨形成鮮明對比。
(二)立場轉(zhuǎn)變:太平洋國際學(xué)會的日益左傾
作為太平洋國際學(xué)會的機(jī)關(guān)刊物,《太平洋事務(wù)》視域下中國共產(chǎn)黨形象的變化與太平洋國際學(xué)會立場的轉(zhuǎn)變不無關(guān)系。在成立之初,學(xué)會一直保持中立,并盡量避免在有爭議的政治問題上表達(dá)立場。學(xué)會的第一任總干事約翰·戴維斯曾強(qiáng)調(diào),學(xué)會是非爭論性、非宣傳性的組織,扮演的是事實(shí)發(fā)現(xiàn)者與解釋者的角色(46)J.B. Condliffe(ed.),Problems of the Pacific(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Honolulu, Hawaii, July 15 to 29, 1927),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8, p.6.。而1933年戴維斯的離職和卡特的任職成為太平洋國際學(xué)會發(fā)展的重要轉(zhuǎn)折點(diǎn)。卡特作為一名左翼人士,有著強(qiáng)烈的反殖民主義傾向,同情殖民地人民和共產(chǎn)黨。在擔(dān)任學(xué)會總干事后,他任用了具有左翼思想的拉鐵摩爾、菲爾德、陳翰笙等人。1933年,拉鐵摩爾擔(dān)任《太平洋事務(wù)》主編,在他的領(lǐng)導(dǎo)下,該期刊呈現(xiàn)強(qiáng)烈的左翼色彩。1934年,美國左翼作家菲爾德被任命為美國理事會總干事,菲爾德與美國共產(chǎn)黨關(guān)系密切,曾被認(rèn)為是“紅色百萬富翁”。由于美國理事會與太平洋理事會在同一棟大樓內(nèi),卡特與菲爾德有密切的溝通與合作。中共黨員陳翰笙的加入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了學(xué)會的左翼色彩。1931—1936年,他先后成為太平洋國際學(xué)會秘書處主要成員和《太平洋事務(wù)》副主編。任職期間,陳翰笙不僅借此平臺撰寫文章積極介紹中國共產(chǎn)黨,還協(xié)助了拉鐵摩爾等學(xué)會領(lǐng)導(dǎo)層成員對延安的訪問。他與菲爾德建立了緊密的關(guān)系,二人共同為《太平洋事務(wù)》編輯文章,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國的進(jìn)步力量是如何抵抗法西斯侵略的。有學(xué)者曾指出,通過陳翰笙的努力,這家頗富影響力的雜志逐漸向“左”的方面發(fā)展,隨之發(fā)表的有進(jìn)步思想的文章也多了起來(47)田森:《三個(gè)世紀(jì)的陳翰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101頁。。
隨著多位左翼人士的加入及其在學(xué)會中骨干地位的確立,太平洋國際學(xué)會立場逐漸“左”傾,其下的會議和刊物也呈現(xiàn)大量同情和支持中國共產(chǎn)黨的論述。例如,畢森就曾在學(xué)會的另一份刊物《遠(yuǎn)東觀察》上發(fā)文稱,國統(tǒng)區(qū)是“封建的中國”,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根據(jù)地是“民主的中國”(48)T.A.Bisson, “China’s Part in a Coalition War”, Far Eastern Survey, Vol.12, No.14,1943,pp.135-141.。《太平洋事務(wù)》不僅發(fā)表了大量褒揚(yáng)和同情中國共產(chǎn)黨的論述,還推介了很多相關(guān)研究成果。同時(shí),在抗戰(zhàn)期間,該期刊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認(rèn)知從“紅色威脅”轉(zhuǎn)變?yōu)椤拌驳募t星”,對國民黨的描述則從“如日方升”逐漸轉(zhuǎn)變?yōu)椤叭諠u衰頹”。對于學(xué)會的這一“左”傾態(tài)度,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還曾指責(zé)其走的是“共產(chǎn)黨路線”(49)Senate Internal Security Committee, Hearings on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Washington:U.S.G.P.0,1951,p.1043.。
(三)對外宣傳: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正面形象建構(gòu)
《太平洋事物》對中國共產(chǎn)黨積極認(rèn)知的生成亦與中國共產(chǎn)黨加強(qiáng)對外宣傳、撕掉污名化標(biāo)簽的努力有關(guān)。抗戰(zhàn)時(shí)期,中國共產(chǎn)黨主動(dòng)作為、精心部署,努力打破國民黨的輿論封鎖和造謠污蔑,向外界有效展示了中國共產(chǎn)黨在抗戰(zhàn)中的中流砥柱形象。一方面,斯諾和《紅星照耀中國》的成功使中國共產(chǎn)黨看到了對外宣傳的積極作用,加之抗戰(zhàn)的需要,中國共產(chǎn)黨決定加強(qiáng)對外宣傳的力度與措施,把對外宣傳工作做為一項(xiàng)重要議程。1937年底,中國共產(chǎn)黨在延安設(shè)立了對外宣傳交際處。毛澤東曾指示交際處的同事,凡是要求見他的一律先答應(yīng),并把他們的要求盡快轉(zhuǎn)告給他(50)林之達(dá):《中國共產(chǎn)黨宣傳史》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2頁。。這標(biāo)志著對外宣傳工作的正式開展。1938年,鄧小平強(qiáng)調(diào):“大大加強(qiáng)對外宣傳工作,把我們真實(shí)的戰(zhàn)斗生活反映到國際上去”(51)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頁。。1940年8月,周恩來指出,海外報(bào)紙影響特別大,需特別關(guān)注(52)趙春生:《周恩來文化文選》,北京: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1998年,第21頁。。此后,他多次強(qiáng)調(diào),對外宣傳工作要采取宣傳出去和爭取過來的方針(53)中共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北京: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1998年,第587頁。。另一方面,在對外交往過程中,中國共產(chǎn)黨熱情歡迎國際友好人士來訪抗日根據(jù)地,并對他們給予了全力支持和幫助。1937年,拉鐵摩爾和畢森到延安進(jìn)行考察,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同他們進(jìn)行了交談。令拉鐵摩爾驚訝的是,毛澤東居然愿意花上數(shù)小時(shí)與不相識的美國人交談,且他愿意實(shí)事求是、以最簡單的表達(dá)方式同他們探討問題。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人給拉鐵摩爾的印象是,他們“知道自己的經(jīng)歷將吸引全世界反帝人士,他們懂得怎樣談話才能使美國報(bào)紙有利地引述他們的言論,他們盡最大努力使自己的故事具有吸引力”(54)[日]磯野富士子整理:《蔣介石的美國顧問——?dú)W文·拉鐵摩爾回憶錄》,吳心伯譯,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96年,第53頁。。值得注意的是,拉鐵摩爾此行之后,有關(guān)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正面介紹在《太平洋事務(wù)》中愈來愈多。1938年,漢森來到華北抗日根據(jù)地,聶榮臻等人熱情地接待了他,毛澤東等人向他介紹了根據(jù)地的情況。基于實(shí)地了解,漢森發(fā)表了《中國游擊隊(duì)背后的人民》一文,高度贊揚(yáng)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抗日行為。張聞天也接受了威爾斯的采訪。基于這一采訪,尼姆·威爾斯在《太平洋事務(wù)》中向國際社會介紹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歷史,并闡明了中國共產(chǎn)黨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的緣起與具體立場。因此,正是中國共產(chǎn)黨對外宣傳的不懈努力為《太平洋事務(wù)》作者們的來訪提供了有利條件,并有力推動(dòng)了他們對中國共產(chǎn)黨積極形象的建構(gòu)。
結(jié)語
抗戰(zhàn)時(shí)期中國共產(chǎn)黨的國際形象無疑是極為關(guān)鍵的問題。作為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頗具國際影響力的期刊,《太平洋事務(wù)》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介紹與研究盡管存在誤解與局限之處,但該期刊視域中中國共產(chǎn)黨形象的正向變化以及其最終所凸顯的“璀璨紅星”形象,不僅推動(dòng)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深入了解,更從“他者”的視角印證了中國共產(chǎn)黨在抗戰(zhàn)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可以說,在中華民族危亡之際,中國共產(chǎn)黨就像一顆閃耀的紅星,照亮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前行之路。
《太平洋事務(wù)》視域下中國共產(chǎn)黨形象的正向變遷,對于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構(gòu)建中國共產(chǎn)黨的國際形象亦具有重要的啟發(fā)性意義。其一,應(yīng)積極邀請海外記者、學(xué)者來華參觀和考察,并為他們了解中國共產(chǎn)黨提供豐富的“原材料”。國際形象建構(gòu)的前提是他者對該主體的深入了解。抗戰(zhàn)時(shí)期,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人多次放下手頭緊急公務(wù),屢次同來訪的外國人士促膝長談、深入交流,從而使海外人士轉(zhuǎn)變了原有的偏見與誤解,并進(jìn)一步推動(dòng)了他們在國際社會中對中國共產(chǎn)黨形象的良好塑造。因此,我們應(yīng)當(dāng)充分發(fā)揮來華外國人士的橋梁作用,使之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故事的見證者與傳播者,實(shí)現(xiàn)借“筒”傳聲,借“嘴”說話。其二,應(yīng)當(dāng)積極推動(dòng)一批學(xué)者走向海外宣傳中國共產(chǎn)黨。抗戰(zhàn)時(shí)期,在《太平洋事務(wù)》中始終活躍著一批既具有中國傳統(tǒng)文化學(xué)術(shù)根基、又接受過西方文化熏陶的中國學(xué)者,他們致力于在海外宣傳與介紹中國共產(chǎn)黨,力求為中國共產(chǎn)黨抗戰(zhàn)尋求國際支持與援助,并取得了積極成效。因此,我們應(yīng)推動(dòng)一批中國學(xué)人走向海外,使其以西方人所喜歡與接受的學(xué)理性表達(dá)方式,通過國外社交媒體、期刊等媒介講好中國和中國共產(chǎn)黨的故事。其三,對外宣傳應(yīng)當(dāng)秉持開誠布公、以誠相待的原則。中國共產(chǎn)黨故事之所以精彩動(dòng)人,至關(guān)重要的原因是其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fā)點(diǎn),以所取得的偉大成就為事實(shí)基礎(chǔ)。抗戰(zhàn)時(shí)期,中國共產(chǎn)黨在與來訪的海外人士交流互動(dòng)過程中,始終堅(jiān)持以誠相待、用事實(shí)說話,這種自信與至誠既打動(dòng)了來訪人士,也打動(dòng)了國際社會的讀者,使中國共產(chǎn)黨故事廣為傳播。時(shí)至今日,中國共產(chǎn)黨帶領(lǐng)中國人民取得了一系列偉大成就,但在發(fā)展中也面臨一定的問題和挑戰(zhàn)。對此,我們既應(yīng)展示成就,也應(yīng)敢于承認(rèn)不足之處,以實(shí)事求是原則積極開展對外傳播。總之,在新時(shí)代百年征程中,如何對外講好中國共產(chǎn)黨故事,堅(jiān)定地把黨的國際形象推向新的高度,是一個(gè)值得持續(xù)探討的議題,也是一個(gè)需要為之努力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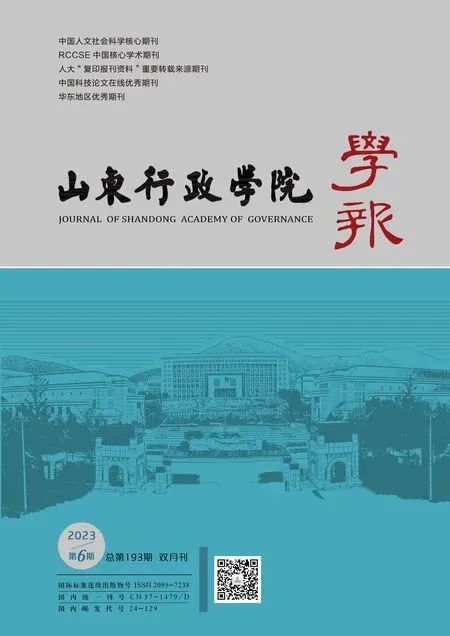 山東行政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23年6期
山東行政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23年6期
- 山東行政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內(nèi)卷化視域下的中國技術(shù)創(chuàng)新之路
- 生態(tài)整體論視域下生態(tài)保護(hù)地方立法的完善進(jìn)路
——基于黃河流域地方立法實(shí)踐的考察 - 海外對中國共產(chǎn)黨社會治理的研究考察
——?dú)v史、范式、觀點(diǎn)及評議 - “制度—權(quán)力—技術(shù)—個(gè)體”:鄉(xiāng)村治理數(shù)字化下農(nóng)民主體性重塑的四維邏輯
- 政策試點(diǎn)學(xué)習(xí)機(jī)制的邏輯樣態(tài)與建構(gòu)理路
- 數(shù)字化賦能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發(fā)展的效應(yīng)與實(shí)現(xiàn)路徑
——以山東省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