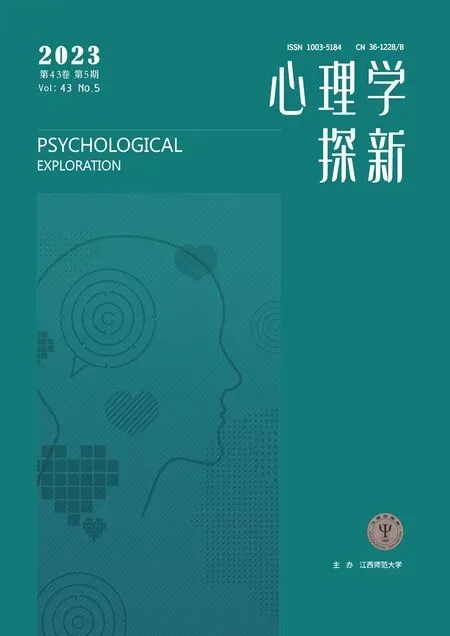中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感與職業幸福感:基于組織的自尊和組織支持感的作用
潘晨晨,方 平,姜 媛
(1.北京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北京 100048;2.首都師范大學心理學院,北京 100048;3.北京體育大學心理系,北京 100084)
1 問題提出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教師隊伍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并強調要努力提高教師政治地位、社會地位、職業地位,讓廣大教師享有應有的社會聲望(崔榮,郭孝杰,劉亞,2018)。其中,教師職業幸福感的培養至關重要。職業幸福感通常是根據自身標準對其工作相關各個方面的主觀體驗,是對與職業相關的認知、動機、情感和身心幸福等方面的積極評價(Diener et al.,2003;Joan et al.,2004;劉穎麗,任俊,2010)。《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2018)特別指出,要提升廣大教師在崗位上的幸福感。而最新研究發現,我國中小學教師職業幸福感狀態存在 “隱憂”,教師健康幸福感等子維度處在較低水平,影響著教師自我發展的內動力(李廣,蓋闊,2022)。教師職業幸福感是權衡中小學老師的身心狀態的指南針(李清 等,2021),關系到教師的工作滿意度及職業承諾(Herscovitch &Meyer,2002;王鋼,2013),也影響著教師心理健康水平,較低的幸福感水平易產生抑郁傾向等心理健康問題(李燕,余菊芬,2014)。由此可見,教師職業幸福感關系到中小學教師身心、職業及教育事業的長久發展。因此,探究影響中小學教師職業幸福感的因素尤為重要。
教師職業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尤其體現在工作中的效能感上,具有較高效能感的教師更滿意他們的工作和人際關系(Bandura,1977;Clegg &Spencer,2010;Tsigilis et al.,2010),更容易在職業中產生幸福的體驗(Klassen et al.,2011)。然而,目前對于中小學教師職業幸福感的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人格、個人動機和客觀環境等因素上(Diener &Lucas,2000;Panatik &Shah,2011),較少涉及以教學為中心的信念如教師教學效能感作為前因變量的研究,即大多是以個人一般效能感作為前因變量,而忽略教師效能感的職業特征;其次,以往研究沒有考慮到外部支持、組織中的價值判斷等因素在教學效能感與職業幸福感中的作用,教師在教學工作過程中需要獲得自尊和價值的肯定,同時也需要獲得實現其價值的物質及心理支持,以提升個體在組織中的自尊(張向葵 等,2004),緩解工作過程中的不良體驗,提升職業幸福感(Maslach,2001)。因此,有必要聚焦探討教師教學效能感對教師職業幸福感的影響,以及基于組織的自尊、組織支持感在其中的作用,進一步明確在學校和組織情境下,教師教學效能感“如何”以及“在何種情況下”影響教師職業幸福感,以為教師營造良好工作氛圍,促進教育事業發展提供針對性的建議。
1.1 教學效能感和職業幸福感的關系
根據Bandura(1977)自我效能理論,個體的自我評估的結果將直接對個體行為體驗及動機產生影響,較高職業幸福感意味著在工作中體驗較多的積極情感(Diener,1984),于教師而言,這種積極情感會受到其在教學中的效能感的影響。教學效能感是教師對自己能否有效完成教學及實現教學目標的信念(俞國良 等,2000),具體指教師對自己能否掌握教師設計能力與方法、順利激勵學生、影響學生發展及能否有效促進課堂教學順利進行的一種主觀判斷和信念。
一般而言,效能感越高,越易于感知到工作意義,且會以此重塑工作方式,有益于增強職業幸福感(Clegg &Spencer,2010;鄒璐 等,2014),減少抑郁和焦慮情緒(Caprara &Steca,2005;Cohen &Cairns,2012)。Tsigilis等(2010)的研究表明,具有較高的效能感的教師更滿意他們的工作和關系,更容易產生職業幸福的體驗(Klassen et al.,2011)。國內大量的實證研究也表明,教師在職業和生活中的幸福感會隨著教學效能感的提升而升高(陳美榮,曾曉青,2008;崔榮寶 等,2018;羅小蘭,韓娟,2019)。
以上研究表明,教師教學效能感對職業幸福感的預測作用已有較為明確的理論和研究支撐,相應的假設為H1:教師教學效能感可以正向預測教師職業幸福感。
1.2 基于組織的自尊的中介作用
按照個體心理發展理論,效能感是個體在所在組織或者群體中的自尊得以發展的前提(張向葵 等,2004),同時,自尊的發展也是積極幸福感體驗獲得的前提(Cheng &Furnham,2003)。關于自尊、效能與幸福感關系的研究表明,自尊在一般自我效能感對幸福感的影響中起著部分中介作用(黃希庭 等,2014),這為探討基于組織的自尊在教學效能感與職業幸福感之間的作用提供了理論支撐。基于組織的自尊,又稱組織自尊,是“自尊”概念的情景化與具體化,即組織成員相信他們可以通過參與組織中的角色滿足他們需要的程度,它反映個體在組織環境中對自我價值以及重要性的評估(Pierce et al.,1989)。從自我效能感理論看來(Bandura,1977,1986),教學效能感的提升,有助于提升教師自我價值評判,循此觀點,教學效能感的增加可以提升個體的基于組織的自尊。同時,有關探討自尊和自我效能感之間關系的研發現,自我效能感越高,自尊水平也就越高(袁文萍,馬磊,2020;鄭顯亮,趙薇,2015),這也為教師教學效能感與基于組織的自尊的關系提供了研究和支撐。
資源保存理論(Hobfoll,1989)提出,資源充足的人更善于獲取新能量,獲得正向體驗。因此,較高的基于組織的自尊能使教師更好地吸收心理能量、增益認知,個體傾向于選擇一些積極的反應來強化這一認知,如在職業生涯中提升幸福體驗(Pierce &Gardner,2004)。Cheng和Furnham(2003)也提出,自尊是幸福感的強大預測因子。循此邏輯,基于組織的自尊水平較高的教師對所從事工作帶來的滿足感等積極體驗會更深刻,所感受到的幸福感會更高。實證研究也證實了基于組織的自尊較高的教師在工作中擁有較高的職業幸福感(彭堅 等,2021)。因此,根據以上理論和已有的相關實證研究,提出假設H2:中小學教師基于組織的自尊在教學效能感與職業幸福感之間起中介作用。
1.3 組織支持感在變量間的調節作用
組織支持感是指個體能夠直覺到的組織或單位對其貢獻及其核心利益重視程度的感知(Eisenberger et al.,1986),其是一種重要的社會支持資源。在資源保存理論看來(Hobfoll,1989,2001),資源豐富的個體,會積極謀求更多資源,社會支持不僅能提供物質支持,避免資源損失,還可以提升個體對生活目的及意義的感知(Taylor &Turner,2001),提高個體的正向自我評價(Wethington &Kessler,1986),進而提升在職業或生活中的幸福感。當教師感受較多組織支持時,其能從組織或學校中積累更多的能量,此時,員工(教師)對能量獲取更為敏感(Halbesleben et al.,2011)。在這種情況下,教師能得到更多的心理能量(如幸福感體驗,積極自我評價),這些能量能使教師更相信自身的價值與能力,進而獲得更高的基于組織的自尊和職業幸福感。
同時,基于工作—要求資源模型,工作資源能夠緩沖負面要素對員工的損耗,組織支持感作為重要工作資源,對于緩解工作過程中的職業倦怠、不良體驗和個人評判有著重要的作用(Melchiorre et al.,2013),因此教師可以依靠較高組織支持感,緩解負面要素對基于組織的自尊和職業幸福感的消極作用。
以上理論很好地證明了組織支持感的緩解負面體驗與評判、強化積極體驗與評判的功能。大量的研究也表明,在高組織支持感下,即便個體出現了較多負面個人評判(如較低的自我效能感),個體自尊、價值感及個體與他人的交往中積極體驗也能處在不錯的水平(Taylor &Armor,1996),即高支持水平能緩沖負面心理問題給帶來的消極體驗(Cohen &Wills,1985),這有利于說明組織支持感在教學效能感與基于組織的自尊間的作用。然而,在低組織支持感下,個體較難從組織中獲得支持資源(Beehr et al.,2000),此時,個體會對丟失資源更加敏感(Hobfoll,1989),從而引起較低的幸福感水平。
基于以上理論和研究,提出假設H3:中小學教師組織支持感在教學效能感與基于組織的自尊、教學效能感與職業幸福感以及在基于組織的自尊與職業幸福感之間起調節作用。

圖1 結構方程圖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選取北京、浙江、廣東、安徽、河南、山東、湖北、廣西等城市不同年齡階段教師共計1100名。刪除漏填、重復填寫、重復選項及未通過測謊題作答的問卷181份,剩余有效問卷為919份,問卷有效率為83.55%,被試平均年齡38.23±9.53歲,平均教齡15.40±10.69年。其中,男教師262人(平均年齡39.67±9.82歲,平均教齡17.42±10.35年),女教師657人(平均年齡37.73±9.36歲,平均教齡14.60±10.73年)。
2.2 工具
2.2.1 自編中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感量表
采用自編中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感量表,分為教學策略與設計效能、動機激發效能和課堂管理效能共3個維度,包含18個項目,量表采用Likert 5計分,1~5代表了“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五個水平。對401名來自全國隨機抽取的中小學教師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形成18個項目組成的量表,并采用該量表對820名中小學教師進行調查,回收數據并分析其信效度。最終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95,各維度Cronbach’sα系數在0.81-0.92之間,累計方差解釋率為54.24%。驗證性因素分析表明模型擬合良好,RMSEA=0.07,GFI=0.91,IFI=0.94,TLI=0.93,CFI=0.94。因此,中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感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6。
2.2.2 教師職業幸福感量表
采用劉穎麗(2010)制定的教師職業幸福感問卷。問卷分為認知疲乏、從業動機、人際關系、身體健康以及成就感五個維度,共計18個項目。量表采用Likert 5計分,1~5代表了“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五個水平。總分越高表明職業幸福感越高,反之亦然。其中項目1、3、4、7、8、10、13、15、17、18為反向計分。問卷Cronbach’sα系數和分半信度均為0.81,信度檢驗良好。該量表在本研究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3。
2.2.3 基于組織的自尊量表
采用Pierce等(1989)開發的基于組織的自尊(OBSE)的量表,量表基于教師、管理者、工人等多類群體開發和驗證,包括10個項目,區別于一般自尊的測量。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為0.91,復本效度為0.87,各項指標良好。此量表在不同群體中有較高的相關性,有較好的聚合效度。該量表在本研究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6。
2.2.4 組織支持感量表
采用劉智強在Eisenberger等人編制的組織支持感短版量表的基礎上修訂的含有6條有效題項的量表。該量表采用Likert-5點量表進行測量,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8,CR值為0.91。該量表在本研究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9。
2.3 施測程序
使用問卷星在線發放電子問卷進行調查,采用SPSS25.0和Process3.3對數據進行處理。
3 研究結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研究數據均通過問卷調查法得來,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可能。因此,首先采用了Harman單因子檢驗法來檢驗共同方法偏差,即將問卷所有的題目均納入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未旋轉的分析結果顯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9個,第一個因子的解釋率為13.67%,小于40%臨界值。同時,采用潛在誤差變量控制法進一步檢驗共同方法偏差,結果表明,將共同方法偏差作為潛變量加入模型后,RMSEA值由0.077提高至0.081,CFI、TLI及IFI的值由0.910以上,分別降低至0.887、0.905、0.897,即加入共同方法偏差潛變量后,模型的擬合指標并沒有優化,說明未出現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中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感、職業幸福感、基于組織的自尊和組織支持感的相關分析
對中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感、職業幸福感、基于組織的自尊和組織支持感進行相關分析,四個變量之間存在兩兩的顯著性正相關。教師教學效能感與職業幸福感、基于組織的自尊和組織支持感均存在顯著正相關(r=0.443**、r=0.194**、r=0.277**);職業幸福感與基于組織的自尊和組織支持感之間均存在顯著正相關(r=0.296**、r=0.428**);基于組織的自尊和組織支持感存在顯著正相關(r=0.384**)。相關分析的結果為進一步探究以上變量間的關系奠定了基礎。具體數據見表1。

表1 中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感、職業幸福感、基于組織的自尊和組織支持感的相關分析
3.3 中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感對職業幸福感的影響:基于組織的自尊的中介作用
為了檢驗中小學教師基于組織的自尊在教學效能感和職業幸福感之間的中介效應,采用Hayes(2003)開發的PROCESS中的Model 4進行分析,其中教學效能感為自變量,教師職業幸福感為因變量,年齡和性別為控制變量,為避免共線性問題,變量均進行了標準化處理。具體分析數據見表2。

表2 中小學教師基于組織的自尊的中介效應檢驗
從表2分析結果可知,中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感能顯著的正向預測職業幸福感(β=0.51,t=15.27***),即教師教學效能感越高,職業幸福感越高;同樣,教學效能感也能顯著的正向預測基于組織的自尊(β=0.25,t=7.58***)。在加入中介變量基于組織的自尊之后,教師教學效能感仍可以顯著的正向預測職業幸福感(β=0.39,t=13.21***);最后,基于組織的自尊能顯著的正向預測職業幸福感(β=0.28,t=9.54***)。

表3 總效應、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分解表
從表3中可知,中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感對職業幸福感的直接效應為0.46,Bootstrap 95%置信區間不包含0,基于組織的自尊在教學效能感與職業幸福感之間的間接效應為0.07,Bootstrap 95%置信區間不包含0。這表明,教學效能感不僅能直接預測職業幸福感,還能通過基于組織的自尊間接的影響職業幸福感,其中直接效應占總效應的84.78%,間接效應占總效應的15.12%。
3.4 中小學教師組織支持感的調節效應檢驗
為了檢驗基于組織的自尊的調節效應,采用了Hayes(2003)開發的PROCESS中的Model 59(模型前半段、后半段及直接路徑受到調節)進行分析,其中,年齡和性別為控制變量,結果發現,組織支持感在模型前半段即后半段調節效應顯著。具體分析數據見表4,結果表明教學效能感組織支持感的交互項能顯著負向預測基于組織的自尊(β=-0.10,t=-3.47***),基于組織的自尊和組織支持感的交互項能顯著的正向預測職業幸福感(β=0.12,t=4.16***)。

表4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表
為了更好的闡明組織支持感的調節作用,進行了簡單斜率分析。圖4表明,在低組織支持感下(M-1SD),中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感對基于組織的自尊正向預測作用顯著(β=0.19,t= 5.04***,p<0.001);在高組織支持感下(M+1SD),中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感不能顯著預測基于組織的自尊(β=0.01,t= 0.84,p>0.05)。

圖2 組織支持感在教師教學效能感與基于組織的自尊間的調節作用
圖5表明,在低組織支持感下(M-1SD),中小學教師基于組織的自尊對職業幸福感的正向預測作用顯著(β=0.29,t=6.70***,p<0.001);在高組織支持感下(M+1SD),中小學教師基于組織的自尊也能顯著預測職業幸福感(β=0.36,t= 9.64***,p<0.001),且作用程度更高。

圖3 組織支持感在教師基于組織的自尊與教師職業幸福感間的調節作用
最后,對組織支持感在中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感與教師職業幸福感間的調節作用進行探究可知,組織支持感不能在教師教學效能感與教師職業幸福感間起調節作用。
4 分析與討論
4.1 中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感與職業幸福感的關系:基于組織的自尊的中介作用
研究結果表明,中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感對職業幸福感有顯著正向預測作用,教師教學效能感的提升會提升職業幸福感,這一結果驗證了假設H1的猜想。教學效能感高的個體通常在教學上信心十足,這種信心可提升積極情感的概率,從而增強幸福感(鄒璐 等,2014)。教學效能感高的教師在遇到困難時的信心能有效控制不良情緒反應,從而可以更好地調節個人行為及體驗。反之,教師則會質疑個人應對突發教學情況的能力,因而容易體驗到強烈的負面情緒(劉曉明 等,2008;龐麗娟 等,2005),這些體驗進一步強化教師受挫感、低自我認同等消極心理,從而導致職業幸福感下降。
在明確中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感和職業幸福感的關系之后,進一步分析了基于組織的自尊在二者之間的作用,結果表明,基于組織的自尊在教學效能感與職業幸福感之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教學效能感可以通過基于組織的自尊來影響職業幸福感,這一結果與假設H2一致。其中,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15.12%。根據個體心理發展理論,自我效能感是組織或群體中的個體的自尊發展的基礎(張向葵 等,2004);自我效能感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教學效能感和基于組織的自尊的關系(Bandura,1977,1986),效能感的提升有利于個體增加自我評價和自我控制感,于教師而言,利于提升個體的教學和課堂控制感,進而促使個體增強自我價值評價,提升個體在組織中的自尊(Betz &Klein,1996)。基于組織的自尊的中介作用可以用資源保存理論(Hobfoll,1989)來解釋。當個體心理資源缺失時(如出現較低的教學效能感),高基于組織的自尊將幫助個體吸收更多心理能量,從而提升職業幸福感。基于組織的自尊水平較高時,員工相信自己在組織中具備價值和能力(黃澤群 等,2019),為了與這種認知匹配,個體傾向于做出一些積極反應來增強這種認知,如增強在職業幸福體驗(Pierce &Gardner,2004)。
4.2 中小學教師組織支持感在不同路徑的調節作用
4.2.1 中小學教師組織支持感在基于組織的自尊與職業幸福感間的調節作用
研究表明組織支持感在教師教學效能感和基于職業幸福感間起調節作用,驗證了假設H3的部分猜想。具體而言,較于低組織支持感,在高組織支持感下,基于組織的自尊對職業幸福感的正向預測作用顯著程度更高,組織支持感的調節方向為正向。基于依據資源保存理論(Hobfoll,1989),擁有高資源的教師對資源獲取更為敏銳(Halbesleben et al.,2014)。在這種情況下,教師將利用獲取資源的機會來獲得一定積極的心理資源,這些資源能夠讓組織里的教師體驗到更高的職業幸福感水平。因此,高水平組織支持感下,教師基于組織的自尊對職業幸福感正向作用更強。然而,在低程度的組織支持感下,員工較難獲得支持性資源(Beehr et al.,2000),此時,基于資源保存動機,教師會對失去資源更加敏感,且會將低效能感作為一種任務干擾及對自身資源的潛在威脅或消耗(Hobfoll,1989),因此,在低水平組織支持感下,教師基于組織的自尊對職業幸福感的影響作用更弱。
4.2.2 中小學教師組織支持感在教學效能感與基于組織的自尊的調節作用
結果表明中小學教師組織支持感在教學效能感與基于組織的自尊間起調節作用,驗證了假設H3的部分猜想。具體而言,在高組織支持感下,教學效能感高低對基于組織的自尊沒有顯著影響,但基于組織的自尊均處于較高水平,組織支持感的調節方向為負向。該結果產生的原因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高組織支持感作為個體重要的心理社會資源,能使得個體保持較高的意義感和目標感(Taylor &Turner,2001)即積極的自我評價(如基于組織的自尊)(Wethington &Kessler,1986)。值得注意的是,高組織支持感雖然存在保留積極心理資源的效果,但資源保存理論也強調個體會盡全力保存并維護有意義的資源,以避免資源損耗。因此,在低組織支持感下,教師對現有的教學效能感的資源保存更為敏感,并盡全力保存該資源;另一方面,組織支持感和基于組織的自尊均是基于組織的變量,兩個概念均涉及到與個人價值及重要程度相關的要素,基于組織的自尊是在組織中的自我感知,組織支持感是對組織如何作用于自己的感知(Eisenberger et al.,1986;Pierce et al.,1989)。因此,具有較高組織支持感的教師,不論其教學效能感水平如何,都會有較高的自我價值及重要性感知水平,即較高的基于組織的自尊水平;相反,如果組織支持感較弱,教師基于組織的自尊會更多受到教學效能感強弱的影響。
4.2.3 中小學教師組織支持感在教學效能感與職業幸福感間的調節作用
研究結果表明,組織支持感在教師教學效能感與教師職業幸福感間的調節作用不顯著,這一結果與假設H3不符。究其原因,雖然資源保存理論、工作-要求資源模型等為組織支持感在變量間的調節作用提供了較為有力的支撐,但以上理論模型多用于組織管理領域,研究以中小學教師群體為研究對象,效能感對教師職業幸福感的直接效應占總效應的84.78%,這意味著教師教學效能感對職業幸福感的影響作用占有較大的比重。此外,以往研究也表明,教師職業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尤其體現在工作中的效能感上(Bandura,1977;Clegg &Spencer,2010;Tsigilis et al.,2010),綜合而言,不論其組織支持感水平如何,教師職業幸福感都可能較多地受到教師教學效能感的影響。
5 研究意義與展望
5.1 理論價值與實踐價值
首先,對中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感與職業幸福感中間機制進行了探討,有助于明確基于組織的自尊和組織支持感在教師教學效能感與職業幸福感之間的作用,增加了有關教學效能感結果變量的實證性研究,也拓展了教學效能感的研究范圍。
其次,通過量表可以深入了解教師教學效能感的現狀,為之后的研究奠定基礎;通過教師教學效能感和基于組織的自尊對職業幸福感影響作用及組織支持感對基于組織的自尊影響作用的探究,可以從多方面入手提高教師自尊及職業幸福感,為培育良好和諧的教師心態方面提供有效幫助。
5.2 研究局限和未來展望
(1)研究層面的擴展。研究更側重于變量的個體及教師職業層面,如關注教師在學校這一組織中的自尊、支持感與幸福感,這既是局限也是特色所在。未考慮教師一般心理層面問題,如教師教學效能感的不足會對教師一般性自尊和工作場所之外的幸福感產生何種影響,后續的研究可以更多的關注教師職業心理健康狀況是否會泛化到一般生活狀況中,是否會影響到個體情緒狀態等等。此外,還需要進一步考慮一般心理問題的研究結論是否可以完全推論到教師心理層面。
(2)研究機制進一步深入。可以進一步探討教師教學效能感、基于組織的自尊與職業幸福感之間的幾條路徑是否存在其他變量調節,例如個體在學校領導及成員社會關系比較傾向的差異。
(3)樣本和架構的擴展。后續的研究可以擴大教師樣本量以保證研究的代表性,同時可以豐富樣本群體,針對幼兒教師、中小學教師及高校教師的不同特征進行探索。
(4)研究方法的進一步拓展。本研究模型搭建均采用自評型問卷調查的橫斷研究。此方法有一定的便捷性及大規模施測性,但是無法得到確切的因果關系,且不適用于發展的穩定性問題。未來可以采用實驗法、他評法或情景測驗以保證研究數據的代表性,同時,也可以考慮于縱向研究相結合,獲得職業幸福感研究的發展性數據。
6 研究結論
(1)中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感與職業幸福感、基于組織的自尊和組織支持感存在顯著相關。其中,教師教學效能感與職業幸福感存在顯著正相關,組織支持感和基于組織的自尊與職業幸福感存在顯著正相關。
(2)中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感可以顯著正向預測職業幸福感,基于組織的自尊在教師教學效能感與職業幸福感之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組織支持感在教師教學效能感和基于組織的自尊之間起負向調節作用、在基于組織的自尊與職業幸福感之間起到正向調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