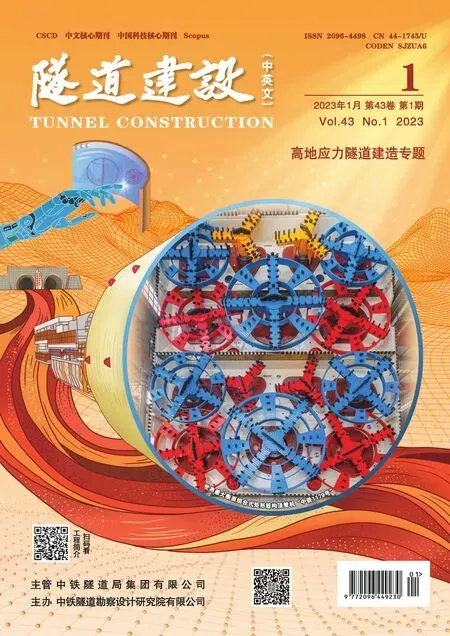深埋TBM隧洞巖性界面區圍巖破壞特征與支護技術研究
姚志賓, 熊永潤, 付廉杰, 全永威, 牛文靜, 胡 磊, *
(1. 東北大學 深部金屬礦山安全開采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遼寧 沈陽 110819; 2. 東北大學 遼寧省深部工程與智能技術重點實驗室, 遼寧 沈陽 110819; 3. 新疆額爾齊斯河流域開發工程建設管理局, 新疆 烏魯木齊 830000)
0 引言
在“向地球深部進軍”戰略的實施下,我國加快了隧洞工程建設的步伐。隨著隧洞工程的不斷發展,埋深大、長度大、修建難度大是目前及今后較長時期隧道及地下工程建設普遍面臨的問題,有眾多的新難題和科技創新需求需要攻克和解決[1-2]。特別是深部硬巖開挖時,除常見的結構型塌方災害外,受較高的原巖地應力影響,在開挖過程中或隨后一段時間內,可能出現巖爆、應力-結構型塌方等高地應力災害,嚴重威脅施工人員及設備安全[3]。
巖爆是在開挖或其他外界擾動下,巖體中聚積的彈性變形勢能突然釋放,導致圍巖爆裂、彈射的動力災害現象。在深部巖體工程開挖過程中,巖爆常常威脅施工人員和設備的安全,導致施工進度延誤,造成較大的經濟損失[4-5]。巖爆的孕育過程及發生受地應力、開挖、支護方式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在隧洞工程建設過程中,出現過眾多類型的巖爆,其破壞等級各異、特征多樣、機制復雜[6]。
此外,應力-結構型塌方和結構型塌方的發生也使得隧洞圍巖破壞類型更加復雜,對現場施工、支護設計等提出了更嚴峻的挑戰。在深埋TBM隧洞中,將具有良好自支撐能力的圍巖在應力和結構面等共同作用下發生的坍塌破壞定義為應力-結構型塌方[7]; 將圍巖自支撐能力差,在結構面和自重作用下發生的坍塌定義為結構型塌方。應力-結構型塌方區域有顯著的諸如平行臨空面的片狀、薄板狀等高應力破壞特征。由于深埋TBM隧洞災害的復雜性,已有許多學者對不同類型災害的發生機制、預警及防控等進行了室內試驗、數值模擬及現場監測研究,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8-14]。
隨著隧洞巖體工程所處地質和應力環境日漸復雜,地質條件對隧洞圍巖的破壞也有著重要影響。Li等[15]基于現場巖爆調查、微震監測,對深埋TBM隧洞軟硬交互地層區域巖爆孕育規律及機制進行了研究,研究表明隧洞開挖過程中自硬巖至軟巖方向圍巖中巖爆頻率、強度大于軟巖自硬巖方向,開挖順序、地質情況密切影響著隧洞圍巖巖爆情況。李桐等[16]基于微震監測系統研究了某深埋隧洞開挖過程中巖爆位置偏轉現象、巖體破裂演化規律及巖爆位置偏轉機制,認為圍巖中結構面的存在對巖爆位置偏轉有一定的影響,巖爆位置偏轉與局部應力集中密切相關。
地質條件復雜的區域,圍巖破壞類型、破壞機制等更加復雜。周輝等[17]基于層狀復合巖石開展三軸壓縮試驗,研究圍巖對復合地層巖體變形破壞的影響,研究表明應力作用下層狀復合巖石層理間易產生膨脹,且不同層理巖體間變形不協調,在層間黏結力作用下,層狀巖體發生相對錯動現象。王曉雷等[18]針對不同層理傾角片麻巖開展單軸壓縮試驗,研究了不同層理傾角片麻巖力學性質及應變場演化特征,表明片麻巖破壞模式隨著層理傾角的增加逐漸由張拉剪切混合破壞向沿層理面的剪切滑移破壞轉化。Yang等[19]利用有限元方法研究了復合地層中深埋隧洞的收斂變形和破壞特征,研究結果表明,軟巖在水平方向發生拉伸破壞,頂部和底部軟巖區出現剪切破壞,隧洞圍巖的破壞規律同時受應力和巖性的控制。Feng等[20]借助數值模擬方法分析了隧洞軟硬巖接觸帶區域開挖前后的應力應變變化規律,結果表明巖性界面區開挖后應力向硬巖區轉移和集中,軟巖區雖有更大的塑性變形范圍,但其應力釋放程度低于硬巖區,因而軟巖側以擠壓性的大變形破壞為主。Yang等[21]對嘉園隧洞工程中4種軟硬地層的接觸條件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接觸帶下方的支護結構承受的圍巖壓力比一般地層大。
上述研究均表明,不同地質條件下圍巖破壞特征差異明顯,相較于地質良好的情況下,開挖區域圍巖中存在巖性分界導致該區域的破壞呈現頻次高、規模大和機制復雜的特征; 另外,巖性界面區域破壞預警難度相對較大,且往往需加強支護強度,工程難度顯著增加。但無論是巖性界面區圍巖破壞特征還是系統性的支護技術,目前研究均不成熟,仍需深入研究。
鑒于此,本文以深埋TBM隧洞巖性界面區域圍巖為研究對象,綜合應用災害現場調查、微震監測、支護體受力監測等手段開展巖性界面區域圍巖破壞與支護體受力特征研究,以期研究結果為隧洞安全高效開挖及支護提供參考。
1 工程背景
1.1 工程概況
某深埋隧洞埋深約700 m,洞徑7.8 m,采用敞開式TBM開挖。隧洞巖性為華力西晚期侵入變質黑云母花崗巖及奧陶系黑云母石英片巖等,局部區域發育有蝕變帶、片理及片麻理等地質結構。隧洞巖性屬于堅硬巖,巖石強度超過120 MPa。通過水壓致裂法對該隧洞開展了地應力測量,得到最大埋深處的水平應力分量分別為21.6 MPa和15.0 MPa。其中,平均最大水平主應力方向為N45°E,與隧洞軸線呈70°~80°的夾角。勘察設計階段利用強度應力比法評估出該隧洞K22+200~K34+655段存在中等巖爆風險。
隧洞施工階段在K22+200~K34+655段遭遇了較突出的巖爆、應力-結構型塌方和結構型塌方等災害,造成設備和支護系統損壞(如圖1所示),常需采用鋼筋排和鋼拱架加固圍巖,不僅增加工程支護量,還嚴重制約施工進度。為此,對該隧洞開挖過程中的災害進行微震監測與預警。

(a) 巖爆破壞錨網支護(爆坑深度0.8 m)

(b) 巖性界面區發生的巖爆導致鋼拱架變形圖1 隧洞典型巖爆災害導致的支護系統損壞Fig. 1 Typical rockburst disaster and support characteristics of tunnel
1.2 微震監測布置
選用中科微震的SSS微震監測設備,在隧洞掌子面后方布置2組監測斷面,共8個傳感器,監測開挖過程中的巖體破裂微震活動。每組監測斷面布置4個傳感器,第1組布置在護盾后5 m范圍內,編號G1—G4; 第2組布置在護盾后約20 m位置處,編號G5—G8。2組傳感器在空間上呈交錯布置。微震監測系統布置示意如圖2所示。在微震傳感器的選型方面,速度型傳感器和加速度型傳感器的靈敏度均能滿足開展隧道巖爆微震監測的要求。但對于TBM隧洞工程,掘進速度快、工序銜接程度高、施工環境嘈雜,綜合考慮傳感器快速隨鉆移動、頻繁拆裝過程中的使用壽命,速度型傳感器更具優勢,更適合工期較長的隧洞微震監測[22-23],且速度型傳感器已在多個深埋隧道工程的巖爆監測預警中得到成功應用,如巴基斯坦N-J引水隧洞工程[15]。因此,本工程選擇了速度型傳感器對該隧洞開挖過程中的巖爆進行微震監測。微震監測信息采集設備布置在主控室附近,通過光纖與洞外建立通訊,實現設備的遠程監控和數據的實時傳輸。為有效監測開挖區域的破裂信號,微震傳感器隨掌子面的推進而動態移動。當掌子面向前推進15~20 m時,在護盾后方5 m范圍內布置新的監測斷面,并回收第2組傳感器將其重新布置在該斷面。

圖2 微震監測系統布置示意圖(單位: m)Fig. 2 Layout of microseismic monitoring system (unit: m)
2 巖性界面區圍巖破壞特征
2.1 巖體結構特征
通過空間展布圖可以很直觀地對研究區域的地質條件、破壞情況等進行描述。在TBM隧洞中,通常參考時鐘的刻度將隧洞斷面劃分為12個方位(如圖3所示),并將其作為空間展布圖的縱坐標,橫坐標為隧洞樁號。因此,隧洞洞壁上的某個確定的點與空間展布圖橫、縱坐標唯一對應。將結構面或巖性界面跡線、出水點、爆坑邊界輪廓等在空間展布圖上進行繪制,即可得到相應地質展布圖或破壞展布圖。

圖3 隧洞斷面方位劃分示意圖(面向掌子面)Fig. 3 Schematic of tunnel cross-section orientation division (facing working face)
K36+060~+010段巖性界面區的地質及破壞展布圖如圖4所示。其中,K36+040~+010段結構面較發育,主要賦存3組陡傾結構面,產狀分別為100°~130°∠70°、270°~290°∠60°、10°~20°∠60°。此外,該洞段局部發育有寬度較小的暗色礦物條帶。

圖4 K36+060~+010段巖性界面區的地質及破壞展布圖Fig. 4 Geological profile and disaster distribution of lithologic interface area of section K36+060~+010
隧洞開挖至K36+040附近時,在拱頂9:00~3:00方位揭露1條延伸較長的蝕變帶,寬約1.5 m,傾角70°,走向320°~330°。蝕變帶兩側的巖性有明顯差異,形成了典型的巖性界面。蝕變帶南側區域為灰白色變質黑云母花崗巖,北側區域為黑云母富集的灰黑色變質黑云母花崗巖,如圖5所示。

(a) 灰白色變質黑云母花崗巖(南側)

(b) 灰黑色變質黑云母花崗巖(北側)圖5 隧洞南北兩側巖性Fig. 5 Different lithologies on south and north sides of tunnel
2.2 巖性特征
在K36+060~+010段左右兩側分別選取巖樣,利用X射線衍射試驗測定2種巖樣的礦物成分與含量。2種巖樣主要礦物成分均為石英、斜長石和黑云母。其中,灰白色變質黑云母花崗巖試樣中黑云母質量分數僅為2%,而灰黑色變質黑云母花崗巖試樣礦物成分中的黑云母質量分數高達70%。
基于單軸壓縮試驗,分別獲取灰白色、灰黑色變質黑云母花崗巖的力學參數。灰白色變質黑云母花崗巖單軸抗壓強度為168 MPa,彈性模量為75 GPa; 灰黑色變質黑云母花崗巖單軸抗壓強度為92 MPa,彈性模量為43 GPa。通過對比發現,灰白色變質黑云母花崗巖的單軸抗壓強度、彈性模量等力學參數顯著高于灰黑色變質黑云母花崗巖,即隧洞南側的巖性較硬,北側相對南側較軟,在同一斷面隧洞巖性呈南硬北軟的特征。
2.3 圍巖破壞特征
K36+060~+010段巖性界面區開挖過程中主要發生了巖爆、塌方等災害,其中,塌方災害包括應力-結構型塌方和結構型塌方。K36+060~+010段巖性界面區3種典型圍巖破壞如圖6所示。高應力環境下隧洞同一斷面位置南硬北軟的巖性特征,導致隧洞開挖過程中的圍巖破壞類型及其沿巖性界面的空間分布呈現出不同特征。
2.3.1 圍巖破壞類型
巖性界面區域開挖過程中巖爆和結構型塌方災害頻發,且同一個斷面既有巖爆又有結構型塌方災害。圖6(a)示出K36+039~+037段9:00~0:00方位發生的巖爆,爆坑長約2 m、寬約3 m、深約0.48 m,破壞巖石呈片狀、板狀,爆坑內壁光滑、新鮮。根據《水利水電工程地質勘察規范》[24]中的規定“中等巖爆爆坑深度為0.3~1.0 m”,判定該次巖爆為中等巖爆。圖6(b)示出K36+039~+037段0:00~2:00方位發生的結構型塌方破壞,塌腔附近巖體破碎,以暗色礦物為破壞邊界,塌腔最大深度約為0.82 m。

(a) K36+039~+037段中等巖爆

(b) K36+039~+037段結構型塌方

(c) K36+057~+055段應力-結構型塌方圖6 K36+060~+010段開挖過程中巖性界面區3種典型圍巖破壞Fig. 6 Typical damage during excavation of section K36+060~+010
2.3.2 圍巖破壞空間分布
由圖4可知,巖性界面區域的災害類型以蝕變帶為界在硬、軟兩側呈區域性分布特征。其中,巖爆均發生在隧洞南側硬巖區域的完整部位; 應力-結構型塌方災害發生在南側硬巖區域結構面較發育且交匯的位置,結構面走向常與應力方向呈小角度相交。圖6(c)為硬巖側(灰白色變質黑云母花崗)區域0:00~1:00方位發生的應力-結構型塌方。該區域圍巖較完整,發育1組產狀265°∠85°的結構面。結構型塌方均發生在北側的軟巖側區域,且區域內多發育2~3組結構面,以暗色礦物邊界為結構型塌方的邊界。
分析巖性界面南北兩側的災害特征可知: 南側硬巖區域發生的破壞數量較多,且巖爆等級以中等為主,局部發生1次強烈巖爆(如圖7所示),深度為1.1 m,對圍巖的破壞程度大; 北側軟巖區域發生的破壞數量相對較少,且主要為沿著不利結構面發生的結構型塌方,塌腔深度受結構面和暗色礦物分布特征控制。

圖7 K36+031附近區域發生的強烈巖爆Fig. 7 Strong rockburst occurred in section K36+031 section
3 巖性界面區開挖過程中的微震時空演化特征及圍巖破壞機制
3.1 微震時空演化特征
為研究巖性界面區不同類型破壞的形成機制,分析開挖過程中圍巖破壞的微震響應特征及規律。選取K36+041~+035段作為同一斷面巖爆和塌方伴隨發生的典型區段,對該區域開挖過程中的微震監測結果進行分析,結果如圖8所示。

(a) 2021-02-13—2021-02-14

(b) 2021-02-14—2021-02-15

(c) 2021-02-15—2021-02-16E代表能量; 顏色由藍轉向紅表示能量升高。圖8 K36+041~+035段開挖過程中微震時空分布及參數特征Fig. 8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parameter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seisms during excavation of section K36+041~+035
由圖8可知,K36+041~+035段開挖期間微震事件聚集區主要分布在隧洞南側,隧洞南側硬巖區域的微震事件數、微震釋放能顯著大于隧洞北側的軟巖區域。例如: 2021-02-14—2021-02-15共掘進5 m,隧洞南側區域累計微震事件數為31個,微震釋放能為181 970 J; 隧洞北側區域累計微震事件數為9個,微震釋放能為372 J。
K36+080~+000段開挖過程中微震事件云圖如圖9所示。由圖9可知: 1)K36+080~+000段開挖過程中微震事件的分布呈區域性特征,沿隧洞斷面方向巖爆、結構型塌方破壞與微震活動具有良好的空間相關性。2)隧洞南側主要發生巖爆和應力-結構型塌方災害,而隧洞北側主要發生結構型塌方災害。除此之外,沿隧洞軸線方向不同類型破壞區域微震活動性也存在顯著差異。該區域開挖過程中K36+080~+050段圍巖微震活動性相對較弱,僅發生較少次數的應力-結構型塌方和結構型塌方; K36+050~+030段開挖過程中圍巖微震活動性強,對應區域發生多次中等巖爆和強烈巖爆。由此可見: 巖爆區域能量釋放程度高于應力-結構型塌方區域,結構型塌方破壞區域能量釋放最少。

顏色由藍轉向紅表示微震事件數升高。圖9 K36+080~+000段開挖過程中微震事件云圖Fig. 9 Characteristics of damage and microseismic activity during excavation of section K36+080~+000
3.2 圍巖破壞機制
馮夏庭等[25]的研究表明,巖爆發生前,巖體內部小破裂事件形成的裂紋貫通,通常會產生能量高的大破裂事件。譚雙等[13]的研究結果表明,微震視體積突增是深埋隧洞塌方發生的前兆信號。基于此,結合隧洞南北兩側圍巖的情況可知,大能量破裂事件(簡稱大能量事件,本文中指微震釋放能大于1 000 J的破裂事件)與南側巖爆活動有較好的相關性,隧洞北側微震視體積最大的破裂事件與塌方活動有較好的相關性。將上述事件作為關鍵事件進行分析,其發生時間、微震釋放能、微震視體積等主要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開挖過程中的關鍵微震事件信息Table 1 Key microseismic event information during excavation
結合圖8和表1對微震事件發生的先后順序、部位等信息進行分析,結果表明: 1)絕大部分大能量事件發生于TBM掘進期間,主要位于掌子面附近,少部分大能量事件發生于TBM檢修期間,如事件⑦發生于掌子面后8 m的已揭露區域。2)大能量事件發生部位均位于隧洞南側,隧洞北側區域無大能量事件發生。此外,對事件①等大能量事件與事件②等微震視體積大的破裂事件發生的先后順序進行分析。結果表明,隧洞南側大能量事件發生時間較隧洞北側微震視體積大的破裂事件早。由此可知,深埋TBM隧洞順隧洞軸向巖性界面區域開挖過程中,巖爆活動早于塌方活動發生。
以上對巖性界面區微震活動特征及規律的分析結果表明,受南硬北軟的巖性特征影響,在硬巖側產生了更大的應力集中,對應該側圍巖發生了更多的巖體破裂。當圍巖較完整時,能夠聚集更多的能量,能量的突然釋放導致圍巖產生大量的破裂且伴隨大能量事件產生,可誘發較高等級的巖爆,因而圍巖呈片狀、板狀、塊狀的高應力破壞特征,而當爆坑揭露后,未充分釋放的能量仍有可能進一步釋放,進而加劇圍巖破壞程度; 當圍巖發育有一定數量和規模的結構面時,圍巖內部聚集有一定的能量,在能量釋放過程中導致巖體產生破裂,且與部分不利結構面交錯切割發生規模較大的應力-結構型塌方破壞,因而在塌腔內部有結構面揭露,但在塌腔邊緣有顯著的片狀、板狀等高應力張拉破壞特征。北側軟巖區域的微震活動性相對較弱,表明該側圍巖產生的破裂事件較少,主要沿較軟弱的暗色礦物或交匯的不利結構面發生結構型失穩破壞,因而其破壞邊界受暗色礦物控制。
在更大的應力集中下,隧洞硬巖側大能量事件隨著掌子面的推進不斷產生,呈現“邊挖邊爆”的特征,而結構型塌方的發生時間受地質及施工條件的控制,通常滯后于掌子面的開挖。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受南硬北軟的巖性特征影響,在巖性界面區域圍巖能量釋放程度和破裂呈現不同的特征。隧洞開挖后,硬巖側應力集中程度較高,對應的破壞數量較多且較易產生以高應力巖爆、應力-結構型塌方為主的局部破壞; 軟巖側應力集中程度較低,高應力破壞特征不顯著,產生的破壞主要受暗色礦物、交匯的結構面等不利地質結構影響,發生結構型塌方破壞。因而,隧洞開挖過程中發生的災害呈現為同一斷面既有巖爆又有塌方,對圍巖支護措施選取有較大的影響。
4 巖性界面區支護體受力特征
4.1 空間分布特征
巖性界面區域開挖過程中同一斷面既有巖爆又有結構型塌方發生,圍巖支護的選取常較難決策。為保證安全采用了“錨桿+鋼拱架+鋼筋排”的高強度聯合支護體系。但高強度支護不僅增加施工成本,且嚴重影響施工進度。為此,在微震監測的基礎上對巖性界面區不同災害類型下的支護體受力特征進行監測,并利用拱架應變計分別分析了巖爆區域、結構型塌方區域和既有巖爆又有結構型塌方區域的拱架受力特征。
不同災害類型下的鋼拱架受力情況如圖10所示。僅發生巖爆的區域圍巖巖性主要為灰白色變質黑云母花崗巖,圍巖堅硬且完整性較好,在10:30~0:00方位形成了1個深約0.58 m的爆坑,采用間距1.8 m的HW125型鋼拱架支護; 僅發生結構型塌方的區域圍巖巖性主要為灰黑色變質黑云母花崗巖,強度較低且完整性較差,在0:00~3:30方位形成了1個深約1.4 m的塌腔,采用間距0.9 m的 HW150型鋼拱架支護; 巖爆和結構型塌方伴隨發生的區域圍巖巖性主要為變質黑云母花崗巖,局部發育蝕變礦物和多條軟弱結構面,同一斷面不同位置分別形成了深約0.7 m的塌腔和0.4 m的爆坑,采用間距0.9 m的HW125型鋼拱架支護。

(a) 僅發生巖爆的區域

(b) 僅發生結構型塌方的區域

(c) 巖爆和結構型塌方伴隨發生的區域“-”表示測點受壓,“+”表示測點受拉。圖10 不同災害類型下的鋼拱架受力情況Fig. 10 Stress of steel arch frame in different disasters
由圖10可知: 僅發生巖爆的區域鋼拱架間距較大,但整體受力較小,爆坑中心測點受壓值為68.4 MPa; 僅發生結構型塌方的區域鋼拱架強度較大,但整體受力較大,且塌腔中心測點受力最大,達到393.88 MPa; 巖爆和結構型塌方伴隨發生的區域爆坑中心與塌腔中心受力均較大,分別為270.77 MPa和165.27 MPa。通過對比可知: 僅發生巖爆的區域爆坑外圍巖完整性較好,拱架整體受力并不大; 僅發生結構型塌方的區域圍巖自穩能力差,鋼拱架受力大,尤其是當塌腔深度超過1.0 m時,可能導致鋼拱架變形; 巖爆和結構型塌方伴隨發生時,會導致該區域鋼拱架整體受力較大。僅發生巖爆的區域受力較小,主要由于巖爆是較完整巖體局部破裂化形成的災害,雖然局部位置產生了破壞,但整體仍具有一定的自穩性,因而工程中也常對巖爆區域采取非對稱支護。
4.2 時間演化特征
采用鋼拱架受力與最終受力的比值可對鋼拱架受力的收斂趨勢進行定量化分析。當鋼拱架受力與最終受力的比值超過95%時,則視為該鋼拱架受力已趨于穩定。不同類型災害區域鋼拱架受力與最終受力的比值隨開挖天數的變化曲線如圖11所示。由圖11可知: 開挖30 d時,僅發生結構型塌方的區域鋼拱架受力已超過了最終值的95%,巖爆和結構型塌方伴隨發生的區域鋼拱架受力約為最終值的88%,而僅發生巖爆的區域鋼拱架受力為最終值的86%。此外,僅發生結構型塌方的區域鋼拱架受力穩定時間約為28 d,巖爆和結構型塌方伴隨發生的區域鋼拱架受力穩定時間約為43 d,而僅發生巖爆的區域鋼拱架受力穩定時間約為60 d。

圖11 不同類型災害區域鋼拱架受力與最終受力的比值隨開挖天數的變化曲線Fig. 11 Stress stability time of steel arch in different disasters
由此可見,僅發生結構型塌方的區域雖然鋼拱架整體受力較大,但是其受力穩定時間較短,這表明在結構型塌方發生后圍巖內部沒有明顯的能量釋放和巖體破裂,按照相應結構型塌方段支護的設計要求支護即可加固圍巖。然而,僅發生巖爆的區域及巖爆和結構型塌方伴隨發生的區域在開挖后較長一段時間內支護體受力仍未達到收斂,表明圍巖內部仍有能量釋放和巖體破裂,因而其支護除需按照要求設計外,還需在硬巖側的應力集中區域進行應力釋放。
5 巖性界面區圍巖支護及防控技術
5.1 破壞風險評估
災害的識別和評估是進行災害控制的首要步驟。對于深埋TBM隧洞,巖性交界面往往處于壓密狀態,同時由于TBM刀盤的阻隔難以直接觀測到掌子面的地質信息,巖性交界面的識別難度增加。可采用多種手段綜合識別巖性交界面,例如: 通過觀察巖渣判斷是否存在不同巖性; 通過TBM參數變化判斷巖體性質的變化程度; 通過超前地質預報中反射面的形態和位置判斷交界面的產狀和出露位置; 通過微震監測結果中微震事件的空間分布,特別是掌子面前面微震事件的空間分布規律,判斷巖體結構的特征。識別出巖性交界面后,進一步分析微震事件的能量、數量和空間分布特征等信息,并結合巖性界面的空間位置、性質等信息,綜合判斷掌子面前方巖爆及塌方的風險。
5.2 圍巖適應性支護及防控技術
基于對巖性界面區域的圍巖破壞特征、微震響應規律、識別方法、破壞風險判斷和支護體受力特征的分析,結合巖爆防控“三步走”的總體思想[26],可對該隧洞開挖過程中的圍巖支護措施進行優化。
當巖爆等級較低時,巖爆破壞性小,以結構型塌方為主體進行支護即可。隨著巖爆等級升高,支護及防控的主體逐漸過渡為巖爆。當巖爆等級為中等時,除采取與塌方破壞規模對應的支護措施外,還需施作應力釋放孔以釋放圍巖內部積蓄的能量; 當巖爆等級為強烈及極強巖爆時,圍巖應力集中程度高、巖爆破壞范圍大,需以巖爆為主體,采用“減能—釋能—吸能”的防控體系,控制并降低巖爆等級。綜上所述,巖性界面區不同災害類型的支護及防控技術如表2所示。

表2 巖性界面區不同災害類型的支護及防控技術Table 2 Support methods of different disaster types in lithologic interface area
6 結論與討論
本文以深埋TBM隧洞順軸向巖性界面區圍巖為研究對象,結合微震監測、支護體受力監測等手段,對某具有南硬北軟巖性特征的隧洞圍巖破壞與支護體受力特征進行了研究,并對不同類型破壞提出了支護措施優化建議,得到以下結論:
1)受南硬北軟巖性特征的影響,該隧洞巖性界面區域開挖過程中同一斷面巖爆與結構型塌方伴隨發生,硬、軟兩側的災害類型呈區域性分布,且硬巖側破壞數量及破壞程度均高于軟巖側。
2)巖爆、結構型塌方破壞與微震活動具有良好的空間相關性。巖性界面區域圍巖應力集中程度和破壞呈現不同的特征。
3)僅發生結構型塌方的區域鋼拱架整體受力較大,受力穩定時間較短,依據塌腔深度采取相應的支護措施即可加固圍巖; 僅發生中等巖爆的區域及中等巖爆與結構型塌方伴隨發生的區域,鋼拱架受力穩定時間較長,除需按照設計要求進行支護外,還需在硬巖的應力集中區域進行應力釋放。
4)當巖爆等級較低時,以結構型塌方為主體進行支護。隨著巖爆等級升高,支護及防控的主體逐漸過渡為巖爆。
本文依托某TBM隧洞工程,針對巖性界面與隧洞軸線呈小夾角時的圍巖破壞特征及支護技術進行了研究,但巖性界面與隧洞軸線呈不同夾角時圍巖的破壞特征及支護技術尚待研究。此外,巖性界面區的識別技術和風險預測方法尚不完善,亦待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 洪開榮. 我國隧道及地下工程發展現狀與展望[J]. 隧道建設, 2015, 35(2): 95.
HONG Kairong. State-of-art and prospect of tunnels and underground works development in China[J]. Tunnel Construction, 2015, 35(2): 95.
[2] 錢七虎. 依托中國的獨特優勢,加速邁向科技強國的偉大目標[J]. 科技導報, 2020, 38(10): 1.
QIAN Qihu. Relying on China′s unique advantages, accelerate the great goal of becoming a powerful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J]. Science & Technology Review, 2020, 38(10): 1.
[3] 李永亮, 喬志斌, 牛文靜, 等. 微震監測技術在某深埋鐵路隧道施工管理中的應用[J]. 隧道建設(中英文), 2019, 39(11): 1881.
LI Yongliang, QIAO Zhibin, NIU Wenjing, et al. Application of microseismic monitoring technology to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a deep buried railway tunnel[J]. Tunnel Construction, 2019, 39(11): 1881.
[4] 馮夏庭, 陳炳瑞, 張傳慶, 等. 巖爆孕育過程的機制、預警與動態調控[M].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13.
FENG Xiating, CHEN Bingrui, ZHANG Chuanqing, et al. Mechanism, early warning and dynamic regulation of rockburst incubation process[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3.
[5] FENG X T. Rockburst: mechanisms, monitoring, warning, and mitigation[M]. Holland: Elsevier-Health Sciences Division, 2017.
[6] 馮夏庭,肖亞勛,豐光亮. 巖爆孕育過程研究[J]. 巖石力學與工程學報, 2019, 38(4): 649.
FENG Xiating, XIAO Yaxun, FEGN Guangliang. Study on incubation process of rockbursts[J].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2019, 38(4): 649.
[7] XIAO Y X, FEGN X T, FENG G L, et al. Mechanism of evolution of stress-structure controlled collapse of surrounding rock in caverns: a case study from the Baihetan hydropower station in China[J]. Tunnelling and Underground Space Technology, 2016, 51: 56.
[8] 趙周能, 馮夏庭, 肖亞勛, 等. 不同開挖方式下深埋隧道微震特性與巖爆風險分析[J]. 巖土工程學報, 2016, 38(5): 867.
ZHAO Zhouneng, FENG Xiating, XIAO Yaxun, et al. Microseismic characteristics and rockburst risk analysis of deep buried tunnel under different excavation methods[J]. Chinese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2016, 38(5): 867.
[9] FENG G L, FEGN X T, CHEN B R, et al. A microseismic method for dynamic warning of rockburst development processes in tunnels[J]. Rock Mechanics and Rock Engineering, 2015, 48(5): 1.
[10] ZHOU J, LI X B, MITRI H S. Evaluation method of rockburst: State-of-the-art literature review[J]. Tunnelling and Underground Space Technology, 2018, 81: 632.
[11] FEGN X T, YOUNG R P, REYES-MONTES J M, et al. ISRM suggested method for in situ acoustic emission monitoring of the fracturing process in rock masses[J]. Rock Mechanics & Rock Engineering, 2019, 52(5): 1395.
[12] 劉乃飛, 李寧, 李國鋒, 等. 庫尉輸水隧洞塌方機制分析及加固效果評價[J]. 巖石力學與工程學報, 2015, 34(12): 2531.
LIU Naifei, LI Ning, LI Guofeng, et al. Analysis of the collapse mechanism of the Kuyu water conveyance tunnel and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its ground reinforcements[J].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2015, 34(12): 2531.
[13] 譚雙, 李邵軍, 王雪亮, 等. 深埋引水隧洞塌方孕育過程微震規律研究: 以Neelum-Jhelum工程為例[J]. 巖石力學與工程學報, 2018, 37(增刊2): 4115.
TAN Shuang, LI Shaojun, WANG Xueliang, et al. Study on microseismic law during landslide preparation of deep diversion tunnel: Taking Neelum-Jhelum project as an example [J].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2018, 37(S2): 4115.
[14] FENG G L, FENG X T, ZHAO Z N, et al. Analysis of a collapse in deep tunnel based on microseismic monitoring[J]. Applied Mechanics & Materials, 2012, 256/257/258/259: 1181.
[15] LI P X, FENG X T, FENG G L. Rockburst and microseismic characteristics around lithological interfaces under different excavation directions in deep tunnels[J]. Engineering Geology, 2019, 260: 105209.
[16] 李桐, 馮夏庭, 王睿, 等. 深埋隧道巖爆位置偏轉及其微震活動特征[J]. 巖土力學, 2019, 40(7): 2847.
LI Tong, FENG Xiating, WANG Rui, et al. Rockburst position deflection and microseismic activity characteristics of deep buried tunnel[J]. Rock and Soil Mechanics, 2019, 40(7): 2847.
[17] 周輝, 宋明, 張傳慶, 等. 水平層狀復合巖體變形破壞特征的圍壓效應研究[J]. 巖土力學, 2019, 40(2): 465.
ZHOU Hui, SONG Ming, ZHANG Chuanqing, et al. Study on confining pressure effect of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characteristics of horizontal layered composite rock mass[J]. Rock and Soil Mechanics, 2019, 40(2): 465.
[18] 王曉雷, 蔣鵬程, 閆順璽, 等. 層狀片麻巖力學性質與變形場演化特征研究[J]. 采礦與安全工程學報, 2020, 37(6): 1255.
WANG Xiaolei, JIANG Pengcheng, YAN Shunxi, et al. Study 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deformation field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ayered gneiss[J]. Journal of Mining & Safety Engineering, 2020, 37(6): 1255.
[19] YANG S Q, TAO Y, XU P, et al. Large-scale model experiment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convergence deformation of tunnel excavating in composite strata[J]. Tunnelling and Underground Space Technology, 2019, 94: 103133.
[20] FENG W K, HUANG R Q, LI T B. Deformation analysis of a soft-hard rock contact zone surrounding a tunnel[J]. Tunnelling and Underground Space Technology, 2012, 32: 190.
[21] YANG W B, JIANG Y J, GU X X, et al. Deformation mechanism and mechanical behavior of tunnel within contact zone: a case study[J]. Bulletin of Engineering Ge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21, 80: 5657.
[22] XIAO Y X, FEGN X T, CHRN B R, et al. Excavation-induced microseismicity in the columnar jointed basalt of an underground hydropower st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 Mining Sciences, 2017, 97: 99.
[23] HU L, FENG X T, XIAO Y X, et 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croseismicity resulting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a deeply-buried shaft[J]. Tunnelling and Underground Space Technology, 2019, 85: 114.
[24] 水利水電工程地質勘察規范: GB 50487—2008[S]. 北京: 中國計劃出版社, 2009.
Code for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GB 50487-2008[S]. Beijing: China Planning Press, 2009.
[25] 馮夏庭, 陳炳瑞, 明華軍, 等. 深埋隧洞巖爆孕育規律與機制: 即時型巖爆[J]. 巖石力學與工程學報, 2012, 31(3): 433.
FENG Xiating, CHEN Bingrui, MING Huajun, et al. The law and mechanism of rockburst preparation in deep buried tunnels: Instant rockburst[J].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2012, 31(3): 433.
[26] 馮夏庭, 張傳慶, 陳炳瑞, 等. 巖爆孕育過程的動態調控[J]. 巖石力學與工程學報, 2012, 31(10): 1983.
FENG Xiating, ZHANG Chuanqing, CHEN Bingrui, et al. Dynamic control of rockburst incubation process[J].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2012, 31(10):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