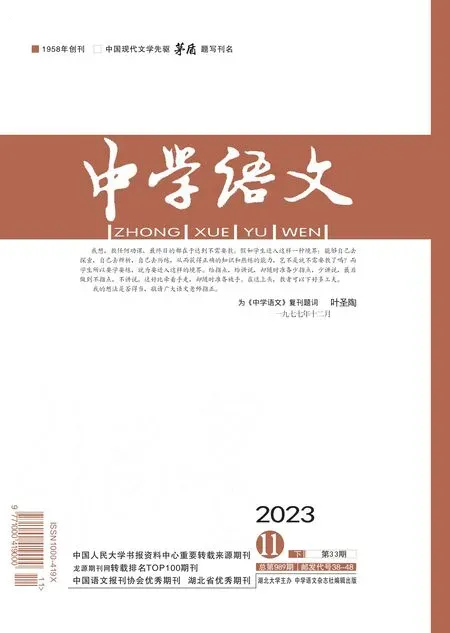雙重視角解讀《送東陽馬生序》
包 群 胡鐵強
明代文學家宋濂的贈序《送東陽馬生序》是帶有回憶性的散文。回憶性散文有一個顯著特征,即寫作中按雙重敘述視角進行敘事:一個是回憶往事正在發生時的“過去”的“我”的視角,即經驗自我視角敘事;一個是回顧往事時的“現在”的“我”的視角,即敘述自我視角敘事。前者表現“過去”的“我”正經歷這件事時的體驗和感受,后者表現“現在”的“我”回顧往事時的體驗和感受。解讀出回憶性散文中兩個不同的“我”的形象,很有必要且有價值。
一、經驗自我視角中的艱苦求學之路
據記載,宋濂家境貧寒,自幼多病,但他聰敏好學,號稱“神童”。《送東陽馬生序》開篇即寫幼年艱苦求學經歷——“余幼時即嗜學”,第一人稱“余”表明這一段回憶屬于敘述主人公的經驗視角,這一視角將學生直接引入“余”正在經歷事件的內心世界。它具有直觀生動性,極易激發學生的同理心,讓學生直接進入人物的內心世界。宋濂幼時因家貧“借書”,正是年少時的借書“抄書”經歷,才使得他博覽群書,增長見聞。讀書借書之難并沒有讓他望而止步,怨天尤人,相反他非常重視這段求學經歷。這段經歷也是有很多困難的。首先是身邊無名師指教,要跑到百公里外的的地方,向當地的大學問家請教問題。其次求學路程是非常遠的,客觀物質條件也不好,只能徒步而行,“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加上當時還有惡劣的天氣,“大雪深數尺”,遠行數里才到達客棧。再次就是面對德高望重的名師的艱難處境,當他請教問題時要俯下身子側著耳朵恭請老師的指導,這是一種非常謙卑的姿態。而當遇到老師斥責時,宋濂也不敢發一言,靠著自己的恭敬小心把老師的怒火耗盡。在今天看來這種方式有點過于小心,但古代儒家知識分子講究“天地君親師”,宋濂的謙卑姿態正是儒家尊師重道的體現。
接下來是宋濂自謙的一段話,現在面對的太學生生活優渥,教育資源豐富,跟自己當年相比,那簡直是天壤之別。現在的太學生有了國家圖書館,在理論上他們應當是國家棟梁。否則的話,就是對學習沒有那么上心。這里宋濂強調的是學習的態度,敘述自己的求學經歷即是表明在困苦的條件下自己能夠全身心投入學習,不受外界條件干擾。而今太學生擁有如此優渥的條件,心思更應該用在學習上面。從回憶求學歷程到勸誡太學生,言語中的真誠懇切無不讓人動容,學生從這一經驗視角更能通過人物正在經歷的事件時的眼光來觀察體驗,讀到的是“我”之艱難——借書之難、拜師之難、求學之路艱難,能直接自然地感受到宋濂細致、復雜的內心活動。
二、敘述自我視角中的惶恐謙卑之態
人教版原文只是部分節選,節選了從“余幼時即嗜學”到“蓋余之勤且艱若此”的內容。剩下大約有三百字未被選入課文,統編初中語文則將全文納入新教材。但其實正是這樣平淡無奇的一段話,隱藏著這篇文章的真實目的。而當我們的目光落到這句“承天子之寵光”時,這篇文章另一層隱秘的含義就從歷史的塵埃里浮現出來,那就是——“頌圣”。宋濂身為明代“開國文臣之首”,這個稱號雖然響亮,但背后其實有宋濂的難言之隱。明朝開國以后,朱元璋不僅在政治上建立了君主獨裁的體制,對士大夫也十分嚴酷與猜忌。曾有官員因為上書字數太多被廷杖,還有人因為在上奏的謝表中使用了“作則垂涎”“遙瞻帝扉”這樣的詞語,因為“作則”近似“作賊”,“帝扉”聽起來像是“帝非”,竟被誅殺。宋濂作為文臣之首自然也逃不過這種壓迫。
宋濂采取一種“平行姿態”講述自己的故事,這種敘事的“平行姿態”被認為并非全是宋濂發自內心的。因為在他撰寫《送東陽馬生序》的前一年,朱元璋寫過一篇《黃陵碑文》,朱元璋追述了自己早年的窮苦經歷,認為“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為后世子孫戒”。統編本的《送東陽馬生序》后兩段里,對皇恩浩蕩的感召難以掩飾地從字里行間流露出來。所以即便文采斐然的巨儒,因為這種“頌圣”之語,宋濂入明之后的文章被認為是為了做官“被迫無生氣”。其實這種“江郎才盡”的背后所埋藏的是他更多我們在課本里面所看不到的苦衷。從明朝開國時59 歲,一直到他請辭返鄉時68歲,在這近十年的光陰里,宋濂大部分時間都耗在奉命應酬的文章上,因為被盛贊為“文章之首”,所以不管是朝廷上的還是同鄉里都以得到宋濂的文章為榮,《送東陽馬生序》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他在《故巾山處士林君墓碣銘》中寫道:“嗚呼,予為文所累,幾欲燔毀筆硯!”那些在外人看來光鮮的文字,其實早已經成為了宋濂人生的沉重鐐銬。
洪武朝的幾次大案將功臣幾乎一網打盡,宋濂的孫子宋慎卷入了胡惟庸案,朱元璋想要下旨將宋濂賜死,最后皇太子朱標拼命力保,最終將宋濂貶往四川茂州,途中病死,結束了他平實而又精彩的一生。《送東陽馬生序》這篇文章,剛好也暗含了宋濂一生的起伏變化,從開頭的情深意切到后面的頌圣之語。于是,在這篇文章里,我們讀到的也不僅是一代文豪的求學故事,更是一個曾經血肉鮮活的文學才子在宏大的封建體制中,如何消耗著生命的靈光從高峰走向死亡。
宋濂在回憶完求學時光后總結一句“蓋余之勤且艱若此”,文本敘事又轉換到了敘述自我。他針對少年求學之路作了簡短的評價后,再以謙卑的姿態敘述現今的成就,言語之間透露出他的謹慎,接著又以懇切之語勸誡當今的太學生勤奮學習。通過宋濂的主觀視角,我們能窺見這位年近古稀的老者勤奮、謹慎、敏感的性格,也理解了宋濂始終以積極向上的心態看待自己貧寒的出身與艱苦的求學路,以親身經歷勸諫,能夠使后生理解求學路的不易與良苦用心。
經驗自我中的宋濂專注于求學,即使求學之路異常艱辛,他一直是熱愛的,孤勇的,真摯的,在極端困苦下依然能追尋快樂。在他的晚年自述中,字里行間中仍能讀出他當年的赤子之心。晚年宋濂的心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面對太學生不專注于學的現狀,他是焦急的;面對風云詭譎的政局和變化莫測的皇帝,他內心是沉重的,所寫之語也是以一種謙卑的姿態呈現出來。無論是經驗自我還是敘述自我中的宋濂,他始終一如既往堅守求學的赤誠之心,我們從后兩段文字中能讀出宋濂晚年的處境,讀出他宦海沉浮后的兢兢業業,更能讀出他關心后輩、心系國家前途的拳拳之心。
年近古稀的宋濂送給后輩的贈言,通篇也不會有什么豪言壯語,只是敘述了他自己的求學經歷。宋濂現身說法,以卑微到塵埃中的姿態,勸勉太學生,盼望家國永安的懇切之心當溢于言表。今天讀這篇散文,看到的是他求學的艱難:石硯結冰、手指凍僵、長途求學。他這種認真求學的精神,堅毅不退卻的性格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送東陽馬生序》里,宋濂用深入淺出的話語對后輩講述了自己一生勤學苦讀的經歷,讀來余味無窮,給人以啟迪。先生好學如炳燭之明,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學子的艱苦求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