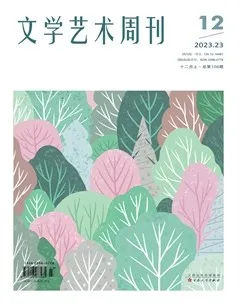哈姆雷特能否算作“健全”的王子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亞于?16?世紀初創?作的一部悲劇作品,講述丹麥王子哈姆雷特為 父復仇的故事。原作的悲劇性在于哈姆雷特所?懷有的美好的人文主義理想與殘酷強大的社會?現實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其悲劇是自身局限?性造成的,也是時代造成的。哈姆雷特堅持人?道主義的精神,想用最正義的手段復仇但優柔?寡斷看不清社會現實,從而低估了對手的強大?而導致了必然的悲劇。其聚焦于哈姆雷特的復?仇引發的悲劇,愛情悲劇是為前者服務。而德?國邵斌納劇院的改編拋棄了時代背景,在混亂?的時代特征中聚焦于哈姆雷特極端的復仇手段?給自己及身邊人帶來的痛苦甚至是毀滅,借災?難性的復仇來彰顯新的主題——突顯社會虛偽?丑惡的嘴臉,讓哈姆雷特逐漸看清面具下的偽?裝并與之斗爭。相較原作的哈姆雷特——那位?多重精神相互糾纏的、極富魅力令無數讀者為 之著迷的王子哈姆雷特,我們不禁問:邵斌納?劇院版哈姆雷特能否算作“健全”的王子?
從物理層面看,是否健全顯然意味著是否身有殘疾,那么答案自然是肯定的,邵斌納劇?院版的哈姆雷特不僅四肢健全甚至有些“營養?過剩”。但在此問中, “健全”指向的是精神?層面,它就變成了一個非常主觀的詞匯,沒有?固定的標準,人們常以是否符合主流作為判斷?它的依據。在此本文先做出否定的假設,并從?以下三方面進行論證。
一、向“不健全”的轉變
經典改編最重要的問題不僅在于如何改動?情節以適應不同主題,還在于如何展現情節以?達到符合主題的目的又不落入經典的模式中。?邵斌納劇院在改編時為了符合新的主題,從人?物、布景及道具三方面入手展現哈姆雷特從健?全向不健全的轉變。
其一,在人物塑造上,除哈姆雷特外,每?個人都有著多重身份,他們在性格相反的兩個?人中相互轉換,自身本就是一個矛盾的集合。?與其說這部作品將不同的兩個人融入同一個軀殼中,不如說是通過一個軀殼展現人的虛偽與??本性。羅蘭·巴特認為,文本的意義網絡由行??動的、闡釋的、文化的、內涵的、象征的五種??符碼構成。盡管在意義層面上,象征符碼呈??現為:新王(小人與無能)/?舊王(正統與能??力)?,葛特羅特(欲望與誘惑) /?奧菲麗娜(美??麗與貞潔)?,霍拉旭(摯友)/?羅蘭克茲(背??叛)?,雷歐提斯(善良) /?克爾登斯(愚蠢) 。?與這些人相對比,哈姆雷特似乎才是全劇唯??一一個“完整”的人,但他真的是個“健全”?的人嗎?事實上,這些人都是被揭露的對象, ?作品真正想要展現的,是作為揭露者的哈姆雷??特面對真實與虛偽,由健全向不健全的轉變。??當他意識到每個人都是虛偽的,都帶著假面生??活時他不再相信任何人,用極端的暴行來矯正??扭曲的社會。
其二,在布景方面,狄德羅在《論戲劇?體詩》中寫道:“舞臺畫里……不應該有分散?注意力的東西,同時除了詩人有意激起的印象?外,也不應該有可能在我心里引起其他印象的?端倪。”邵斌納劇院很好地契合了狄德羅的觀?點,這出戲劇的舞臺可以簡單分為土地——前?景與餐桌——后景。前者表示人內心的本能與?欲望,后者表現人努力維護的虛偽的體面與道?德。
同樣,狄德羅還說過“任何東西,假使?不是渾然一體,就不會美;正是第一個事件決?定了整個作品的基調”,該版的第一個決定基?調的場景正是老國王的葬禮,眾人在土地上以?其真實的本性行動著:滑稽無能的新王、悲悼?痛哭的王妃、憤世嫉俗的王子以及小丑似的掘?墓人。土地有“野”的意味,當眾人處于這?種狀態時,無須再戴上假面盡情地暴露自己的?本性。也因此,當眾人回歸餐桌——帶有“文?明”的虛偽的地方時,唯有哈姆雷特一人坐在?“文明”的邊緣,腳踩著本能的土地。這是哈?姆雷特活在本性中的表現,是他不愿步入需要偽裝的、充滿“文明”的世界的體現。此時的?他仍是健全的,雖與眾不同仍保有文明禮貌和?克制的行為,但內心不愿偽裝,與偽裝虛偽的?社會形成強烈的矛盾沖突,從而進一步導致了?他的瘋癲。
餐桌作為“文明”世界虛偽的象征,眾?人在他的領域里都戴著面具。哈姆雷特幾乎從?未走進過這個領域,第一次登上是“覺醒儀?式”——《捕鼠器》上演前的癲狂,整個餐桌?聽從他的指揮,向前或向后開幕和閉幕,他用?文明世界的勺子打碟,把牛奶當禮炮,在這里?宣示自己的瘋狂。第二次則是與葛特羅特的斗?爭,也是與“文明”世界的斗爭,并在這里槍 殺了偷聽的大臣;新王與王妃在覺醒儀式之前,?總是戴著墨鏡,盡量偽裝自己的罪惡。當餐桌?變成了哈姆雷特攻擊的主體,作品想要表達的?就不再是個人的復仇,而是更宏大的本能與虛?偽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在激化后將他變成了?一個暴怒癲狂的“不健全者”。
其三,在道具的使用上,邵斌納劇院版的?《哈姆雷特》加入了極具象征意味的攝影機。?攝影機是哈姆雷特揭露人的本性的工具,甚至?可以說,在瘋癲之前,攝影機是哈姆雷特的眼?睛,比如當哈姆雷特把攝影機搖向餐桌上的葛?特羅特時,她開始瘋狂地舔舐自己的新夫,竭?盡所能地誘惑他,肆意展露自己的欲望,并沖?著哈姆雷特怒吼,一切都回歸原始的本能,每?個人都把自己真實的本能暴露在攝影機下,哈?姆雷特也因本能與虛偽的矛盾逐漸變得瘋癲。?但瘋癲之后,?哈姆雷特的眼睛如同攝影機一樣,?具有直接洞穿人性的功能。他捏住葛特羅特的?臉把攝影機近距離地放在對方面前,驚恐不安?的面龐映射在舞臺上,恐懼自內心深處蔓延,?這時的哈姆雷特已經成了復仇的機器。
原版中的哈姆雷特曾說過: “蛆才是我們 ?真正的‘食客之王:我們把世上所有的動物??養胖后來喂我們,而卻把自己養胖后喂蛆。”所有人到頭來都不過是桌上的菜,外在的身份?是毫無意義的。因此在邵斌納劇院版中,眾人?在餐桌上暴食,不過為蛆蟲積攢養分,卻要維?持一份虛假的偽裝,毫無意義。
二、暴力式的人文主義
原版的哈姆雷特擁有強烈的人文主義精?神,反封建、崇尚理性但又有悲觀、消極的一?面。他的人文主義理想和他對現實的悲觀認識?的沖突,體現在他對父親的突然去世深感悲?痛,對母親的快速改嫁疑惑不解;當他聽到鬼?魂的話時,他一方面半信半疑,另一方面又為?自己的猶豫和軟弱而感到自責;他意識到,他?的復仇關系到國家的命運、正義的伸張,但又?感到自己勢單力薄,懷疑自己是否能擔當如此?重任。哈姆萊特的悲劇結局有宮廷斗爭險惡復?雜的一面,也有他自身性格局限的原因。莎士?比亞通過這個人物的悲憤與失望、苦悶與彷?徨,批判了丑惡的現實,也揭示了哈姆雷特悲?劇性的必然,其理智與瘋狂、健全與不健全的?矛盾是始終存在的,甚至理智時常占據上風。?但邵斌納劇院版賦予了哈姆雷特極端的、暴力?的“不健全”行為來維護人的本真與自然。如?原版中所說“‘理智是我們成為懦夫,而?‘顧慮能使我們本來輝煌之心志變得黯然無?光,像個病夫。再者,這些更能壞大事,亂大?謀,使它們失去魄力”。所以在邵斌納劇院版?中這個“不健全”的王子似乎徹底成為斗爭的?工具,異化為時刻噴涌的火山,把虛偽的面具?挨個兒撕破給人看。
攝影機原是哈姆雷特觀察人性的窗口,但?在隱喻強烈的“雙重舞臺”——《捕鼠器》的?上演后,它就成了哈姆雷特揭露偽裝的工具。?當哈姆雷特把作為工具的攝影機對準眾人時,?他們大都扭曲恐懼或不愿面對。清楚看透這一?切的哈姆雷特變得瘋癲和歇斯底里,是真實的癲狂,于是他陷入短暫的絕望并開始反擊:暴?躁地摧毀餐桌上的一切、用各色食物擊打自己?的叔父、啃食泥土、把皇冠反戴在頭頂……沒?有懷疑,更多的是對這個虛偽世界的仇恨與憤?怒,想要將其毀滅的決心到達了頂點,也是哈?姆雷特從“健全”向“不健全”轉換的過程。
原本正義的、呼吁人道主義的行為在這里?變成極端的、充滿暴力的行為,無一不是對人?道主義催生的“文明社會”的一種諷刺:既然?正義的、反暴力的運動促生了社會的虛偽,那?就用暴力來摧毀這個不健康的世界,重塑“文?明”的條約。
三、悲劇的“敵我同源”
邵斌納劇院版的哈姆雷特對人性本真與自?然的呼吁體現在女性身上是要求其保持節烈的?德行。魯迅在《我之節烈觀》中對節烈觀進行?了詳細的闡釋: “女子死了丈夫,便守著,或?者死掉;遇了強暴,便死掉;將這類人物,稱?贊一遍,世道人心便好了。”這部戲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就是哈姆雷特與母親葛特羅特以?及愛人歐菲莉亞的關系。對于前者,哈姆雷特?怒其不貞,在丈夫死后很快另覓新人;對于后?者,哈姆雷特則要求其忠貞,哪怕強暴是自己?的幻想,不忠貞也是捏造的。
狄德羅在《關于〈私生子〉的談話》中對??于德行有這么一段描述: “不管從哪個角度考??慮,德行總是自我犧牲。在思想上具有自我犧??牲精神,?等于事先準備好在事實上犧牲自我。”?這樣強制性的自我犧牲精神于歐菲莉亞和葛特 ?羅特兩人來說,不正是一次被毀滅的過程嗎???或許葛特羅特參與了老國王的謀殺案,或許她??與新王早有勾結,或許她可以被判作一個蛇蝎??毒婦,但是那個單純無辜、被父親當作工具而??又不自知的歐菲莉亞又有何錯呢?一個女子因??其貌美就被懷疑沒有貞操,進而被打上不貞的標簽,?自此認為她就是個違背德行的女人。哈?姆雷特告誡她“早點去修道院吧”,說她是?“一窩罪人的生母”,并惡毒地詛咒其“無法?逃離流言的誹謗”。邵斌納劇院版將這一行為?放大到肉體上,哈姆雷特嘗試用暴力喚醒所謂?的節烈德行:用粗鄙的言語攻擊曾經的愛人,?用不可反抗的男性力量強暴了她,并用代表本?性的土地將她埋沒,用盡一切暴力行徑傷害著?無辜的人,只因哈姆雷特不再相信美麗與純潔?能夠并存;毫無保留地撕開母親葛特羅特的偽?裝,把她肆無忌憚的欲望和對他人赤裸的誘惑?作為攻擊她的武器,讓虛偽無處逃遁。
原版中哈姆雷特說: “我們以后不許再有??婚姻。已婚之人可以繼續生活下去,除了一個??人之外,?其他的人均應保持現狀, 不許結婚。”?是他復仇的指向與對人性失望的暗示,邵斌納??劇院版中讓哈姆雷特又加了一段獨白:“他們??每天戴著面具,根據各式角色演戲……”加強??對虛偽人性的控訴,讓哈姆雷特的憤怒更有針??對性。但這被社會扭曲了的可憐蟲把憤怒施加??在身邊人身上,更多的是兩位女性身上,把犧??牲精神凌駕式的“賦予”無辜者,最終造成了??歐菲莉亞與葛特羅特的自我毀滅。
原版中歐菲莉亞絕望時說道: “我們知??道我們現在是怎樣,但不知道將來會如何。”?但邵斌納劇院版將其改為“我們都知道沒什么??好指望的了”。前者是她被愛人拋棄與喪父之??后,對未來的茫然;后者則是把她的茫然無助??與絕望的范圍擴大到整個人生,是對自己保守??貞潔卻被污蔑的不解,是最后寄托喪失后的??絕望,她的自我毀滅是二者相加所必然會導致的。王后的結局卻是對這個虛妄世界的悔悟式的看破。她真的愛上了自己的小叔子,但這段禁忌之戀令她與兒子心生嫌隙。同時她又為自己的過錯后悔, 在《捕鼠器》演出后跌坐在地,把象征著假面的墨鏡丟在腳下,幡然醒悟,用死亡來做無聲的斗爭。決斗時,她明知酒里有毒卻固執提出要代哈姆雷特喝酒,國王大聲地制止她。她卻一意孤行,她明白自己做過的選擇無法再修改, 只有死亡才能換回內心的平靜。佩戴面具使人虛偽,掃射式的毀滅又使尚存本真的人陷入絕望,這是哈姆雷特矛盾的外化沖突,也是邵斌納劇院版的悲劇所在。
四、結語
由此可見,邵斌納劇院版中的哈姆雷特并非一個“健全”的王子,也正是其“不健全”才能揭露這個社會的虛偽面具。這種怒行造成眾人的悲劇,但其所蘊含的對本真與自然的追求才應當是健全的新標準。在此之后便誕生了新的問題:哈姆雷特成功的復仇使得“文明”世界的一切都歸于寂靜,未來的新人是遵循本性,還是重蹈虛偽的悲劇?這是我們觀眾應當思考的問題, 而對于哈姆雷特的世界來說, “讓一切歸于平靜吧”,這個世界不需要“文明”的餐桌。
[ 作者簡介 ] 武庭英,男,漢族,山西晉中人,廣西民族大學相思湖學院教師,碩士,研究方向為電影、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