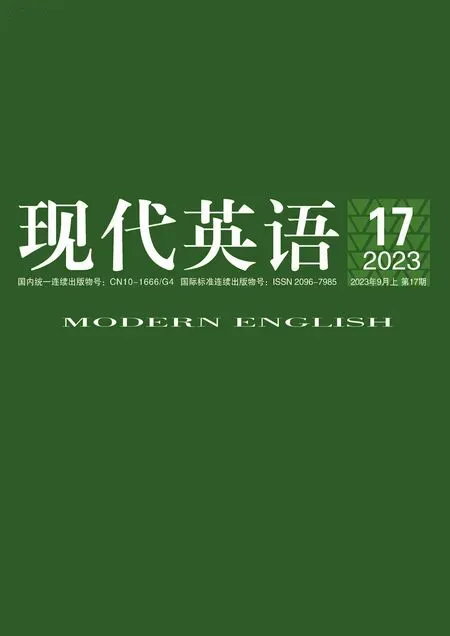“三美論”視角下?Crossing the Bar?兩個中譯本對比分析
——以黃杲炘、汪飛白譯本為例
努爾比亞?吐爾迪
(新疆大學,新疆 烏魯木齊 830000)
詩歌是一種特殊的文學體裁。 詩人在詩歌中,通常運用高度凝練的語言來表達思想感情,并運用節奏、韻律和特定的排列形式來讓詩歌這一體裁得以呈現。 在翻譯詩歌時,譯者不僅要努力再現詩歌的主題和作者在詩歌中所表達的思想感情,還要使詩歌的韻律和形式得以再現。 許淵沖先生提出的“三美論”在詩歌翻譯中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文章從意美、音美、形美三個層面對?Crossing the Bar?的黃高炘和汪飛白的兩個漢譯本進行對比分析。
一、 作者和作品介紹
?Crossing the Bar?的作者是維多利亞時期的著名詩人阿爾弗雷德?丁尼生(1809—1892)。 他于1850 年因著名詩歌?悼念集?的出版被授予“桂冠詩人”稱號。 維多利亞時代,工業革命迅速發展,自然科學也獲得了空前的突破,舊的思想和不斷涌現的新知識和新觀念(如達爾文的進化論)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碰撞,工業化過程中的社會動蕩和價值觀念的變化造成了信仰危機。 丁尼生在作品中尖銳地反映了維多利亞時代科學與舊思想的沖突。 一方面,丁尼生出生于一個牧師家庭,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他雖對舊思想產生過懷疑,但是最終調和了科學與舊思想之間的這一沖突。 另一方面,丁尼生自身的經歷也影響著他的創作。 父親的去世和好朋友哈勒姆的早逝給他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他將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融入詩歌作品中。 丁尼生的詩歌充滿了與離世相關的意象,離世主題成為他眾多詩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Crossing the Bar?這首詩寫于1889 年,是丁尼生晚期的作品。 這首詩不是丁尼生寫的最后一首詩,但他要求把這首詩放在他詩集的最后。 丁尼生的對舊思想的態度經歷了早年的模棱兩可、中年的幻滅與思考和最后晚年的平衡與和解[1]。 這首詩是作者晚年時的創作,當時他已經在科學和信仰之間做出了折中與調和。 在這首詩歌中反映了作者視死如歸的觀念。 他認為離世不是人類的終結,而是與上帝的精神結合、信仰的回歸。 整首詩表達了作者對離世超然豁達的態度。
在這首詩中,詩人用“日落”“晚星”“暮色”等名詞,為讀者描繪了一幅寂靜的黃昏圖,一日中的黃昏景象象征著詩人也步入生命的黃昏。 詩人將抽象的情感寄托在具體的意象上,表達了晚年面對死亡的平靜、安寧的態度。 “當我出海去,河口沙洲莫悲哭”“當我登船去,別離時分莫哽咽”,流露出詩人對將要來臨的死亡的坦然的思緒。
文章選擇了流傳較廣的黃杲炘和汪飛白的譯文。 汪飛白的譯本出版于1985 年,而黃高炘的譯本出版于1995 年,兩個譯本出版時間相差十年,有較高的對比分析意義。 下文中將從“意美”“音美”和“形美”三個層面進行詳細的對比分析。
二、 “三美論”概述
20 世紀下半葉,許淵沖先生基于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所說的“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提出了“三美論”[2],即“詩歌翻譯不僅應忠于原文,還應做到意美、音美和形美”[3]。 “三美”的基礎是三似,即意似、音似和形似。 “追求意似就是要傳達原文的內容,不能錯譯、漏譯、多譯”[4]。
許淵沖先生認為,意美是詩歌翻譯的第一要務,是“三美論”的核心和關鍵。 “意美”要求在譯文中再現原文的象征、雙關、深層含義等。 意境美是詩歌形式美和音韻美的最終目的和歸宿,也是詩歌美的最高境界[5]。 詩歌中的“意美”有時與文化和歷史有較大關系,將詩歌翻譯到另一種語言時,不同語言背景下的文化和歷史差異導致原詩的“意似”無法實現,而原詩的“意美”也不容易傳達。
音美,指的是“詩要有節調、押韻、順口,聽起來好聽”[4]。 音美要求在譯文中要體現原詩的節奏,韻律等。 盡管因為中西方語言差異,較難做到“音似”,但譯文中也不能忽略“音美”的傳達。
形美,主要是指詩歌的長短和對稱兩個方面最好也能夠做到形似,至少也要做到大體整齊[4]。 想要體現原詩的形美,就要做到譯文的行數和節數與原詩一致,在句子的長短和對仗工整方面做到形似。
許先生還認為,“三美”的地位不是并列的,而是有輕重、主次之分的。 “三美”之中,意美是最重要的,音美是次要的,形美是更次要的。 我們要在傳達意美的前提下,盡可能做到三美齊備。 如果三者不可兼得,那么首先可以不要求形似,也可以不要求音似,但一定要盡可能傳達原文的意美和音美[4]。
三、 原文與譯文對比分析
(一)意美層面
原文題目:?Crossing the Bar?
黃杲炘譯:?過沙洲,見領航?
汪飛白譯:?越過海灘?
原詩題目“Crossing the bar”中的“crossing”用了雙關的修辭手法。 一方面,它有十字架的意思;另一方面反映作者的死亡觀,即死亡是從一個世界過渡到另一個世界。 題目中的“bar”的本意是指河道或港口泥沙淤積處,漲潮時沒入水中,退潮時部分裸露出來的地方;而“bar”往往會阻礙船的順利通過,因此常常被喻為“生死關口”,象征著生與死的界限。
黃杲炘譯文中的“沙洲”和汪飛白譯文中的“海灘”都再現了“bar”本意。 兩位詩人都通過使用注解,向讀者說明了“bar”在詩歌中的含義。 兩位譯者的譯文中都沒有體現出“Crossing”的十字架這一層含義。
原文[6]:But such a tide as moving seems asleep,
Too full for sound and foam,
Turns again home.
黃杲炘譯[7]:海深邃,洋空闊,
潮來海洋總須回頭流;
滿潮水悠悠,
流水似睡靜無皺。
汪飛白譯[8]:渾然流動的潮水似已睡去,
加強外部環境的防護與監督,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企業財務人員可能面臨的風險,只有找到會計職業風險防范的長效機制才能從源頭上處理將風險最小化。通過分析,本文建議增強風險意識教育才是最長效的防范機制。
潮太滿了,反而無聲無息,
從無邊的海洋汲取的,
如今又復歸去。
原詩前兩句描寫了海面平靜的景象,襯托出作者面對死亡時平靜的心態。 原詩第三句中的“that”指的是第一句中的“tide”,第四句中的“Turns again home”中的“again”代表來生,表達了作者視死如歸,將死亡看作是生的延續的死亡觀。
黃杲炘譯文中,將原詩第三句中的“that”與第四句相結合翻譯為“潮來海洋總須回頭流”,將“that”明確的翻譯為“潮”,向譯文讀者明確指明了原詩中的景象。 汪飛白譯文中,第三句中的“that”所指代的“tide”沒有明確的翻譯出來,使譯文前兩句和后兩句脫節。
原文[6]:For though from out our bourne of Time and Place,
The flood may bear me far.
I hope to see my Pilot face to face,
When I have crossed the bar.
黃杲炘譯[7]465:塵世小,人生短,
這潮卻能載我去遠方;
過了沙洲后,
但愿當面見領航。
汪飛白譯[8]:雖然潮水會把我帶到無限遙遠,
越出我們的時間、空間,
我希望見到領航人,面對著面
當我越過了海灘。
原詩第一句中的“bourne”是指“boundary”,意思為“邊界、界限”;“Time”和“Place”大寫為專有名詞,并非指特定的“時間”和“地點”,而是指詩人將要結束這一次的人生,實現生命的延續;第三句中的“Pilot”指的是上帝;第四句“When I have crossed the bar”與題目相呼應。
黃杲炘譯文中,將“bourne”與“Time”和“Place”相對應,翻譯為“塵世小,人生短”;將第三句中的“Pilot”譯為“領航”;第四句的翻譯和原詩一樣與題目相呼應。 汪飛白譯文中,將“Time”“Place”直接譯為“時間”和“空間”,沒有直觀地譯出原詩中作者想要表達的意境;將第三句中的“Pilot”譯為“領航人”;第四句的翻譯和原詩一樣與題目相呼應。
(二)音美層面
?Crossing the Bar?這首詩由四節組成,每一節有四句,各節的尾韻分別是abab, cdcd, efef, baba。下面分別列出原文、黃高炘譯本和汪飛白譯本中的韻律,見表1:

表1 原文中的韻律

表2 黃高炘譯文中的韻律:

表3 汪飛白譯文中的韻律
押韻是達到音美的重要手段。 從上述表格可以看出,在原詩中,詩人通過頭韻和尾韻的結合使用,使詩歌朗讀起來節奏分明。 另外,詩人在第一節與第四節采用了一對重復的韻腳,形式上前后對仗,使詩歌富有節奏感。
由于中西方語言差異較大,在詩歌的翻譯時較難實現譯文與原文的“音似”,但可以通過中文中常用到的韻律來再現詩歌的“音美”。 黃杲炘和汪飛白的兩個譯本雖和原詩不“音似”,卻都通過使用尾韻再現了原詩節奏上的“音美”,使譯文與原文一樣富有節奏感。
(三)形美層面
詩歌是文學作品中最注重形式的一種文學體裁,形式也是詩歌區別于其他文學作品的重要特征。詩歌譯文的形美,主要表現在行數長短整齊,句子對仗工整方面。
原文全詩共4 個詩節、16 行、102 個單詞。 雖然每一節詩歌的長度都不一樣,但每一節詩歌的第一行和第三行都比第二行和第四行長,長短句的交替出現使詩歌在形式上產生了抑揚頓挫的效果。 還有詩歌中的第一、三、四節最后一句都以“When I...”開頭,形成了平行結構,增強了詩歌的氣勢。
黃杲欣譯文共4 個詩節、16 行、108 個漢字。 譯文中在保持原文意義再現的同時,通過交換原詩的行序,使詩歌每一節中第一句和第三句都比第二句和第四句長,長短句交替出現的特點得以再現。 四節詩歌每一節都嚴格做到了第一句6 個字,第二句9 個字,第三句5 個字,第四句7 個字,實現了每一節詩歌字數和形式上的統一。 原詩第一、三、四節最后一句中以“When I...”開頭的三個句子,譯文中在第一節第三句和第三節的第三句以“當我……”的形式再現。
汪飛白譯文共4 個詩節、16 行、137 個漢字。 譯文嚴格按照原文的行序翻譯,也做到了長句和短句的交替出現。 原詩第一、三、四節最后一句中以“When I...”開頭的三個句子,譯文中在第一、三、四節的最后一句以“當我……”的形式再現,形式上與原詩保持一致。
四、 結論
詩歌是一種特殊的文學體裁。 詩人用凝練的語言,借助具體的意象營造詩歌的意境美、音樂美和形式美,從而表達思想情感。 通過上文對?Crossing the Bar?的兩個中譯本在意美、音美和形美層面上的對比來看,黃杲炘和汪飛白的譯文都各具特色。 在意美層面上,黃杲炘譯本較大程度實現了原文意境美的再現,而汪飛白的譯本中有上文指出來的個別幾處之外,也再現了原文的意境美;在音美層面上,因為中西方語言上的差異,較難實現譯文與原詩的“音似”。 二者的譯文都沒有實現與原詩“音似”,但通過對“音美”表現形式的調整,都在較大程度上再現了原文的“音美”;在形美層面上,黃杲炘的譯文中,通過嚴格控制每一節中每一行的字數,實現了每一節字數和形式上的統一,形式較為對仗工整;而汪飛白的譯文中,雖沒有像黃高炘的譯文中那樣嚴格控制字數,但是長短句交替出現,譯文形式較為自由。 黃杲炘和汪飛白的譯本都在較大程度上再現了原詩的形式美。 總而言之,兩位譯者運用適當的翻譯方法和技巧,都以最大限度地傳遞了詩歌的意美、音美和形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