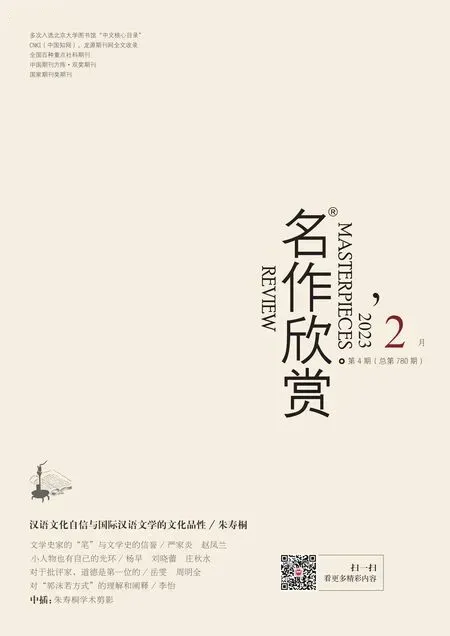對“郭沫若方式”的理解和闡釋
——郭沫若研究的方法隨想
四川|李怡
對任何一位作家的研究,其實都是研究者對作家本人的特殊“方式”的理解和闡釋。所謂的“方式”包括思想、情感以及思維等,之所以特別以“方式”命名,乃是指這樣的內(nèi)容并不簡單就是“人類共同認知”的一部分,而是深深地烙上了這一位作家自己的個性與風格,需要我們做出對應性的體認和剖析。“理解”就是對其中的個人化的內(nèi)在邏輯的把握,“闡釋”就是對這種“方式”的歷史價值的分析和認定。
所有的作家研究,其根本的成效其實就是取決于我們對這種個人化內(nèi)涵能否準確地把捉和發(fā)掘,在這個意義上看,“方式”的捕捉和呈現(xiàn)就是學術(shù)觀察的焦點,能夠理解“魯迅的思想方式”“茅盾的文學方式”“沈從文的感受方式”等,就構(gòu)成了文學研究的主要目標。郭沫若研究更是如此,這是因為無論作為詩人還是散文家,郭沫若的感受方式、思維方式都格外強大,以致在他所涉足的一切領(lǐng)域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記,“百科全書”式的文化巨匠,顯然有自己一以貫之的風格與趣味,球形天才的四面擴展,也有自己的內(nèi)核與軸心。這里所存在的“郭沫若方式”是我們理解和解釋的重要基礎(chǔ)。
郭沫若方式究竟有哪些內(nèi)涵呢?我覺得這正是未來郭沫若研究還需要進一步挖掘和剖析之處:作為文學家,郭沫若的文學創(chuàng)作遍及詩歌、戲劇、小說、散文等各種文體,這究竟一般性地證明了他的“全才”還是其中蘊含著特殊的文學氣質(zhì)?作為文化巨匠,郭沫若與古今中外諸多的思想文化思潮關(guān)系緊密,且從不避諱將它們左右聯(lián)系,統(tǒng)而論之,又該如何加以描述?作為情感性的創(chuàng)作者,他顯然并不為文學的抒情所限制,一生不斷跳脫出感性的表達,一再轉(zhuǎn)入理性的探求之中,關(guān)于歷史,關(guān)于考古,特別是在他人眼中頗為枯燥乏味的甲骨文考訂,這情感與理性的背后,又服從什么樣的考量?奉先秦的自由與個性為理想的他,又堅定地選擇了革命之路,以群體意識的“新國家主義”為旨歸,其中的心理脈絡(luò)值得我們深究。
以上的這些問題在郭沫若研究中早有注意,但是進一步的研究實有不足,需要引起我們更多的關(guān)注。
例如,在郭沫若全才般的寫作之中,詩人氣質(zhì)和散文家氣質(zhì)始終是主導,應該可以借此解讀郭沫若文學的核心趣味。詩人氣質(zhì)過去我們討論較多,其實郭沫若的散文寫作與他的新詩創(chuàng)作同時起步,且形式多樣,貫穿一生,題材豐富,從個人抒懷、自然風物到人生自傳以及雜文、評論和小品,應有盡有。所以說,郭沫若文學在所謂的“詩性寫作”之外,同樣洋溢著一種“散文氣質(zhì)”。歷來的文學史家都在談論郭沫若的“詩人氣質(zhì)”,不僅郭沫若首先以詩聞名,而且他的其他創(chuàng)作如戲劇、小說甚至學術(shù)著作都充滿了詩性的想象,洋溢著詩人的浪漫;其實,同樣的描述也可以用于散文,我們可以稱郭沫若的文學在一開始也是散文的,在他的眾多寫作中——小說、戲劇、學術(shù)研究甚至歷史考訂,都可以發(fā)現(xiàn)是以“散文”的方式在自我敘述。進一步追問,我們則可以發(fā)現(xiàn),“詩性”與“散文性”又是可以交融溝通的,它們都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感受性的表述,它們的寫作都流淌著鮮明的自我意識,是個人內(nèi)在精神的更直接的表達。有時候,我們以“詩性”名之是重其想象的浪漫,有時又以“散文”定位,則是指代一種主觀化的“敘述”。因為這種“詩性”與“散文性”的交融生長,郭沫若的寫作酣暢淋漓、自由無礙,甚至論文都絕無板滯,絕無學究腔和匠人氣,而是情感充沛、通曉平易,包括那些歷史的追溯和考證也往往能夠訴諸生動可感的生命體驗,令人想起那些揮灑自如的藝術(shù)小品。問題來了:除了一般的文學創(chuàng)作,對于這些貫穿“詩性”與“散文性”的郭沫若學術(shù)著作,我們應該如何解讀方能得其神髓?是簡單置放在中國現(xiàn)代學術(shù)史的宏大背景之上,繼續(xù)挖掘其“學術(shù)貢獻”,還是抓住其中可能存在的瑕疵大加抨擊,以此顛覆郭沫若的學術(shù)地位?如果不能理解其中的“郭沫若方式”,兩種取向都可能自陷于認知的隔膜,而郭沫若真正的精神追求反而難以獲得彰顯。
再如,郭沫若與“五四”以后中國文壇上的各種思想藝術(shù)思潮都有聯(lián)系,且還不斷地“與時俱進”,不斷在歷史的復雜運動中添加著新的內(nèi)容——不僅在創(chuàng)作中一再表現(xiàn)了這樣的豐富或者繁復,往往還借助各種各樣的理性的述說來確定著自己與所有這些復雜思潮的聯(lián)系。這為我們今天的研究帶來了豐富多彩的主題,就像多年來郭沫若研究當中最方便的選題設(shè)計一樣——“郭沫若與××文化”,似乎這樣的話題可以持續(xù)不斷地開展下去,又極容易與時代變化的需要掛上鉤。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郭沫若文本里本身就漂浮著大量各種各樣的“文化符號”,完全可以為我們自由調(diào)用,而郭沫若本人從理性意義上所做的諸多的說明也似乎正好成了我們有力的論據(jù)。然而,作為學術(shù)研究卻不能停留在這一類論題的取巧上,我們難道只能成為作家表述的附庸而始終缺乏對作家內(nèi)在精神脈絡(luò)的把握與透視?而且,我們越是隨著作家表層的自述將復雜的精神現(xiàn)象簡明地“嫁接”到中外文化當中以后,我們的研究也越發(fā)顯出了一種矛盾與尷尬:是的,我們已經(jīng)如此全面地揭示了郭沫若的“文化內(nèi)涵”,但是郭沫若本人究竟是什么樣的呢?顯然,無論是“像”儒家、道家、墨家還是“像”泛神論馬克思主義,無論是孔子、莊子、屈原、王陽明還是惠特曼、泰戈爾、歌德都不能代替郭沫若自己的創(chuàng)造活動,郭沫若最根本的意義不可能是由影響他的哪一種中外文化與文學來確立的,說他是由以上這些文化文學因素“綜合”決定的也未免過于“大而無當”了,郭沫若只能是自己確定著自己,這也就是說,我們應當在“郭沫若與××文化”這樣的命題之下,發(fā)掘出一些更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東西出來,郭沫若感受這個世界與人生的獨特方式如何?他有著一些什么樣的思維習慣,面對他所理解的這個世界,他本人有過什么樣的“語義編碼”?
在我看來,未來的郭沫若研究還應該下一些“笨功夫”,也就是在最表面的思想文化的概括之外,梳理和總結(jié)郭沫若的詞語、符號、意象,從最基本的語言習慣、語義方式中揣摩他內(nèi)在的思維和意蘊,繪制“郭沫若語義地圖”,當然也包括他在不同的語境中所做出的自我調(diào)整,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勾勒出一個具有精神結(jié)構(gòu)意義的郭沫若。借助這樣一個“語義地圖”,郭沫若自我表述中一些無不含混但卻相當關(guān)鍵性的概念就有望獲得詳解,如“泛神論”,究竟是斯賓諾莎造就了郭沫若還是泰戈爾、莊子、王陽明造就了郭沫若,抑或是巴蜀的民間信仰形成了這種本土的思維?①還有,文學史長期以“浪漫主義”描述《女神》的風采,但是來自歐洲的浪漫主義文學傳統(tǒng)與中國傳統(tǒng)文人的“浪與漫”傳統(tǒng)的相遇卻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郭沫若精神深處的趣味不是表面的概念就能說明的,恰恰是來自歐洲的漢學家如高利克不愿以“浪漫主義”視之,倒是另有唯美印象主義、表現(xiàn)主義的命名,②這都啟發(fā)我們,即便是在我們自以為了解甚多的郭沫若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其實也存在許多語義的復雜,值得我們更加仔細地辨析。
郭沫若與革命文化的關(guān)系也是如此。一方面,正是“五四”時期的個性主義與狂飆突進奠定了郭沫若情感和思想的基礎(chǔ),這種對個性與自由的追求絕非一時的權(quán)宜之選,而是貫穿他一生的社會文化理想的基礎(chǔ),不僅《女神》中有奔騰的天狗,歷史著作中更有對先秦“澎拜城”的迷戀與向往,那樣的自由與個性已經(jīng)滲透到了他的骨髓;另一方面,正是出于對普遍自由的理想,他又走出了“五四”的個性解放,轉(zhuǎn)入群體解放——革命的道路,從打破一切束縛的自由到犧牲個體自由遵奉“新國家主義”的原則,這是一種需要我們認真梳理的思想邏輯。在這里,只有將前后兩種理想融會貫通,才是我們體認“郭沫若方式”的基本依據(jù),我們當然應該充分理解革命洪流取代“五四”個性的必然與必要,但也不能簡單以“革命”之后的群體性原則取消郭沫若精神深處的自由的“初心”,更應該充分意識到這樣的精神追求同時也是他持久保留的文化觀、價值觀與歷史觀,是郭沫若完成歷史敘述與現(xiàn)實批判的深層邏輯。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理想的日益實現(xiàn),郭沫若的這一精神理想也將不斷顯示出深遠的價值。
①李怡:《〈女神〉與中國“浪漫主義”問題》,《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年第1 期。
②M·嘎利克(今通譯“高利克”):《郭沫若從唯美印象主義者發(fā)展為無產(chǎn)階級批評家》,《國外中國文學研究論叢》,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8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