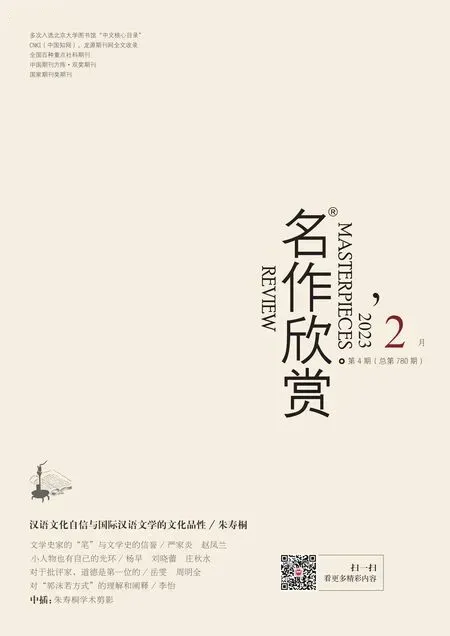《駢拇》:斥“仁義”而歸重“道德之正”
上海|方勇
外篇第一篇名為《駢拇》,采自文章前二字,其余十四篇篇名也大致是這樣命名的,和內七篇篇名概括自文意,有特殊含義而有所不同。而內外篇命名方式的不同,也引起了關于內外篇關系以及真偽的討論,這些問題我們稍后再展開論述。現在讓我們進入文本分析。一方面,莊子在內篇中的一些篇章已經提到了“仁義”,并對其進行了否定,如言“仁義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亂”(《齊物論》)。又云“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人間世》)。內篇七篇是將“內圣外王”之道的“內圣”提升到養心悟道的高境界,追溯萬物本源,而“外王”之事,則認為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就是只有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出來治理天下,而走上“外王”的道路,并且即使是出來治理天下,而“莫若無為”,因為只有“無為”才能“安其性命之情”。而《莊子》一轉入外篇,即開始大力批判仁義,反觀當時諸侯力爭,交相侵伐,世人逐利,雖然社會上也有儒者在大講仁義道德,但實質上更多的人卻是利用仁義之說來獲得好名聲,邀買人心,達到個人或家族的政治經濟目的,《胠篋》就提到齊國田氏家族通過偽行仁義、宗法圣人而達到了竊取政權的目的,最終代姜氏而有齊國,其行為正是莊子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的真實反映。
在莊子看來,仁義除了束縛個人自身人性之外,往往會淪為一種約束他人的工具,無論是對于個人還是對于當權者來說,均是如此。此種情況,古今相同,別有用心之人會加以利用,竊國大盜往往成為真理的化身統治天下,將仁義外化為政教文章來束縛人心,束縛人的自然本性。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當數歷史上有名的“田氏代齊”,《左傳·昭公三年》中記載田氏用大斗借出、小斗回收的方式,使得民心“歸之如流水”,最后運用各種手段代姜氏而有齊國。莊子認為要達到“內圣”,必須拋棄仁義,要走向“外王”,不得已才出來治理天下,即便如此,追求仁義也是不可取的。所以外篇開始即痛批仁義道德,并將《駢拇》《馬蹄》《胠篋》等主題思想相關的一組文章放在外篇開篇,接連從不同側面批評“仁義”非自然之性,非天下之至正,反對用仁義來壓制天性自由,以及揭示出仁義圣智的危害。
莊子在《駢拇》中提出“道德”兩個字,卻極力批判否定仁義,然后極力肯定道德。《莊子》書中的“道德”一詞,如同“圣人”一樣在全書中多有混用情形,所持態度也是褒貶不一,具體感情色彩如何需要結合上下文進行分析。《老子》三十八章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道德”這個詞在莊子作為肯定意思的時候,也不是儒家所言的“德”,而是一種根植于本性里面的“德”,是先天就有的,而非在后天養成的“德”,因此這種德是比較接近于道的。我們要知道,老、莊并不一概否定道德,他們所否定批判的是后天形成的那種儒家所提倡的外加于人本性之上的道德。而對于人本性所包含的德,則是持一種肯定的態度。《駢拇》一方面極力批判仁義,另一方面極力抬高自然本性中的道德。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于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于五藏之情者,淫僻于仁義之行,而多方于聰明之用也。
是故駢于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于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于辯者,累瓦結繩、竄句,游心于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開篇即用駢拇枝指設喻,指出人的“道德”在于人的自然本性,而儒家強加給人的“仁義”教條,只是“多駢旁枝之道”,并非人的純樸本性。“駢拇”是指腳趾的第一個大拇指和第二指連生合為一指,也有人認為是指手的大拇指和第二根手指相連,但是根據下文的“枝指”顯然是指手指,以及“駢于足者”等內容,可以判斷出這里就應該是指腳趾,在實際生活中出現駢拇的情況并不多。“枝指”是手的大拇指旁邊又長一個小指,變成六指,相較于“駢拇”,這種情況則出現得要多一些。“侈”是多余、過多的意思。“德”在這里一般有兩種解釋,莊子文中的“德”有時作“得到”講,因此這里的意思是指“駢拇”“枝指”對于正常五趾、五指的人來說,是多余的。還有另外一種解釋,是將“德”字作為本字來講的,解釋為“容”,《盜跖》篇云:“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此兩處的“德”即是指容貌。因此,結合上下文,這里的“德”作“容”講更為恰當。“附贅縣疣”指身體上長出的肉瘤,非是本性生來具有的,所以是“出乎形”,且為多余。而前面的“駢枝”卻是先天長出來的,所以叫“出乎性”。這里莊子用了“駢枝”“贅疣”兩個比喻,是一種“喻意”,緊接著拋出的“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而非道德之正也”才是莊子真正想表達的內容,是“正意”。“多方”是指多個角度、多種方式來推行仁義。“五藏”,一般指心肝脾肺腎五個器官,同時還暗合著五行,根據《漢書》《白虎通·性情》等記載,漢代把仁義和金木水火土五行及五臟相配起來,一一對應,即“肝木,仁也;肺金,義也;心火,禮也;腎水,智也;脾土,信也”。總之,儒家運用各種手段造作仁義,這樣的便不是莊子心目中蘊含于自然本性的道德,所以說“非道德之正也”。“多方駢枝于五藏之情者”一句里的“多方”,古代研究者如羅勉道、方虛名、焦竑、宣穎都認為是衍文,聯系上下文,可知前人看法有理。“駢枝于五藏之情”,意謂在五藏之情以外又生出枝節。所以,在莊子看來行仁義是一種淫僻之道,類同于多方面濫用了聰明。
文章在開篇即用“駢拇”“枝指”兩喻意引起“道德”這個正意,接著又添出“仁義”“聰明”二項,即原文所云“淫僻于仁義之行,而多方于聰明之用也”,此處也揭示出二者俱為淫僻之具。其中“非道德之正”的“道德”二字實為全篇之綱,屬于領起下文的單起,后面又引出的無用之“仁義”“聰明”,則屬于雙承,這是“單起雙承”的筆法。反觀文意,事實上,莊子對先天的聰明并不反對,他反對的是用“明”以至于“亂五色,淫文章”,用“聰”以至于“亂五聲,淫六律”。他所反對的是人們后天刻意培養、蓄意提倡的那種聰明,認為這樣形成的聰明往往會成為本性的負累,會“擢德塞性”,如此就與《老子》(三章)“虛其心,實其腹”,黜聰明、去才智的主張剛好相反。概言之,此段主要就是對無用之“仁義”進行批判,末尾又帶出了同樣對天性有害的“聰明”,以引起下文,從而自然無痕地實現了文章內容的過渡,這種行文的巧妙之處,不可不察。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這里“聰明”是作為文章的枝節曼衍,其主干仍是談“道德”與“仁義”的關系,批判“聰明”也是為批駁“仁義”服務的。《逍遙游》言“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在文章學上的寫作模式與此處相類似。明清學者從文章學的角度研究《莊子》,發明了“正意”“喻意”兩個術語,細讀《逍遙游》原文即可知:其中“小知不及大知”是正意,總結了上文內容,順帶的“小年不及大年”則是前一句的喻意,從而由此開啟下文一段文字,后面所提到的“朝菌”“蟪蛄”“冥靈”“大椿”“彭祖”等都是喻意。如果我們明白了《莊子》文中所提到的何屬正意,何屬喻意,便往往可以把握住《莊子》文章的正穴,就能更為準確地把握住莊子真正想表達的意思,而不會迷惑于其瑰瑋宏肆的文辭之中,不知所云。這里“淫僻于仁義之行,而多方于聰明之用也”中“仁義”和“聰明”的表達亦是如此,它們與“非道德之正”的“道德”也形成了喻意、正意之分。前文我們已曾提到此處為“單起雙承”,此外本文尚有“雙起單承”“雙起雙收”的筆法。如果一篇之內交迭運用此種起收承遞的筆法,就會出現猶如碧海波濤,一浪連一浪接踵而至的景象,也正因為《莊子》有此行文方式,才能得到后來人所謂“汪洋恣肆、儀態萬方”的評價。
第二段關于“是故駢于明者”一句中的“駢于明”的解釋,涉及文章學的字法問題,《莊子》文章中有很多字很難用訓詁方法直接解釋,古人有時把這部分字稱為“替字”,明代徐渭在詮釋《天道》“斫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時,曾言“南華妙于用替字”(劉鴻典:《莊子約解》引)。“駢”字本義是指兩物并列相連,如標題“駢拇”,這個解釋卻無法用于此句。如果把此處的“駢”看成一個“侈”或“多”的替字,聯系上下文,概括大意,應該是過分、過度的意思。“五色”指青黃赤白黑五種顏色,“文章”原來指顏色,其中青色配赤色為文,赤色配白色為章,引申為文采。“黼”,指黑和白相配,“黻”,黑和青相配。“而”借為“如”,此種解釋為古文所常見,如“人而無儀,胡死遄為”(《詩經·碩鼠》)。“離朱”,相傳為黃帝時候的人物,視力很好,說他百步之外能看見鳥獸秋天新長出的細毛。此處句意是說過度追求視覺明察的,會使得五色迷亂,文采泛濫,這難道不正像是用色彩華美的花紋來擾亂人們的視覺嗎?如離朱就是那樣的人。“五聲”是指宮商角徵羽五個古樂音符,“六律”指黃鐘、大呂、姑洗、蕤賓、無射、夾鐘六個古樂諧音。“金石絲竹”代指“八音”,除了金石絲竹外,尚有匏土革木四種,總共八個音調。“師曠”,為晉平公樂師,精通音律。此處句意是說矢志于提高聽覺的,混淆五音,矢志于六律,豈不是用金石絲竹、黃鐘大呂那樣紛雜的音調來混亂人們的聽覺嗎?如師曠就是那樣的人。這兩個例子,在同時代文獻中也有提到且是并舉的。儒家經典《孟子》一書就提到過,《孟子》中的“離朱”寫作“離婁”。其《離婁上》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在儒家看來,即使如離婁、師曠般有高明技能的人物,也要遵循一定的規矩禮法,才能展示其特殊才能,而不是僅僅依靠原來本性直接施為,如果沒有一定的規矩約束,再高明的技能,也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產生廣泛的影響。這是孟子所倡導的有約束的離朱、師曠。而在莊子這里,離朱、師曠的視聽能力已達到極高的水準,常人難以企及,他們卻仍倡導要追求更極致的境界,而不滿足于目前的水平,還常引得其他天賦平常的人們紛紛效仿,所以莊子批判他們帶來了“亂五色,淫文章” “亂五聲,淫六律”的壞影響。不過這并非是莊子認為最緊要之處。緊接著莊子即展開了對“仁”的批判,認為“枝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
離朱、師曠兩個例子分別闡發“駢于明”“多于聰”的非正之道,但他們相對于仁義也還只是喻意。“枝于仁”的“枝”也是一個替字,這里的“枝于仁”解釋為“造作仁義”。《莊子》文章從不向古人討得一字,常常自鑄新辭,從靈活運用借字替字,即可看出。莊子是充分肯定蘊含在本性之中的仁義道德的,認為那是天性的一部分,而那些對于在本性之外,虛飾偽作出來帶有虛假性的,莊子則是極力否定的。曾參,作為孔子的弟子,常以孝著稱于世,其事跡主要見于《大戴禮記》的“曾子十篇”,以及《禮記》的部分篇章。史,是春秋時期衛靈公的大臣,與曾參并以仁孝著稱,因此莊子又以曾、史為例,此處句意是說造作仁義的,就特意表現仁義道德,壓抑本性以沽名釣譽,并號召天下人吹簧打鼓地去學習效仿那不可企及的仁孝,如曾參、史就是那樣的人。批判了仁義,后面又從“聰”“明”,帶出“辯”的話題。這里“敝跬”,“敝”指精神疲敝,“跬”原指行半步,這里指分外用力的樣子。“譽”為吹捧。郭嵩燾把“跬譽”連讀,認為是指眼前的微小名利。此處句意是說那些致力于詭辯的,常疊聚無用之詞如累瓦,連貫荒誕之言如結繩,心思游蕩在堅白同異的名實論題之中,精神疲敝還竭盡心力地去吹捧那些無用的話,如楊朱、墨翟就是那樣的人。而根據先秦文獻記載,楊朱、墨翟在當時影響很大,孟子就言:“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可見從其學說者甚眾,流毒甚廣。
以上所談到的明、聰、仁、辯四種情況都是駢枝之屬,均非出于自然本性最為純真的道德,所以被莊子一一否定,并加以批判。本段中的“辯”也是由對“明”“聰”的批判順帶出來的一項,它們三者都是對于人自然本性的文飾,在這里作者想表達仁義也本非道德之正的主題,用以糾正世人長期形成的誤解。因此,即可明白在本段“枝于仁”是正意,其余的明、聰、辯則是喻意。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余,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且夫駢于拇者,決之則泣;枝于手者,龁之則啼。二者或有余于數,或不足于數,其于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上文所提到的“駢于明”“多于聰”“枝于仁”“駢于辯”等種種皆為“駢枝之道”,都不是最純正的道德體現。而本節文字就什么樣的道德才是至正之道進行討論,所以本節開頭即緊接上一段末尾提到的“天下之至正”來展開論述。這里的“正正”,多家注《莊子》學者認為應該作“至正”。所謂的至正之道,即是要不失去性命的真實,如果出于自然天生,則即使是腳趾合在一起的也并不為“駢”,手指多出一指的也不是“跂”,也就不算多余,他們只是形體上看起來的贅余,其道德上卻沒有任何造作,因為它們都是最自然的生長狀態,并沒有因為不同于常人,不美觀,而去人為地進行改變,這里莊子欣賞的正是保持的本生本性的自然狀態,故而有此議論。這種議論正好對應著《莊子》書中出現的許多形體丑陋而德性完善的怪人、畸人,如《德充符》中提到的闉跂支離無脤、甕?大癭等。而在開篇說“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則更多是出于身體本身而言,的確是身體的多余部分,此處則強調其全身保性、不改故常的一面,因此我們可以總結成是“自然而然,駢者不為駢,跂者不為跂”。
文章接著又宕開一筆,由駢枝之奇引出了長短之異,所謂物各有性,只要是展現了性命的本真狀態,則即使顯得長的也不可謂其多余,顯得短的也不能言其不足,比如野鴨腿短,白鶴腿長。但如果人為地損其所長補其所短,就會為雙方增添無窮傷悲,把本性自然作為常態,則長者不需截斷,短者不需接續,這樣才會遠離憂愁。王弼在注《周易·損卦·彖辭》時進一步發揮說:“自然之質,各定其分,短者不為不足,長者不為有余,損益將何加焉?非道之常,故必與時偕行也。”“意仁義”,有人認為“意”通“噫”,為嗟嘆之辭,而很多學者則認為,應該作動詞講,因為下文還有一句“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這樣聯系起來,則訓為“料想”更為恰當。這兩句話的意思是說:料想仁義不合乎人的自然本性吧,而那些推重仁義的人為什么總是顯得憂心忡忡呢?
無論是將駢結在一起的兩個足趾分開,還是斷掉多余的手指,這都會讓人哭泣流淚,這兩者相比正常情況,或少一個,或多一個,都不合正常之數,而多者少者所產生的憂愁卻是一樣的,這里的“憂”,聯系下文,應該不僅僅指駢枝者的憂,還有來自那些仁人、圣人憐生傷世表達出的對他們的憂。“蒿目”指眼睛用得發花,昏亂不明的樣子。那些仁人因為憂世讓自己眼睛都發花了,情況類似的,如因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勤勞至“腓無胈,脛無毛”(《天下》)的大禹,發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岳陽樓記》)之嘆的范仲淹,就是其中蒿目憂世的代表。而那些不仁之人,就用損害自然本性之中最純真的道德來追求榮華富貴。由此,可以料想仁義并不是人性本來道德所包含的真實內容,自夏商周三代以來,天下持續動蕩囂亂、久不安寧,都是由倡導追逐仁義所引起的吧。
這段文字在寫法上還有兩個方面需要注意。“彼正正者”一節文字主要是講“無所去憂”,這是從正面來講的;后面一節講仁人、不仁之人,雖然他們的做法不一,“其于憂一也”,又是從反面來講的,上下兩節,剛好形成一正一反,從正反兩方面更加全面論證了“不失性命之情”是“至正之道”這個主旨。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游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
“鉤繩規矩”原來指的是將改變物體形狀的四種工具,其分別對應生活中曲直圓方四種樣子。句意是說依靠外物來改變形體樣式的做法是殘害削減物體本性的。同樣,需要繩索膠漆來固定的,也并不是發揮了事物的本性,而是對本性還有侵害,因為這樣假借外物改變形體是壓制本性的表現。下文緊接著講“屈折禮樂”“呴俞仁義”,即是指為了表現禮樂,而屈折肢體,如不斷行拱手、跪拜之禮,同時還得假裝面露和顏悅色一副仁義的樣子,來安慰天下人的心,這同樣也是失去了事物本真面貌的。對于這樣的行為,《田子方》中就借溫伯雪子之口說“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進退一成規、一成矩”,表達出那些仁人君子崇尚繁重禮儀,而實際上人心簡陋,是舍本逐末的行為。我們要注意這里除了仁義之外,莊子又添出一個“禮樂”,這是前文所沒有提及的。而天下事物的真常自然之性是什么樣的呢?陸西星解釋“常然者,真常之性,渾然天成,不假安排布置而常自然”(《南華真經副墨》),結合文章就是指曲不用鉤彎,直不用繩定,圓不用規量,方不用矩比,依附一起的不用膠漆黏合,需要約束的不用繩索捆綁。這里的“離”通“麗”,附、離同義,均作依附講。“誘然”即“油然”,自然而然生長。天下事物油然而生而不知怎樣生,各有所得而不知為何緣由得,所以古今的道理都是一致的而并無不同,并不需要我們用外力外物去增添或虧損事物的本性。既然如此,仁義又何必連續不斷地像膠漆繩索一樣貫穿于道德行為之間,讓天下人迷惑昏亂呢!
此段寫出了仁義的無用而有害,最后一句用“奚……為”這樣一個古漢語里的固定結構來加強對仁義批判的語氣,認為仁義只會讓世人脫離常然本性,目迷心亂,這又何嘗不是一種“駢枝之道”。在莊子看來,道德是蘊含在自然本真當中的,相當于頑石中之玉,未經雕琢,又如原始混沌,這樣的狀態才是與大道吻合的道德,即前文提到的“至正之道”。寫法上,此段主要是批評仁義,段末又再次回應“道德”這個主題,同時,談仁義又帶出了新的議題——“惑”。于是,下文就仁義“惑”天下而展開。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圣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于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游。二人者,事業不同,其于亡羊均也。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于其間哉!
這段緊接著上文結尾談“惑”,并且是從“小惑”“大惑”兩個方面來談,文章學上把這種行文叫作“單起雙承”。具體來看,小一點的惑是迷惑了方向,大的惑就是迷失了自然本性,這個“性”就是前文提到的“常然”。接下來文章又是“雙起單承”,單從“大惑”下筆,也就是專講“大惑易性”,也意味著“易方”只是喻意,“易性”才是正意。這里用了虞舜的例子,莊子認為以仁義觀念迷惑、擾亂天下是從上古帝王虞舜開始的,“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義”,莊子感嘆這是用仁義為號來改變人的本性。然后繼續申論宣揚仁義的危害,夏商周三代以來,天下沒有不用“物”來改變自然本性的。需要注意這里的“物”指代什么,需要我們認真體會思考一番。我們現在所說的物,一般就指具有物質形態的事物,而《莊子》中那些脫離了自然本性的仁義道德,如名稱、是非、美惡等有人為觀念摻雜其中的都可以稱作物,所以書中就常會出現“外物”一詞,即外加給自然本性的都可以稱為“物”。《山木》云:“物物而不物于物,則胡可得而累邪?”這里莊子是說把外物看作普通事物,自己不被外物所役使,這樣又怎么會被外物所累呢?兩處所言的物的觀點可以相互參證、生發。由此,可以說莊子認為人應該把物當物,而不是役于物,用物來代替本性,成為自己的主人。從本篇行文來看,這里的“物”當是指仁義。小人殉利,士人殉名,大夫殉家邦,圣人殉天下。這里所列舉人的地位由低到高,層層推進,至于圣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圣人(這里指儒家圣人)代表著道德知識最高的標準、最高的人格典范,是理想人格的化身。他們所從事的事業不同,代表身份也相異,但在喪身失性方面卻是一樣的。
后面文章分別用“臧”“穀”牧羊的故事與伯夷、盜跖的例子來說明迷失本性與殘生傷性,不管是讀書、追求仁義等所謂正向的方面,還是從事游玩、盜竊等所謂負向的方面,不論是小人還是圣人,他們在“失其性命之情”這點上卻是一樣的。這里為了更好地理解寓言,需要提示幾個字詞的解釋。“臧”,漢代揚雄《方言》云:“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壻鄙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可以理解為奴隸。“穀”,指孺子。在這里均代指奴仆。“挾筴讀書”的“筴”,一種解釋為趕羊的牧羊杖,《左傳·文公十三年》有“繞朝贈之以策”的例子;另一種解釋為書冊,均可說通。“博塞以游”的“博塞”,通“簙簺”,是下棋類的一種游戲。臧與穀二人都在放羊,卻都把羊弄丟了,只不過一個是為了讀書,一個是因為游戲,但他們本業放羊而亡羊的結果卻是一樣的。故事里用讀書比喻追求仁義,博塞比喻逐利,用牧羊指保持人的自然本性的事業。這個小故事從結構上來說,是伯夷、盜跖例子的喻意,也是前面小人、士、大夫、圣人的喻意。下面則以伯夷與盜跖為例。伯夷義不食周粟,餓死于首陽山(今山西永濟縣南),盜跖為盜天下,死于東陵之上(在今山東境內),他們二人死的原因不一樣,一者為義,一者為利,但從殘生傷性的層面來看卻是一樣的。由是之故,則有必要肯定伯夷,而否定盜跖嗎?是謂“又惡取君子小人于其間哉!”“取”,區別、分別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這里將伯夷置于盜跖之后,表達出莊子認為伯夷所追求的仁義在世人看來是正面向上的東西,因此他殘生損性的程度更甚,他追求仁義的行為對于世人的影響更大,也更壞,因為小人之害易別,君子之害則難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又哪里需要區分君子、小人呢!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于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文章最后一段,先反后正,總括全篇旨意。一開始“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就回應文章開頭所批評的“淫僻于仁義之行”非至正之道,這里“屬”是系、從屬的意思。于是再次重申世俗所崇尚的代表天性某一方面的杰出人物,如代表仁義的曾參、史,代表識味的俞兒,代表耳聰的師曠,以及代表目明的離朱,這些優秀人物的獨特品質都不是真正地體現了自然性命之情,都是一種自然之外的“駢枝”,是應該被摒棄的。文章用排比的方式,從反正兩方面來論述,先反言何者非我所謂臧,然后再說我認為的臧是什么,即:“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意謂我所說的完善不是什么宣揚的仁義,而是本性完整,且能順應自然本性;我所說的聽覺敏銳不是能聽到什么曲調變化萬端,而是自然地用耳傾聽;我所說的視力清晰,不是能看見什么秋毫之末,而是放眼去觀察。概言之,莊子所說的道德完善就是順其自然天性,而非刻意、過度運用天賦官能。
后接著談論“自見”與“見彼”之道,即:“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那些善于明見他者而不自見,善于欣羨他人而不自賞的,都是在求外物而非順其自然性命之情,這就和盜跖、伯夷一樣,同樣是淫僻邪行,并不是應該追求的“至正之道”。此外,這幾句話的意思在《大宗師》中也有類似闡述:“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余、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最后作者表示自謙,說:“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有些人因為這句話而判斷本文非出自莊子之手,認為莊子哪肯為此謙語,這種說法值得大家思考。這一段在寫法上,前面由“明”“聰”“仁”帶出來一個“辨”,在這里減去“辨”添了一個“五味”,并且提到了“不自見”“不自得”,按照上文文意,這里可能省去了“不自聞”,后面又添加了“不自適其適”。最后現身說法,自呈謙詞,歸結到人性固有的道德之上,具有曲終奏雅之妙。全文反復申論何為“道德之正”,而在作者看來,在追求道德之正的過程中最主要的是摒斥“仁義”,因此文章最后也總結說:“愧乎道德”,不敢為“仁義之操”,這也呼應了開篇“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而非道德之正也”之語,在文章主題安排上實現了雙起雙收,同時添加“聰明”“巧辯”“禮樂”等道德“駢枝”,而使文章顯得豐富完整、跌宕多姿;在敘述上,批駁對象的安排又主次井然,過渡無痕,最終整篇文章達到說理透辟、圓融自然的地步,《山木》所謂“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可用來形容本篇的行文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