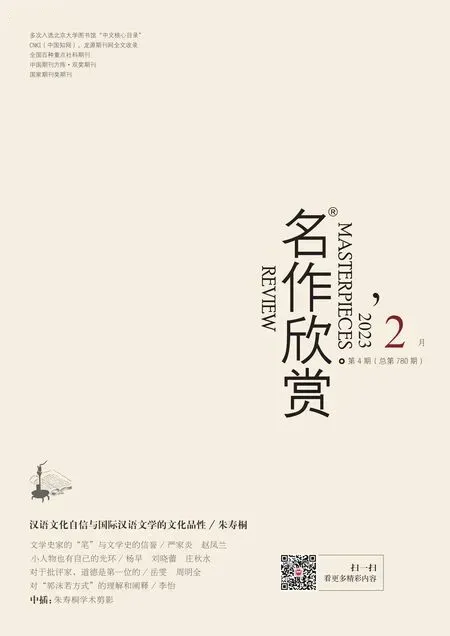《凱風》:孝子的悲傷
山西|劉毓慶
在《詩經》三百篇中,讀之最讓人心痛不已的是《邶風·凱風》篇。全詩共四章,原文如下: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從表面上看,這首詩并不難理解。凱風,即南風,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所以曰“凱風”。這里是以南風象征母氏對家庭的溫愛。棘心、棘薪,指酸棗樹的赤心和樹株。夭夭,少壯之貌。母氏,即母親。劬勞,謂辛苦勞累。圣善,聰明善良。令人,善人。寒泉,水名,在濮陽東南的浚城,這里是以寒泉浸潤浚土,喻母氏對子女之愛。母親用自己的勤苦,養大了七個子女,而七個子女,卻不能安慰一個母親。這讓孝子情何以堪!這便是孝子的傷痛之處。但問題出在哪里?緣何“有子七人,莫慰母心”?這則是關鍵所在。在中國古代各種關系中,最繁雜、最難理清的是家庭關系。因為家庭不是講理的地方,往往是情和理各參其半。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永遠說不清,故有諺曰“清官難斷家務事。”就此詩而言,兩千多年來,雖然人們都能感受到孝子那傷痛的心,反復詠讀,不禁泣涕如雨,但對其中的原委,也只能各憑猜測,臆想家庭矛盾中的種種可能性。
四家《詩》舊說
最早對《凱風》做清晰解釋的是《毛詩序》,其云:“《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美孝子”,這應該是經師相傳的古義。“衛之淫風流行”以下,則是經師續說。這續說故事應該是根據先代傳言而編織的,只是加入了價值判斷而已。“淫風流行”一說,顯然有強調貞節觀的意義,這與漢儒所編的《列女傳》是同一路數,在春秋時尚無此種觀念。至于“不安其室”云云,則是故事的內核。鄭玄箋《毛詩》,解釋“不安其室”為“欲去嫁也”。簡單地說,就是母親要改嫁,七個兒子自責沒有盡孝道,以自我懺悔的方式挽留母親。孟子說過:“《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孟子·告子上》)故朱熹說:“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詩序辨說》)《毛序》倡于前,朱說和于后,這便成了一種主流觀點。因為詩中提到了“母氏圣善”,既是“圣善”,何不能守節?于是后儒又圓其說云:“古今聰明婦人,如天后與南子盡不可及,然情欲究掩通辨之才,可惜將聰明錯使了也。”(顧懋樊:《桂林詩正》)
《毛詩序》母氏“不能安其室”而要改嫁的傳說,受到了后儒的批判、否定(詳后)。但如果結合《詩經》時代的習俗,并把經師傳說考慮在內,就會發現《毛詩序》并非完全沒有道理。母“不安其室”,這應該是一個很古老的傳說。《毛詩序》派與孟子十分密切。先秦諸子引《詩》與《毛詩序》皆有出入,唯有《孟子》引《詩》與《毛詩序》全合。《毛詩序》不可能不知道孟子所說的“親之過小”是什么意思。在“過小”這一價值判斷約束下,“欲去嫁”之說不可能憑空產生。從《左傳》中不難看出,貴族婦女改嫁者非一,而且此時看不到“貞節觀”的存在。在《詩經》的時代,很少見到“夫婦”或“夫妻”并提的情況,更多的則是用“男女”或“士女”代替。《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傳說:“男女同姓,其生不番。”這里的“男女”實指夫妻。《孟子·萬章上》說:“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這里的“男女”實際上指的也是夫妻。《鄭風·女曰雞鳴》:“女曰雞鳴,士曰昧旦。”《鄭箋》則云:“此夫婦相警覺。”此種情況甚多。戰國之后,情況發生變化。從《荀子》開始,到漢儒編撰的《禮記》,“夫妻”出現的頻率便大大增加。概念的變化,代表著人的意識與觀念的根本性改變。“男女”或“士女”,是生物性別角色,而“夫妻”或“夫婦”則是家庭角色,是家庭穩定的反映。女性貞節觀是為穩定家庭結構產生的。在先秦偶爾也可以看到人們對于貞節問題的認識,但只是對守貞節的女性表示贊許而已,如《戰國策·秦策》說:“貞女工巧,天下愿以為妃。”《史記·田單傳》記王斶說:“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從國家法律與輿論上,并沒有對此重視。《管子·五行篇》中有“不誅不貞”之語,為了人口的繁衍,對不貞的行為是不作苛求的。而秦漢之后,從統治者到儒家學者,都無不倡導女性的貞節。秦始皇巡狩各地,勒石為文,幾次提到貞節問題。如《泰山刻石》云:“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凈,施于后嗣。”《會稽刻石》云:“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佚,男女潔誠……妻為逃嫁,子不得母。”漢宣帝神爵四年,曾詔賜“貞婦順女帛”。漢安帝元初六年,詔賜“貞婦有節義十斛,甄表門閭”。劉向撰《列女傳》,系統整理了關于女性的傳聞,褒揚女子不事二夫,從一而終。《毛詩序》所謂“衛之淫風流行”,也正是在這樣的一種觀念背景下,根據先師“不安其室”的傳說產生的。否則,他們完全可選擇別的解釋,何必把這種不能守貞的行為與“圣善”之母聯系在一起呢?方玉潤《詩經原始》曾分析說:“故愚謂七子之母猶欲改節易操者,其中必有所廹。或因貧乏,或處患難,故不能堅守其志,幾至為俗所搖。然一聞子言,母念頓回,其惻然不忍別子之心,必有較子心而難舍者。而謂之為淫也得乎?不然,欲心已動,詎能速挽?故知其斷非為淫起見也。此詩之存,豈獨以美孝子,亦將以表賢母耳。”
《毛詩》之外的齊、韓、魯三家《詩》,關于《凱風》沒有留下系統的解釋。只是三家《詩》的承習者,在《詩》說的引述中,留下了一些蛛絲馬跡。清代學者曾為還原其說做過種種努力。據牟庭《詩切》對三家《詩》的研究,認為《凱風》與繼母有關。他首先對孟子所說的“親之過小”進行了分析。認為:“《小弁》,伯奇之父信后妻之讒,放殺其子,人倫之變,是過之大也。《凱風》,七子之母,性行嚴酷,不悅其子,非有放殺之慘,是過之小也。二者皆不得于親之詩,故孟子比例而論之。據趙注,知三家《詩》本無不安其室之說。察《毛傳》亦無此意。而衛宏作《序》乃云:‘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鄭箋》亦云:‘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此皆憑臆造謗,厚誣孝子之母。后儒遵守為說,而莫知其非,豈不惑哉!通而論之,‘《凱風》親之過小者也’,此古周之舊說也。《后漢書》肅宗賜東平憲王蒼書曰:‘送光烈皇后假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和帝詔清河孝王慶曰:‘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常有《蓼莪》《凱風》之哀。’《易林·咸之家人》曰:‘凱風無母,何恃何怙?’皆據三家《詩》,《凱風》為母亡之后,孝子哀思之詩。此先漢之誤說。與孟子已不合矣。而衛宏乃云‘不安其室’,此東漢以下之偽說也。此一詩三說,后學或不盡知。雖知之又不能強合也。今以《易林》證之,而知三說本無異也。《易林》曰:‘《凱風》無母,何恃何怙?幼孤弱子,為人所苦。’此用三家《詩》說。《凱風》為母沒之后,七子不見愛于后母,而作詩以自責也。則《后漢書》云‘《凱風》寒泉之思’,‘《蓼莪》《凱風》之哀’,皆謂哀思其亡母也。而孟子所云‘親之過小者’,謂后母也。后母不愛其前子,是為后母者之過也。自其子言之,不愛己身是親之過小者也。如此,則三家《詩》與孟子合矣。而衛宏序云‘不安其室者’,當謂后母無出,以不愛前子而有去志。此亦非無根之談。但不應妄言‘淫風流行’也。”牟氏對《后漢書》及《易林》有關資料的分析,很值得注意,只是后面繞了個大彎子。這個彎子主要是由遷就孟子及四家《詩》說造成的。
清之魏源也曾對《齊詩》遺說做過考證和推衍,不過結論與牟氏全不相同。其《詩古微》云:“《凱風》,美孝子也。七子不同母,母愛不均。七子自責,母遂感悟,化為慈母。故詩人美之。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親之過小者而怨,是不可幾也。’趙岐注:‘《凱風》言母心不說,是過之小也。’后漢江肱事繼母,感《凱風》之義,兄弟同枕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是明為七子不同母之證。而漢碑、漢詔、漢樂府皆引是詩,以頌母德之劬勞。”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亦云:“齊說曰:‘《凱風》無母,何恃何怙。幼孤弱子,為人所苦。’……《后漢·姜肱傳》: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感《凱風》之義,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據此則《易林》所稱無母而孤子‘為人所苦’者,人即繼母,故肱讀此詩而感其義也。魯韓說當與齊同。”
朝鮮尹廷琦《詩經講義續集》考三家遺說,得出的結論是“悼亡母”。其云:“詳究孟子語致,則蓋以不善于子為‘親過’。宜臼廢逐,為親過之大;則《凱風》之小過,即次于逐子,而為忿怒悍惡以加其子,是其過也。其母忿怒以拒其子孝養之誠,子不得以申其孝。母沒而七子追哀傷痛之。此詩之所以作也。《后漢·東平王傳》:‘賜光烈皇后遺衣一篋,以慰《凱風》之思。’則此以《凱風》為親歿后之追思也。又《章八王傳》遣諸王就國詔曰:‘弱冠相育,常有《凱風》之哀。’此亦以凱風為親歿而昆弟啣哀之詩。《凱風》者,其母既歿而追哀之詩也。”
因三家遺說零而不完,故各家從只言片語中揣摩、還原,自然會出現分歧。
宋元以下的新說
在《詩經》研究上,最大之弊在于務求創新。所謂務求創新,就是以“新”為價值取向,凡是前人曾經說過的自己再說,便覺得沒有意思,只有“立異”,才算標新,才有意義,于是新說叢出。今將其要者羅列于下。
一、媳婦不賢說。王質《詩總聞》云:“令人,賢婦也。七婦未必皆不賢,而其子憐其母,故責其婦也。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俞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幾也。’《凱風》之過,不能從其子之善意,必寡識者也。《小弁》之過,不能救其子之顛危,必寡情者也。此孟子所謂大小之別也。趙氏以謂:‘《凱風》言以慰母心,母心不悅,親之過小也。《小弁》言行有死人,尚或墐之,而曾不閔己,親之過大也。’此頗得孟子之意。”因婆媳矛盾而逼寡母改嫁者,民間比比有之。王質顯然是受此啟發而為此說的。
二、子念母勞說。宋劉克《詩說》說:“以詩辭求之,莫見其母之不安其室也。序詩者例以衛之淫風言之,及末章有‘莫慰母心’之辭,遂謂其母之不能安室也。然以事推之,一母而鞠七子,誠為勞苦也矣。其長育者七人,其間豈皆長育哉。由是言之,七子皆相若,念其母之至勞而為此詩也。”俞德鄰《佩韋齋輯聞》也說:“《凱風》,孟子謂親之過小者也。余友廬陵龍仁夫曰:是詩當于‘劬勞’一語觀之。夫以棘心之微,凱風吹之,至夭夭之盛,則母之撫我、育我,出入腹我,其劬勞亦甚矣。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況于小過而敢怨乎?故曰:‘母氏圣善,我無令人。’又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惟知自責,而一毫怨懟之意不萌焉。是非勉強矯飾而然也,皆天理人心之自然而發見者也。”
三、子不能悅母而自咎說。戴溪《續呂氏家塾讀詩記》說:“《凱風》,七子作也。凱風長養萬物,吹棘心而至于成薪,不以惡木而廢長養之功,雖倍費吹噓,不憚也。此七子自訟之辭,且懷其母之恩也。母有劬勞之恩,又有圣善之德,生子至于七人,獨無一人可當母意,若此可以自咎矣。寒泉清洌能以養人,為子不能逸其母。黃鳥好音能以悅人,為子不能娛其母。曾泉水之不如,禽鳥之不若,可謂痛自克責矣。”管世銘《韞山堂文集·凱風說》也說:“《凱風》為孝子之詩,親過之說,出于《孟子》。然謂之過小,度不過年老之人喜怒失節,虐使其子而已。其子深自咎責,惟媿己之不能悅母而絕怨懟之心。圣人列之于經,以教孝也。若如《序》《傳》所云,母生七子,而其子又皆能賦詩,母之齒亦長矣,必無不安其室之理。萬一有之,乃是人類之不祥,家庭之大變,安得謂之小過?孝子有不垂涕泣而諫之哉?漢章帝賜東平、瑯琊二王詔云:‘今送光烈皇后假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章帝之于經深矣,其引義必不當若是失倫。”
四、幾諫說。此說朱熹倡之,其云:“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為辭,婉辭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劉玉汝《詩纘緒》也說:“然母非實勞苦,而以勞苦為詞,故曰微指其事,而婉詞幾諫焉。”明儒郝敬更發揮之說:“此詩以凱風、棘心比何也?美其子之孝,則不忍斥其母之惡,故若為幾諫以達孝子和氣之衷。凱風以比和氣,棘小棗叢生,以比七子也。為孝子言,則凱風似母,棘心似子。為詩人言,則凱風、棘心,皆諷其母之微辭也。凱,樂也,物通淫曰風,棘之言急也。心,花蘂,俗云棗花多心,婦不貞之比,即性晚發,夏始生心,東風吹桃李,則男女及時,炎風至,桃李實落,而棘生心,非桃夭之時矣。母生七子,猶有淫行,詩人不忍言母老,而但言子晚成,勞凱風之吹,善諷喻也。棘雖非大材,叢生為籬,中赤而外多刺,比七子衛護一母也。二章比薪,三章比水,子雖無用亦足供薪水,豈其悅母不如黃鳥乎?黃鳥應節,又為審時之比也。”這是純粹的經學思維,照此解說,似乎字字暗藏玄機。
五、以七子不足恃說。明袁仁《毛詩或問》說:“或問《凱風》,曰:衛人有夫死,而以其七子不足恃,思再嫁者。七子悔罪自咎,以感其母,卒成守節之志。詩人歌以美之,此《凱風》所以錄也。”依此說,作者是第三者,而非七子。是母親感覺到兒子不足依靠,而非子真的不可依靠。
六、子奉養有闕說。明季本不同意改嫁之說,認為是兒子孝敬不周,導致母怒。其云:“衛有七子,不能安其母之心,故作此詩以自責,無怨言也。孟子曰:‘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幾也。’所謂過小,必奉養有闕,而其母憤怒,諸子欲自勞苦耳。非謂衛之淫風盛行,而其母欲嫁也。如此尚得為小過哉?自《小序》以后說《詩》者,蓋皆失之矣。”此說得到了不少人的呼應,如何楷云:“然夫有子七人,既皆成立,母年亦當邁矣,而尚欲嫁耶?《子貢傳》亦云:‘寡母欲去而子自訟焉,賦《凱風》。’《申培說》則云:‘邶人母不安其室,七子自咎而作。’總之勦襲序義,固不如季氏之說,較為近于人情。”但同時也受到質疑。如姚際恒說:“《大序》謂‘母不能安其室家’是也。季明德疑之,以為若時,豈得為‘小過’?因以為子闕奉養而母憤怒,要是杜撰。按孟子曰‘親之過小’,若子闕奉養而母憤怒,乃子之過,非親之過矣。過小云者,較《小弁》‘親之過大’而言。古婦人改適,亦為常事,故曰‘過小’。”
七、不能養母而自責說。賀貽孫《詩觸》說:“七子特以不能養母,故自責耳。其曰‘淫風流行’,謂衛多淫風,則其為共姜《柏舟》之風者寡,故母不能守志以安其室,非謂其母淫也。特毛、衛輩文字拙滯,詞不達意耳。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亦謂欲嫁之過小也。今人見‘淫風流行’四字,遂謂‘七子以母淫作詩自責’。夫以母淫作詩,雖曰‘自責’,與揚母之丑何異?豈得謂之孝子哉!”此是對當時“母淫”之說的修正。
八、自責以感母說。方苞《朱子詩義補》說:“一則曰‘母氏劬勞’,再則曰‘母氏勞苦’,非徒念母,亦使其母念育子之艱,而不忍去室也。一則曰‘有子七人’,再則曰‘有子七人’,非徒自責,亦使其母覺年歲已長,而顧惜名義也。” 許伯政《詩深》也說:“孝子自責以感母心,故詩人敘其志以美之。”
九、母與鄉黨爭子說。胡文英《詩經逢原》說:“衛之賢母,與鄉黨競七子,賦《凱風》。”又說:首章言“薰風正可解慍,而鄰里生荊棘,母氏苦與之較量也”。二章言“棘成薪而有芒刺也。彼棘薪,其不遜愈甚也。圣善母恐其子受害,而已當之也。……七子之婦,無能調停承順,亦以自責也”。第三章言“地寒而泉出不廣,以比家寒而不能沾溉鄉黨,致母氏爭競也”。第三章“簡簡鳥聲,喻幾諫復諫”。此說甚怪,可以說是自言自語,幾無從之者。
十、成母守義之志說。趙容《誦詩小識》說:“《凱風》,七子之母不安其室,此非欲嫁也。一母生七子,七子又當成立,能作詩自責之時,母年度已五十余,且六十余矣,胡為乎欲嫁也?夫背夫為不義,棄子為不慈,思嫁為宣淫,忘老為昧老,而孟子乃以為親之過小,又何也?觀序云:‘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鄭康成解之曰:‘母有嫁志,孝子自責以安母心,母遂不嫁。’然后知序之說極明,而鄭氏之解謬也。蓋志者,守義之志。成其志者,不負其勞苦守義之志也。此緣母以家貧勞苦之故,謂七子不能成立,使之身受勞苦,怒欲大歸,而終以七子之將順,自訟自克,足慰其心也。”此與諸家不同的是把欲改嫁換作了“怒欲大歸”。這樣既與孟子“過小”之論相合,又不違《毛詩序》“不安其室”說。這是就孟子與《毛詩序》間尋找平衡得出的結論。
十一、母不堪父虐而思去說。聞一多《詩經通義》說:“夫母以不堪父之虐待而思去,則咎不在母,故《孟子·告子下》篇以為‘親之過小’。趙注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說也,知親之過小也。’‘不悅’蓋即遇人不淑之意。《孟子》之意,蓋謂婦人當從一而終,今乃欲舍其夫與七子而去,則失為妻為母之道,此其所以為過也,特以其被迫至此,故又為過之小者。”“母以不堪父之虐待而思去”,既不見于古之傳說,也不見于詩中敘述,顯系臆測。
以上諸說,基本上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根據現實生活中的經驗還原詩旨。所羅列出的種種可能,其實都是中國社會中錯綜復雜的家庭矛盾的反映。盡管未必符合詩之本義,但對于我們了解生活在中國傳統家庭矛盾中的每個個體不同的心理感受和生活態度,還是有一定意義的。無論家庭矛盾多么繁雜,無論處于何種無奈的境地,“孝”都是每個人必須堅守的道德原則。
《凱風》的情感世界
《凱風》一詩千載之下讀之,猶使人涕零,這并不在于它藝術表現多么超眾,而在于其所蘊含的倫理道德力量。中國詩歌的一大特點,就在于它的倫理道德內涵。詩中所展示的情感世界,往往充盈著人類向上與向善的精神力量。大概西方文學中所著力的愛情,在中國文學中多半會與善良、溫厚結緣。中國人對于世界的認識,多半不是向外索取,而是自省。在情感的世界里,嚴責己而寬待人,從自我反省中,發現自己的道德不足,從而訴諸情感表達,給讀者以強大的自察自省自新的力量。在這首詩中,盡管我們難以確定這位自責的孝子,其內心真正糾結之所在,但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對于給予自己生命、養育自己成長的母親的深深之愛,以及他無力解除母親內心痛苦的無限悲傷。在無奈之中,他不是責世界對己不公,而是“自責”無能為力。
諸多《詩經》研究者從“自責”這一意義出發,在發掘詩中的倫理道德蘊含時,也在不時地做深刻的自我反思,從而強化著詩的情感張力與道德說服力。如宋之袁燮云:“責人而不責己,則本原之地用志不篤,見善不遷,有過不改,而感格之至,邈不可冀。修已而不責人,則朝夕思念,求所以齟齬不合者,誰實為之。積其誠意,自足以感人動物,此得失之所以殊也。……母子之際,人所難言,順從則害義,諫止則傷思。惟有反躬自責,不以為母之過,而以為己之咎,則庶乎其足以感動矣。故曰‘母氏圣善,我無令人’。泉之清寒者,能使人甘之。鳥之好音者,能使人樂之。而我獨不能慰其母,是豈母之罪哉?比之凱風,其稱甚美,而寒泉、黃鳥之不若,其自責也深矣。負罪引慝,此舜所以為大孝。”(《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二)這里所說的不只是當如何做孝子的問題,而是包括做人,面對問題當如何思考。責己則能修己,修己方能化人,這是中國經典中反復出現的邏輯。明之朱善,則從為人子當如何孝敬父母的角度,來認識其意義。其云:“母之于子,其乳哺之恩,抱負之勤,必三年而后免,而具長育教誨之功不與焉。七其三年,則為二十一年矣。以二十一年乳哺之勞,抱負之苦,而又俟其成立,則顏色之榮華者,亦已悴矣;氣力之壯盛者,亦已衰矣,此正母老受養之時,人子報恩之日也。而乃或不安其室焉。雖曰母以淫風流行之故,無亦七子之事其親,果有未盡善者乎?使七子之中果無一人之不盡善,則必能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而非僻之心無自萌矣。既不能先意承志,以消弭其過于未萌,及其過之已形也,乃悔悟而自責,吁已晚矣。君子取之,亦以其猶賢于冥然,悍然全不悔悟,而不能自責者云爾。而或者乃引大舜負罪引慝之事以明之。噫!舜有不可事之親,而乃能使之變惡以為善;七子之親非必不可事也,而不能潛消默止其過于冥冥之中,是豈可與大舜同日語哉。為人子者,必知此義,而后可與言事親矣。”(《詩解頤》卷一)明顧懋樊《桂林詩正》則從為子者當如何對待父母的態度上立說,其云:“天下無不是底父母。臣弒君,子弒父,多只見君父有不是處。此章開口說‘母氏圣善’,實實見得母底是,已底不是,方為真孝,非世俗打掃作門面說。韓愈作《文王羑里操》云:‘臣罪當誅,天王圣明。’正此解。”這些體會大大豐富了《凱風》的情感世界與道德內涵。
人對子女的愛,這是本能;對父母的孝,這是人性。孔子的高徒有子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孝”是人性生長的基礎。人一生下來首先接觸的人就是自己的父母,而其愛心的萌芽,便是在與父母的相處中展現的,這愛的具體體現便是“孝”。其次便是對兄弟姐妹及其他長輩的愛——“悌”。在家庭環境中培養起來的愛心,是人生道德的基礎。推而至于社會,便會表現為對所有人的尊重、關切,如對上司、同事的尊敬與友善等。“君子務本”,這“本”就是“孝悌”。由“孝悌”的親親之道,推己及人,由近及遠,就可逐漸進身于人格的最高境界——仁的境界。孔子說:“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孔子家語·弟子行》)所以中國文化中特別強調“孝”。而此篇的孝子自責,所展現的正是為孝之道的一種典范。
這里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對母德的贊美。詩一再言“母氏圣善”“母氏劬勞”“母氏勞苦”,即表達了兒子對母親的感戴,也反映了母親的勤勞、善良。這是作為孝子對母德應有的基本認識。二是對自己不足的檢討。詩一再說“我無令人”“有子七人,母氏勞苦”“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表達了一位孝子內心的愧疚。在對待父母的問題上,兒子沒有資格自夸付出和貢獻,因為父母對子女之恩,是子女無論如何都報答不完的。只有永遠處于“自責”的心理狀態,才能永遠銘記父母的養育之恩而無懈于奉養。“孝”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正是在這樣的心理狀態下,才得以承傳的。
從藝術的角度言,全詩四章,首章言母勞。連用三句比喻,末句始點出“母氏”二字,給人以心情沉重之感。輔廣《詩童子問》云:“以凱風直比其母,以棘心直比其子之幼時。下更不言所比之事,故曰‘母氏劬勞’,則是言其母之病苦而已。然七子之作此詩,非徒為是言也。必其心之誠實,見其母之恩,真若凱風之生養萬物;而已身幼少之時,真若棘心之夭夭然難長而未成。然后真知其母之病苦,而自責其不能成母之善志也。”姜文燦《詩經正解》云:“首三句喻母育子之恩,末句嘆其勞也。此即凱風吹棘心于少好之時,比慈母育眾子于童稚之日也。劬勞只就幼時說,蓋此本其始言之也。夫母既劬勞,則子當孝,故曰起自責之端。”
二章自責。通篇精神在“母氏圣善”二句。“母氏勞苦”“莫慰母心”,皆從此生出。鐘惺曰:“棘心、棘薪,易一字,而意各入妙。古人用筆如此。”無名氏曰“‘母氏圣善,我無令人’,‘天王圣明,臣罪當誅’,千載同心,亦復同調。” 《詩義折中》云:“言吹棘心,而至于成薪,則凱風至仁,而薪非美材,有負于風。養七子而至于成立,則母氏圣善,而子無令人,有愧于母也。”
三章責不能養母。冉覲祖《詩經詳說》云:“‘爰有寒泉’,一水流耳。‘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于浚,而邑人賴之以生養矣。況有子七人,皆生于母者也,反不能奉養一母,而使之勞苦不得自安適乎?曾寒泉之不如也矣。”
末章責不能安母之心。以鳥有好音娛人,反喻子無令詞慰母。姜文燦《詩經正解》云:“黃鳥猶能悅人,興子寔不能悅母。總見無令人也。‘莫慰母心’,言其心不免于經營,承歡無道。此與上章,俱要得自惡自艾口氣。”牛運震《詩志》云:“末章特自托于黃鳥之好音,以慰其母爾。卻說莫慰母心,深婉入妙。”
詩中反復強調母親的深恩,而字里行間卻充滿著苦楚,既言“我無令人”,再言“莫慰母心”,而卻不說出所以然來,其中自有難言的“家丑”。黃文煥《詩經嫏嬛》從幾諫的角度分析詩之藝術說:“首章是喻母有育子之恩,以起自責之端。下三章是興子無報親之孝,以致自責之寔。通詩以‘我無令人’為主,下‘母氏勞苦’‘莫慰母心’,正見‘無令’處。蓋一心自責,而諷母之意婉然不露,孝子之深恩也。”牛運震《詩志》則云:“苦在說不出卻又忍不得,算來惟有自責一著,而委曲微婉,更與尋常自責不同。悲而不激,慕而不怨,為孝子立言,故應如是。”李灝《詩說活參》說:“述‘母氏勞苦’,所以觸母心之惻怛。述‘我無令人’,所以動母心之哀傷。終云‘莫慰母心’,正所以深慰母心。有子如此,尚頑然不感泣回心者,非人也。詩可以興,其信然哉。”方宗誠《說詩章義》則從“孝子自責”上立說而分析之云:“以‘凱風’比母,見母之慈。以‘棘心’自比,見己之不才。‘吹’字形容母之撫摩鞠育,妙!妙!‘寒泉’‘黃鳥’,是反比己之不如。通篇情詞懇切,纏綿、沈郁、深厚。真孝子也!”日本竹添光鴻《毛詩會箋》則從詩之用喻立說云:“以‘凱風’喻母氏顧養,恩同天地之施。言‘吹心’,喻襁褓之誠求;言‘夭夭’,喻孩抱之色笑。二章為薪,喻無令人。三章勞苦,見不能有益于母。卒章‘莫慰’,見不能善其容聲也。”這些分析,雖未皆得詩意,但皆妙趣。可作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