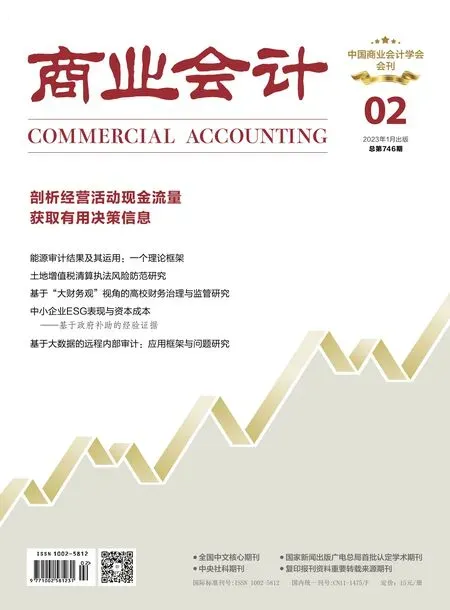剖析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獲取有用決策信息
馬永義 (教授) (北京國家會計學院 北京 101312)
比對利潤表“凈利潤”項目和現金流量表“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以下簡稱經營現金凈流量)項目的金額已經成為企業財務報表分析的必由之路,但究竟應該從哪些視角進行比對、通過比對能夠獲取哪些有助于利益相關者決策的信息,從實務角度而言,恐怕就仁智各異了。本文擬談談筆者對此話題的思考,與同行們一同探討。
一、凈利潤與經營現金凈流量相互關系的簡要概述
筆者習慣于將凈利潤(以下簡稱前者)與經營現金凈流量(以下簡稱后者)的相互關系描述為:有關聯、不相等、調整后應相等。
兩者之間之所以“有關聯”,是因為兩者均與經營活動相關,前者反映的是經營活動實現的凈損益情況,后者反映的是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量狀況;兩者之間之所以“不相等”,是因為兩者遵循不同的計量基礎,前者遵循的是權責發生制,后者遵循的是收付實現制,對同一交易事項的確認和計量,權責發生制與收付實現制存在時間或金額上的差異;兩者之間之所以“調整后應相等”,是驗證兩者之間是否維系固有勾稽關系的技術性需要,如果在凈利潤金額基礎上經過規定路徑的調整后,所得金額與經營現金凈流量相等,就意味著兩者之間維系著固有的勾稽關系,反之,就意味著利潤表或現金流量表的編制存在技術性差錯。
既然不相等是兩者金額之間的常態,那么,透過兩者之間的不同相對狀態,能夠獲取哪些重要信息呢?人們圍繞兩者金額之間的相對狀態,達成了哪些共識呢?業界普遍認為,當后者大于前者時,通常意味著企業凈利潤的含金量比較高、現銷能力較強、商業信用利用得較為充分、會計政策較為穩健;反之,當后者小于前者時,通常意味著企業凈利潤的含金量較差、賒銷占比較高、商業信用利用得比較欠缺、會計政策較為激進;當前者金額為正數,后者金額為負數時,通常意味著企業賒銷政策極端冒進或者貨款回收不夠理想,也有可能存在利潤操縱之嫌。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經營活動、投資活動、籌資活動現金流量中各自存在“收到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投資活動、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支付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投資活動、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兩類“兜底性”項目,實務工作中,通常會出現通過操縱“收到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或“支付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項目來虛增或粉飾經營現金凈流量的現象,借此來迎合業界所達成的上述共識。各類報表閱讀者要有意識地獲取現金流量表附注中,關于“收到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和“支付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項目的相關陳述與說明,以便從中甄別出“蛛絲馬跡”,尤其在這兩個項目的絕對金額較大時,更應緊盯不放。當后者與前者相比的倍數值較大時,如果在下一會計年度的年初出現集中大額支付關聯方應付款項的跡象,通常就意味著上年度經營現金凈流量存在被粉飾的可能性。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在財務報表分析實務中,對于業界圍繞凈利潤與經營現金凈流量之間相對金額狀況所達成的共識,也不宜做絕對化認同或片面化理解。有些行業的經營活動現金流量,呈現出明顯的季節性特征,除了依循上述業界共識,分析同一會計期間的凈利潤和經營現金凈流量外,還需要通過不同時期的縱向比較,識別出該行業(企業)經營活動現金流量的季節性特征,進而做出更加科學合理的判斷。
此外,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下,部分高科技企業的主要客戶是依托財政撥款運行的行業主管部門,鑒于各級財政撥款具有明顯的規律性、季節性特征,在分析此類高科技企業經營活動現金流量時,有必要兼顧其季節性特征做出綜合研判。
二、交叉比對利潤表和現金流量的相關聯項目,獲取有用決策信息
除了直接比對凈利潤和經營現金凈流量外,通過進一步比對利潤表和現金流量的相關聯項目,還可以挖掘出更多的有助于決策的有用信息。
通過比對利潤表“營業收入”項目的金額和現金流量表“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收到的現金”項目的金額,可以對企業銷售業務獲取貨幣資金的能力做出研判。如果后者大于前者,就表明企業銷售業務非賒銷占比較高、銷售業務變現能力較強、市場占有率相對較高、產業鏈中的話語權較強;如果后者小于前者,就表明銷售業務賒銷占比較高、產業鏈中的話語權較弱、銷售業務變現能力較差、貨款回收不夠理想。如果各會計期末應收賬款占流動資產總額的百分比在逐年上升,就表明企業貨款回收能力在逐步惡化,所面臨的信用風險在逐步增大。
通過比對利潤表“營業成本”項目的金額和現金流量表“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項目的金額,可以對企業運營效率和貨幣資金周轉能力做出研判。如果后者大于前者,通常就意味著企業運營效率相對較低、采購生產銷售各環節的銜接不夠順暢。如果各會計期末存貨占流動資產總額的百分比逐年上升,就表明存貨增長占用資金過多、市場風險在增大。
通過比對“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占“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收到的現金”的百分比和毛利率,可以對毛利率的含金量做出研判。如果前者小于后者,就意味著企業毛利率的含金量較高、商業信用利用得較為充分、面對客戶或供應商具有較強的話語權;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就意味著企業毛利率的含金量相對較低、商業信用利用得較為欠缺、面對供應商或客戶具有相對較弱的話語權。
三、關注凈利潤與經營現金凈流量之間的調節信息,深度挖掘有用信息
我國現金流量表采用直接法進行編制,同時要求在報表附注中披露把凈利潤調節為經營現金凈流量的相關信息,伴隨企業會計準則體系的不斷演進,需要調整的具體項目也幾經調整。
從技術和實務層面而言,由于調整項目含有兜底性的“其他”項目,經調節后凈利潤不等于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的現象幾乎不會出現。在某種程度上而言,這也恰恰導致了業界對該調節信息缺乏足夠的關注熱情。
需要強調并著重指出的是,如果將關注的視野鎖定調節過程或具體調節項目上,同時注重與其他相關信息的相互印證,就可以挖掘出更多的有助于科學決策的信息。
在企業會計準則體系框架下,把凈利潤調節為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凈流量的信息(以下簡稱“調整信息”)是在現金流量表的附注中披露的。自2006年發布以來,《企業會計準則第31號——現金流量表》及其應用指南(以下簡稱31號準則及指南)尚未進行過修訂,盡管2017年至2019年財政部陸續發布了一般企業報表格式修訂的通知,然而這些通知并未涉及隸屬于現金流量表附注層次的“調整信息”,但筆者注意到,目前上市公司年報中所披露的“調整信息”(以下簡稱“最新調整信息”)中的調整項目已經與31號準則及指南有所不同了。本著實務優先原則,本文以“最新調整信息”為依托,在適當分類的基礎上加以具體剖析。
(一)關于“資產減值準備”項目的調整成因及其影響剖析
自2006年以來,由于官方確立的“調整信息”并未進行過修訂,上市公司所披露的“最新調整信息”之間,也就存在著細微差異。筆者發現,有的上市公司在“資產減值準備”項目中所披露的調整內容包括了“信用減值損失”,有的上市公司將“資產減值準備”和“信用減值損失”分別加以列示,本文分別對資產減值準備和信用減值損失加以剖析。
1.資產減值準備。在我國現行企業會計準則體系框架下,各項資產的后續計量規則嚴格依照《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所界定的資產定義來加以確立,因而就出現了資產減值準備“遍地開花”的局面。
需要強調的是,盡管官方確立的“調整信息”中被冠以“資產減值準備”,但從更嚴格的意義上而言,如果由“資產減值損失”取代“資產減值準備”,會更有助于從理論角度加以闡釋,也更有助于實務界的理解和執行。
由于涉及到計提減值準備的資產“遍地開花”,加之有的資產在計提減值準備后,允許在規定范圍內轉回,有的資產在計提減值準備后,不準許轉回,資產減值準備又涉及到計提、轉回、轉銷(核銷)等多個環節。從會計科目設置的角度而言,也涉及到“存貨跌價準備”“固定資產減值準備”等若干個會計科目。從賬務處理角度來加以研判,各項資產減值準備科目與利潤表的“凈利潤”相去甚遠。
綜合考量上述因素,筆者認為,用“資產減值損失”項目取代“資產減值準備”項目,是更加科學、合理、可行的路徑選擇。
從科目對應關系和相關賬務處理可以得知,“資產減值損失”科目應按期結轉“本年利潤”科目,與此相呼應,“資產減值損失”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凈利潤”的構成項目。盡管“資產減值損失”影響到了“凈利潤”,但并不存在與“資產減值損失”項目相對應的現金流出,因此,在“調整信息”中應將其作為“加:”計項目予以列示。
在財務報表分析過程中,建議注意比對“調整信息”中的“資產減值準備”項目和利潤表的“資產減值損失”項目,在正常情況下,兩者之間的金額應該是相等的,通過觀察兩者之間是否維系著勾稽關系,也可以對該企業財務報表編制是否存在技術性差錯來加以研判。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資產減值損失對凈利潤產生了影響,但并未影響到企業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同時也與企業本會計期間供產銷的“基本面”無直接關聯,但本會計期間計提或列支的“資產減值損失”金額,確實會對企業相關存量資產的未來變現能力形成理論上或事實上的負面影響。盡管“資產減值損失”項目無關本會計期間的“基本面”,但借助該項目確實可以實現操縱或平滑年度間凈利潤水平的目標,當圍繞各類監管或考核指標出現了“擦邊球”現象,且年度間該項目的絕對金額或占營業收入的百分比出現巨幅變動時,各類報表閱讀者尤其要注意甄別和有效應對。
2.信用減值損失。“信用減值損失”是《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以下簡稱新22號準則)應用指南(2018)中新增設的會計科目,該科目用來核算企業按照新22號準則要求計提的各項金融資產減值準備所形成的預期信用損失。
需要指出的是,在啟用“信用減值損失”科目以前,企業各項金融資產所計提的減值準備一并納入“資產減值損失”科目予以核算。筆者認為,之所以單獨啟用“信用減值損失”科目,是因為各項金融資產所面臨的價格變動風險或不確定性要遠遠大于非金融資產,在判定金融資產是否存在減值跡象時,新22號準則除了要回顧過去、著眼現在外,還需要展望未來,換言之,需要在更長的時間窗口期內來識別是否存在減值跡象。此外,在測算減值準備金額時,還需要采用統計學上的期望值法,以便對各項金融資產減值做出更加科學合理且更加謹慎的估計。
筆者認為,既然已經單獨設置了“信用減值損失”科目,在“調整信息”中就有必要單獨列示“信用減值損失”項目,以便報表閱讀者從更加寬泛的視角,對企業各項金融資產減值準備計提的合理性做出研判。
依據“信用減值損失”科目的使用說明,該科目應按期結轉“本年利潤”科目,與此相呼應,在官方確立的利潤表格式中,“信用減值損失”就成為了單獨列示的項目。盡管“信用減值損失”影響到了“凈利潤”,但并未發生與之相關聯的現金流出。因此,在“調整信息”中,應將其作為“凈利潤”的“加:”計項目予以列示。
在財務報表分析過程中,應注意比對“調整信息”中的“信用減值損失”項目和利潤表的“信用減值損失”項目,兩者之間的金額通常應該是相等的,通過觀察兩者之間是否維系著勾稽關系,同樣也可以對該企業財務報表的編制是否存在低級性差錯來加以研判。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信用減值損失也與本會計期間供產銷的“基本面”無直接關聯,也沒有對本會計期間的經營活動現金流量帶來任何影響,但本會計期間列支的“信用減值損失”確實很有可能會對相關金融資產未來變現能力產生重大的實質性影響,進而對企業未來的償債能力和流動性風險產生連帶影響。此外,本期列支的“信用減值損失”金額,也會對終止確認相關金融資產會計期間的凈利潤產生實質性影響,本會計期間各項金融資產減值準備計提環節的任何主觀故意所為,均會對年度間凈利潤的可比性施加人為干預或影響。
(二)長期資產折舊或攤銷類項目的調整成因及影響剖析
在“調整信息”中分別設有“固定資產折舊、油氣資產折舊、生產性生物資產折舊”“使用權資產攤銷”“無形資產攤銷”“長期待攤費用攤銷”等與長期資產相關的折舊或攤銷類項目,由于這些項目具有相同的調整成因和計算規則,本文將其并稱為長期資產折舊或攤銷類項目一并加以剖析。
由于計提各項長期資產折舊或攤銷時,應借記相關成本費用類會計科目,各成本費用類會計科目應按期結轉“本年利潤”科目,與此相呼應,在利潤表中分別通過“營業成本”“銷售費用”“管理費用”“研發費用”項目(以下簡稱“相關費用類項目”)對“凈利潤”產生了相應的影響,然而源于各項長期資產折舊或攤銷而形成的“相關費用類項目”并未發生相應的現金流出,因此,在“調整信息”中,應作為“凈利潤”的“加:”計項目予以列示。
需要著重提醒并指出的是,將“調整信息”中的“相關費用類項目”的金額除以各對應項目計提基數(對固定資產而言,指的是固定資產原值)的月加權平均金額(注:可通過資產負債表附注中披露的相關信息加以計算后獲取),就可以計算出財務報表層面實際體現出的各項長期資產年度加權平均折舊率或攤銷率(以下簡稱“結果1”)。此外,通過企業所披露的各項資產的折舊或攤銷政策(應換算成百分數),結合企業各該項長期資產內部結構性占比,就可以推算出基于企業會計政策的各項長期資產的年度加權平均折舊率或攤銷率(以下簡稱“結果2”)。如果“結果1”小于“結果2”,通常就有理由判定或懷疑該企業存在長期資產折舊或攤銷不足的跡象,也意味著該企業并未嚴格執行其所披露的會計政策,同時也標志著該企業存在粉飾“營業利潤”“利潤總額”“凈利潤”的嫌疑。一旦企業沒有嚴格執行與各項長期資產相關的會計政策,就意味著該企業的誠信度存在較大程度的“瑕疵”,需要引起各類報表閱讀者的高度警覺和有效防范。
(三)長期資產處置或報廢類項目的調整成因及影響剖析
“調整信息”中設有“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的損失(收益以“-”號填列)”項目和“固定資產報廢損失(收益以“-”號填列)”項目,由于這兩個項目的調整成因和計算機理基本一致,本文將其合稱為長期資產處置或報廢類項目并加以剖析。
1.長期資產處置類項目的調整成因及影響。伴隨《企業會計準則第42號——持有待售的非流動資產、處置組和終止經營》及其應用指南的發布,企業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所形成的損益一并納入“資產處置損益”科目予以核算(注:其他資產包括在建工程、生產性生物資產以及劃分為持有待售的非流動資產或處置組中的資產)。與此相呼應,官方確立的利潤表中相應地單獨增設了“資產處置收益”(損失以“-”號填列)項目。“資產處置損益”科目具有收益和損失的雙重屬性,但“資產處置收益”項目作為利潤表中營業利潤計算過程中的“加:”計項目,通常填列的是資產處置收益,如果實際發生了資產處置損失,則需要以“-”號填列。
需要提醒的是,“資產處置收益”項目所列示的內容實質上屬于各項長期資產處置所發生的凈損益,如果實際發生的各項長期資產的處置收益總額與處置損失總額之間的差異不大,盡管利潤表上列示的該項目金額不大,但實際發生的長期資產處置規模和處置收益或損失金額卻遠非如此,在利潤表分析過程中要注意該項目報表附注中所披露的相關信息,以便更加準確地評判非流動資產處置所帶來的影響。
盡管“資產處置收益”項目被納入了營業利潤的構成要素,但該類損益的發生不具有持續性和穩定性,對于該項目所列報的金額,不宜過喜也不宜過悲。但不容否認的是,發生長期資產處置不可避免地會對未來持續經營能力產生聯動性影響。如果一家上市公司利潤總額或凈利潤出現了圍繞相關關鍵監管指標“走鋼絲”的跡象,且“資產處置收益”項目又“功不可沒”時,各類利益相關者對此要高度警覺。
從賬務處理過程中,我們不難獲悉,“資產處置損益”科目應按期結轉到“本年利潤”科目,“資產處置收益”項目相對應地也影響到了“凈利潤”,但該影響因素所形成的凈利潤份額,實質上是來自于相關長期資產的結轉,并不存在相對應的現金流入或流出,因此,在“調整信息”中應予以調整。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資產處置損益”科目核算的是多項相關長期資產處置所發生的損益,加之“調整信息”中所單獨列示的項目均被作為對“凈利潤”的“加:”計項目來加以列示,在“調整信息”中與“資產處置損益”科目或利潤表“資產處置收益”項目相對應的調整項目就被命名為“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的損失(收益以“-”號填列)”(以下簡稱“該項目”)。
順便指出的是,在分析“調整信息”過程中,要注意比對“該項目”與利潤表中“資產處置收益”項目金額間的勾稽關系,以便對財務報表編制是否存在低級的技術性差錯加以甄別。
2.“固定資產報廢損失”項目的調整成因及影響。固定資產報廢所形成的損失或收益被結轉到“營業外支出”科目或“營業外收入”科目,“營業外支出”和“營業外收入”科目應按期結轉到“本年利潤”科目,而“營業外收入”項目和“營業外支出”項目是一以貫之的利潤表中單列項目,并分別影響到了“凈利潤”。
從賬務處理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感知,此類“營業外收入”或“營業外支出”來源于尚未通過成本費用加以補償的固定資產賬面價值的結轉,該部分“營業外收入”或“營業外支出”并無對應的現金流入或流出。因此,在“調整信息”中,應予以列示。鑒于“調整信息”中的所有單列項目均被設定為“加:”計項目,與固定資產報廢相關的調整事項就被冠以“固定資產報廢損失(收益以“-”填列)”。
在分析“調整信息”時,也需要注意該單列項目與利潤表“營業外收入”和“營業外支出”項目的綜合比對,以便識別該企業財務報表的編制是否存在技術性差錯。
(四)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調整成因及影響剖析
在企業會計準則體系框架下,有多個資產類具體準則要求采用公允價值進行后續計量,且要求將公允價值變動計入當期損益。此外,《企業會計準則第39號——公允價值計量》對金融資產和非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計量方法做出了具體規范。
“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作為單獨設置的損益類會計科目,應按期結轉“本年利潤”科目,與此相呼應,“公允價值變動收益”也成為了利潤表中構成“營業利潤”的單列項目,因而也影響到了“凈利潤”項目的金額。
盡管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影響到了“凈利潤”項目的金額,但并不存在與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相對應的貨幣資金的流入或流出,因此,在“調整信息”中應予以體現。與上述其他調整項目的列報方式相類似,作為統一的“加:”計項目,在“調整信息”中就被冠以“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公允價值變動損益除了并未對經營活動現金流量帶來影響外,也與企業“基本面”無直接關聯,但該變動確實影響到了“凈利潤”,只要相關投資未終止確認,相關公允價值的變動就會對企業的利潤表帶來無法主動施加干預的持續性影響。從企業管理角度而言,管理層應關注相關投資的公允價值變動趨勢,既不應“掩耳盜鈴”,也不宜“望梅止渴”。
作為報表閱讀者或利益相關者,要意識到公允價值變動具有持續波動性、被動承受性、尚未變現性等特征。
(五)類別間重復因素的調整成因剖析
與籌資活動相關的財務費用以及與投資活動相關的投資收益類屬利潤表中營業利潤、利潤總額、凈利潤的構成要素,但在現金流量表中,償付利息支付的現金和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分別類屬籌資活動的現金流出和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入,因而,在計算經營現金凈流量時,就不應包含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和支付利息付出的現金,否則就會重復計算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和支付利息付出的現金,同時也無法維系現金流量表與資產負債表之間的勾稽關系。因此,在“調整信息”中,就需要對凈利潤中的與財務費用和投資收益相關的份額加以調整。有鑒于此,本文將財務費用和投資收益的調整并稱為類別間重復因素的調整。由于“調整信息”中的調整項目均采取“加:”計方式列示,結合財務費用、投資收益與凈利潤之間的內在影響機理,“調整信息”中分別將其確立為“財務費用(收益以“-”號列示)”“投資損失(收益以“-”號列示)”。
需要著重提醒并指出的是,利潤表中列示的“財務費用”和“投資收益”采用的是權責發生制計量基礎,但“調整信息”中的“財務費用”和“投資損失”只能選取收付實現制計量口徑,在填列“調整信息”過程中,應注意對計量基礎口徑的把握。換言之,不能簡單地將利潤表中“財務費用”和“投資收益”項目的列示金額照抄到“調整信息”的“財務費用”和“投資損失”項目上。
(六)遞延所得稅調整的成因和影響剖析
從技術層面而言,與遞延所得稅相關的調整項目,理解起來難度較大。《企業會計準則第18號——所得稅》(以下簡稱18號準則)要求必須采用納稅影響會計法來核算企業所得稅,既要核算“所得稅費用——當期所得稅費用”(以下簡稱“當期所得稅費用”),又要核算“所得稅費用——遞延所得稅費用”(以下簡稱“遞延所得稅費用”)。
從科目對應關系上而言,計提當期所得稅費用時,“當期所得稅費用”與“應交稅費——應交企業所得稅”相對應;繳納所得稅費用時,同時核減了“應交稅費”和“銀行存款”,在現金流量表中就體現在“支付的各項稅費”項目中。需要注意的是,實務工作中,計提當期所得稅費用和實際繳納企業所得稅費用有可能存在時間差。
由于資產類科目和負債類科目的賬面價值和計稅基礎之間存在差異(以下簡稱兩者差異),在納稅影響會計法下,“遞延所得稅費用”是通過兩者差異乘以企業適用的所得稅稅率計算獲取的。從賬務處理的角度而言,“遞延所得稅費用”科目與“遞延所得稅資產”或“遞延所得稅負債”科目相對應。盡管“遞延所得稅費用”科目按期結轉到了“本年利潤”科目,利潤表中的“所得稅費用”也含有“遞延所得稅費用”的影響因素,但本會計期間并不存在與“遞延所得稅費用”相對應的現金流出。因此,在“調整信息”中應予以調整。
需要強調的是,在對“遞延所得稅費用”的影響因素予以調整時,應通過與該科目存在對應關系的“遞延所得稅資產”或“遞延所得稅負債”科目來間接加以計算。而“遞延所得稅資產”和“遞延所得稅負債”科目的本期發生額,均是通過各該科目期末累計余額和期初累計余額的差額倒擠出來的,因此需要通過比較資產負債表“遞延所得稅資產”項目和“遞延所得稅負債”項目期末余額和期初余額來加以判斷。
如果“遞延所得稅資產”項目的期末余額小于期初余額,即遞延所得是資產減少時,貸記“遞延所得稅資產”科目時,應同時借記“遞延所得稅費用”科目,此舉沖減了利潤表中的“凈利潤”,因此在“調整信息”中被命名為“遞延所得稅資產減少”。為了盡可能減少“調整信息”中的單列項目,當遞延所得稅增加時,“調整信息”中將其一并納入了“遞延所得稅資產減少”項目,但需要以“-”號填列,這就是“調整信息”中“遞延所得稅資產減少(增加以“-”號填列)”項目“現身”的根本原因。
如果“遞延所得稅負債”項目的期末余額大于期初余額,即遞延所得稅負債增加時,貸記“遞延所得稅負債”科目時,應同時借記“遞延所得稅費用”科目,此舉沖減了利潤表中的“凈利潤”,因此在“調整信息”中被命名為“遞延所得稅負債增加”。同樣基于盡可能簡化“調整信息”的考量,當遞延所得稅負債減少時,“調整信息”中一并納入了“遞延所得稅負債增加”項目,但需要以“-”號填列,這就是“調整信息”中“遞延所得稅負債增加(減少以“-”號填列)”項目“誕生”的根本原因。
需要進一步強調、提醒并指出的是,與“遞延所得稅資產”或“遞延所得稅負債”科目存在對應關系的科目,除了“所得稅費用——遞延所得稅費用”科目外,還有“資本公積”(“其他綜合收益”)科目,對于“遞延所得稅資產”科目而言,還有可能與“商譽”科目相對應。在本會計期間賬務處理過程中,如果與“遞延所得稅資產”或“遞延所得稅負債”科目相對應的不是“所得稅費用——遞延所得稅費用”科目,就意味著該等情形下確認的遞延所得稅資產或遞延所得稅負債并未影響到利潤表中的“凈利潤”,因此,在判斷“調整信息”中的“遞延所得稅資產減少(增加以“-”號填列)”和(或)“遞延所得稅負債增加(減少以“-”號填列)”項目時,應格外小心。與此相呼應,財政部會計司組織編寫的《企業會計準則講解(2010)》(以下簡稱《2010版講解》)(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的第537頁在講解“遞延所得稅資產減少(減:增加)”和“遞延所得稅負債增加(減:減少)”時,均明確指出:本項目可以根據資產負債表“遞延所得稅資產”項目或者“遞延所得稅負債”項目期初、期末余額分析填列,其中“分析”二字“意味深長”,具體含義已在上文加以闡釋,不再贅述。
(七)存貨項目的調整成因和影響剖析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存貨只是資產負債表中單獨列示的報表項目,并非是單獨設置的會計科目,但屬于存貨類的會計科目卻數量眾多。“調整信息”中均將存貨類會計科目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對待,且采取了“現購現銷、盤存計銷”的計量假設和計算規則。
如果存貨的期末余額小于期初余額(以下簡稱存貨的減少),就表明當期銷售的存貨大于當期新增加的存貨,換言之,當期計入營業成本的金額有一部分是來源于期初存貨的結轉,該部分營業成本并未發生相應的現金流出,因此,在“調整信息”中需要對“凈利潤”加以調增處理。
如果存貨的期末余額大于期初余額(以下簡稱存貨的增加),就表明當期銷售的存貨小于當期新增加的存貨,當期新增加的一部分存貨形成了期末的存貨,即當期新增加的存貨有一部分并未結轉到本期的營業成本,但該部分存貨的形成發生了現金流出。換言之,與存貨相關聯的現金流出大于本期的營業成本。因此,在“調整信息”中需要對“凈利潤”加以調減處理。
需要指出的是,將本期減少的存貨全部視同為本期銷售的存貨,只是理論層面公認的假設,但在實務工作層面,存貨減少并非僅僅源于存貨銷售,如果存貨的增減變動是源于投資活動,如在建工程領用存貨,則應將這一因素予以剔除。
與其他調整因素相一致,存貨類項目的影響因素也采取了“加:”計項目列示。因此,在“調整信息”中,就被描述為“存貨的減少(增加以“-”號填列)”。
(八)經營性應收項目的調整成因和影響剖析
《2010版講解》中指出:經營性應收項目包括應收賬款、應收票據、預付賬款、長期應收款和其他應收款中,與經營活動有關的部分,以及應收的增值稅銷項稅額等。
如果經營性應收項目的期末余額小于期初余額(以下簡稱經營性應收項目減少),就意味著本期收回的應收款項小于本期新增加的應收款項,換言之,本期銷售額小于本期回款額。因此,在“調整信息”中,應對“凈利潤”予以調增處理。
如果經營性應收項目的期末余額大于期初余額(以下簡稱經營性應收項目增加),就意味著收回的應收款項小于本期新增加的應收款項,企業本會計期間發生的銷售收入有一部分沒有收回現金,換言之,本期銷售額大于本期回款額。因此,在“調整信息”中,應對“凈利潤”予以調減處理。
由于對經營性應收項目的影響仍然一并以“加:”計方式列示,在“調整信息”中就被描述為“經營性應收項目減少(增加以“-”號填列)”。
需要指出的是,經營性應收項目的減少或增加代表著本會計期間企業對商業信用利用趨勢的變化,經營性應收項目的減少意味著本期被客戶占用的資金在減少,反之,被客戶占用的資金在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企業與客戶話語權的相對漸強或漸弱。
(九)經營性應付項目的調整成因和影響剖析
《2010版講解》中指出:經營性應付項目包括應付賬款、應付票據、預收賬款、應付職工薪酬、應交稅費、應付利息、長期應付款和其他應付款中,與經營活動有關的部分,以及應付的增值稅進項稅額等。
如果經營性應付項目的期末余額大于期初余額(以下簡稱經營性應付項目增加),就意味著本期償還的應付款項小于本期新增加的應付款項,換言之,本期采購金額大于本期付款額,但在計算本期凈利潤時,是假設本期的存貨采購金額全部轉化為本期銷售成本。因此,在“調整信息”中,應對“凈利潤”予以調增處理。
如果經營性應付項目的期末余額小于期初余額(以下簡稱經營性應付項目減少),就意味著本期償還的應付款項大于本期新增加的應付款項,換言之,本期付款額大于結轉為銷售成本的本期存貨采購金額。因此,在“調整信息”中,應對“凈利潤”予以調減處理。
受制于統一的“加:”計列示格式,“調整信息”中被定義為“經營性應付項目增加(減少以“-”號填列)”。
同樣需要指出的是,經營性應付項目的增加或減少代表著本會計期間企業對商業信用利用的變化趨勢,經營性應付項目的增加,意味著本期占用客戶的資金在增加,反之,占用客戶的資金在減少。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企業對客戶話語權的相對漸強或漸弱。
需要提醒的是,如果企業前一會計期間的經營現金凈流量遠遠大于凈利潤或者兩者比值過大,同時經營性應付款項金額較大或增幅過大,且在本會計期間的期初出現集中大額償還關聯方應付款項的現象,通常就意味著前一會計期間的經營現金凈流量存在被粉飾的跡象或可能性。
(十)其他項目的調整成因及影響剖析
盡管“最新調整信息”中設定了16項單獨列示的項目,但仍無法窮盡所有應予調整的因素,例如,上市公司因實施股權激勵而計提的各項費用,在賬務處理環節,借記相關費用類科目時,貸記的是“資本公積”科目,這就意味著并未發生與此類費用相對應的現金流出,因此就需要在“調整信息”中予以調整,但此類費用不宜歸入16項單獨列示項目中的任何一項中。有鑒于此,就必須設置具有兜底性質的“其他”項目來加以應對。
但是,毋庸回避的是,“其他”項目的設置,就會給粉飾經營現金凈流量的企業提供了技術上的“空間”或“機會”,即便有的公司并不存在粉飾經營現金凈流量的行為或現象,“其他”項目的存在也會給以敷衍塞責心態填列“調整信息”的企業提供了“有力武器”。有鑒于此,各類報表閱讀者有必要關注“其他”項目列示內容的具體說明,尤其在該項目的列示金額相對較大時,更應嚴加識別。
總而言之,比對經營現金凈流量和凈利潤是企業財務報告分析過程中的“必選動作”,此舉可以對企業凈利潤的含金量、商業信用的利用程度、會計政策的穩健程度及執行力度、獲利能力的持續性和穩定性做出有針對性的研判,進而為科學決策提供有益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