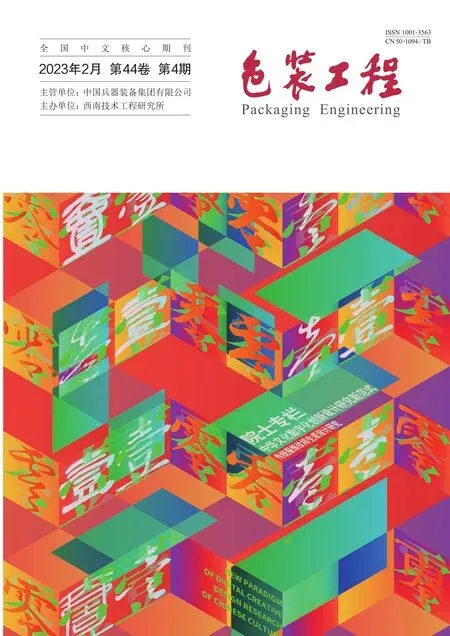互文性視域下紀念館視覺形象設(shè)計創(chuàng)新思路
王玥,陳磊
互文性視域下紀念館視覺形象設(shè)計創(chuàng)新思路
王玥,陳磊
(清華大學 美術(shù)學院,北京 100085)
以紀念館為研究對象,探討了視覺形象設(shè)計中互文釋義的方法建構(gòu),論證了視覺形象設(shè)計方法的創(chuàng)新思路。聚焦符號學、修辭學中“互文性”理論的發(fā)展與轉(zhuǎn)向,采用文獻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對相關(guān)學科領(lǐng)域的理論延展進行歸納梳理,提出互文性理論研究趨于“多重性”與“工具型”轉(zhuǎn)變。以毛主席紀念堂視覺形象設(shè)計實踐為例,分別從歷史文本、建筑、文物等方面系統(tǒng)構(gòu)建“視覺語境-視覺語意-視覺語法”三個層次的視覺形象設(shè)計方法,并采用圖解分析法和實證研究法開展設(shè)計分析。形成了設(shè)計中“脈絡(luò)互文-意象互文-結(jié)構(gòu)互文”的多重釋義路徑。以學科交叉的視角深化視覺形象設(shè)計相關(guān)思考,互文機制的探討不僅有利于時代語境流變中創(chuàng)新文化符號的傳承方式,更有助于在不同媒介關(guān)系中擴展視覺形象設(shè)計的系統(tǒng)方法。
互文性;紀念館;視覺形象設(shè)計;毛主席紀念堂;創(chuàng)新思路
2021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lián)十一大、中國作協(xié)十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中提到:“用情用力講好中國故事,向世界展現(xiàn)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1]作為講述“中國故事”和構(gòu)建“大國形象”的文化陣地。國內(nèi)許多紀念館順應(yīng)時代需求,文化建設(shè)活躍,趨于多元化,呈現(xiàn)出“集群化”和“品牌化”兩個趨勢:趨向集群化,以人物紀念館為例,多以故居或是主要活動地點建設(shè)主題紀念地,形成紀念館網(wǎng)絡(luò)。不同區(qū)域的紀念館往往以挖掘當?shù)靥赜械募o念資源為主旨,推動文化旅游應(yīng)融盡融,創(chuàng)建區(qū)域性紀念文化聯(lián)盟;趨于品牌化,例如雨花英烈紀念地,以雨花臺烈士為紐帶串聯(lián)26家紀念館,以紀念館相關(guān)人物、文物、事件為文化意象打造IP、品牌聯(lián)名的設(shè)計層出不窮。
然而,較之紀念館相關(guān)展覽的視覺形象設(shè)計工作,許多紀念館自身形象的視覺設(shè)計仍未跟上公共文化服務(wù)的需求和數(shù)字媒體傳播的轉(zhuǎn)變,相關(guān)設(shè)計及文化傳播的思考仍不均衡:一方面,部分紀念館比較關(guān)注標志設(shè)計,但整體視覺形象系統(tǒng)設(shè)計缺乏整體性、規(guī)范性;另一方面,面對多渠道、多層次、不斷變化的信息傳播媒介,紀念館后期應(yīng)用面臨整合線上線下的挑戰(zhàn),如何挖掘展館特色以及豐富的視覺語言,如何構(gòu)建視覺形象傳播的深層邏輯,成為我國紀念館文化建設(shè)的重要突破點。本文聚焦我國紀念館視覺形象設(shè)計現(xiàn)狀及問題,在跨學科視角下分析探討紀念館在文化文本、視覺敘事、意象語言等多方面的互文釋義層次,探討建構(gòu)視覺形象的創(chuàng)新思路,在實證研究與圖解分析中論證紀念館視覺形象系統(tǒng)設(shè)計中互文性方法構(gòu)建的可行性與創(chuàng)新思路。
1 國內(nèi)紀念館視覺形象設(shè)計的現(xiàn)狀
紀念館是紀念重要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的專題展館,以人物、事件的相關(guān)資料或人物故居、事件原址為建設(shè)基礎(chǔ),從而達到宣傳教育、研究、收藏、紀念等目的[2]。其中,紀念館視覺形象系統(tǒng)設(shè)計是展館對外統(tǒng)一宣傳、對內(nèi)優(yōu)化管理的規(guī)范制定,其目的主要是明確基礎(chǔ)視覺形象要素和應(yīng)用規(guī)范兩個部分的應(yīng)用方式,從而優(yōu)化其文化宣傳管理的系統(tǒng)性,提升其形象辨識度和延展性。
近20年,紀念館建設(shè)更是蓬勃興起,紀念館不僅通過歷史物件、人物、事跡構(gòu)建著主題文化,其空間本身也構(gòu)成了文化體驗和記憶的載體,因此,其視覺形象的傳播不僅包括紀念館的建筑空間、展覽內(nèi)容、園林景觀,還包括傳統(tǒng)媒介(各類衍生品、出版物、主題產(chǎn)品)、數(shù)字媒介(官方網(wǎng)站、線上展館、各大平臺運營等)[3],為了在更復(fù)雜多元的媒介和場景中強化紀念館的完整形象、豐富紀念文化的延展,有必要對視覺形象系統(tǒng)及應(yīng)用規(guī)范進行系統(tǒng)性管理。
目前國內(nèi)紀念館的視覺形象建設(shè)存在諸多不足之處:
1)視覺形象設(shè)計語言思路較單一,重視標志設(shè)計的更新,忽視視覺形象要素應(yīng)用關(guān)系,較少關(guān)注數(shù)字傳媒時代形象傳播的動態(tài)化、互動化趨勢創(chuàng)新。
2)紀念館通常包括許多與歷史記憶相關(guān)的物質(zhì)文化元素,例如路標、歷史標志、地標、雕像、遺址等,共同構(gòu)成了紀念或遺產(chǎn)景觀。目前不少展館的形象設(shè)計創(chuàng)意多從建筑外形、文字造型、文物史料等方面提取元素,但針對其特色文化資源或歷史事跡有待深層挖掘,如何有效解析展館文化傳統(tǒng)內(nèi)涵,從歷史文本、空間文本、物料文本中塑造視覺形象的系統(tǒng)敘事是亟需關(guān)注的課題。
3)視覺形象不僅需要與紀念館文化定位相符,更要關(guān)注新時代與觀眾的信息連接方式。相比之下,國外紀念館的文化形象及推廣方式更關(guān)注多向互動。例如美國9·11國家紀念博物館視覺形象設(shè)計[4]主標志設(shè)計將雙子大樓的建筑融于事件代號911中,以黑白為主色調(diào)配以藍色,有效凸顯了緬懷之情的表達,同時結(jié)合史料圖像、采訪資料、紀念活動不斷豐富形象傳播的圖像和文本,強化了事件中的集體記憶和情感表達。
紀念館蘊含著特定主題的視覺文本形態(tài),不僅體現(xiàn)在空間中歷史元素與記憶圖景的表達,也交織著過去與當下、個體與集體之間文化闡釋與價值定位的流轉(zhuǎn)。因此,紀念館的視覺形象設(shè)計不僅重在傳達文化的視覺符號,更需要構(gòu)建視覺符號所含載的文本意義,從而實現(xiàn)跨時代、跨媒介、跨文化傳播中的文化認同。
2 互文性理論視角下的視覺形象設(shè)計思考
2.1 “互文性”的概念發(fā)展及轉(zhuǎn)向
互文性的概念起源,是西方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思潮中所產(chǎn)生的一種關(guān)于語言符號關(guān)系的文本理論,從索緒爾到巴赫金,都關(guān)注到了不同文化、文本間的相互關(guān)聯(lián)、相互滲透。作為作家和學者的巴赫金最早提出文學結(jié)構(gòu)不僅存在,而且是在與其他結(jié)構(gòu)的關(guān)系中生成的,從而開始了他對文本結(jié)構(gòu)以及文本之間對話性的動態(tài)研究[5]。在當時結(jié)構(gòu)主義符號學和語言精神分析學理論的影響下,朱莉婭·克里斯蒂娃在1967年首次明確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正如“Inter-textuality”中的“inter”和“text”兩個詞根所示,“互文性”的建構(gòu)重在論述“文本間的關(guān)系”,既包括前后文本之間的歷時性聯(lián)系,也存在于作者、讀(聽)者等多角色之間互動的表述循環(huán),甚至影響到社會、歷史的意識形態(tài)傳遞和連接。在泛文本基礎(chǔ)上,意義不再只存在于封閉的文本結(jié)構(gòu)內(nèi)部各因素間的關(guān)系中,而是不斷流轉(zhuǎn)在各個文本的重讀、更新、摧毀、位移和再生成中。克里斯蒂娃將其定義為符號系統(tǒng)的互換關(guān)系,或文本生成的意義結(jié)構(gòu)[6]。

圖1 互文性理論發(fā)展與演進
如果將文本中的“語匯”或釋義中的“符號”視為意義的網(wǎng)絡(luò),而非固定的意義,那么互文性則代表動態(tài)化的表意實踐。如圖1所示,隨著克里斯蒂娃的“解析符號學”、羅蘭·巴特的“多元文本”等理論的深化,“互文性”具有了文本間邏輯結(jié)構(gòu)、轉(zhuǎn)變機制及意義生成的方法屬性,具有了更強的思辨性、批判性。發(fā)展至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布魯姆更是強調(diào)互文性獨特的“修正”意義,鼓勵跨文本不斷更迭、重修釋義的互文結(jié)構(gòu)[7],在修辭形式上也引申了多種動態(tài)化方法,互文性概念也從“結(jié)構(gòu)型理論”發(fā)展為“解構(gòu)型工具”。
在不同時代、不同角色、不同語境的話語系統(tǒng)中,因差異化的媒介、理解、散播、轉(zhuǎn)譯,任何文本都存有對相關(guān)文本的吸收和轉(zhuǎn)化[8],今天的專家學者更趨向?qū)Χ鄬W科、多領(lǐng)域的互文關(guān)系進行探討。互文性這一概念不僅擴展到文學與其他藝術(shù)門類關(guān)系的研究,更促成了跨領(lǐng)域、跨學科理論的共生互動。好比文學、建筑、戲劇、舞美、設(shè)計各個領(lǐng)域之間的共通性和敘事性[9],文化研究視域下互文理論可被視為創(chuàng)新既有結(jié)構(gòu)和認識范式的有效工具。
2.2 視覺形象設(shè)計中的互文性思維
媒介技術(shù)的變革使視覺文化語境與傳播手段更為豐富,互文關(guān)系更加多變。近年來,“互文性”研究主要集中在修辭學、符號學、傳播學等領(lǐng)域,部分研究將互文作為文本分析的策略展開論述,例如馮德正等[10]提出不同符號模態(tài)不僅可以內(nèi)部建構(gòu),也可以相互轉(zhuǎn)換,從而生成多模態(tài)互文,部分研究針對品牌間互動傳播機制提出了基于意義、符號、實踐三層次的互文空間,使用多模態(tài)語篇豐富傳播策略[11]。對于面臨著的“再語境化”問題,在敘事設(shè)計、設(shè)計心理、體驗設(shè)計等交叉理論催化下,藝術(shù)設(shè)計領(lǐng)域研究方法出現(xiàn)了關(guān)于文本轉(zhuǎn)譯、釋義分析的互文性思考,但大多側(cè)重歸類敘述,沒有從設(shè)計方法層面展開視覺設(shè)計中互文性系統(tǒng)構(gòu)建的思考。
與文本一樣,視覺形象背后也存在釋義發(fā)展的網(wǎng)絡(luò)系統(tǒng)。從宏觀層面,視覺形象設(shè)計中的互文性思維不僅體現(xiàn)為同一形象或信息符號的縱向交織和更迭,也存在于不同視覺語言或媒介形式之間的橫向交叉與轉(zhuǎn)變中;從微觀層面,視覺形象設(shè)計的互文路徑也可結(jié)合歷史語境、空間語序、視覺語意、媒介方式四個層面展開創(chuàng)新。例如俄羅斯衛(wèi)國戰(zhàn)爭紀念館視覺形象設(shè)計[12],提取了紀念館建筑中的立柱陣列、紅星等元素,以建立策略方法,其互文性不僅僅體現(xiàn)在歷史文化元素和空間敘事的互象、互聯(lián)、互動關(guān)系中,也體現(xiàn)在整體視覺形象多重表意網(wǎng)絡(luò)中,其中的釋義邏輯值得進一步形成可參照的方法框架。
3 以毛主席紀念堂為例探討紀念館視覺形象設(shè)計中互文釋義的創(chuàng)新思路
自1977年開放至今,毛主席紀念堂這座莊嚴肅穆、氣勢恢宏的建筑接待了數(shù)億的瞻仰群眾,是廣大人民群眾悼念、緬懷偉人的重要場所。為了彰顯紀念堂的新時代風貌,2020年底,中央辦公廳毛主席紀念堂管理局委托清華大學美術(shù)學院,啟動了視覺形象系統(tǒng)設(shè)計工作。
此前,毛主席紀念堂曾使用過基于主體建筑繪制的圖形,但其并非是嚴格意義上的標志,更沒有建立規(guī)范的視覺形象應(yīng)用系統(tǒng),因而不太適應(yīng)當下多元文化體驗和交互的需求。此次,圍繞紀念堂相關(guān)文獻、圖像、設(shè)計圖紙等資料,研究團隊開展調(diào)研及數(shù)據(jù)收集整理,通過征求各方建議,明確了三個設(shè)計原則:一要體現(xiàn)毛主席紀念堂的獨特空間元素;二要兼具紀念性與政治性的形象氣質(zhì);三要創(chuàng)新輔助元素以適應(yīng)文化建設(shè)與延展。
基于互文性相關(guān)理論,本研究在提出“脈絡(luò)互文-意象互文-結(jié)構(gòu)互文”三層文本釋義的同時,試圖圍繞“視覺語境-視覺語意-視覺語法”三個層次創(chuàng)新視覺形象設(shè)計方法(見圖2),強調(diào)核心元素、組合方式、延展應(yīng)用等相關(guān)設(shè)計規(guī)范的合理性和整體性,著眼于紀念堂相關(guān)主題文化傳播與文創(chuàng)開發(fā)的長遠規(guī)劃,聚焦紀念館視覺形象設(shè)計的互文性創(chuàng)新路徑開展實踐探索。

圖2 紀念館視覺形象設(shè)計的互文釋義網(wǎng)絡(luò)
3.1 通過提煉“脈絡(luò)互文”拓展視覺語境
毛主席紀念堂作為國家最高紀念堂具有獨特的政治地位。本著“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設(shè)計建造思想[13],紀念堂建筑風格方正對稱、莊重典雅。此次,設(shè)計實踐圍繞建筑空間考察、館藏史料、專家口述三類文本資料,分析提煉出視覺形象設(shè)計的基本文化脈絡(luò)依據(jù)。
1)毛主席紀念堂主體建筑是歷史文本凝結(jié)的符號,是特殊的文化地標,本身就體現(xiàn)了視覺形象塑造中雙重釋義的互文性。一方面,紀念堂相關(guān)文獻史料、圖像資料、采訪資料豐富且互為補充,激活了對現(xiàn)存場域的文化敘事;另一方面,毛主席紀念堂作為位于天安門廣場建筑群中心的建筑,與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大會堂、天安門等共同形成了重要的公共文化區(qū)域,視覺形象設(shè)計中也需兼顧其間的呼應(yīng)與互動。
2)紀念堂建筑裝飾語言極富寓意。建筑中的石雕裝飾與綠化中的四季植被之間生成了互為文本、多重敘事的語言關(guān)系。紀念堂建筑周圍高低錯落種植著常青樹、油松、山楂,三月開花,九月結(jié)果,春華秋實,象征著毛主席播種的革命果實,一片火紅,代代相傳[14]。紀念堂建筑室內(nèi)的石雕裝飾圖案則選用了梅花、葵花、萬年青、松柏等20多種題材,各具寓意,既保持了紀念堂室內(nèi)的莊嚴肅穆,也使文化主題更加鮮明突出,同時構(gòu)建了多種具象與抽象的釋義符號。特色鮮明的裝飾在體現(xiàn)歷史敘事的同時,形成了互文性釋義的網(wǎng)絡(luò),也構(gòu)成了廣大觀眾空間認知體驗的記憶點。
3)通過資料梳理生成了不同的媒介文本,建構(gòu)了多重的觀看結(jié)構(gòu)。使原本固化的互文性,也因記憶和視角的關(guān)聯(lián)而趨向語境化,為視覺形象設(shè)計的轉(zhuǎn)化提供了更多思路。
通過梳理提煉設(shè)計要素間的互文性,可以平衡內(nèi)容與形式之間的意形轉(zhuǎn)移,從意象材料轉(zhuǎn)向視覺敘事,逐漸演化出具有創(chuàng)新性的設(shè)計邏輯。
3.2 通過構(gòu)建“元素互文”重組視覺語意
1)在宏觀層面,強調(diào)關(guān)注多視角的意象互文性。如圖3所示,本研究團隊從展館建筑特征、廣場建筑群語境、人物內(nèi)涵象征、文獻文本幾個方面進行了設(shè)計方案的不斷嘗試,先后創(chuàng)作了十多個標志形象方案,其中或以“東方紅”為概念,強化人物的精神意象,或結(jié)合漢字與象征性花卉表達,最終明確了以主體建筑造型為標志的設(shè)計方向,通過不斷優(yōu)化視覺語言表達,最終形成了融合紀念性、政治性和藝術(shù)性的標志圖形,得到了委托方及專家的一致認可。
2)在微觀層面,深入挖掘元素語義中的互文性。除了標志圖形,通過提煉建筑裝飾中的代表性圖樣,視覺系統(tǒng)的輔助圖形選取了向日葵、梅花、松柏、萬年青作為造型元素(見表1):向日葵象征了全國各民族大團結(jié);梅花象征了黨的第一代領(lǐng)袖集體堅韌不拔的革命意志;松柏象征了對偉人的深切緬懷;萬年青象征了共產(chǎn)黨人永葆青春。圖形元素既緊扣毛主席紀念堂的歷史文本意義,又凸顯了空間文本營造出的儀式感,與標志圖形一起構(gòu)建了系統(tǒng)的視覺文化表述體系基礎(chǔ)。

圖3 紀念堂標志設(shè)計解析
表1 紀念堂建筑空間裝飾元素分析

Tab.1 Analysis of decorative elements in the architectural space of the memorial hall
此外,在造型元素互象關(guān)系的基礎(chǔ)上進行再設(shè)計、再解讀,以三類圖解方法論證視覺語言中的互文性構(gòu)建思路(見表2):
第一,重心解析圖。通過解析建筑裝飾圖案的視覺重心及節(jié)奏,整理出視覺元素造型中位置和比重等布局關(guān)系。
第二,組合比例圖。在定位元素視覺重心的基礎(chǔ)上,通過網(wǎng)格分析確定造型的節(jié)奏比例。
第三,意象解構(gòu)圖,通過分解、重構(gòu)、共形等方式提取造型意象,構(gòu)筑視覺造型元素。
3.3 通過轉(zhuǎn)化“結(jié)構(gòu)互文”重塑視覺語法
視覺語法分析旨在豐富視覺文本的元素構(gòu)成與編碼原理,針對形式、色彩、構(gòu)成等敘事成分進行數(shù)據(jù)和特征推理[15]。在毛主席紀念堂視覺形象系統(tǒng)設(shè)計中,充分利用視覺語言的空間敘事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將文化文本潛在結(jié)構(gòu)融于視覺形象的設(shè)計邏輯中,強化主題文化基因的關(guān)聯(lián)性。
1)基于建筑空間的色彩比例關(guān)系,設(shè)定視覺形象系統(tǒng)標準色彩的應(yīng)用層次。毛主席紀念堂在建筑設(shè)計之初,始終在西方古典建筑色彩與民族色彩之間不斷調(diào)節(jié),強調(diào)在融合協(xié)調(diào)中凸顯中國傳統(tǒng)色彩的現(xiàn)代表達[16],此次研究結(jié)合建筑自身色彩,設(shè)定金色為視覺形象主色,既體現(xiàn)紀念性,也凸顯傳承性,便于形象宣傳及后續(xù)開發(fā)應(yīng)用。
2)基于視覺系統(tǒng)輔助圖形的良好適用性,嘗試圖形元素繁簡切換的多層次應(yīng)用方式。在視覺形象核心元素關(guān)系中,主標志圖形強化紀念堂外部莊嚴形象,輔助圖形則以建筑裝飾延展,達到內(nèi)外呼應(yīng)。輔助圖形創(chuàng)作設(shè)計了豐富版和簡化版兩種類型(見圖4),可根據(jù)應(yīng)用需求靈活應(yīng)用:豐富版輔助圖形適用于尺度較大、能夠充分展現(xiàn)細節(jié)的媒介中;在媒介尺寸較小的應(yīng)用場合,則使用簡化版輔助圖形。圖形可通過鏡像組合、二方連續(xù)組合以及局部分解重組進行使用,便于在適應(yīng)不同尺度和工藝效果的同時,為豐富視覺形象表達層次提供適合的表現(xiàn)語言。視覺語言層次的細分強調(diào)了表現(xiàn)意象和互文性,可以有效引發(fā)觀眾的記憶。
表2 以紀念堂中“梅”元素為例開展三類圖解分析
Tab.2 Three types of illustrated analysis of the "plum" element in the memorial hall

綜上所述,視覺形象設(shè)計中的互文性并非僅聚焦于視覺語言間“超文本”的結(jié)構(gòu)或規(guī)律探討,更重要的是通過此次項目設(shè)計創(chuàng)作,實踐了互文性理論在視覺形象設(shè)計方法維度的創(chuàng)新路徑,強化了深層次的文本創(chuàng)新思路和理論邏輯。
4 結(jié)語
今天的紀念館視覺形象設(shè)計處于復(fù)雜的傳播媒介中,在交織的文本網(wǎng)絡(luò)中不斷再敘述、再詮釋,在跨文本敘事設(shè)計中構(gòu)建多維度的互文性釋義網(wǎng)絡(luò)。在毛主席紀念堂視覺形象設(shè)計實踐過程中,通過梳理史料拓展視覺語境,以重組意象締結(jié)視覺語意,運用同構(gòu)空間創(chuàng)新視覺語法,闡釋了視覺形象設(shè)計中“脈絡(luò)互文-意象互文-結(jié)構(gòu)互文”三層釋義建構(gòu),最終形成完整有效的視覺形象系統(tǒng)。通過設(shè)計過程中四個階段的邏輯思考和圖解方法,依據(jù)互文性相關(guān)理論進一步啟發(fā)了視覺形象系統(tǒng)設(shè)計創(chuàng)新視角,為視覺設(shè)計釋義建構(gòu)提供了新思路。
[1] 習近平. 在中國文聯(lián)十一大、中國協(xié)作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 2021年12月14日[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XI Jin-ping.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11th Congress of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and the 10th Congress of China Cooperation: December 14th, 2021.[M]. Beijing, Chin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1.
[2] 中國博物館協(xié)會紀念館專業(yè)委員會. 中國紀念館發(fā)展報告[M].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20.
Professional Committee of Memorial Hall of China Association of Museums.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Memorial Hall[M].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20.
[3] 孫鳳群. 更新·體系化·動態(tài)化: 論博物館視覺識別系統(tǒng)的建設(shè)[J]. 博物館管理, 2021(2): 55-64.
SUN Feng-qun. Update, Systematic, Dynamic: The Museum Construction of Visual Identification System[J]. Museum Management, 2021(2): 55-64.
[4] Exhibitions of the 9/11 Memorial & Museum [EB/OL]. (2001-9-11)[2021-9-10].https://www.911memorial.org.
[5] 王瑾. 互文性[M]. 桂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5.
WANG Jin. Intertextuality[M]. Guilin, China: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5.
[6] 李道國. 符號闡釋的互文性建構(gòu)[J]. 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8, 7(6): 130-133.
LI Dao-guo. Intertextual Construction of Symbol Explanation[J]. Journal of Jiangnan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8, 7(6): 130-133.
[7] 梁曉萍. 互文性理論的形成與變異——從巴赫金到布魯姆[J]. 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9, 36(4): 37-40.
LIANG Xiao-ping. The Formation and Variation of the Intertextual Theory[J].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9, 36(4): 37-40.
[8] 王銘玉. 符號的互文性與解析符號學——克里斯蒂娃符號學研究[J]. 求是學刊, 2011, 38(3): 17-26.
WANG Ming-yu. The Intertextuality of Symbols and Semianalysis—A Study of Kristeva’s Semiotics[J]. Seeking Truth, 2011, 38(3): 17-26.
[9] 王璐筠. 跨學科視角下文學與建筑的互文性探析——基于羅蘭·巴特文本理論的啟示[J]. 美與時代(城市版), 2021(2): 19-20.
WANG Lu-yun.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Literature and Architecture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Enlightenment from Roland Barthes's Text Theory[J]. Beauty & Times, 2021(2): 19-20.
[10] 馮德正, 張德祿, Kay O'Halloran. 多模態(tài)語篇分析的進展與前沿[J]. 當代語言學, 2014, 16(1): 88-99, 126.
FENG De-zheng, ZHANG De-lu, O'HALLORAN K. Advances and Frontiers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J].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2014, 16(1): 88-99, 126.
[11] 吳蓉. 互文性視角下城市品牌與企業(yè)品牌互動傳播機制探究[D]. 廣州: 華南理工大學, 2019.
WU Rong. 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urban brand and corporate brand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textuality[D]. Guangzhou: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9.
[12] Exhibitions of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Memorial of Russia [EB/OL].(2006-1-1).https://victorymuseum.ru.
[13] 朱亮. 毛主席紀念堂建筑方案設(shè)計過程[J]. 裝飾, 2009(9): 30-32.
ZHU Liang.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Process of the Chairman Mao Memorial Hall[J]. Art & Design, 2009(9): 30-32.
[14] 毛主席紀念堂規(guī)劃設(shè)計組. 毛主席紀念堂總體規(guī)劃[J]. 建筑學報, 1977(4): 3-12, 50.
Chairman Mao Memorial Hall Planning and Design Group. Master planning of Chairman Mao Memorial Hall[J]. Architectural Journal, 1977(4): 3-12, 50.
[15] 劉濤. 媒介·空間·事件: 觀看的“語法”與視覺修辭方法[J]. 南京社會科學, 2017(9): 100-109.
LIU Tao. Media, Space, and Event: The “Grammar” of Seeing and Visual Rhetoric Methodology[J]. N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7(9): 100-109.
[16] 毛主席紀念堂規(guī)劃設(shè)計組. 毛主席紀念堂建筑設(shè)計方案的發(fā)展過程[J]. 建筑學報, 1977(4): 31-47.
Chairman Mao Memorial Hall Planning and Design Group.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scheme of Chairman Mao Memorial Hall[J]. Architectural Journal, 1977(4): 31-47.
Innovative Ideas for Visual Identity System Design of Memorial Hall under the View of the Intertextual Field
WANG Yue, CHEN Lei
(Academy of Arts and Desig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5, China)
The work aims to take memorial hall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discuss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textual interpretation method in visual identity design and demonstrate the innovative ideas of visual identity system design method.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textuality" theory in semiotics and rhetoric,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case study method were adopted to summarize and comb the theoretical extension of related disciplines and propose that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intertextuality" tended to be "multiple" and "tool-type". With Chairman Mao's Memorial Hall as an example, a three-level visual identity system design method of "visual context-visual semantics-visual grammar" was built from historical texts, architecture, cultural relics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memorial hall. Then, graph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were adopted to carry out design analysis. Thus, the multiple intertextual paths of "contextual intertextuality-image intertextuality-structural intertextuality" were formed in the design.The thinking related to visual identity system design is deepe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disciplinarity. The discussion of intertextual mechanism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the inheritance of innovative cultural symbols in the context of the times, but also beneficial to extending the systematic approach of visual identity system design in different media relations.
intertextuality; memorial hall; visual identity system design; Chairman Mao's Memorial Hall; innovative ideas
TB472
A
1001-3563(2023)04-0212-07
10.19554/j.cnki.1001-3563.2023.04.026
2022–09–06
國家社科基金藝術(shù)學重大項目(21ZD24);2021年度清華大學自主科研計劃文科專項項目(20215080006)
王玥(1988—),女,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文博展示及文創(chuàng)設(shè)計。
陳磊(1970—),男,碩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國家形象視覺設(shè)計。
責任編輯:馬夢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