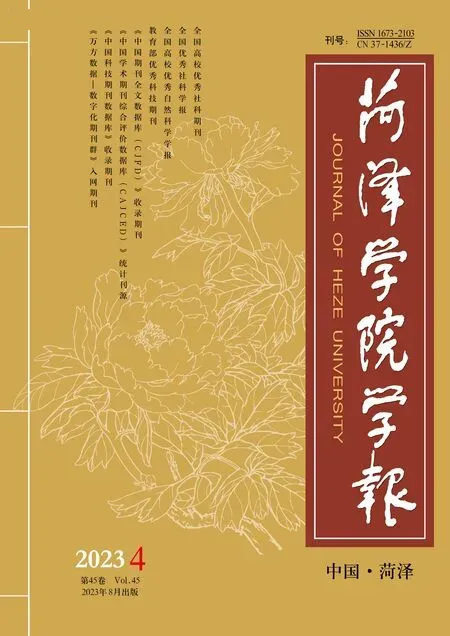從《金瓶梅詞話》透視古本《水滸傳》武松形象
——兼及杭州容本《水滸傳》萬歷時代之創新
宋伯勤,楊東鋒
(1.鹽城鹽都區政法委,江蘇 鹽城 224001;2.鹽城實驗中學,江蘇 鹽城 224001)
《金瓶梅詞話》中武松打虎和殺嫂兩個情節所描繪的武松人物形象,與杭州容與堂本《水滸傳》中的武松形象是截然不同的。筆者以為《金瓶梅詞話》中的武松打虎與殺嫂情節所涉及的武松形象,應該是源自正德嘉靖時期的古本水滸傳故事,甚至也可能是更早的故事版本。本文意圖通過考察《金瓶梅詞話》與之前古本的關系來探測古本《水滸傳》故事中武松的原始形象,并由此推定杭州容與堂本《水滸傳》(以下簡稱容本《水滸傳》)的武松形象可能與萬歷時代的文化訴求和讀者期待有關。
一、兩個不同的武松形象
《金瓶梅詞話》自明代萬歷十七年(1589)就記載有傳抄,關于創作的起始時間可能還要追溯到更早的嘉靖末期。到萬歷二十四年時,該作品在江南已經廣泛傳抄,但到萬歷四十五年,《金瓶梅詞話》方才初次刻版,可見在刊刻之前,《金瓶梅詞話》本故事已經流傳了幾十年。
可以確定的是,《金瓶梅詞話》移植了萬歷初年杭州流行的水滸傳說中的武松殺嫂故事,而第1回至6回,第9、10回,第87回,《金瓶梅詞話》中的情節與容本《水滸傳》第23至31回的情節也基本相同。
現有的研究多傾向于《金瓶梅詞話》本中的作品人物系自《水滸傳》第23、24回演化,認為只因《金瓶梅詞話》主角是寫市井細民,并無意展現武松英雄本色,并且在情節安排上,《金瓶梅詞話》與《水滸傳》相比刪減了武松的英雄事跡,所以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金瓶梅詞話》刻意“矮化”了武松,顛覆了容本《水滸傳》表達的英雄主義形象,把讀者熟知的容本《水滸傳》中的武松,改寫成了薄情寡義矮小猥瑣的亡命徒。研究者之所以產生這種觀點,原因在于多把萬歷時期杭州流行文化里所刻畫出來的英雄武松形象作為標準,即以萬歷新編容本《水滸傳》第23回中的新武松形象作為標尺去對照《金瓶梅詞話》本中的舊武松而得出的結果。容本《水滸傳》中彩繪的英雄武松,一身豪氣,蓋世英雄,而《金瓶梅詞話》本(以下簡稱《金》本)中的武松,平庸世俗,殘忍兇惡,二者形象完全不同。
那么,《金》本中的武松形象,有沒有其它來源的可能呢?比如是源自早期正嘉古本的原創人物?截止目前來看,學界尚無人探討,更無《金》本中武松形象或源自早期正嘉古本的原創人物的說法。造成這種狀況有著不難理解的現實原因,一是資料的缺失,古本及之前的材料我們現在幾乎都難以尋覓到。二是人們或難以想到,也許古本人物遺跡還存在于另外的作品中被保存下來的可能。
二、《金瓶梅詞話》本中武松形象的來源
“互文性”雖是近年興起的一種文本理論,但在我國古代文學創作中一直都存在,這是一種借鑒式的抄襲方法,也是文學文本創新中,借鑒抄襲當時經典文化的一種普遍現象。《金瓶梅詞話》本中古樸的舊武松形象,筆者以為應該是采用了拿來式的“互文性”方法,借用了先前比容本還要早的水滸故事中的武松形象,從而保留了一個與后來萬歷新編容本《水滸傳》中完全不同的舊人物形象。
考察《金》本中打虎與殺嫂兩個段落中展示的舊武松形象,與容本中創新的萬歷時代化了的英雄武松形象是全然不同的。《金》本呈現出的武松形象是坍塌的,這一形象的選擇應該與《金瓶梅詞話》故事背景的需要有關。
《金瓶梅詞話》的故事背景假托于北宋末年政和年間,而萬歷時期杭州最新流行的水滸故事中的武松、王婆、西門、潘金蓮,已經是屬于時尚化了的新鮮形象。顯然萬歷時代已成英雄的武松新貌不符合宋代底層人物的粗陋殘暴的形象,因此為更符合北宋政和時代的民風民俗,《金》本可能在創作時刻意地讓武松形象呈現先前文本的矮化乏味,即把先前老故事舊版本中粗陋殘暴的武松形象直接抄襲保留下來,從而有別于容本從時尚作品互文來的嶄新形象。這樣做并不影響《金》本中主要人物故事,因為武松僅僅是串聯場景的一個角色而已。反過來說,如果古本故事與容本萬歷時代化了的武松是兩個一致的形象,《金》本的作者則無須一開篇就放棄如容本武松人物造型的“高大上”,再逆向地涂抹毀改,把幾近完美的如容本中的英雄武松,改寫成打虎的平庸,殺嫂的奸詐且兇殘。《金瓶梅詞話》需要一個返樸歸真的古代武松形象,因而《金》本在創作時轉向更早前的文本中去選擇摘抄。當然這只是一種可能的推測。
筆者以為,《金瓶梅詞話》成書時,當時的杭州坊間應該流傳著不同水滸傳類型的故事文本。一個是正嘉時期的古本,是按照正德嘉靖時期的文化理念而創作形成的(其初始創作還更可前溯到成化、弘治時代文化)。另一個是正嘉古本在南方流傳后,經過商業都市的杭州書會再度創新增改,二次新編成書的萬歷時代化了“容初本”(容本借以批評的母本)。“容初本”在早期的正嘉古本基礎上糅合了更多的嘉靖后期到萬歷時期杭州的時尚精神文化元素。古文本與新編“容初本”的時間跨度,超過了50年的光景。
在古本《水滸傳》成書后并且在杭州“容初本”二次成書之前,杭州書會的作者可能為迎合市民趣味,曾將古本等流行的水滸作品中敘述武松人物的故事劈出單列成篇增補添加,創新演化出了另外一部新鮮的長篇人物故事話本,此話本專講武松打虎、王婆茶坊設計、西門慶潘金蓮勾搭、武松殺嫂等。后來經過嘉靖中期至萬歷初年的說唱藝術演化,終于在古本結構的基礎上演繹出了另外一部具有萬歷時代理念杭州文化特色的新鮮“武松殺嫂”作品。這部作品雖然后來又被再吸收乃至湮滅,但其對稍后成書的《金瓶梅詞話》和“容初本”的貢獻巨大。“容初本”與《金瓶梅詞話》本(以下簡稱《金》本)兩部作品,可能都是對這部萬歷初年極具杭州特色的新編“武松殺嫂”作品做了“互文性”抄襲。而“容初本”與《金》本的成書過程在時間上也幾乎是同一時期,如果有先后的話,可能《金》本的成書時間或許還略為超前于“容初本”。
三、從《金瓶梅詞話》本中還原古本武松形象
元代至明初雜劇中的水滸人物形象都不甚高大,尤其武松。宋代龔開《宋江三十六贊》:“行者武松:汝優婆塞,五戒在身。酒色財氣,更要殺人。” 羅燁《醉翁談錄》及宋元《大宋宣和遺事》,武松更是僅存名號而已。
《金瓶梅詞話》中存在著的先前古本水滸故事文本的痕跡,保留了先前的古文本的樣貌,武松形象極有可能就是出自更早前古文本的描繪。由是,我們擬從《金》本中的武松人物,試圖來還原古文本中的武松形象。
《金》本中武松出場,應該是古本水滸傳的武松出場,一開始便沒有建立起英雄的形象。其首回是“景陽崗武松打虎,潘金蓮嫌夫賣風月”,打虎情節的互文是:武松就在路傍酒店內,吃了幾碗酒,壯著膽,浪浪滄滄,大扠步走上崗來。與萬歷容本拔高了的刻畫相比,《金》本中武松的形象和精神是“矮化”著的,是一個人性弱點顯著的平庸人物。
《金》本武松,獅子樓誤殺李外傳,“迭配孟州牢城”,義奪快活林、大鬧飛云浦,直到第87回碰到趙佶立太子大赦天下,才又回到清河當都頭。流放多年后,此時英雄氣概早已折磨殆盡。《金》本寫其以色相,施展詭計,為“迎兒”招婿,用上門求娶的計策,哄騙王婆、潘金蓮。其虐殺潘氏、王婆,非常殘忍狠毒,“跳過墻來”殺王潮兒未遂,劫掠首飾,竟不顧迎兒生死,越后墻,“上梁山為盜去了”。殺人逃逸,人物面目基本是市井猥瑣人物形象,連帶梁山也成了盜匪的窩巢。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金》本在這大一節“互文”來的文字后面,作者還刻意寫下一句感嘆:“武松這漢子端的好狠也!”
《金》本中,武大有個女兒叫“迎兒”,其屢遭后母潘金蓮打罵,第10回武松被押解孟州,央托左鄰姚二郎看管迎兒:“倘遇朝廷恩典,赦放還家,恩有重報,不敢有忘”。古本中武松故事結構,寫有“迎兒”作襯托。還有一個與金蓮一起長大的“玉蓮”,但在《金》本中,有人物,卻無故事,也應該是從更早期古本作品中,只將人物互文式抄襲過來,但情節又被刪減了。王婆說雌兒來歷:“小名叫做金蓮,娘家姓潘。原是南關外潘裁的女兒。”這也應是原來古文本對人物出身的交待。
所以據以上推斷,正嘉時期的水滸故事或更早期的古本,塑造了先前演繹作品中的草莽人物形象,但都還只是水滸故事在文學演進史上的過渡,人物形象還遠沒有達到如后來杭州容本用萬歷時代理念重新塑造的高大英雄。從《金》本移植的古本,描寫的武松是早期的本色面目:殘殺了婦人、婆子,“倒扣迎兒在屋里。迎兒道:‘叔叔,我也害怕。’武松道:‘孩兒,我顧不得你了!’”,倉促中遺棄侄女迎兒。這些古本文化的原作文字,更非是如后來萬歷時期的容本中那樣理想化升華了的英雄豪杰面貌。
此外,古本武松止于上梁山卻沒有到杭州。《金》本寫武松結局:“提了樸刀,越后墻,趕五更挨出城門,投十字坡張青夫婦那里躲住,做了頭佗,上梁山為盜去了”。古本應該只有正嘉之前的故事,眾英雄止于上梁山,沒有受招安的結局,也沒有歸宿杭州的信息。這應是古文本對武松的終結,并不是《金》本作者互文時做了省略。古本撰創時,還沒有發展到萬歷時代,還沒有萬歷新編容本中匯集的萬歷時代更加豐富的杭州時尚文化,還沒有萬歷初年才新編出現的攻打杭州方向諸多新鮮故事的創意和想象。明末清初金圣嘆說:其所見古本戛然而止,信其言之不妄。
《金瓶梅詞話》中的武松是古本遺跡,是正嘉之前文化的標本。如果認為《金》本武松是自容本形象逆向改寫,那么所看到的是一個將大英雄向平庸“丑化”的涂改過程。但若更換成一個全新視角,循跡文學作品創作的路徑,看到正嘉之前的是古文化草創,塑造出的還是尚處于平庸中的舊式的武松人物,《金》本正是抄襲采用了古本原作的武松舊貌。再看到萬歷初年是新時代的新文化爆發,新時代催生了文學創新潮流,升華成就了容本中全新的武松蓋世英雄的形象。這個對武松人物再度創新的時段,是從正德(1506—1521年)嘉靖(1522—1566年)時代,再到萬歷(1572—1620年)時代的文化演化過程,是由正嘉之前舊時代舊文化向萬歷新時代杭州新文化的創新升華發展的過程。
容本《水滸傳》的創新,是全面的整體的創新。書中的林沖、盧俊義、燕青,也都是萬歷時代杭州新時尚文化中創新的理想化了的文學人物,他們都是與《金》本的舊武松魯莽形象格格不入的文學新面貌,這些新鮮人物的面貌上更有著萬歷新時代新文化觀念的嘉許期待,已是萬歷新文化所崇尚的軍官、富豪、城市游民階級的英豪。而《金》本透視到的古本中“矮化”著的武松,則顯然是一種舊文化時期的舊人物的立照,這是早前的時代文化對底層市民粗野魯莽人物的文學形象的寫照。這類舊武松之類的人物身上,還保留有更原始(作品初成的成化、弘治時代)的流匪氣息,形象如同市井平凡,舉止粗鄙庸陋,仍不甚完美,也無需要完美,但卻是更加的古樸寫真。
四、容本增添了萬歷時期杭州文化元素
晚明萬歷時期,經濟繁榮國勢中興,杭州城市擴大,時代理念影響著文化創新,文學演進也飛躍發展。此時江南印刷技術日漸成熟,更刺激著大眾文化的傳播。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萬歷新編容本《水滸傳》才升華了水滸的人物形象。此時容本對武松再創新,最明顯的是增添了武松打虎英雄色彩。萬歷新編的文本,武松成為了水滸故事的頭號英雄,“武十回”擴寫英雄武松,在一百單八將中獨占了最大篇幅,本真善良,行事果敢,坦蕩磊落,疾惡如仇,力量與正義集于一身,形象被演化得幾乎完美無缺。新編容本砍去枝蔓,緊湊過程,一改《金》本互文中武松殺嫂時間拖延,請鄰居姚二郎等“做個證見”,讓士兵把守門口,防止眾人逃散,請胡正卿錄下潘氏口供,留下王婆活證。武松說:“小人與哥哥報仇雪恨,犯罪正當其理,雖死而不怨”,帶著人頭、口供,押著王婆到官府自首伸冤。新寫成的容本的武松,不貪財不戀色,快意恩仇、大義凜然。萬歷時代的創新,讓新武松擺脫了舊文本中“帽兒光光”的“窄袖兒”詐婚描寫的平庸狡詐,形象騰地“高大”起來。而且,容本還比《金》本豐富了整三回篇幅的醉打蔣門神,大鬧飛云浦,新增添的血濺鴛鴦樓、夜走蜈蚣嶺、醉打孔亮等情節,彰顯了英雄形象色彩。又寫武松樸實的性情,被施恩父子利用;寫玉蘭給武松帶來妻室的念想,既是頂天立地的大英雄,又是生活在煙火氣息中的凡人。讓武松對前程懷抱希望,渴望建功立業,但一挫再挫,逼上梁山,英雄形象在一系列情節安排中持續推高,成為水滸英雄中“上上人物”。
如果說酒、色、財、氣是之前古本塑造的武松形象,那么萬歷時期杭州文化結晶的新編容本則以忠義品德重新定位,人物塑造得以拔高提升,向著英雄豪杰層面凈化升騰。不僅武松被演化,水滸英雄整體都在演進提升,向著叱咤風云般的傳奇英雄升華,如魯智深化身俠義,楊志怒砍牛二,李逵砍倒杏黃旗,燕青風流倜儻,花榮儒雅有加,等等,眾多英雄人物的面貌,經過萬歷初年的再度創新,經過“容初本”成書的凝練,已經全部煥然一新。
在《水滸傳》的結局上,《金》本互文出來的舊式武松,止于“上梁山為盜去了”,未著杭州方向一個字。容本自第72回后,搜集了嘉靖中后期到萬歷初期的杭州書會藝人們新編的各種指向杭州地域的故事,匯寫出了攻蘇州、杭州,打清溪縣幫源洞、戰方臘等種種新鮮故事。容本新編增添的后續,描摹了杭州地理,詳盡了杭州文化,張順西陵橋“遠望城郭四座禁門,臨著湖岸”,宋江祭奠“朝著涌金門”“仰天望東而哭”,魯智深聽錢塘江信潮、“燒化于六和塔后”,武松“在六和寺出家,盡將身邊金銀賞賜,納此六和寺中,后至八十善終”,林沖“風癱在六和寺后,半載而亡”,在這些萬歷杭州書會新編增添的杭州新文化故事中,過于將武松等眾多人物向杭州地域歸納,英豪呼嘯山林的野性、人物出自山東的北方特色,已經蕩然無存。
從萬歷本《金瓶梅詞話》的互文中,透視到以前古《水滸傳》文本的武松面目,可以辨識出,《金瓶梅》是在容初本之前的杭州流行水滸故事基礎上演化成書,而不應該是從其后來成書的容本《水滸傳》中演進。《金》本中的相關回目,也絕不是從還在其稍后才創新成書的容本《水滸傳》中借鑒而來。容本《水滸傳》是以萬歷時代文化理念重塑創新人物的一部全新的作品,與正嘉之前的古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