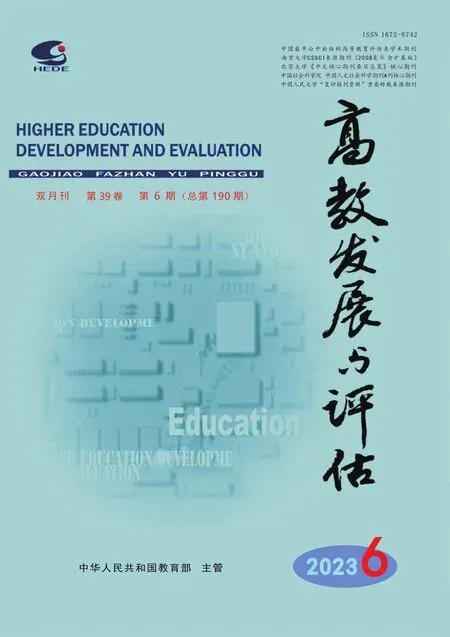蔡元培與北京大學的德育困局
朱鮮峰
(1. 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2. 湖南師范大學鄉村教育研究中心,湖南 長沙 410081)
蔡元培執掌北京大學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節點,對此后中國高等教育的走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因此受到學界的極大關注。就已有研究成果來看,一方面,不少研究著重探討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成就,淡化其在辦學過程中面臨的困難,甚至通過紀念蔡元培的貢獻來表達自身的訴求,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蔡元培神話”[1];另一方面,對于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學界也多有關注,但其教育思想如何轉化為教育實踐,其間又有何種調整,相關研究仍不夠充分。蔡元培在北大的德育探索及其面臨的困局即處于這一理想與現實、思想與實踐交織的地帶。對上述困局進行分析和探討,有助于我們返回歷史現場,重新思考蔡元培的教育理念與辦學語境。
一、德育地位的確立與動搖
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借助德國古典大學理念,將北大改造為研究高深學問的現代學府,學界對此多有關注和研究。與此相對應,德育在德國古典大學觀中占有何種地位,蔡元培在實際辦學中如何處理德育問題,似仍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就理念層面而言,德國古典大學并非不強調德育。研究者指出,德國古典大學的“修養”(Bildung)觀念即具有道德、宗教、精神等多方面的內涵,但在德國大學的實際辦學中,往往強調通過心智訓練獲得通識性的修養[2],此種“修養”偏重理性而非道德。以德國教育家包爾生《德國大學與大學學習》一書(蔡元培曾譯介該書的總論部分)所介紹的情況為例,該書僅有極少數篇幅談及道德,而其所論述的道德為“自由”和“榮譽”,即學術的自由與追求真理的榮譽,二者與理性有密切聯系。[3]由此可見,在當時的德國大學中,通常意義上的德育并未占有重要地位。
作為一位對中外道德傳統有深入認識、人品堪為楷模的教育家,蔡元培對于德育問題有獨到的見解。在其為人所熟知的“五育并舉”思想中,公民道德教育即處于中堅地位。因此,在大學德育層面,蔡元培并未對德國古典大學觀亦步亦趨,而是將其作了本土性轉化。例如,在論述“修養”時,蔡元培主要是從道德層面著眼,“修養道德”“修養德性”等表述在其著述中并不鮮見。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著名演說中,針對此前北大存在的問題,蔡元培提出“抱定宗旨”“砥礪德行”“敬愛師友”三大主張[4]8-10,其中第一點指向“學術”,后兩點則指向“道德”。蔡元培在其他演講中明確指出:“大學目的有二:一為研究學問,二為培養人格。”[5]可見他對大學的學術使命與道德使命均有清醒的認識。
然而,盡管蔡元培在演講中往往將“學術”與“道德”并舉,但在實際辦學中必然會有所偏重。就客觀情況來看,應當說,蔡元培更為看重的是學術研究。擔任北大校長一年之后,蔡元培試圖加強學校的德育,并對此作了解釋:“會一年來鞅掌于大體之改革,未遑及此。”[6]3可見德育的改革并非蔡元培心目中最急迫之事。在著名的《致〈公言報〉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中,蔡元培坦言個別教員德行有虧,又進而指出:“對于教員,以學詣為主……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7]為求得學術人才而不惜降低道德標準,固然是特定歷史環境下的不得已之舉,但這同時也成為影響北大德育工作開展的一個隱憂。
從這一時期北大的課程設置來看,課表中與道德較為密切的是倫理學課程,并未開設修身課程。[8]對于倫理學與修身書的區別,蔡元培曾作過如下分析:“修身書,示人以實行道德之規范者也……倫理學則不然,以研究學理為的……其于一時之利害,多數人之向背,皆不必顧。蓋倫理學者,知識之徑途;而修身書者,則行為之標準也。持修身書之見解以治倫理學,常足為學識進步之障礙。”[9]蔡元培清楚地指出,倫理學研究不必考慮社會的道德觀念,若試圖通過研究倫理學來為社會樹立道德標準,反而不利于學術的進步。可見,北大開設倫理學課程并非從德育的角度著眼,而是偏重學理分析。這也意味著,就課程層面而言,德育的地位并未凸顯。
在實際教學中,“道德”也受到“學術”的擠壓,處于相對次要的位置。例如,章太炎弟子、著名史學家朱希祖上課時,常有學生起身質問或指摘講義中的紕漏,甚至一度發展為寫匿名信進行人身攻擊。[10]燕樹棠、王世杰在行政法、國際法課程上一改傳統的“純粹講義制”,采用“簡單講義方法”,部分學生并不贊同,通過寫匿名信甚至張貼匿名揭帖的形式表達不滿,極大傷害了師生感情,以致燕樹棠與王世杰一度以辭去北大教職相抗爭。[11]在上述事例中,學生為爭學術之是非與教學方法之優劣,忘卻了對教師的尊敬,也從側面反映出德育的地位在教學中并不明確。
由上可知,蔡元培在借鑒德國古典大學重視理性修養這一傳統的同時,進一步強調道德的修養。然而,求“善”與求“真”二者存在內在沖突,在北大的辦學實踐中,德育的地位受到學術的沖擊。在師資層面,蔡元培為求取學術人才而放寬了道德標準;在課程層面,北大并未開設專門的德育課程;在教學層面,學術上的平等觀念消解了傳統的師道尊嚴,尊敬師長這一基本的道德準則也因此受到動搖。在此情形下如何重新樹立德育的地位,采用何種方式開展德育,成為蔡元培面臨的巨大挑戰。
二、私德的培育及其困境
新文化運動興起后,知識界對中國傳統過于重視私德的傾向多有批判。蔡元培并不贊同這一觀點,明確指出:“今人恒言:西方尚公德,而東方尚私德,又以為能盡公德,則私德之出入,曾不足措意。是誤會也。吾人既為社會之一分子,分子之腐敗,不能無影響于全體。”[6]2在北大的德育實踐中,蔡元培始終將培育私德作為重要的一環。
上文談到,蔡元培強調研究高深學問的理念決定了北京大學的課程設置以傳授專業知識為中心,并未正式開設修身課或類似的德育課程。蔡元培在演講中也曾談及科學對于修養的助益,以及以美育促進道德修養的提升,然而上述方式只能作為輔助手段。經過斟酌,蔡元培決定通過創立進德會來培育私德。
1918年1月19日,《北京大學日刊》發表蔡元培的《北京大學之進德會》一文,標志著該會初步成立。文章將進德會會員分為三個等級: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娶妾;乙種會員,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二戒;丙種會員,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三戒。[6]4(后略有調整,規定前三條為基本戒約,其他五條戒約可自由選擇。)入會時由本人注明愿為某種會員。
從形式來看,蔡元培之所以選擇社團性質的進德會,其直接淵源為李石曾、吳稚暉等人1912年在上海發起成立的進德會。蔡元培此前曾加入該會,對其組織結構較為熟悉。對比北京大學進德會的戒約與上海進德會的會約,兩會所定的條目相同,只是等級劃分稍有差異[12],可見二者的承襲關系。在北大內部,1917年4月,學生朱一鶚發起成立“北京大學同學儉學會”,該會簡章曾呈給蔡元培,得到其首肯。儉學會規約中亦有“勿賭博”“勿狎妓”“勿吃煙”“勿吃酒”等條目。[13]該會在當時北大的眾多社團中雖不顯眼,但由此可見,學生層面也有涵養私德的呼聲,這無疑為蔡元培在北大創立進德會提供了合適的土壤。若將視野進一步放寬,進德會在某種程度上融合了中國士人的結社傳統與西方大學的社團傳統,進德的取向及師生共同參與的特點又使其區別于以興趣為導向的學生社團,為當時的大學德育開拓了新的途徑。
就內容而言,進德會的上述要求存在以下幾個特點:其一,強調個人的修養與習慣,不涉及私人交往中的道德準則。通常來說,私德既包含前者,也包含后者,特別是親人朋友間的道德關系。盡管蔡元培本人是著名的孝子[14],但北大進德會回避了在當時引起激烈爭論的孝道等傳統倫理道德,客觀上擱置了相關爭議。其二,突破了“內圣外王”的儒學傳統。蔡元培提出“不作官吏”“不作議員”,與“學而優則仕”的儒家傳統截然相反,意味著其切斷了“內圣”與“外王”之間的聯系。而在當時官場腐敗、風氣污濁的背景下,不做官吏與議員顯然超出了職業選擇的范疇,實質上是潔身自好的體現。其三,標準較低,且均為否定性的道德。蔡元培本人對此作了解釋:“進德之名,非謂能守會規即為有德……乃謂入德者當有此戒律,即孟子‘人有不為,而后可以有為’之義也。”[15]較之相對抽象的肯定性的道德,否定性的戒約更具有操作性,這也表明了蔡元培務實的姿態。今日看來,其中幾條戒約似屬于道德底線,由此亦可見當時私德普遍受到輕視的嚴峻現實。
1918年1月20日,《北京大學日刊》公布進德會首批會員,包括甲種會員19人,乙種會員9人,丙種會員2人,其中蔡元培本人為乙種會員。[16]此后會員人數不斷增加,截至1918年5月18日,校內會員人數已達469人,其中包括職員92人,教員76人,學生301人。[17]據統計,這一時期北大教員總數為217人,學生總數為1 980人[18],按照比例計算,加入進德會的人數已十分可觀。1918年秋季學期開學后,又不斷收到入會申請。1919年3月18日,進德會在《北京大學日刊》發布啟事,公布新入會會員,其中包括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校長陳寶泉,1918 年9 月開學后收到的申請至此已達436份。[19]按照常理,進德會的會員人數達到新高,影響也逐步擴大,正處在蓬勃發展的階段。然而,該會的工作竟戛然而止,此后未再發布公告。
北大進德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革命烈士王復生(原名王濡廷)1918年秋考入北大,入校前已聽說蔡元培發起成立了進德會。在給父親的家書中,他提出入學后擬盡早加入進德會,“入會后各方面監視綦嚴,己有所懾。他人雖欲強之冶游取樂,亦易謝絕”[20]。王復生在1918年10月遞交了入會申請,除三條基本戒約之外,還選擇了“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不吸煙,不飲酒”四條戒約,體現出嚴于律己的態度。[21]教員錢玄同加入進德會后,基本能夠遵守戒約,1919 年2 月4日,因天氣太冷,到西車站吃了一頓西餐,并喝了一杯白蘭地酒。為減少內心的不安,他在日記中為自己辯解:“為驅寒而喝酒,或可以說是喝藥酒,不算犯進德會會規罷!”[22]可見進德會戒約對其仍有所約束。
與此同時,進德會也面臨一系列的難題。其中包括如何切實幫助會員“進德”,如何進行監督,對違反戒約者如何懲罰,等等。總體來看,進德會在上述幾方面均無行之有效的辦法。第一個方面,有會員提議通過時常開會來促進會員的交流[23]3-4,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這一建議并未被采納。第二個方面,按照蔡元培最初的計劃,進德會設評議員與糾察員,前者負責審議,后者負責監督。在1918年6月29日召開的評議員糾察員第一次會議上,被選為糾察員的李大釗指出,糾察員的職責不易履行,建議取消這一名目,會議表決將已選出的糾察員全部改為評議員,這也就意味著由會員進行相互監督。第三個方面,在取消糾察員之后,進德會規定,如有違反戒約的情況,由其他會員簽名報告,書記收到報告后通信勸告該會員,若此后仍違反戒約,經會員十人以上簽名報告,由評議員展開調查,如果屬實,開評議會宣告除名。[24]可見,上述規定較為繁瑣,不易執行。
由于進德會的制度設計不夠完善,在實踐中也出現諸多問題。首先,進德會戒約的執行基本上依靠會員的自覺,而個人的自覺是不可靠的。自蔡元培發起成立進德會后,學校內外對于部分會員不守戒約的責難之聲就未停止過。1918 年10 月17日,學生梁紹文上書蔡元培:“我常常聽見別人說,進德會的人,亦有叉麻雀的,贊成進德會的人,亦有逛窯子的,這樣子看來,進德會的條文,不過一種欺人之具罷了。”[23]3其次,會員之間相互檢舉的約戒既不現實,也不利于組織內部的團結。事實上并未有人因受到檢舉而被除名。此外,也有人認為,道德是個人的事情,不應通過社團來標榜,因此不屑于入進德會。[25]面對外界的質疑,蔡元培最初尚能以進德會會員眾多,難免有人不守戒約作解釋。然而,隨著攻擊北大文科學長、進德會評議員陳獨秀私德不修的報道鬧得沸沸揚揚[26],蔡元培不得不作出回應。1919 年3 月26 日,蔡元培、湯爾和、馬敘倫等連夜開會商討,最終決定免去陳獨秀的文科學長職務。但此次風波對進德會還是造成了巨大沖擊,在此之后,進德會再未發布消息。
總體而言,蔡元培通過進德會培育私德的嘗試不乏新意,但并未取得預期成效。從進德會的會員數量來看,蔡元培對私德的重視得到大量師生的認可,表明進德會在觀念層面并未遭遇大的阻礙。然而,北大進德會的戒約系從他處借鑒而來,并未根據自身的環境和特點作大的調整,相關規章制度也不夠完善,加之此時北大正處在從“官僚養成所”向現代大學轉化的時期,舊習仍有一定慣性,難免出現泥沙俱下的情形,進德會也因此遭受嚴重挫折,難以為繼。
三、公德的培養及其問題
作為一位具有宏闊視野的現代教育家,在私德之外,蔡元培亦十分重視公德的培養。他指出,在傳統社會中,人們的舉動“往往就一人一家著想,而乏團體社會之觀念”[4]102,亦即缺乏公德。在蔡元培看來,“公爾忘私之心,于道德最為高尚,而社會之進步,實由于是……使人人持自利主義,而漠然于社會之利害,則其社會必日趨腐敗,而人民必日就零落……”[27]116。蔡元培在論述公德時,強調的是對社會利益的關心,而非一般意義上的公共生活中的規范與準則。對當時的北大學生而言,國家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學校則是微型的社會,“愛國”與“愛校”是公德中較為顯著的兩個方面,以下即圍繞這兩個方面作重點討論。
對于“愛國”與“愛校”,蔡元培均有獨立的見解。蔡元培的道德觀念含有某種世界主義的立場。他曾指出:“故為國家計,亦當以有利于國,而有利于世界,或無害于世界者,為標準。而所謂國民者,亦同時為全世界人類之一分子。茍倡絕對的國家主義,而置人道主義于不顧,則雖以德意志之強而終不免于失敗,況其他乎?”[4]531可見,愛國是蔡元培非常重視的一種道德品質。但另一方面,鑒于“一戰”當中極端的國家主義給人類帶來的災難,在愛國主義之上,蔡元培又強調人道主義,力求實現二者的統一。作為一校之長,蔡元培認為,學生理應對學校有認同感。他強調“團體的榮譽,就是個人的榮譽”[28]140,在給學生的復信中也指出,作為北大學子“宜愛護母校”[29],要求學生自覺維護學校的名譽。
就這一時期的北大而言,學生“愛國”與“愛校”最集中的體現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的爆發和蔡元培有著密切的聯系。一方面,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學校長,本身即懷著一種深摯的愛國情懷。在各種場合的演講中,他多次提醒學生關心國家與社會。另一方面,蔡元培在1919年5月3日向學生透露了巴黎和會的消息[30],直接促成了五四運動的爆發。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一頁,五四運動充分展現了學生的愛國精神和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在1919年5月4日的游行示威結束之后,學生們積極營救被拘捕的同學,并在蔡元培辭職出京后以罷課要求“挽蔡”,充分彰顯出愛校的熱忱。從上述角度來說,蔡元培對公德的培養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然而,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既不容許學生的“愛國”行為,也不容許蔡元培大力提倡“愛國”。1919年5月4日當天下午,32名參與游行的學生被軍警拘捕,其中有北大學生20人。[31]據傳北洋政府已決定將蔡元培免職,由馬其昶接任北大校長,甚至更有傳言稱有人要焚毀北京大學,暗殺蔡元培。[4]629-630顯然,在北洋軍閥統治下的中國,嚴重缺乏開展公德教育的空間。
就蔡元培而言,從現實的角度考量,欲維持學校、保護學生,勢必要對學生的愛國運動有所約束。在觀念層面,蔡元培對五四運動亦持一種矛盾的態度。他在內心認可學生對國事的關心,但他同時也認為,因罷課而影響學業是一件得不償失的事情。對于這一問題,學界已有所探討,此處擬從德育的角度對蔡元培的立場作進一步的分析。1920年5月,蔡元培在《新教育》雜志發表文章,對一年前的五四運動作了回顧與反思。他指出,五四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引發學生的“虛榮心、倚賴心,精神上的損失,也著實不小”[28]140。所謂虛榮心,指的是學生將運動視為出風頭、邀名譽的機會,而倚賴心指的是學生對群眾運動的依賴,把其當作解決問題的一個便捷途徑。
針對上述情況,蔡元培嘗試在德育方面采取相關措施對學生進行引導,一個重要做法是將學生的愛國之心引導到愛民的途徑上。這種引導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開展平民教育,其二是關心民間疾苦。
前一方面,在1919 年9 月的開學典禮上,蔡元培著重指出:“儻沒有養成博愛人類的心情,服務社會的習慣,不但印證的材料不完全,就是研究的結果也是虛無。所以本校提倡消費公社、平民講演、校役夜班與《新潮》雜志等,這些都是本校最注重的事項,望諸君特別注意。”[4]701對于五四運動,蔡元培斷言:“五四后的惟一好結果,是平民教育。乘我們用功的余暇辦些學校,教育那些失學的人,就是犧牲光陰,也是值得的。”[28]210可見蔡元培希望學生將目光從抽象的國家轉向切實的平民教育問題。
后一方面,蔡元培則是以身作則,做出表率。1920年,中國北方地區遭遇大旱,蔡元培聯合學校部分教職員工發起成立北京大學賑災會,倡議師生踴躍捐款。部分學生到災區調查災情,用文字或照片發表出來,以求引發更為廣泛的關注,蔡元培對此給予了充分肯定。[28]3371922年,浙江遭受特大水災,蔡元培兩次在《北京大學日刊》發布啟事,號召學校師生特別是浙籍師生施以援手。[28]822
上述言論和舉措表明,蔡元培試圖將愛國主義教育與以“自由、平等、親愛”[27]10為核心的公民道德教育相結合。這能對學生起到潛移默化的德育作用,但其成效亦不能過分高估。五四運動三周年之際,蔡元培曾發表文章感慨:“聽講以外,聽聽戲,打打撲克,把時間消遣去了,不肯在公益上盡點義務,現在已經沒有這種人了么?怕不但不是沒有,而且還是很多。”[28]616可見雖有蔡元培的極力倡導,仍有部分學生對公共利益并不關心。
就“愛校”這一層面而言,當學校利益與個人利益產生沖突之時,學生往往不能體諒校方的難處,甚至出現過激舉動。發生于1922 年10 月的“講義費風潮”即集中反映出蔡元培面臨的德育困境。由于辦學經費拮據,北京大學決定在1922年秋季學期對免費發放講義的制度進行調整,向學生收取講義費。部分學生得知消息后,感到自身權利受到侵犯,遂于10月17日下午群擁至學校會計課,謾罵乃至恫嚇相關職員。10月18日一早,又有數十名學生涌到校長室,蔡元培與教職員多方解釋,學生依然激憤異常,一向溫文爾雅的蔡元培也不禁說出“我給你們決斗”[32]的憤怒之語。第二天蔡元培即遞交辭呈,最終在學生的挽留下復職。此次風潮經報章披露后,一時輿論嘩然,對學校的聲譽和辦學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蔡元培之所以將此事看得極重,主要是在道德層面對北大學生失望。在辭呈中,蔡元培不無沉痛地寫道:“此種越軌舉動,出于全國最高學府之學生,殊可惋惜。廢置講義費之事甚小,而破壞學校紀律之事實大,涓涓之水,將成江河,風氣所至,將使全國學校共受其禍。”[28]784-785在復職后召開的全校大會上,蔡元培再次談及此次風潮,并著重指出三點:第一,此種有損人格的舉動竟然出自于大學學生,使人失望;第二,講義費問題本可以通過協商解決,不應訴諸暴力;第三,此次風潮竟有不少學生盲從,更有不少學生隔岸觀火,令人心寒。[28]788上述幾點均指向道德層面的批評。
對于如何避免類似的風潮再次發生,蔡元培并未止于強調遵守校紀校規,而是更進一層,一方面是動之以情,喚起學生的道德情感:“本校現正在最困難的地位,不是全校同人齊心協力來維持他,怕的終不免有破壞的一日呵!”[28]789另一方面則曉之以理,指出應敬愛師長,建立良好的師生關系:“我們若是為維持本校……總要大家保持一種良好的感情,不要多所猜疑。”[28]789在他看來,“愛校”應從外在的要求轉化為學生內在的自覺。
不過,就在“講義費風潮”發生三個月后,蔡元培因“羅文干案”辭職(有論者指出,此次辭職與“講義費風潮”亦有關聯)。[33]1923年6月,北大學生會派代表赴上海請蔡元培返校復職,蔡元培在給學生會的信中說明了無法返校的緣由,同時特別指出:“培以為電報政策,群眾運動,在今日之中國,均成弩末。諸君愛國愛校,均當表示實力(指共同籌措學校經費——筆者注),請于維持母校一試之。”[34]其對運動式的“愛國愛校”的態度顯而易見。蔡元培此后數年只在名義上擔任北大校長,德育方面的改革和探索自然也就此中斷。
由上可知,五四運動凸顯了北大學生愛國愛校的情懷,但學生運動這一形式有其弊端,“講義費風潮”則暴露出部分學生愛校意識的欠缺。蔡元培試圖對此作出引導,力求將抽象的“愛國”落實為具體的“愛民”,并在“情”與“理”兩方面增強學生愛校的自覺。然而,一方面,政治的黑暗令學生不能滿足于埋頭讀書與從事成效較緩的社會服務;另一方面,運動的勝利也助長了部分學生心態的膨脹,不再安于聽從師長的教導。在惡劣的政治生態之下,蔡元培亦不免屢次辭職,其培養公德的舉措和成效也隨之受到影響。
結語
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正值近代中國政治與文化的變革與動蕩之際,加之德育本身的復雜性,使得蔡元培在北大開展德育之時面臨諸多困難。
首先,從理念層面來看,蔡元培對德國古典大學觀作了本土轉化,在強調學術研究的同時,將德育置于極為重要的地位。然而,學術的求真取向與道德的求善取向之間存在內在沖突,蔡元培未能充分調和二者的矛盾。就德育觀而言,面對“中西”與“公私”之爭,蔡元培持相對穩健的立場,試圖融通中西,兼重公德與私德,但同時也為不同道德觀念的沖突留下了空間。此外,“公”“私”截然二分的方式實質上延續了梁啟超《新民說》中的思路[35],有其歷史局限性。
其次,就制度層面而論,由于德國古典大學制度強調通過系統的學術訓練培養學生的理性,蔡元培將這一制度移植到中國時,在德育方面并無充足的制度資源可供借鑒。另一方面,蔡元培對古代書院重視德育的傳統有所體認[36],但在實際辦學中,受制于“教授治校”“選科制”等北大整體的治理原則和制度設計,并未充分利用書院在德育方面的相關經驗和舉措。進德會作為蔡元培在北京大學培育私德的主要方式,融合了中國的結社傳統與西方大學的社團傳統,在德育形式上有所創新,但其構想與規章并非來自教育領域,總體而言組織較為松散,規章制度亦不夠完善。對于公德的培養,蔡元培則主要借助個人的演講及校役夜班、平民講演等相對靈活的形式。總之,這一時期北大在德育方面并未形成固定而成熟的制度,因而缺乏約束力。
最后,在實踐層面來看,蔡元培在開展德育的過程中面臨嚴峻的挑戰。當時北大的師資、課程與教學均以學術為中心,德育的地位發生動搖。蔡元培試圖在私德與公德兩方面加強德育,然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通過進德會培育私德的努力受舊習的制約而遭受挫折;另一方面,蔡元培嘗試引導學生將“愛國”落實為“愛民”,而非罷課與游行,并注重增強學生愛校的自覺,但這一時期政治腐敗、社會動蕩,公德教育的開展受到政治現實的掣肘,加之北大學生的自主意識空前高漲,不安于聽從師長的道德說教,使得蔡元培培養公德的相關舉措不易收到成效。
更進一層而言,蔡元培與北大的德育困局并非近代中國特定大學所面臨的個別性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也折射出現代大學德育面臨的普遍困境。在20 世紀上半葉,西方大學同樣出現了“知識”與“道德”的分離,以及隨之而來的德育的削弱。[37]就這一層面來說,重溫蔡元培對大學德育的探索與嘗試對于當前的大學教育依然有其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