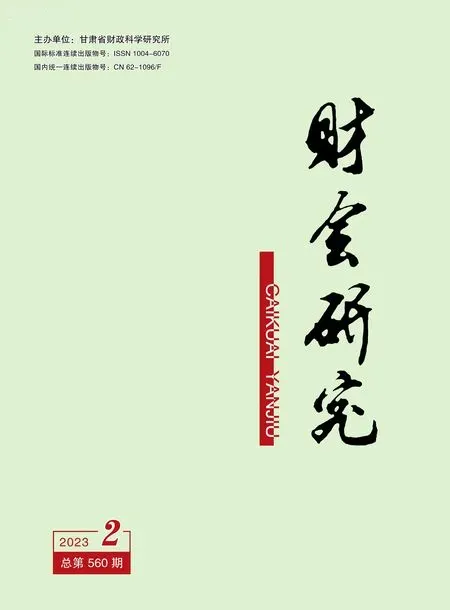公司治理與避稅研究述評
■/ 杜永奎 彭 慧
一、引言
近些年,明星偷稅漏稅事件頻繁爆出,將相關企業避稅問題推向風口浪尖,據此調查發現,企業利用注冊到“稅收洼地”、進入“特殊行業”等手段實施避稅已成為常見現象,極大破壞了市場秩序。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首先,為緩解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導致的經濟下行壓力,新政策的出臺成為各國干預市場的一種手段,政策的不斷調整形成外部政策環境的不確定性。尤其是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經濟高質量發展時期,更是出臺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例如“減稅降費”“創新扶持”等。面對經濟政策的高度不確定,企業可預測能力降低,經營風險增加;銀行等金融機構對企業的信用水平要求提高,融資約束加劇,導致企業利用避稅活動確保內源資金的留存、彌補資源的不易獲取性。其次,外部宏觀環境影響避稅的同時,稅收監管制度也加劇企業避稅行為的發生,《稅收征管》第三十五條規定:納稅人申報的計稅依據明顯偏低,又無正當理由的,稅務機關有權核定其應納稅額,但制度僅對核定征收作出了規范,未對避稅行為作否定規定,法律政策的不完善性提高了避稅行為的高發生性。最后,公司治理影響公司行為,尤其是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背景下,催生并加劇了代理沖突,增加了管理層、大股東的“經濟人”行為,以激進避稅實現自身私利的謀取和對企業財富的轉移,這無益于企業永續長存的發展目標。由此,本文著重于通過梳理分析國內外有關公司治理與避稅的研究成果,以“公司治理—公司行為—經濟后果”為行文邏輯,對內外部公司治理機制如何影響避稅及產生的經濟后果進行總結和述評,為改善公司治理制約避稅行為提供理論支撐和實踐方向。
二、內部治理機制與避稅行為
(一)管理者特征
“高階梯隊理論”揭示了高管個人特征是影響企業戰略導向和決策行為的關鍵誘因。一方面,女性高管有著高風險厭惡性(Marianne,2011)和高信息透明度要求,這有利于減少企業涉稅風險操作和避稅活動。尤其是在代理沖突背景下,提高高管團隊中的女性比例,利用女性高管的低自利性行為能有效降低代理成本、緩解代理問題,發揮女性高管的“公司治理效應”,制約激進避稅行為。另一方面,高管權力特征會加劇避稅(代彬等,2016),高權力的管理者擁有實質上的控制權,高自由度以及低約束力導致管理層以避稅實現對私利的攫取。并且,一旦股東、董事會、CEO 的權力制衡機制出現偏差,將減少對CEO的約束,導致形成私利謀取的高發生性以及尋租途徑的多元化,使得機會主義行為成為管理者的權力體現,避稅策略成為管理者對避稅收益、成本及風險權衡后的結果,進一步加大了企業稅收激進度(謝盛紋等,2014)。
(二)內部控制
現代企業兩權分離制度的模式促使形成復雜的代理問題,產生較高的代理成本(葉康濤等,2014),不僅加劇經理人的尋租行為,侵蝕企業利益,也助長了避稅活動的高發生性,產生嚴重的稅務風險。以合規為導向的內部控制作為一項治理機制,能有效作用于稅務風險管理,通過高效監督和嚴格控制的方式減少激進避稅活動。而且,合理有效的內部控制可以制約管理者的機會主義行為,降低代理成本(楊德明等,2009;劉冰熙等,2022),同時,企業利用自身合理的組織結構提高內控效率和稅務管理能力,增強企業的投融資效率,緩解融資約束,有助于減少企業為保證充分的內源資金而實施激進的避稅行為。另外,內部控制的有效實施使得企業各部門責任明確,有利于提高稅務職能部門的風險承擔能力、增強其責任意識,從根源上遏制激進避稅行為,保障企業健康可持續發展。
(三)股權集中度
已有成果表明,良好的內部控制有利于制約企業的激進避稅行為,然而,高股權集中度對避稅與內部控制呈現出反調節作用,即企業控股股東股權比例的提升將明顯減弱內部控制對避稅行為的約束作用(張琦,2021),在股權集中度較低的企業中,股東之間互相監督,能有效均衡企業的權益和風險,一旦股權高度集中,大股東權力將凌駕于內部控制制度之上,相比中小股東,大股東有絕對的信息優勢,更傾向于實施激進避稅謀求稅后利益最大化,大股東權力的制約作用,即第二類代理問題大大減弱了內部控制在避稅決策過程中的積極作用。但是,高股權集中也有一定的正向調節作用,根據“利益趨同假說”,高股權集中度能有效抑制第一類代理問題,有助于增強對管理者的監督和約束,降低企業的財務風險(Jensen et al.,1967),而且有利于制約代理問題下管理層的激進避稅行為,減少其尋租動機下的私利攫取,提高企業資源的配置效率最大化,實現帕累托最優。
(四)管理者激勵
股權激勵作為公司的長期激勵機制,對管理者具有一定的約束作用。在代理理論下,管理者并不完全致力于增加股東利益,而是傾向于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尤其是當高管認為自身薪酬在行業中處于較低水平時,往往會利用自身職務的便利性實施復雜、隱蔽的激進避稅活動,將實現的現金流量歸為自身的隱形報酬,基于此,給予高管股權激勵措施,有利于提高對其約束力,有效降低避稅程度(Desai et al.,2009)。然而,管理者激勵也具有負面效應,當企業考慮到避稅的風險性較高時,為防止稅務機關的嚴格稽查和評估,往往采用股權激勵的方式反向引導管理者的行為,促使其實施風險性較小但更為積極的避稅活動,即通過隱蔽性手段降低企業的當期所得稅費用,減少納稅金額。而且,企業給予管理者更高的激勵補償實則是將委托者和代理者的利益趨同于一致,利用股權激勵比重的提高促進管理者增加公司收益的主動性,但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會加大其尋租行為以及更嚴重的代理沖突,導致產生嚴重的納稅不遵從行為(劉華等,2010)。

圖1 內部公司治理機制與避稅行為
三、外部治理機制與避稅行為
(一)董事高管責任保險
在已有董事高管責任保險與避稅的研究成果中主要呈現出不同的兩種觀點,其一,機會主義假說認為,企業的避稅活動源于管理層的機會主義動機,董責險的認購形成了“過度庇護”效應,提升了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Lin et al.,2013),加劇避稅。而且,避稅活動的實施與管理層的風險承擔能力高度相關,擁有高風險承擔能力的管理者,其面對風險的態度表現更為積極,趨向于高估避稅收益、低估避稅成本,加之董責險的“財產兜底”效應,增強了激進避稅的活躍性。其二,外部監督假說認為,董責險的認購是一種外部監督,通過引入“第三方”,即職業保險人,參與公司治理,遏制董事高管的信息隱藏,降低企業的違規概率(李從剛等,2020)。同時,認購董責險會增加保險公司對企業進行定期的檢查和評估活動,有助于緩解信息不對稱,有效抑制避稅活動的發生。
(二)審計
首先,審計作為外部治理機制之一,能有效制約激進避稅。管理層為避免審計師實施消極審計程序,出具不利審查結果,進而向利益相關者傳遞負面信號,降低利益相關者的信任度,極大可能會自覺減少稅收激進行為(金鑫等,2011),尤其在CEO權力較大,企業避稅較嚴重時,審計行業專長的進入能有效減弱CEO權力與避稅行為的正相關性;但是,相反觀點認為,具有專長的審計師具備專門的行業知識和相關政策法規,能充分利用會稅差異為企業提供稅收規避策略,從而加劇避稅程度,導致激進避稅(魏春燕,2014)。其次,強制性內部控制審計對避稅也有雙層效應。一方面,強制性內部控制制度的實施增加了管理層面臨的監管壓力,導致其通過更加隱蔽性的操作提高真實盈余管理程度(王嘉鑫等,2019),換言之,內部控制審計導致復雜的避稅策略成為真實盈余管理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強制性內部控制審計有利于緩解代理問題,通過發揮顯著的治理效應規范管理層行為,減弱管理層激進避稅動機,抑制高避稅水平。
(三)稅收征管
從根源上看,企業避稅程度是由避稅成本和避稅收益決定的,避稅成本是由國家稅收部門認定的經濟損失,避稅收益是由企業稅收規避形成的經濟利益,稅收征管依據有關法律法規由國家保障實施,對避稅活動產生影響。一方面,稅收征管能夠發揮公司治理作用,降低信息不透明性,改善委托代理問題,制約避稅活動。而且,較強的稅收征管意味著高避稅成本,能顯著降低企業負面聲譽沖擊下的激進避稅行為(詹新宇等,2022)。另一方面,稅收征管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企業的稅收負擔,減少了內源資金,形成“內憂”,也形成了負面的“征稅效應”,惡化了企業的融資約束(于文超等,2018),產生“外患”,使得企業無法依靠傳統的融資方式獲取足夠的需求資金,稅收作為一種傳統融資方式的替代品,自然成為企業激進避稅的選擇,形成了融資約束越強,避稅可能性越大的不良后果。

圖2 外部公司治理機制與避稅行為
四、企業避稅行為產生的經濟后果
(一)企業創新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一直堅持創新發展戰略,但在企業避稅行為戰略的選擇下,創新發展受到較大影響。目前,關于避稅行為與創新后果的觀點存有差異,其一,避稅有利于降低企業的實際所得稅率,通過“現金流入”效應增加現金流,提升財務水平,緩解融資約束,即使融資約束抑制創新發展,充足的現金流也是創新發展的重要基礎(Howell,2016)。并且,企業為實現高質量發展,增強競爭力,保證市場份額,必須展開創新活動,這意味著更大比例的現金投入,避稅行為選擇在一定意義上促進了創新發展,尤其在高競爭的行業環境下,避稅對創新的積極作用更為顯著。其二,第一類管理層的代理問題以及第二類大股東掏空行為提高了避稅激進度,降低了投資者的信任預期,形成高“風險溢價”,加劇了融資約束,降低了研發效率,導致研發活動引發道德風險,再一次加劇代理問題(Bauer et al.,2015),促使管理者實施私利謀取行為,導致“現金流”的流出,對創新造成不利影響。
(二)企業非效率投資
所謂非效率投資是指管理層在作出投資決策時,其目標不是致力于股東利益最大化,而是實現私人利益最大化。其中“過度投資”的形成是由于企業將資源投入到不盈利或高風險的項目,“投資不足”的形成是源于企業放棄將資源投入凈現值為正的項目。但無論哪種,都降低了企業對資源的利用率,偏離資源配置最優化,造成生產要素的浪費,降低企業價值。基于避稅的代理觀研究公司行為對經濟后果的影響,發現激進避稅不僅會激化管理層的代理問題,加劇管理者的尋租動機(Mayberry,2012),形成信息不對稱導致的管理層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造成與股東利益的偏離,形成有悖于股東價值最大化的投資(Jensen,1986),即非效率投資;而且會降低信息透明度,加劇信息在管理者與外部股東之間的不對稱情況,導致監管難度增大,出現更多的投資不足和過度投資問題,降低企業投資效率。可見,避稅程度越高,企業的非效率投資也就越高。

圖3 避稅行為與經濟后果
五、述評與展望
(一)文獻述評
1.避稅問題具有持續發酵性。通過對中國知網2010-2022年8月底避稅相關論文數量的整理,發現避稅一直是持續性的研究話題,每年的相關論文數量在100-150 篇左右,并呈現上升趨勢。從近幾年來看,熱度不下,持續發酵。這是由于避稅作為企業發展的一種行為選擇手段,能夠產生避稅的價值效應。在代理沖突日益嚴重的行業背景下,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較高,利用復雜操作實施避稅更加頻繁,形成了避稅產生的“現金流入”效應,增加了內源資金的可利用性,提升了企業財務水平。加之我國避稅相關的法律制度并不健全,避稅問題尚處于“灰色地帶”,由此導致企業避稅行為的多元化、高頻性和持續性。
2.避稅引發蝴蝶效應。復雜隱蔽的避稅行為會引發“蝴蝶效應”。首先,在信息不對稱路徑的作用下,企業信息透明度降低,增加監管難度,加劇融資約束和市場資源的不合理配置,形成“檸檬市場”。其次,受代理沖突的影響,管理層的高機會主義動機易引發道德風險,通過復雜的避稅活動實現尋租行為,減少對資金的合理有效利用,對股東等利益相關者造成巨大損害,引發管理層濫用款項、利潤操縱等問題及挪用資金、高管腐敗等風險,使得避稅活動成為代理問題的“黑箱”。
(二)研究展望
1.加強內部公司治理機制對避稅的制約。在對內部治理機制與避稅的研究成果梳理中發現,股權集中度和管理者激勵政策通過代理問題路徑對避稅有“明”,亦有“暗”。因此,如何加強內部治理機制制約避稅行為具有持續探討的價值。首先,對管理者進行股權激勵時,要確保一定的“度”,在合理可控的范圍內給予管理者適當的股權激勵,避免過高的股權比重,加劇代理沖突,形成激進避稅;其次,對股權過于集中的企業,可以依據產權性質給予對應的措施建議。例如,國有企業更注重自身的聲譽價值,對國有控股企業的避稅行為進行經濟處罰的同時,對大股東、管理者施以名譽壓力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抑制其激進避稅行為。
2.改善外部公司治理機制對避稅的制約。同樣,在對外部治理機制與避稅的研究成果梳理中發現,外部治理機制對避稅具有雙重影響。因此,以制度為準繩改善外部治理機制對避稅的抑制作用尤為重要。對稅收征管制度界定避稅程度做出相關規定,完善監管制度,形成良好的制度環境;對稅務部門的稽查工作保證獨立性,通過互聯網與企業、工商管理、金融機構和銀行建立聯系,查明真實的商業實質,增加避稅行為的可發現性;對審計機構、行業專長審計師加大監督力度,提高違法成本和懲罰力度,增強避稅行為的透明度。打造“有法可依,違法必究,究則必嚴”的制度規范和行業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