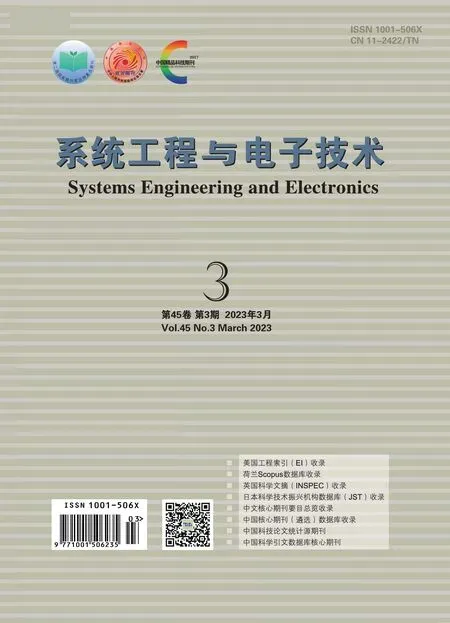基于殺傷鏈的作戰體系網絡關鍵節點識別方法
王耀祖, 尚柏林,2,*, 宋筆鋒,2, 李鵬飛, 科爾沁
(1. 西北工業大學航空學院, 陜西 西安 710072;2. 飛行器體系貢獻度與綜合設計工業和信息化部重點實驗室, 陜西 西安 710072)
0 引 言
隨著現代高新技術在軍事領域的深入應用,戰爭模式正由“平臺中心戰”向雙方作戰體系之間的對抗快速轉變。對作戰體系中的關鍵裝備進行有效識別,一方面可以從“攻”的視角指導實際的作戰行動,擊其要害,實現對敵方體系的有效攻擊;另一方面,也可以從“防”的視角識別我方體系的脆弱部分,為體系的防御與結構優化提供指導。
利用復雜網絡模型將武器裝備體系結構映射為網絡中的節點與邊,是當前作戰體系建模中較為重要的方法[1-3]。基于此,作戰體系中關鍵裝備的識別就可以等價于對網絡模型中關鍵節點的識別,這已成為當前研究的主流趨勢[4]。當前,作戰體系網絡關鍵節點識別的主要方法可分為以下3類。
一類方法是基于網絡的局部或全局結構特征構建各種顯著性指標,用于作戰體系網絡的節點重要度排序,排序靠前的節點即為關鍵節點,常用的指標包括度[5]、節點強度[6]、介數[7]、PageRank[8]等。另一類方法是從體系整體視角出發,通過節點移除后對于體系功能的影響度量節點的關鍵程度,典型的方法包括節點刪除法[9]、節點收縮法[10]等。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學者[11-13]從作戰活動的OODA(observation, orientation, decision, action, OODA)循環出發,綜合考慮節點所經過的作戰功能鏈路數目、長度等因素,提出了相應的節點重要度衡量指標,用于體系網絡中關鍵節點的識別。
總體而言,基于復雜網絡開展作戰體系關鍵節點識別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14],雖然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實際應用中,以上三類方法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第一類方法的核心是通用的復雜網絡拓撲結構參數,這類方法對于實際作戰過程和裝備的功能特征反映不足,因此在實際應用中的魯棒性不強,對不同體系進行識別的結果的準確性有較大差異;第二類方法所得出的結果較為準確,但是存在識別結果可解釋性較差的問題,并且計算復雜程度較高,對于大規模網絡并不適用;第三類方法對作戰過程和裝備節點間的功能關系加以考慮,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但忽視了不同裝備的性能差異、不同任務的重要性等異質因素對體系關鍵節點的影響,存在一定的缺陷。
此外,作戰體系中裝備的性能差異導致了不同的作戰活動成功率,裝備間的功能協同與功能依賴又使各種作戰活動相互關聯。同時,作戰體系的對抗性凸顯了敵方體系的威脅的影響,導致不同敵方目標的重要程度存在差異。因此,為能有效識別作戰體系的關鍵節點,必須反映不同裝備性能差異、功能交互關系、敵方目標的重要性等實際作戰要素的影響,同時兼顧可解釋性較好、識別準確率較高、魯棒性較強的特點。
針對現有方法的不足與作戰體系的特點,本文綜合考慮各種異質因素的影響,提出了以殺傷鏈為核心的節點重要度指標,并利用網絡狀態轉化和子圖同構思想,給出了基于蒙特卡羅和改進Ullmann算法的重要度指標求解方法,用于作戰體系網絡關鍵節點的識別。
1 作戰體系網絡模型的構建
1.1 節點的建模
作戰體系網絡模型的構建是體系關鍵節點分析的基礎,在由敵我雙方武器裝備所組成的作戰體系中,可將武器裝備實體映射為網絡中的節點,并根據裝備的功能特點對節點的類型進行劃分。結合OODA循環理論以及國內外相關研究[1,15-17],可將作戰體系網絡中的節點分為以下4類。
(1) 偵察類節點S,主要作戰任務為對敵方目標實施探測、偵察和監視,獲取戰場信息,并將信息傳輸給體系中的其他裝備節點。
(2) 決策類節點D,主要作戰任務為對輸入的戰場信息進行處理與分析,做出行動決策,將決策信息傳輸給其他節點并進行指揮控制。
(3) 影響類節點I,主要作戰任務為對敵方體系中的裝備節點施加影響,以干擾敵方體系的正常運行,包括火力打擊裝備、電子干擾裝備等。
(4) 目標類節點T,即所要攻擊的敵方武器裝備體系網絡中的以上3類節點。

1.2 邊的建模
作戰體系網絡中的有向邊表征了裝備節點之間的功能交互關系,根據節點的組合類型,理論上共存在16種不同類型的有向邊,但考慮實際的作戰情況,通常只分析7種類型的有向邊[18],如表1所示。

表1 作戰體系網絡中邊的類型

(1)


2 基于殺傷鏈的關鍵節點識別
2.1 作戰體系網絡殺傷鏈的定義
20世紀90年代,美空軍以OODA循環理論為基礎,將針對目標的發現、定位、跟蹤、瞄準、交戰和評估(find, fix, track, target, engage, assess, F2T2EA)6個作戰環節組成的有序鏈路定義為殺傷鏈[19],用于分析對目標的攻擊過程,引起了學者的廣泛關注[20-23]。結合前文構建的作戰體系網絡模型,本文給出了作戰體系中殺傷鏈的定義:作戰體系能夠實現對敵方目標的有效打擊,是由于體系網絡中存在對目標節點實施“發現-感知-決策-打擊”行動的連續路徑,本文將以上包含目標節點的連續路徑定義為作戰體系網絡中的殺傷鏈。根據以上定義可知,在作戰體系網絡中,殺傷鏈以目標節點為起始與終結,當體系裝備形成了包含目標節點的殺傷鏈時,就實現了對于目標節點的有效攻擊。
結構最為簡單的標準形式殺傷鏈如圖1所示,即從目標節點經由偵察、決策、影響節點指向目標節點的連續路徑,可用T→S→D→I→T表示。在典型的作戰體系網絡中,主要考慮如表2所示的7種類型的殺傷鏈[24]。

圖1 標準形式的殺傷鏈Fig.1 Standard form of kill chain

表2 7種類型的殺傷鏈
2.2 關鍵節點識別問題的轉化
由前文可知,殺傷鏈的形成是對敵方目標實施有效攻擊的關鍵,因此節點在殺傷鏈的形成中發揮的作用越大,其關鍵程度就越高。在作戰體系網絡G中,邊的存在性反映了裝備間的功能交互關系,也決定了經過此邊的殺傷鏈的存在性;邊的權值則反映了裝備因性能差異所導致的不同作戰活動的成功率,影響著殺傷鏈的形成概率。對于規模較大的作戰體系網絡,在綜合考慮以上因素后,很難有精確算法能夠評估節點在殺傷鏈形成中的作用。對此,本文通過對邊狀態(連通與否)的蒙特卡羅抽樣實現了網絡狀態的轉化,將G轉化為無權網絡,進一步通過大量重復抽樣獲得統計規律,有效反映了邊的存在性和權值對殺傷鏈形成的影響。
此外,目標節點的權值反映了敵方目標的重要性,權值的不同導致殺傷鏈本身的重要程度存在差異,在重要程度越大的殺傷鏈的形成中發揮作用的節點,其關鍵程度也越高。為此,在獲得某一具體的網絡狀態后,需要搜索包含特定敵方目標的全部殺傷鏈。若將7種類型的殺傷鏈視作特定的網絡結構,則該問題就轉化為體系網絡中特定結構的搜索問題,又由于網絡可采用圖論語言進行描述,因此問題進一步轉化為圖中特定子圖的搜索問題,即子圖同構匹配問題。
在上述思路的基礎上,經分析可知,經過形成概率較大、數量較多且包括重要敵方目標殺傷鏈的節點相對關鍵。后文將構建定量化指標反映上述異質作戰要素的影響,實現基于殺傷鏈的節點重要度描述和關鍵節點識別。
2.3 基于蒙特卡羅的網絡狀態轉化

(2)

經過上述過程,邊權值與邊的存在性實現了統一,作戰體系網絡由有向加權網絡轉化為有向無權網絡。
2.4 基于改進Ullmann算法的殺傷鏈搜索
為定量分析各節點對于體系殺傷鏈的影響程度,需基于子圖同構匹配思想搜索抽樣網絡中的所有殺傷鏈,為構建節點重要度指標打下基礎。子圖同構匹配[26]主要研究在給定目標圖和查詢圖的前提下,如何從目標圖中找到與查詢圖結構相同的所有節點的映射集合,常用的方法包括Ullmann[27]、VF2[28]、GraphQL[29]等。本文將7種類型的殺傷鏈視作查詢圖,將由xk構成的網絡視作目標圖,依據問題的特點對Ullmann算法進行部分改進,用其實現殺傷鏈的搜索。


圖2 節點的初始映射關系示例Fig.2 Example of initial mapping relationship of nodes
(3)


(4)
根據Ullmann算法的同構判定規則,如果滿足:
(5)


2.5 關鍵節點識別與效果分析

在完成對G的K次重復蒙特卡羅網絡狀態抽樣后,本文綜合考慮節點所處的殺傷鏈數與敵方目標的重要性,提出了節點重要度指標R,用于度量節點的關鍵程度:
(6)
由式(6)可知,網絡G中節點的R值越大,說明相應節點在針對多數目標節點或者重要目標節點的形成概率較大的殺傷鏈中發揮的作用越大,相對其他節點就越關鍵,由此完成對于關鍵節點的識別。
為了檢驗本文方法對于關鍵節點的識別效果,可重復移除R值排序第一的節點和與該節點相連的邊,并與現有主要方法的結果進行對比,利用體系網絡效能降低程度的大小反映關鍵節點識別效果。依據文獻[31]的思想,本文規定作戰體系網絡效能Ef的計算方式如下所示:
(7)
綜合前文所述,基于殺傷鏈的作戰體系網絡關鍵節點識別方法的步驟如圖3所示。

圖3 基于殺傷鏈的關鍵節點識別方法流程圖Fig.3 Flowchart of key node ident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kill chain
3 實例分析
為驗證本文方法的可行性和適用性,同時進一步說明方法的實施細節,本文以某空中攔截任務體系為例進行案例分析。
紅藍雙方因主權問題發生軍事沖突,藍方派出由5架各型戰機組成的空中突擊編隊對紅方目標實施突襲,紅方則依靠己方20件各型裝備組成的作戰體系對藍方突擊編隊進行攔截。針對該典型空中攔截任務,對紅方體系中的關鍵裝備節點進行識別。
3.1 空中攔截任務體系網絡模型構建
根據各種裝備在作戰任務中的功能特點和關聯關系,將紅藍雙方裝備映射為如圖4所示的網絡模型。其中,目標節點T1~T5表示藍方的5架各型戰機,并規定目標節點的重要性權值向量w=(0.05,0.10,0.50,0.30,0.05),偵察節點S1~S7、決策節點D1~D6、影響節點I1~I7分別表示紅方的20件不同功能裝備。為方便展示,本部分將目標節點拆分為源節點和匯節點,分別繼承相應目標節點的流入邊與流出邊。

圖4 空中攔截任務作戰體系的網絡模型Fig.4 Network model of air interception mission operational system-of-systems
接下來,根據專家經驗為邊賦予權值:除表3所列出的邊外,T→S邊權值均為0.5,S→D邊權值均為0.8,D→I邊權值均為0.9,I→T邊權值均為0.6,S→S、D→S和D→D邊權值均為1。

表3 部分邊的權值
3.2 關鍵節點識別


圖5 某次抽樣獲得的網絡GkFig.5 Network Gkfrom a certain sample

(8)

(9)


(10)
可得其對應的矩陣C如下式所示:
(11)

(12)
接下來,對包含目標節點T3的其他類型殺傷鏈進行搜索,可獲得Gk中包含T3的全部殺傷鏈,所得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Gk中所有包含T3的殺傷鏈
對表4的結果進行統計分析,可獲得除目標節點外的其他所有節點處于包含T3殺傷鏈的次數,如表5所示(未列出節點的次數均為0)。

遍歷所有的目標節點,便可以得到網絡Gk中各個節點所處的殺傷鏈的數目,如表6所示。

表5 節點處于包含T3殺傷鏈的次數

表6 Gk中各個節點所處殺傷鏈的數目
最后令K=100,并重復上述過程K次,根據式(6)便可獲得除目標節點的其他各個節點的R值,如表7所示。

表7 目標節點外的其他節點的R值
根據所得結果可知,D2節點在體系中的R值最大,故D2是此狀態下體系中的關鍵節點;同時,還可根據R值的大小對其他節點的重要性進行排序。
3.3 不同方法識別效果對比分析
根據構建的網絡模型,采用度、節點強度、介數和環介數[11]等現有常用的復雜網絡關鍵節點識別方法,與本文方法的識別效果進行對比分析。不斷移除不同方法下重要度值最大的節點及相應的連邊,直至體系網絡效能降為0,最終所得結果如表8和圖6所示。

表8 不同方法依次移除的節點

圖6 關鍵節點識別效果對比圖Fig.6 Comparison diagram of key node identification effects
通過所得結果可以看出:在本研究案例中,本文方法所識別的關鍵節點被移除后,體系網絡效能下降最快,本文方法表現出了最好的識別效果。從具體識別結果來看,5種方法首先識別出的關鍵節點均為D2,但接下來本文方法所識別的節點S6、S3和S4等均處于包含重要目標(T3和T4)的形成概率較大的殺傷鏈上,因此對于體系網絡效能的影響較大。而其他方法的識別結果僅表現出了部分因素的作用,無法綜合反映邊的存在性、邊權值、目標重要性等對關鍵節點的影響,因此識別效果不及本文方法。
4 結束語
針對當前研究的不足和作戰體系裝備功能各異、交互復雜、對抗性強的特點,本文提出了基于殺傷鏈的作戰體系網絡關鍵節點識別方法,為體系中關鍵裝備的辨識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文重點探討了各種異質因素對關鍵節點識別的影響,利用蒙特卡羅抽樣實現了網絡狀態轉化,并通過大量重復抽樣獲得的統計規律,提出了邊的存在性和權值對殺傷鏈形成影響的定量分析方法,可適用于大規模網絡;基于子圖同構匹配思想,引入改進的Ullmann算法獲取包含特定目標的全部殺傷鏈,構建了節點重要度指標;對空中攔截任務體系的實例分析和與現有方法的對比表明,節點重要度指標R能夠反映不同裝備性能差異、功能交互關系、敵方目標的重要性等異質作戰要素的影響,驗證了本文方法的可行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此外,本文方法未詳細研究作戰體系網絡邊權值的計算、級聯失效等問題,這也是未來需要進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