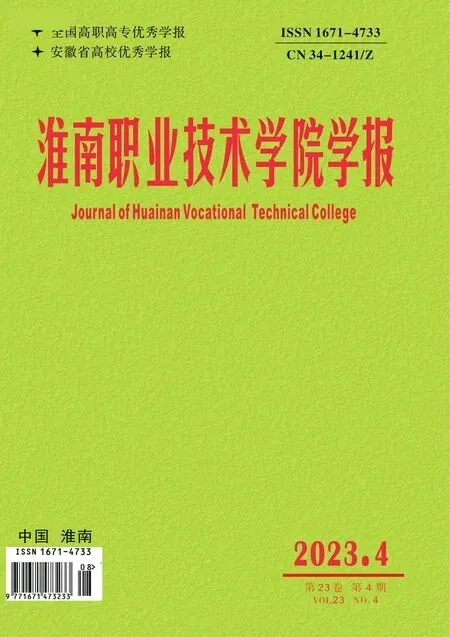孟子“浩然之氣”思想對理想人格培養(yǎng)的啟示
葛 萍
(蕪湖職業(yè)技術學院, 安徽 蕪湖 241003)
古代儒家思想家孟子提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1]”的理想人格,與新時代同向同行的中國人民同樣需要具有這樣的“大丈夫”的品格。對于品德高尚的“大丈夫”人格,孟子認為可以通過養(yǎng)“浩然之氣”來達成。因此,探析“浩然之氣”的本質目標及其修養(yǎng)方法,為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與社會主義理想人格的培育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培養(yǎng)“浩然之氣”其實質是為“不動心”
張岱說“此章叫作養(yǎng)氣,實無一字于氣上討力,通章只是‘持志’二字[2]。”關于“志”與“氣”之間的關系,孟子有所論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至,無暴其氣’[1]”。“志”統帥“氣”,朱熹給出的解釋為“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3]”。即把“志”解釋為“心”所向往的地方。楊升庵說:“次者,次舍之次,而非次第之次也[2]”。不是志先到,氣后來,而是氣隨志至,氣隨心志,“心”成為“氣”背后的道德力量,“心”才是“氣”真正的統帥,“持志”即是持“心”,持“心”的目的是練就“不動心”。“氣”作為孟子哲學中構成肉體的內在力量,“守氣”必然成為孟子修煉內心的一種手段。孟子用北宮黝、孟施舍兩位勇士與曾子作比較以論述“不動心”的修養(yǎng)之道。他認為北宮黝之勇是在身體和精神上都能忍受一切痛苦,又絕不忍受一切侮辱,而孟施舍之勇則是無視外部環(huán)境只存無懼之心。他將兩位勇士比作儒家先賢以印證自己的觀點,北宮黝像子夏,孟施舍像曾子,雖沒有直接說明哪一種勇更好,但他認為“孟施舍守約也”“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1]。曾子之勇,孟子有述“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1]。朱熹說:“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舍比于黝,為得其要也”“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3]。可見,曾子的“自反而縮”才是孟子真正所稱贊的,即“不動心”的修養(yǎng)之要。對于孟子“我四十不動心[1]”,朱熹給出了如下解釋:“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2]”。他認為,孔子的四十不惑與孟子的四十不動心相同。于孟子而言,最重要是要樹立心中的道德標準并加以修養(yǎng)強化,遇事反躬自問,求解于自身內心,不受外界的影響而堅守自己的言行。修養(yǎng)“浩然之氣”是為達成“不動心”。孟子認為,要想達成“不動心”就須“養(yǎng)勇”,而“養(yǎng)勇”的最佳辦法是“自反而縮”,“反”的就是自己的“心”,持“心”就是持“志”,就得修養(yǎng)“浩然之氣”。關于“浩然之氣”,孟子雖然表示“難言也”,但他還是在盡力描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1]”,朱熹對其解釋為“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2]”。“至大”就是指“浩然之氣”的外形之大,沒有限量;而“至剛”是指“浩然之氣”的具體性質,即不會退縮、不會彎曲、不會屈服。這樣的“浩然之氣”明顯不同于其他普通之“氣”,它更為浩大、堅韌而具有毅力。
二、“浩然之氣”的修養(yǎng)方法
孟子論述了他善養(yǎng)“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的方法。他認為可以通過“以直養(yǎng)而無害”“集義所生”和“知言”等方式來培養(yǎng),最終達到“塞于天地之間”的境界。
(一) “以直養(yǎng)而無害”充盈“浩然之氣”
“直”在中國傳統哲學里含義豐富。《說文解字》中說:“直,正見也[4]”本義為直視,引申為不彎曲,又可引申為正直、公正。《詩經》中相關的詩句“靖共爾位,好是正直[5]”,就是指正直的品德。孔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6]”。孔子認為“直”就是用來化解“怨”的方式方法,也可以理解為正直、公正。孔子還熱情的稱頌道:“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6]”。就是對史魚能以“進賢退不肖”為己任的贊許。《荀子·修身》里也提到“是謂是,非謂非,曰直[7]”。于儒家哲學而言,“直”代表著一種優(yōu)秀的道德品質。孟子曰:“以直養(yǎng)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1]”。此處之“直”與其他儒家哲學的觀點一致,也是指正直、公正的品德。孟子認為,如果能用正直的品德來培養(yǎng)而不去損害,就會使天地之間充滿這樣的氣。對于個人而言,想要陶養(yǎng)自身的“浩然之氣”,使其充盈于人的四肢百骸,首先就要有正直德行,只有用正直的德行來“養(yǎng)”,這股氣自會從人的內心獲得力量而游走充斥于人體之內;再次,躬身反問之時亦可因“浩然之氣”在人體之中滿溢,且沒有一絲空間留給不正直,能讓自身內心有機會產生不義的想法而有害于這股氣。運用這樣一正一反的方法來培養(yǎng)“浩然之氣”,體現了孟子對高尚道德情操的重視。
(二) 應“集義”生發(fā)“浩然之氣”
“義”作為儒家理想人格的標志性品質,孟子把“義”當做是一種絕對至上的道德原則。孟子對“義”十分重視,他認為在必要的時候是可以“舍生而取義者也[1]”。他對“義”的達成亦有非常高的要求。他提出,在培養(yǎng)“浩然之氣”之時,如果“行有不慊于心[1]”,只要行為上有一點點不能滿足內心“義”的要求或者是不出于“義”的初心,則最終結果就是“餒矣”[1]。正如馮友蘭所言:“義者宜也,即一個事物應有的樣子。它是一種絕對的道德律。社會的每個成員必須做某些事情,這些事情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8]”。培養(yǎng)“浩然之氣”是一種發(fā)自內心的必然要求,不是為了追求某種目的作出的行為規(guī)定。即使行為符合道德規(guī)定,但內心卻是為了某種私利,亦不可稱之為“義”。孟子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1]。孟子認為,“浩然之氣”不是突然某一次的正義行為就能取得,而是要進行長期的積累才能產生。正如朱熹所言:“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于義也[2]”。“浩然之氣”是靠平時日常的積累所慢慢存養(yǎng)而成。朱熹在解釋“襲”的時候說:“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2]”,他認為此處的“襲”就是軍事戰(zhàn)爭上的突襲、襲擊,是一種偶爾的發(fā)生,不是日常的常態(tài)。關于如何做到“集義”而非“義襲”,孟子認為應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1]”。培養(yǎng)“浩然之氣”是不能停下來的,一定要時時放于心上而不能忘卻。孟子還舉了宋人“揠苗助長”的例子,用以證明培養(yǎng)“浩然之氣”正如培育秧苗,應時時刻刻關注但不能一蹴而就,任何的投機取巧或者偶爾的為之都不能養(yǎng)成,這也讓想走捷徑的人失去了偶變投隙的辦法。
(三) 要“知言”避免蒙蔽“浩然之氣”
“知言”表面上看與“浩然之氣”聯系不大,但是當公孫丑問孟子,先生擅長哪一方面,孟子回答他說:“我知言,我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1]”,孟子將“知言”與“養(yǎng)吾浩然之氣”并列,這兩者的聯系必然是緊密的。《告子章句上》中,從孟子與公都子的問答中可以看出他的一些想法。公都子問孟子,為什么同樣是人,會有君子和小人之分。孟子回答他說滿足“大體”的是君子,滿足“小體”的則是小人。孟子認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1]”,耳朵、眼睛這類器官不會思考,會被外物所蒙蔽的是“小體”;“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1]”,心這個器官職在思考,一思考能得,不思考便不能得,這就是“大體”。“小體”被蒙蔽的原因在于“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1]”,是與外物相接觸造成的。因此,要修養(yǎng)“浩然之氣”以養(yǎng)“心”,則必須要讓“小體”不受蒙蔽,故“知言”十分必要。孟子認為“知言”就是“诐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1]”。孟子很自信地告訴公孫丑,只要讓他一聽,偏頗的言辭能知道它如何偏頗,過分不實的言辭能知道它如何言過其實,邪異不正的言辭能知道它如何背棄正道,狡辯的言辭能知道它理虧的地方在哪。這樣能夠分辨他人言辭的能力就是“知言”。能夠辨析他人的言辭十分重要。孟子認為,這些蒙蔽之辭是從人的內心產生,如果讓有這類言辭的人從事政治或者影響從事政治的人,那么將會危及政事。因此,君子只有做到“知言”,就能避免被“诐”“淫”“邪”“遁”的言辭蒙蔽,從而做到“直養(yǎng)”和“集義”,不損害“浩然之氣”的培養(yǎng),以此達到“不動心”。
三、“浩然之氣”的修養(yǎng)方法對新時代理想人格的培育啟示
(一) 立德
新時代高尚的理想人格就是要“立德”。“德”在孟子這里可以表述為“義”,他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1]”。他認為對于義的追求大于對生命的追求,寧可不要茍且偷生也要完成義的達成。孟子認為“仁,人心也;義,人路也[1]”。這也就是說,他追求“義”其實就是在追求“仁”,這是在完成對道德的追求。人若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則可有益于天地之間。在新時代,“直”對于普通人而言,就是要有正直的品德、高尚的道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個人層面要求公民做到“愛國、敬業(yè)、誠信、友善”,愛國是個人對祖國的最深厚、最直白熱烈的情感,這種情感會讓人對自己的行為進行矯正。在我國,自古以來就有諸如文天祥、鄧世昌、夏明翰這樣的愛國英雄,他們的舉動正是對愛國之大德做出了自己的回答。敬業(yè)就是人們在工作和學習中,嚴格遵守職業(yè)道德的態(tài)度;誠信則是日常行為的誠實,泛指人處事真誠、實誠;友愛是指在日常的人際相處中相互支持幫助,態(tài)度自然親切。這四種道德規(guī)范可以說都有著一個共同的內涵,就是“直”,無論是對待國家、對待職業(yè)、對待他人,都要有正直、公正的態(tài)度。
(二) 正行
要端正自己的品行。對于正行,可以運用孟子的“集義”觀要求自身,不拘泥于大事小情,遇事不煩其小不畏其大。在新時代,用來考察是否“集義”,最重要的是能否遵守社會主義榮辱觀,知什么可為、什么不可為。孟子對于榮辱也有所表述,他提出“仁則榮,不仁則辱[1]”,個體只有具備了榮辱觀,才能在實現個人價值的基礎上得到提高,自覺去實現社會價值,也才會在實現社會價值的時候努力奮斗,克服萬難,甚至能獻出自己的生命。“集義”要求個人在日常行為中不做出任何損害“義”的行為之事。孟子提出的“義襲”理論,讓想要通過偶爾為之的取巧者沒有了可行之路。要時刻以高度的自覺來要求自己,做到“君子慎其獨也[3]”。要堅決反對說一套做一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做到表里如一,始終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與黨同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行、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同進。
(三) 律言
要善于辨別不恰當的言論,并加以抵制。在新時代,很多年紀不大的青少年已不同早前,他們具有自己的時代特征,網絡化、信息化已然成為他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樣的好處很明顯,青少年能夠從網絡中學習到更多的知識,了解到更前沿、更訊時的實事;但缺點也很明顯,網絡的匿名性導致信息紛繁復雜,無論真實還是謠言都充雜其中。絕大部分的青少年還沒有足夠的能力去辨別相關的信息,就需要家長、老師為青少年進行把關、篩選、辨析。作為成年人,更要學會對網絡平臺上的一些不實謠言進行甄別,做到不信謠不傳謠。管好自己的言談。在新時代,孟子的“知言”觀能幫助如果個人管理好自身言行舉止。無論是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在網絡生活中,每個人在發(fā)表言論之時都能加以管理,而不是隨意發(fā)表不實不當不適的信息,社會上將會大大減少因言而生的悲劇,必然會營造出風正清朗的輿論風尚。
四、結語
孟子所善養(yǎng)“浩然之氣”的“大丈夫”理想人格是中國古代傳統儒家追求的理想道德人格。“直”是道德修養(yǎng)要崇高正直;“集義”說明行為處事要一以貫之不能懈怠;“知言”表明不僅要培養(yǎng)自己怎么說話、如何說話,也要具有善于辨析他人言語的能力。總之,這對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以及對社會主義理想人格的追求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