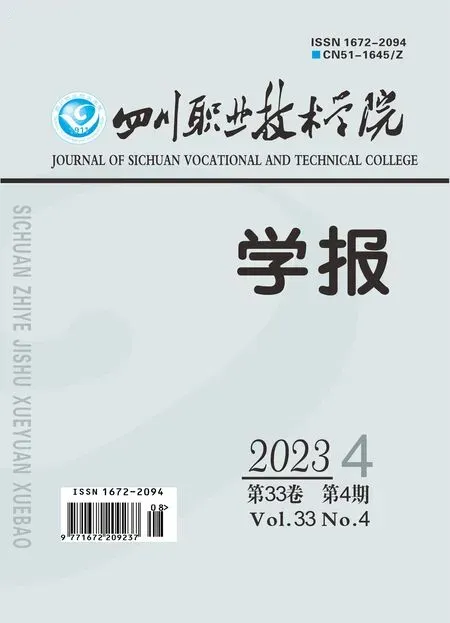羌族神話《燃比娃取火》的神話原型解讀
吳 純
(云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云南 昆明 650000)
神話原型批評作為一種廣為使用的文藝理論,發軔于弗雷澤的人類學理論、榮格的分析心理學理論、卡西爾的象征主義哲學,集成于文藝理論家諾斯萊普·弗萊之手。我國學者葉舒憲率先將其理論予以總結、引入和運用。簡言之,弗萊的原型理論中的“原型”,可以是意象、象征、主題、人物,也可以是結構單位,其特征在于反復出現于文學作品中,具有約定性的聯想;其次,原型體現著文學傳統的力量,能將原本孤立的作品所聯結,使文學成為一種社會交際的特殊形態。而原型的根源,既是社會心理的,又是歷史文化的,它將文學與生活溝通,成為二者相互作用的媒介。該理論注重以宏觀性的視角,結合整個人類文化創造中的各組成部分,以遠觀之法來解讀作品,使之系統而全面地展現文本背后所隱含的深層表達。
分布于岷山山脈深處的羌族,其歷史源遠流長而波瀾壯闊,無數次遷徙與征戰孕育了豐富的民族文化。由于缺少本民族文字,其文學和歷史僅以口傳心授而綿延至今。文學作為一種雜糅著主體觀念的社會現象,是一定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產物。因此在閱讀和分析羌族文學時,需注意其背后所蘊含的族群歷史、道德和宗教觀念等深層表達。羌族神話《燃比娃取火》(異文《燃比娃盜火》《熱比娃取火》《取火種》《蒙格西送火》等)是一則文化起源神話,該神話既流傳于民間民眾口中,也運用于羌族釋比的祭祀中,最早由羅世澤在1982年采集,現以羌族釋比周潤清解讀和翻譯的、收錄于四川省少數民族古籍整理辦公室主編的《羌族釋比經典》中的版本為分析對象,簡述其內容大致為:
在萬物美好的遠古時代,女首領阿勿巴吉帶領族人生產生活,立規約俗。諸神嫌人類愚鈍、人間聒噪,要對世間凡人予以教訓,惡神霍都主動領命,從此人間寒冷。天神蒙格西心疼人間,又見阿勿巴吉人美心善,便予其神果。阿勿巴吉腹中懷下天神之子,生孩后取名燃比娃,令其尋父取火。燃比娃歷經多次磨難,終取神火,從此人間復得溫暖。[1]
該神話內容豐富,囊括了諸多的文化元素和神話原型,運用神話原型批評的相關理論來解讀該取火神話,得以窺見其背后所蘊藏的,具有神話原型價值的神人結合意象、英雄原型、祖先信仰,成人儀禮,以及原始思維對于人類歷史的抽象講述,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哲學思考等內容。
一、神人結合的原始意象
羌族神話《燃比娃取火》流傳于民間,版本眾多。在諸多版本中,取火者燃比娃的父親均為天神蒙格西,母親為羌族的族群首領阿勿巴吉。天神蒙格西憐惜人間,又鐘情于阿勿巴吉,便予其神果,阿勿巴吉因此十月懷胎,產下天神之子。這一情節屬于典型的神人結合意象,天神蒙格西與人類阿勿巴吉結合,交合與受孕的過程被表述為“吞下神果”。而神人之子“燃比娃”,出生后便展現出非同凡人的一面,“渾身長得毛茸茸,又長一根長尾巴,還未落地就說話。”[1]266“一歲能將兔逮住,九歲殺虎又捉豹,十六成人體如山,越嶺跨澗本領高,一步能將山跨過,一躍能渡一條河,空中雄鷹也能擒,飛禽走獸語能通。”[1]267擁有如此神力的燃比娃,在取火過程中更展現出歷盡磨難而百折不撓的意志力,當其取火歸來后,眾人圍火而舞,燃比娃也由此成為族群內的取火英雄。
人類文化發展的歷史,實質上是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不斷協調人際關系、不斷完善社會結構、不斷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歷史。在原始社會初期,先民們僅掌握著初級的工具制造方法,從事著簡單的采集和漁獵活動,當其面臨無法預測和駕馭的自然現象時,僅能臣服和順從于自然,崇拜和依賴于自然的外化物,即主觀建構出的各種“神”。在這一過程中,將自身無法認識和把握的力量予以神化,故而神源于自然,是自然力的人格化后的產物。從該角度出發,神與人的接觸和結合,本質上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反映。此外,雖然神人之間存在著對立斗爭與統一和諧的兩種關系,但對于生產力和生產工具尚未發達的原始先民而言,自然力常是令人生畏和恐懼的。因而神人關系,或言人與自然之關系,更多時候均表現為對立相爭。神人結合的原始意象大量存在于各民族的書面文學和口頭文學中,代表著廣大原始先民們對于自身和自然的思考。正如《燃比娃取火》中眾天神嫌人類愚鈍便降下寒冷,天神霍都阻撓燃比娃取火等情節,不僅體現出神人之間的矛盾對立,也暗含著自然條件對于人類的束縛和壓制。不僅如此,在諸多書面文本和口承表達中,神與人的結合,實質上是人對于神的崇拜行為,人通過與神的接觸、交合、生子,同神產生關系,進而“借”到神力。這種“借神力”的行為,根本上仍是先民對于自然的崇敬,對于無法預測和駕馭的自然力量的臣服與順從,試圖通過神人之交,來提升自我族群的內在能力,也暗示了人類對于掌控自然力的內在渴望,企圖與神所匹敵。在《燃比娃取火》中,父系為神,母系為人,通過二者的神人結合,其子燃比娃具有了神與人的共同血液。換言之,既有神的能力,即前文所提及的落地能言、跨山渡河、通鳥獸語等;也有人的品格,即勇擔族群使命、歷萬難而不摧、意志堅定等。因此,融合了神人血液的燃比娃,憑借著自身的頑強意志力,以及父系天神的幫助,在取得神火后,被族人敬為英雄。
在羌族的神話敘事長詩《木姐珠與斗安珠》(異文《木姐珠與燃比娃》)中,也存在類似的神人結合原型。木姐珠身為天神木比塔的女兒,與凡人斗安珠相遇后相愛,斗安珠在木姐珠的幫助下,順利完成天神木比塔所設下的種種測試,進而成功迎娶天神木姐珠。在該故事情節中,凡人斗安珠先后展現出自己的體魄、智慧、勇氣、力量和品德,天神木比塔所設下的一系列考驗,正是原始農耕社會對于一位青年待婚男子的全面要求。神人的結合,凡人男子迎娶天神女性,在迎娶的過程中展現出凡人的諸多美好品行,這一情節所蘊藏的內在文化因子,即是神人間的斗爭關系。人在斗爭中憑借自身智慧和外在幫助,處于優勢而贏得斗爭,展現出人對于自然的認知和態度,從畏懼到順從,再發展到企圖匹敵,甚至于渴望戰勝。該過程中人的力量被逐漸放大,主觀能動性也逐步突顯,這是同人類的相關歷史發展所同步演化的。另外,羌族民間文學中“迎娶天神”的凡人男性,“嫁與天神”的凡人女性,以及“神人所生”的后代,此類與神產生關系的人物,大都被族群內部奉為英雄,或指定為祖先神,其相關故事更是為羌族釋比在祭祀時所唱誦,成為具有整體性和持久性的族群記憶。此類的神人結合原型,不僅體現在羌民族的遠古神話中,更廣泛分布于華夏各民族的神圣敘事里,深刻反映出早期人類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是具有表層特殊性和深層普遍性的典型原始意象。由此觀之,神人結合的原始意象,在本質上是原始先民對于自身和自然之關系的思考,通過神人二者的結合,達到調和人與自然關系的目的,并以此同神產生關系,進而“借”得神力,建構起族群內的英雄形象,隱含著原始先民渴望戰勝自然、征服自然的內在情感,達到增進族群精神力量,維系族群內部團結的潛在作用。
二、歷盡磨難的英雄原型
在羌族神話《燃比娃取火》中,產生取火的背景為人類世界正經受著漫長的寒冷,其前提為燃比娃之父乃天神蒙格西,且自身擁有神力,在這樣的背景和前提之下,燃比娃一出生雖經受嚴寒,但卻潛藏機遇與使命。在取火的過程中,燃比娃翻山越嶺,經受遙遠的路程而來到天門外,其后三次取火,途中經歷神火燒身和洪水漫卷,燃比娃數次昏迷,毛發盡褪又失去尾巴,在其父蒙格西的幫助下,將神火藏于白石中,最終把溫暖重新帶回人間。何以成為英雄?“一是他做了別人不愿或不能做的事,二是他是為自己也是為一切人而做的。”[2]365由此觀之,該情節中燃比娃三次取火,三遭磨難,屢戰霍都,不僅成功克服了路途中的艱難險阻,更承受住水與火的身體考驗。羌族先民尊燃比娃為取火英雄,不僅是紀念其卓越的取火功績和不凡的意志品格,更希望借此精神來團結族人,鼓舞士氣,增強自身民族的內部凝聚力。
在羌族的族群歷史中,燃比娃的英雄精神具有著深刻的普遍性,是深植于羌民族靈魂深處的精神表現。現代羌族主要分布于岷山山脈的高山深谷間,具體為四川省阿壩州的茂縣、汶川、理縣,以及綿陽市北川羌族自治縣。但依據考古發掘、文獻資料和口承表達的多重證明可知,其背后具有深遠的民族發展史和遷徙史。羌民族原本馳騁于廣袤的西北原野,甘青地區的河湟一帶為古羌的祖居地。在漫長的歷史中,古羌民族或東進中原,成為華夏民族之組成血液;或沿橫斷山脈向南遷徙,與當地其他部族產生交流與融合。因此當我們研究今日之藏、彝、白、哈尼、納西、傈僳、拉祜、基諾、普米、景頗等民族的歷史時,均須探討其與古羌之間的族源關系。費孝通先生將羌族稱為“一個向外輸血的民族”,而這種“輸血”行為的發生,則源自于古羌先民們千百年來不斷地遠離家園和遷徙他方。一個民族的遷徙史,注定充滿著征戰與困苦,注定是歷盡磨難和考驗的族群記憶。羌族史詩《羌戈大戰》記錄著古羌人因戰爭而遷徙至岷山地區的故事,該史詩以浪漫雄奇的語言,講述著羌人與魔兵、戈人之間的戰爭,史詩開篇便提及“訴說著祖先的英勇,訴說著祖先的堅強,他們從曠野的戈壁灘遷徙而來,他們從莽莽的草原上遷徙而來,他們與狡詐的魔兵刀光血濺,他們與兇殘的戈基人斗智斗勇”[1]4,族群間因生存資源而交戰,其中所承載的民族記憶和民族精神,一直為羌族釋比所演述至今。無論是《羌戈大戰》,抑或《燃比娃取火》,英雄形象的背后,所蘊藏的歷經磨難而愈發堅韌的品格,正是古羌先民們的遷徙歷史的真實講述。
歷經磨難的英雄原型,并非羌民族所獨有。于整體人類的歷史進程而言,此類英雄原型代表著遠古先民們同自然抗爭的永恒記憶。當自身力量無法同外界自然抗衡時,必然產生富有理想化和超越性質的個體角色,此角色高度凝煉起族群整體的共同希冀,是具有整體代表性的“超人”形象。歷覽古今中外,以及華夏各民族的書面文本和口承表達,均可發現此類受磨難的英雄原型的存在。射日英雄、取火英雄、治水英雄、創世英雄、文化英雄,抗爭英雄,英雄原型存在于神話的各個題材領域。此類原型代表了整體利益,他們承擔使命而歷盡磨難,是熔鑄了特定族群、特定背景、特定記憶、特定精神的文化綜合體,象征和表達著族群精神,鼓舞并引領著族群的發展方向。
三、“成人禮儀”的神話原型
縱覽人類文學的發展史可知,文學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深植于原始文化。而神話作為原初的文學模式,其研究必定要追溯至遠古的宗教禮儀,以及形而上的哲學和思維層面。因此對于神話原型的探討,本質上是一種文學層面的人類學研究。葉舒憲在《神話—原型批評》一書中論及“原型批評以人類學的理論及視野為基礎,其核心方法,按照弗萊的倡導,叫作‘遠觀’(Stand back),可以說是一種宏觀的全景式文學眼光”[2]。在此處理下,文學已不再作為單獨且孤立的文本,而是同人類整體的文化創造相結合,換言之,文學同宗教信仰、民間風俗、文化禮儀都緊密聯系。因而,以神話原型批評的相關理論來解讀羌族神話《燃比娃取火》,勢必要與相關的人生禮儀和宗教信仰相結合,以“遠觀”之法來審視該神話文本。
《燃比娃取火》講述著神人之子“燃比娃”,歷經磨難而前往天界盜取神火的故事。神話中提及“待你長大成了人,去上天庭把火取”[1]268。可見燃比娃取火之事發生在其成年之時或之后。其次,燃比娃承受住身體與精神的雙重考驗而取得神火,并在取火途中完成了由猴到人的身體形貌轉變,失去原有的猴形的外在表征,而成為“焦黑皮毛全脫盡,健美身形映水中”[1]278的人的基本樣貌。因此取火行為不僅使燃比娃獲得“人型”,成為一個擁有具體人類外在形象的“人”,更讓他經受了精神層面的磨礪,使其品性堅韌而愈加成熟,具有了抽象層面的“人”之品格。取火歸來后,燃比娃被族群內部尊為英雄,更使其完成了具有社會性的“身份轉變”。因此從這三個層面出發,燃比娃取火一事,完成了自身的“成人禮儀”。另外,火的使用對于人類歷史具有深遠意義,可用于照明、取暖、防衛和烹飪等諸多領域,極大地加速了人類文明的歷史演進。就整體層面的族群言之,從無火至有火,“火的使用”使得族群邁入新的歷史階段,生產力獲得極大提高。由此觀之,燃比娃取火一事,不僅是其個體生命的“成人禮儀”,更是族群整體的“成人禮儀”,兩個層面上的“主體”均在取火中獲得了超越原本的自身突破,因而更加完整和成熟。
位于岷江上游的羌民族,恪守著祖輩流傳至今的諸多人生禮儀,例如出生禮儀、成人禮儀、婚姻禮儀、喪葬禮儀等。并以此類禮儀來程序化地界定出人生的各個階段,賦予族人在不同人生階段以不同的社會角色,進而形成一整套既定且獨具民族特色的文化模式。將該神話與羌族傳統的成人禮儀相觀照,可以獲得超越文本層面的獨特理解。羌族男子的成人禮儀在其人生進程中顯得尤為重要,是青年人進入社會交往、尋求配偶、獲取社會認同的關鍵步驟。該禮儀多于年滿十五至十八周歲之際舉行,具體過程又分為屋內屋外兩種冠禮。屋內冠禮籌備于農歷八月,舉行于十至十二月之間,屆時釋比唱經并祭祀家中諸神,族長詳談祖先歷史,為其灌注本民族的內在情感和精神力量。屋外冠禮舉行于祭山大典之后,釋比唱誦族群歷史,為其祈禱祝福。成人禮儀的舉行,標志著羌族青年從此被接納為社會的一員,獲得群體的社會性承認。雖然此類儀禮已隨物質生活的提高而逐漸衰弱,但其背后所呈現的,則是羌人對于自身和外物關系的思考,即企圖通過主觀行為和外在形式達到強化自身生命力的深層目的,并以步驟化的程序來標志其具有社會身份。結合前文對于神話《燃比娃取火》中“成人禮儀”的相關分析,可見羌人在人生禮儀和文學文本中所共同呈現出的人生觀和生命觀,以及對于個體同群體之關系的思考。或言“把他從一個自然人在具體的社會環境和具體的文化背景中,通過周圍人的聯系形成相互作用的合力,使他逐漸認識自我,成為社會群體中的一員”[3]。得益于成人禮儀的存在和施行,燃比娃一類的羌族青年,通過克服挑戰和提升能力,完成身份標簽的轉變,進而融入社會,達到“成人”之目的。
四、原始思維的歷史講述
原始先民的生產生活實踐,以及與自然的矛盾關系是神話產生的基礎,而神話的內容與表達,則與人類思維的發展密切關聯,即“是以特定的社會條件下原始人類特有的思維方式——神話思維為其背景的。”[4]思維結構是指由思維主客體和思維媒介所共同構成的結構,以及在思維過程中諸要素的相互作用。在原始的蒙昧時代,思維的主客體之間常以一種含混不清的關系相伴而生,先民們運用“觀察、類比、摹寫”等方式來感知外部世界,其思維結構主要表現為類比思維和簡單的抽象思維。多種原始思維的含混雜糅,共同構成原始先民對于外部世界的基本表達,即遠古神話中常見的思維和表達方式。神話作為一種口頭文學,產生于民眾的生產生活中,其文本內容是結合了創作者主觀的夸張和想象,以及外在環境的客觀實在的綜合表達。因此,從某一程度而言,神話來源于模仿活動,即趙忠牧先生所言的摹寫—洞察的經驗知識。遠古先民觀察周圍環境,將日常所見之物、所觸之感都予以記錄,通過直接感官來獲取對于外部世界的基礎認知,諸多客觀認知在腦海中形成了簡單的抽象表達,此般內容便成為神話創作的基本元素。它們或關于生產生活,記錄日常;或解釋某種未知,表達關懷與敬畏;或講述自身歷史,謀求族群團結和內生力。諸如此類,神話亦可理解為遠古先民對于外物世界的整體感知和群體記憶,其深層次所蘊含的內在表達,可通過還原思維模式,以類比思維和簡單的抽象思維切入,來解讀神話內部的歷史講述。
羌族神話《燃比娃取火》,蘊含著古羌先民對于歷史的講述和思考。概言之,該神話中體現出父系氏族對于母系氏族的承接和轉變,生物進化視角下的人猴關系,以及火的使用與人類歷史階段之關系。羌人運用簡單的抽象思維和類比思維,在神話中講述社會發展和人類演變的歷史,反映出古羌先民對于“我是誰”“從哪來”等哲學問題的基本思考。聚焦于神話中的具體情節可知,部落首領阿勿巴吉為人類女性,其子燃比娃從母居,燃比娃出生后便問道“我的阿爸他是誰”[1]266。在遠古的母系社會,“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亦不懂得兩性之間交媾和懷孕生產的道理,因而《燃比娃取火》中所涉及到的“阿勿巴吉食用天神蒙格西所予的神果后懷孕”“燃比娃不知其父,從母居”等情節,均是對遠古母系氏族社會的歷史講述。其次,阿勿巴吉作為人類部落的首領,帶領族人尋找食物和組織生產,是該神話前半部分的主角。而取火成功的燃比娃被族人敬為英雄,羌人將獲得火、運載火、使用火的偉大功績都附著于燃比娃一人,使其成為該神話最終的歌頌對象。主角的轉變,也透露出人類社會已悄然從母系向父系開始過渡。而該神話《燃比娃取火》中所記錄的人類社會由無火、被動用火、主動取火,再到兩石相擊而“造火”的相關過程,即是對火的使用與人類歷史階段之關系的抽象講述。在無火時代,天寒地凍,人類刨開積雪食草根,而燃比娃第一次取火時用“油竹火把”,但狂風使神火引燃自身的毛發,這一階段的人類僅能被動用火,且極大地受制于自然火種的偶然性。第二次取火利用“瓦盆”盛火,暗示人類已進入主動保存自然火種的歷史階段。第三次取火,利用兩塊白石相碰撞,產生火星而引燃火把,此時人類已學會“造火”。燃比娃的取火歷程正是原始人類對于火的利用過程,而取火的成功也標志著人類邁進新的歷史階段。
另一方面,出生后的燃比娃,是渾身長滿長毛且有尾巴的“猴毛人”。在取火的過程中,大火將渾身毛發引燃,大水將焦黑的皮毛脫盡,關閉的天門將尾巴夾斷。三次磨難讓燃比娃“由猴變人”,失去原本屬于“猴”的外在表征,從形象上進化為“人”。而羌族的另一神話敘事長詩《木姐珠與斗安珠》也記載斗安珠為“猴毛人”,神話《猴人變人》記載祖先由“猴人”所變。可見在羌族的諸多民間文學作品中,均以猴為人類始祖,暗含“由猴變人”的生物進化過程,此論與現代科學之觀點不謀而合,是羌人對于生物演化和人猴關系的歷史講述。不獨于此,同屬于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的傈僳族、拉祜族、哈尼族、珞巴族和門巴族也有著與羌族《燃比娃取火》所類似的“猴人取火”神話。在珞巴族神話《人和猴子為什么不一樣》中,珞巴族先民“把猴子變人和火聯系了起來,反映了古代珞巴族在自己的實踐中體會到火對人類生存的作用”[5]。門巴族神話認為猴子在食用了燒熟的果子后,毛發脫落,逐漸有了人的模樣。傈僳族神話則認為天神用泥土捏成的獼猴演化成了人。因此,學者王小盾從發生學的角度對目前所見的45例猴組神話進行了分類描述,并依托神話學和語言學的相關資料梳理了漢藏語系民族的猴組神話譜系,認為此類神話“反映了漢藏文化共同體的某種嬗變”[6]。可見,人猴之變和火種的使用是普遍存在于漢藏語系民族間的共同記憶,是具有圖騰信仰性質的神話母題,更是分析原始思維、探討民族間交流與融合的直接論證。
神話《燃比娃取火》中的歷史講述,融合并反映著古羌先民的原始思維,而此類思維又以簡單的抽象思維和類比思維為主。將周圍的生存環境進行抽象化的表達,將自身文化和歷史進行類比化和象征化的講述,以燃比娃的取火歷程來暗示人類對火種的利用進程,以神話細節和神話主角的變化來象征母系父系氏族的悄然轉變,以燃比娃自身的體征變化來暗示整體人類的生物進化。由此可見,羌族先民運用原始思維,將外在事物和自我族群作為演繹對象,結合浪漫瑰奇的藝術語言,在其神話中蘊藏了大量的歷史表述。
五、結語
神話《燃比娃取火》廣泛流傳于羌族民眾口中,唱誦于釋比祭祀的具體儀禮中,講述著羌族先民同自然抗爭、取火以謀求生存的永恒記憶。該神話中所體現的文化基因,如今依然存在于羌族群眾的生活中,外化為“火塘文化”“白石崇拜”“獼猴崇拜”等文化事象。因此,以神話原型批評的相關理論解讀該取火神話,注重以遠觀之法進行審視,聯系羌族的民間風俗和宗教信仰,以該神話為切口,窺見燃比娃這一形象所代表的歷盡磨難的英雄原型,取火行為的背后所蘊藏的“成人儀禮”,原始思維對于自身文化和人類歷史的抽象講述,以及羌族先民對于人與自然之關系的哲學思考。
神話作為人類文學的最原初形態,產生于原始人類生產生活的具體實踐之中,是蘊藏著特殊時代下集體記憶、族群歷史、思維邏輯的綜合性表達。隨著社會生產力和人類思維模式的不斷發展,文學的體裁和樣式也與之同步更新迭代,其內容和形式也愈加豐富。因此,在文學不斷發展的態勢中回望和反觀文學的源頭,重新審視神話文本背后所隱含的豐富的深度表達,以及不同族群在原始思維表達上所具有的普遍共性,則有助于當下“以古審今”地反思人與自身、人與自然之關系,更有助于從文學層面來探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下所共通的原始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