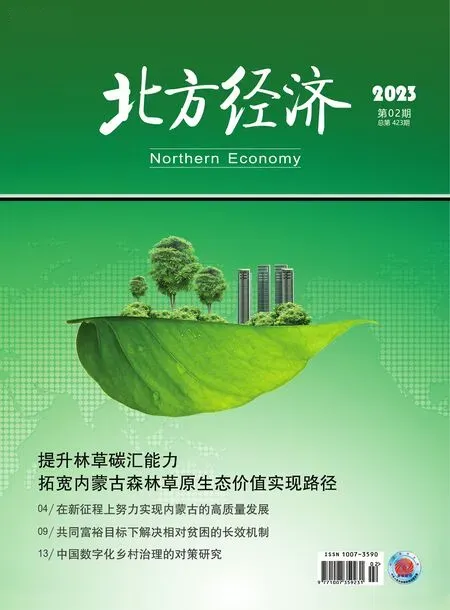草原固碳減排技術平臺體系建設的幾點建議
韓國棟 王忠武 武 倩 李治國 朱愛民

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提出:“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習近平主席在氣候雄心峰會上提出:“2030年,森林蓄積量將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2020年中央工作經濟會議明確提出“ 要開展大規模國土綠化行動,提升生態系統碳匯能力”。中央財經委第九次會議指出“要提升生態碳匯能力,強化國土空間規劃和用途管控,有效發揮森林、草原、濕地、海洋、土壤、凍土的固碳作用,提升生態系統碳匯增量。” “十四五”是碳達峰的關鍵期、窗口期,農業林草部門抓住機遇服務國家戰略,大有可為。
一、我國草原固碳減排處于政策制定和技術研發的關鍵時期
(一)中國碳市場忽視草原碳匯
在草原碳匯方面,除了造林、再造林等固碳項目被“清潔發展機制”(CDM)所承認外,其他土地利用方式固碳項目(或生物固碳項目、包括草原固碳項目)都沒有納入到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的框架中,并且由于土地利用項目的減排額度不允許在歐盟交易體系中進行交易,因此,草地固碳減排項目只能在自愿交易市場中交易。盡管從碳市場的份額看,目前自愿交易市場仍然只占很小的比重,然而其作用仍不可小覷。受金融危機的影響,2011年全球自愿交易市場達到了7900萬噸二氧化碳或5.47億美元的交易規模,而中國的自愿交易市場僅僅達到了23萬噸的交易量,尚處于起步階段。
目前國內外自愿交易市場中有十多個不同的碳標準,其中國內的三個標準,包括青海環境能源交易所的“三江源標準”、北京環境交易所的“熊貓標準”和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的“中國自愿碳減排標準”,都允許草原碳匯項目進行注冊、交易,但目前上述三個標準仍未批準相關的碳計量與監測方法學。國家發改委于2014年公布的“中國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標準(CCER)”,將可持續草地管理溫室氣體減排計量與監測方法學(AR-CM-004-V01)列入到國內有關溫室氣體增匯減排的國家標準之中。
中國草原碳匯資源得天獨厚,發展草原碳匯經濟成為履約國際承諾、打造碳匯新經濟、建設美麗中國的重要載體。目前,全球碳交易市場漸趨完善,我國碳交易市場前景廣闊,我國北方大范圍分布的各類型草原具有可觀的草原碳匯潛力。然而,對于草原碳匯在國家整體碳匯戰略規劃中并為涉及,關于碳匯平臺搭建,碳匯交易體系建立等方面均遠遠落后于其他行業。
(二)草原碳匯監測計量的難點
國內的碳標準已經備案了200個左右的不同領域碳減排計量和監測方法學,其中直接與草地畜牧業有關的減排計量和監測方法學僅有3個,但對于草原碳匯的監測計量方法學僅有1個,其成熟的應用案例僅為青海省的一個縣。我國北方地區的溫性草原,西部地區的溫性荒漠,西南地區的高寒草原,中原地區的暖性草原,南方地區的熱性草叢灌草叢構成了我國復雜的草原資源分布格局。不同類型的草原其植物種類、土壤類型和利用現狀差別很大。局部地區的草原碳匯監測計量方法很難準確評估我國草原碳匯狀況,在碳交易上也很難推動。因此,草地碳匯項目核算方法學尚未被廣泛應用。雖然草原植被光合作用的效率比較高,對碳的固定能力也更強,但是草原有機碳主要儲存于土壤中,監測計量相對復雜,尤其缺乏專家、機構的技術支持和創新研究,使草原碳匯的發展處于不利的地位。以上這些均成為我國草原碳匯計量體系構建的主要障礙。
二、建設國家草原固碳減排技術平臺意義重大
從國際發展趨勢來看,草原是與森林、海洋并列的地球上的三大碳匯之一, 草原碳儲量與森林相當。建立草原固碳減排技術平臺,對于確定草原在國家農業固碳減排中的作用,實現畜牧業的碳達峰和碳中和的目標具有重大的意義。
從我國發展需求來看,我國草原面積60億畝,占國土面積的41.7%。草原植被碳儲量約3.06Pg,草原土壤碳儲量約41.03Pg,草原總碳儲量約44.09Pg,大約占世界草原總碳儲量的9%-16%。我國每年草地固碳量約可以抵消全國年碳排放量的25%,因此,草地在我國陸地生態系統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并具有相當深厚的碳匯潛力。
從國內技術積累來看,近十年來,中國農業大學、內蒙古農業大學和中國科學院等單位完成了全國各種類型草地的植被、土壤和生態系統的碳儲量基礎研究數據,并開展了不同草原家庭牧場的優化放牧研究,積累了放牧利用下的草地固碳和減排技術。迫切需要國家從總體上構建草原固碳減排技術平臺體系,強化草原碳匯領域國家戰略科技力量。
三、草原固碳減排技術平臺體系建設思路
國家草原固碳減排技術平臺體系要以草原增匯和溫室氣體減排為核心,以全面掌握我國草原植被、土壤和生態系統碳的固定和氣體排放的動態變化規律、保護與利用相結合、提升草原固碳潛力為目標,融合碳貿易、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移動互聯和區塊鏈等現代信息技術,深度實現國家及全球尺度草原固碳減排的時空格局、草原畜牧業精準動態管理,并朝著立體化、實時化、定量化和智能化方向發展。基于此,我們建議國家有關部門加強統籌支持力度,著力做好以下重點工作:
(一)重視草原碳匯功能,加強碳匯市場建設
加強草原生態保護相關法律、規范的制定,彌補草原碳匯相關政策的不足。基于兩輪國家生態獎補政策實施的經驗,結合不同地域特色,大力推進禁牧休牧、草畜平衡等草原生態保護相關政策、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并將草原碳匯評價及價值測算納入到生態獎補范疇之內,為完善補償機制建立提供參考依據。
退化草原主要表現在植物種群有構成變差,優質牧草減少,生產力下降,土壤基質變差,土壤有機碳減少等現象。退化草原恢復本質上就是植被和土壤逐漸變好的過程,該過程也使草原可利用面積擴大、生態系統機能恢復,增大草原固碳潛力。我國西部、北部草原區域存在較大范圍的不同退化等級草地,其有著較大的碳匯潛力。基于國家現施行的各項草地生態修復及綜合治理工程,將碳匯能力增加到相關評價指標體系中,并形成較為穩定的草原生態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為未來草地總體生態功能發揮,草原碳匯估算及價值測算提供依據。
草原碳匯經濟應逐步被納入國家低碳經濟發展戰略。我國草原面積大,碳匯資源豐富,每年草地固碳量約可以抵消全國年碳排放量的25%,具有較大的碳交易市場潛力。隨著國際社會對于碳配額的爭奪,以及企業碳減排需求的趨增,開發草原碳匯產品、建設草原碳匯貿易將成為一項重大戰略,是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實現綠色發展的重要舉措。草原碳匯并不是一個新興事物,但是相比森林而言,草原碳匯產品則是個新事物。由于地方政府、企業和牧民均不熟悉碳交易的概念和要求。開發設計林草碳匯產品,發展碳交易需要通過局部地區試點進行推進,建立完善的碳匯交易體系,并將其納入到生態補償政策之中,將其作為草原生態補償和違法處罰重要指標之一。也可以通過建立碳稅激勵機制,限制高排放企業,鼓勵發展清潔能源及推動企業提前購買林草碳匯產品來緩解排放壓力。
我們可以借鑒國際碳交易和森林碳匯經驗,以有條件、有優勢的草原大區為布局重點,搭建交易平臺、完善配套體系、加強橫向合作、強化示范引領,推動草原碳匯經濟的啟動發展。同時,應將發展草原碳匯納入國家整體戰略規劃,并劃定國家草原碳匯經濟先行示范區,實現草原固碳增匯增綠與牧民增收多贏、草原碳匯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共建共榮的發展目標。
(二)科技創新,草原碳匯計量監測常態化
在借鑒國內外草原碳匯相關計量方法,結合我國草原資源的實際,利用已有的相關研究成果,構建相對完善的草原碳匯評價指標體系和方法學。同時,需將國家相關重大生態保護工程、重要科研成果和長期草原監測體系進行整合,在技術層面上構建完善的草原碳匯計量指標體系的長期監測平臺和技術體系,通過構建草原碳匯示范區,搭建草原碳匯交易平臺助力草原碳匯交易的積極推進。
草原溫室氣體排放主要來自與家畜、土壤及植物,通過研究不同家畜品種和數量、草原植物和土壤的溫室氣體排放規律,通過畜群結構調整、放牧載畜率優化和草原生態系統的適應性管理,探索“低碳型草原畜牧業”,達到減少草原生態系統的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這是草原畜牧業發展和草原生態保護并重原則的具體體現,也是實施草原碳匯交易的前提和基礎。
從我國草原利用的基本單元(家庭牧場)著手,發揮家庭牧場的生產經營的自主性,通過生產經營模式的調整優化,降低放牧家畜對草地的利用強度,為草原植被和土壤條件改善提供機會;加大政府及相關部門在家庭牧場尺度上的宣傳和培訓工作,建立信息傳播機制,普及草原碳匯知識;配合完善的碳匯補償機制和相關法律法規的保障體系,推動農牧民自主生產經營的同時注重生態保護,保障草原固碳能力發揮的有序性和持續性。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對于草原資源的監測保持良好,對于草地植被、土壤的相關數據較為齊全,以此為契機,結合國家統計數據和草原碳匯計量方法學的構建,建立完整的草原碳匯指標的監測體系,通過一定的政策、項目、資金、人員支持,使草原碳匯指標監測步入常態化并納入國家生態監測系統之中,從而助力我國草原碳匯經濟的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