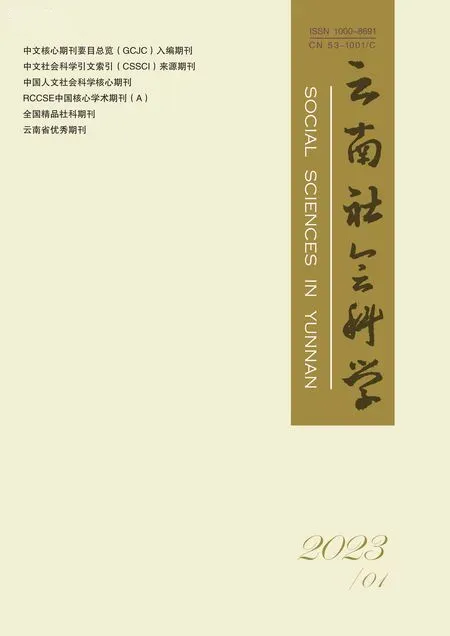戰略傳播視域下的文博業國際傳播敘事體系構建及路徑研究
——以故宮博物院為例
黃 蕙
一、研究背景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堅守中華文化立場,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和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分別就“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和“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動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發表重要講話,對新時代文博業如何面向國際講好中國故事提供了遵循,“要立足中國大地,講好中華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要講清楚中國是什么樣的文明和什么樣的國家,講清楚中國人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展現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和人文底蘊,促使世界讀懂中國、讀懂中國人民、讀懂中國共產黨、讀懂中華民族”。當前,習近平總書記對國際傳播提出“必須加強頂層設計和研究布局,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戰略傳播體系”,“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①《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 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搜狐網,https://www.sohu.com/a/469973371_362042,2021 年6 月1 日。的指導思想。現代文博業是集文物典藏、學術研究、公共服務和對外交流于一體的非營利公共組織,隨著全球文化與人文交流日益密切,文博業在文化外交、公共外交和文明互鑒中的重要作用愈發凸顯。因其所藏文物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文博業國際傳播在中國對外傳播工作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博業如何在這一指導思想下“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講好中華文明故事”成為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命題。有鑒于此,本文試以戰略傳播理論和國家形象構建理論作為基本理論依據,對新時代以故宮博物院為代表的中國文博業國際傳播敘事體系構建的基本理論問題和具體路徑進行闡釋。
二、文博業國際傳播敘事體系構建的幾個基本問題
(一)邏輯起點
作為負有戰略傳播使命的中國文博業,在“增強中華民族傳播力影響力”的時代要求下,其國際傳播敘事體系構建的邏輯起點應具有戰略性,以戰略傳播理論分析其敘事構建的邏輯起點對敘事框架的確立具有重要意義。戰略傳播(Strategic Communikation)是美國為應對“9.11”事件后美國國家形象受損,旨在實現對對象國的戰略意圖而實施的一整套傳播策略,后來發展成為以塑造國家形象、把握國際話語權和輿論導向為主要目標的傳播理論。由于戰略傳播理論體系較為成熟完備,且對全球傳播生態急劇變化的趨勢有較好的適用性,故逐漸在各國學者的研究中豐富完善。①于朝暉:《戰略傳播管理——冷戰后美國國際形象構建研究》,北京:實事出版社,2008 年,第10—22 頁。
戰略傳播理論認為,為實現國家的戰略意圖,構建符合戰略目標的國家形象需要廣泛動員和調度傳播資源。這種傳播行為是非線性的,體現出系統性的特點,具有動態持續、規模繁瑣、宏微差異的特質。每一個傳播主體在整個戰略傳播和國家形象構建的過程中具有自組織(self-organizatian)的特點,也即分散在各處的群體成員,獨立地遵照一定的行為準則,與所處環境和鄰近成員進行局部交互,從而共同自發地形成群體所要達成的全局模式。②范紅、胡鈺主編:《國家形象:創新與融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7 年,第43—58 頁。戰略傳播的運作模式是通過某種方式對分散的、各為主體的成員的傳播意圖、傳播目標等進行設定,使龐大傳播系統的微觀主體能夠通過設定,自發完成戰略傳播的目標。從戰略敘事來說,就是微觀主體需要根據設定,完成符合傳播主體特質的敘事構建,使之符合戰略敘事的目標。③李健、張程遠:《戰略傳播:美國實現國家安全與軍事戰略的重要手段》,北京:航空工業出版社,2015 年,第23—49 頁。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戰略傳播的基本設定在民眾中已有充分的共識基礎,即服務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個大局”,以“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為主導方向目標,處于頂層的國際傳播政治與文化話語應當成為話語體系和敘事體系構建的邏輯起點。④范大祺:《淺議我國對外政治話語體系建設問題》,《新時代對外話語體系建設實證研究》,北京:外文出版社、朝華出版社,2022 年,第5—16 頁。中國文博業由于其行業屬性,對于元首外交、文化外交、公共外交、文明互鑒、人文交流等具有重要而特殊的傳播意義,是戰略傳播的重要傳播資源和微觀主體。因此,加強戰略傳播自覺,提升文化自信,以國際傳播頂層話語為邏輯起點進行敘事構建是一項基礎工程,也是文博業結合行業特征主動配合國家戰略,達成戰略傳播目標的漸進探索。事實上,故宮博物院以“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為目標的傳播實踐一直在進行,其敘事的邏輯起點既有歷史的繼承性,又不斷在新的時代內涵中尋求更準確的定位,以高度的歷史自覺不斷實現著國際傳播的戰略目標。例如,中國香港(以下簡稱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于香港回歸25 周年之際對公眾開放,九百多件來自故宮博物院的重要文物在香港長時間設展。從戰略傳播的視角來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開設的議程設置與策展主題均緊密配合國家增進香港受眾對文化母體的感知和將香港作為重要文化交流及中華文化傳播中心的目標。特別是利用香港多元文化融合和城市文化國際化的地域優勢,將香港作為重要的中華文明傳播窗口是國家層面的長遠考量。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從策展敘事上一方面堅守故宮博物院傳統敘事,使受眾能夠“原汁原味”地體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另一方面,也力求在香港多元文化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圍中,創造出易于展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現代性和世界性的新話語、新敘事。在展品選擇上,既有代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器”,也有體現多元文明交融和來自不同文明的代表性展品,以文明互鑒的方式傳遞著新時代的文明觀和文化觀,體現了故宮博物院作為戰略傳播主體主動配合國家戰略需要從頂層話語的邏輯起點上進行敘事構建的探索。
(二)價值構建
敘事的價值構建,就是敘事體系將傳遞什么樣的價值觀念的問題。價值觀念往往是一個彼此聯系的系統,要系統性地傳遞并使傳播過程中特別是跨文化傳播中的受者接受并認同,取得好的傳播效果并提高傳播效能,需要在戰略傳播的高度上進行文化比較和跨文化傳播研究。
傳播學框架理論認為,人們認識事物的過程是一個用原有的認知“框架”界限外部事物,同時再造“真實”的過程,這個認知框架的核心是價值構建。①[美]麥赫迪·薩馬迪:《國際傳播理論前沿》,吳飛、黃超譯,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17—56 頁。中國學者黃旦認為,框架理論的中心問題是媒介的生產,即媒介怎樣反映現實并規范人們對其的理解,也即媒介對社會的價值構建。②黃旦:《傳者圖像: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與消弭》,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126—138 頁。戰略傳播從應用出發對框架理論進行了延展,認為在戰略傳播過程當中,傳播主體應當以價值構建為核心,根據傳播目標對議題、話語和意義進行準確組織和闡釋,通過文化比較對傳播對象的認知框架進行分析,從跨文化傳播學角度構建對外傳播的話語和敘事體系,這樣才能貼近目標受眾的認知框架,達成戰略傳播的目標。③于朝暉:《戰略傳播管理——冷戰后美國國際形象構建研究》,第86—120 頁。因此,戰略傳播主體應當根據自身的傳播目標在戰略傳播的總體敘事框架下,通過價值構建對文本、話語和敘事等進行價值構建和框架設計。
故宮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和中華文明的象征,在戰略傳播中承載重要使命。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宏大敘事框架中,故宮博物院正在根據自身使命進行系統性的價值構建,并據此形成話語和敘事體系。故宮博物院將中華文明傳播作為價值基點,以文明互鑒為目的,從中華文明的根本性問題出發,嘗試將中華文明基因與源流、哲學與思想體系、價值與精神標識、中華文明現代性與世界意義闡釋、文明互鑒與比較等作為新時代“大故宮”國際傳播的價值基礎和敘事框架,在文化比較和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立體多維傳播,以適應國家戰略傳播的需要。例如,故宮博物院正在進行的“數字故宮”建設工程,與中國外文局合作搭建了“多語種中國文化數字融媒體平臺”,其依托中國外文局在國際傳播和多語種翻譯方面的優勢和資源,通過對中華文明基因與源流相關信息多語種轉譯、相關融媒體產品的創新與國際化推廣和舉辦國際論壇等方式,較為深入地進行精準傳播。“數字故宮”英語青少版則針對英語國家青少年的認知特點,由淺入深、由表及里地介紹與闡釋中華文明,不僅僅停留在知識層面,還力求以英語國家青少年接受的方式融合中西兩種文明的話語特點,使受眾建立對中華文明的整體認知。
(三)話語方式
在敘事體系構建中,話語方式是重要的基本要素之一,敘事體系的邏輯起點、邏輯框架和價值構建都要通過一定的話語方式來體現。不同傳播主體由于不同的性質和特點,具有不同的話語方式,其關鍵在于如何發揮不同主體的話語優勢,并與敘事的邏輯和價值體系更好地結合。
戰略傳播理論認為,戰略傳播的長期目標之一是國家形象塑造、構建與傳播,國家形象塑造具有穩態構建和動態持續等特點。有研究表明,對國家形象構建起重要作用的有文化符號、古跡名勝、各歷史時期代表人物、出口商品品牌及廣告、時尚元素、流行文化藝術家和其他公眾人物、跨國公司等。其中文化符號、古跡名勝等都屬對穩態構建起重要作用的元素。④孟建、于嵩昕主編:《國家形象:歷史、建構與比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59—132 頁。從符號學的意義來說,一旦受眾認識并接受了符號及其象征意義、意象等,就會形成較為固定的認知。戰略傳播理論借用符號學理論,建構和打造對國家形象傳播有積極意義的符號和符號系統,對其進行有效傳播并改善其運行語境,以此調節國際社會對戰略傳播實施國家的認知、態度和行為。①李崗:《跨文化傳播引論:語言、符號、文化》,成都:巴蜀書社,2011 年,第86—103 頁。從跨文化傳播來看,文博業所藏文物和文化遺產蘊藏著進行中華文化符號和形象傳播的豐富資源,很好地減小了跨文化傳播中的文化折扣,對語境適應性不同的國家都具有較好的傳播效果,是國家形象穩態構建的重要資源。②姜飛:《跨文化傳播理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116—136 頁。如故宮本身對于國外受眾來說就具有典型的符號意義,是中國文化和歷史的象征。有研究表明,兵馬俑、馬踏飛燕、長信宮燈、唐三彩、元青花、紅山文化豬龍、良渚文化玉琮等重要文物在國際傳播中已成為代表中華文明的符號。因此,中國文博業在國際傳播中應發揮符號和形象傳播的優勢,并探索與之相適應的話語方式“讓文物活起來”和“讓文物說話”提取文物的符號價值,構建傳播語境,讓能夠代表中華文明的符號和符號體系傳播成為文博業戰略傳播的主要話語方式。例如,故宮博物院2022 年開年展“何以中國”,展出地點為故宮文華殿,歷時約5 個月,受到國內外受眾的廣泛關注。該展覽從全國各地博物館調集西周青銅重器“何尊”、長信宮燈、藏文《四部醫典》、玉琮、“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代織錦護臂、三星堆青銅太陽輪、云南“滇王之印”金印、大理國“大鵬金翅鳥”等國之重器,以“源”“流”“匯”為主題,從文物中提煉符號價值和對文明的象征意義,用視覺的方式將中華文明從發源、匯流終而成大觀的歷程講述出來,是文化符號提煉與文博業話語方式構建的一次重要探索。在新媒體方面,故宮博物院注冊的抖音號“抖來云逛館”嘗試在抖音國際版推出相關短視頻內容,在建筑、工藝、瓷器、書畫、文化等類別的短視頻中抽取和凸顯符號傳播效果突出的內容,探索文化符號提取與構建的方式,并探索通過短視頻進行國際傳播的規律。
三、文博業國際傳播敘事體系構建的四條路徑
在戰略傳播視域下,構建文博業國際傳播敘事體系是為了更具效能和精準地傳播中華文明、中華文化和塑造新時代國家形象。戰略傳播理論認為,國家形象的塑造、構建、精準化傳播是一個國家政治和文化價值觀念傳播的重要路徑,是一個需要具有頂層設計的系統工程,在某種程度上,國家形象傳播就是一種國家層面的“敘事”,一種有戰略意識的體系化傳播。在元宇宙傳播生態快速發展和數字化、社交化的媒介變革中,如何適應媒介環境和生態迅速變化的客觀條件,高效能和精準化地進行國家形象傳播,是新時代戰略傳播的重要課題。最早提出通過“國家品牌化”(natian branding)構建國家形象傳播路徑的英國學者丹尼(Keith Dinnie)新近提出了“ICON”(偶像)理論,認為在新的媒介生態變化中,國家形象塑造與傳播有四條有效路徑,即整合(Integrated)、語境化(Contextualized)、有機(Organic)和創新(New),這一理論模型為在趨于復雜的國際環境和輿論中進行國家形象塑造及傳播提供了理論框架。③Dinnie,K.(2015).Nation branding:Concepts,issues,practice.Routledge,226-229.該理論適用于對外敘事建構的研究,本文試以該理論模型為框架,對文博業敘事體系構建的路徑進行分析。具體來說,文博業國際傳播敘事體系構建有四條提升傳播效能和精準度的基本路徑。
(一)整合傳播要素
在國家形象塑造中,到達受眾的符號、形象、概念、價值、理念等應該明確和清晰,這需要對傳播資源和整個傳播生態進行整合,特別是在今天日益圈層化、碎片化、社交化的傳播生態中,如果缺乏整合,傳播效果會難以達成,也難以評估。中國文博業擁有龐大的傳播資源、途徑、受眾,對其進行必要整合,以達成戰略傳播和國家形象構建目標,是其構建國際傳播敘事體系的路徑之一。從資源的整合來說,文博業國際傳播的主要話語方式是基于博物館展覽、展陳的符號和形象傳播,通過整合的方式,篩選提煉出能夠代表中華文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華文化當代價值的符號和形象,加大對這些代表性符號和形象的傳播,將會達到更好的傳播效果。例如,在國外受眾的認知中,故宮就是成熟的傳播符號,其蘊藏的象征意義和帶來的形象聯想明確而豐富,且有延伸和拓展的空間,因此,需進一步強化和提升故宮的符號意義,并通過整合資源,篩選出一個符號和形象群,一方面,使故宮的符號意義得到拓展和延伸;另一方面,也使中華文化在故宮符號的傳播優勢中得到更廣泛的傳播。故宮已在符號群的整合和打造上進行了探索,如對故宮古建筑群構件和要素,如脊獸,重要文物如甲骨、石鼓、青銅器、瓷器、玉器等,書畫作品如《千里江山圖》《清明上河圖》《韓熙載夜宴圖》《海錯圖》等進行符號化傳播的探索,研究符號在傳播中的抽象與賦意,以及符號和形象在跨文化傳播中的解碼。從傳播途徑和對受眾的整合而言,文博業應從公共文化和公共教育產品供給者的角度出發,發揮融媒體優勢。例如,故宮博物院注重傳統渠道與新興媒介、社交媒體的整合,構建多層次、立體化的傳播格局,不斷創新抖音短視頻、公眾號和微博等,在原有相對固定受眾群的基礎上,促進不同受眾群之間的整合,形成疊加擴容的受眾效應。
(二)進行語境化傳播
從符號學的角度來說,語境是指符號傳播時對符號意義釋讀起重要作用的要素,這些要素與符號之間的相對關系和彼此之間的關系對釋讀相對抽象的符號起到重要作用,使符號容易記憶,形象化或在不同語境中能較為準確地解碼和釋讀。戰略傳播和國家形象傳播理論認為傳播的主要目的是塑造、傳播代表國家形象的符號或符號群,并調節和改善符號的運行語境①畢研韜:《戰略傳播:溯源、發展及其啟示》,《對外傳播》2022 年第6 期。,符號的意義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語境,調試或對語境進行改變,符號的意義往往隨之改變②朱麟:《對外傳播視野下的中華文化元素符號的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第12—26 頁。。因此,應當進行語境化(Contextualized)的傳播,確保符號所傳達的意義與傳播目的相符。對于敘事而言,孤立的敘事難以達到敘事目標,語境化是敘事體系構建路徑的重要維度。文博業對外傳播的優勢是符號及其形象化傳播,使代表國家形象的符號得到精準傳播也是其戰略傳播和國家形象傳播的使命。因此,應當將語境化傳播的理論運用于其敘事構建中,在傳播中分析對傳播符號起重要作用的語境要素,并根據傳播目標對語境進行設置和調整,以更好地適應國際傳播的環境并達到傳播目的。以故宮博物院為例,明清古建筑群紫禁城是代表中華文明和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符號,但同時這一符號的意義在某些國外受眾心目中也顯現為封建王權和封閉固守,為此,故宮博物院在傳播語境中不斷加入現代元素,用現代審美和當代價值觀解讀故宮的文化和歷史現象,在視覺設計中強化現代感,將封建王權的代表人物——帝王人格化、人性化,講述他們的人性故事;同時,突出對中國制度文明的研究與釋讀,通過對故宮符號的語境化傳播,不斷強化故宮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華文明先進性的代表,并在這一符號之下,不斷加載成體系的中華文明符號,使之也成為一種語境化的傳播。
(三)創造有機的傳播生態
在國際傳播中創造有機的傳播生態是指對對象國的傳播要從過程性傳播轉變為傳播生態運維型的傳播,通過傳播內容和傳播形式、介質的融合創新,注重與對象國受眾、社區、媒介、官方和民間組織等進行互動,使“信息在場”多維度顯現、長時效存在,將傳播生態植入現實和虛擬空間,借用生態的有機化和自生性,長時間地保持傳播效果和創新傳播方式。③孟建、于嵩昕主編:《國家形象:歷史、建構與比較》,第89—120 頁。從敘事來看,就是要將敘事轉化為一個有機和生態化的自主創新過程,豐富話語維度和敘事方式,以適應社會和媒介生態的豐富、多元和共生性。對于文博業而言,世界博物館業和與之相聯系的各圈層本身就是完整的生態圈,隨著博物館在公共文化和教育中的角色日益重要,且更多地被各國作為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的重要媒介,博物館業的傳播生態得到不斷地豐富和拓展,應以“有機”的理念和方式拓展運維博物館生態,并針對不同的對象豐富其敘事方式。故宮博物院一直扮演的“國家會客廳”角色應該成為其對外交流生態和敘事方式的主體和基礎,一方面,其緊跟國家外交議程,圓滿完成元首外交和政府外交的任務;另一方面,故宮博物院以此為基礎,積極發揮公共外交的職能,建立了與各國使領館的友好和常態化關系,“外國使節參觀故宮”等活動取得良好社會效益,也通過類似方式與各國外交、教育、文化、文博部門以及政界、媒體界、學界、藝術界等社會精英層建立良好的互動關系,形成了一個有機的傳播生態圈。故宮博物院在運維其國際傳播生態的同時,也探索著多元化敘事方式,在策展等對外合作領域,與合作方交流探討,融合多元的敘事方式共同完成策展。
(四)創新傳播內涵與方式
國家形象塑造雖然具有穩態構建的特點,但隨著時代命題和國際環境的變化,要在動態中對其不斷創新,賦予其新的內涵。文博業在文明對話和互鑒中有著天然的優勢,應配合國家戰略傳播的需要結合自身特點,在戰略敘事框架下進行文博業國際傳播敘事體系構建。故宮博物院連續多年發起并舉辦“紫禁城論壇”“世界古代文明保護論壇”“太和論壇”等,簽署了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紫禁城宣言》和《太和宣言》,已發揮出對世界博物館業的引領效應,很好地回應了國家在文明議題上的戰略傳播設計。從創新傳播方式來說,隨著元宇宙時代漸進到來,虛擬現實技術變革性地改變著媒介形態,博物館業在數字和虛擬現實技術的應用上較為領先,具備適應“元宇宙”時代傳播方式變革的技術儲備和先進意識。“數字故宮”一直是故宮博物院發展的重要架構,基于160 余萬件套重要文物的數字化工程,故宮博物院開發了虛擬博物館、各類APP、小程序和游戲等一系列數字傳播平臺和渠道,拓展了故宮博物院未來的數字空間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