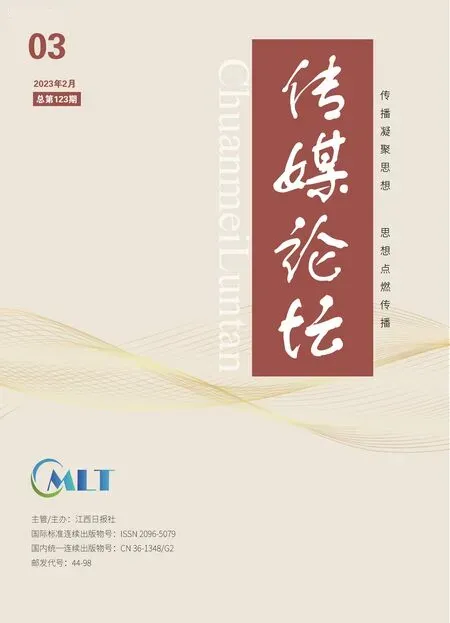養(yǎng)成失格:兒童“吃播”短視頻傳播的倫理問題研究
李 莎 張 玲 賈 夏
一、引言
智媒時(shí)代,萬物皆媒。眾多短視頻平臺在算法推薦、AI人工智能等的助力下實(shí)現(xiàn)爆發(fā)式走紅,為公眾提供了一個(gè)自我文化創(chuàng)造與精神釋放的最佳渠道。[1]基于內(nèi)容發(fā)布門檻降低等原因,不少網(wǎng)民將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趣事錄制成Vlog,或跟風(fēng)創(chuàng)作短視頻平臺中火爆的段子,實(shí)現(xiàn)自我展演的同時(shí),也在收割點(diǎn)贊量和播放量中得到了后續(xù)創(chuàng)作的動(dòng)力。
當(dāng)短視頻帶來的流量和熱度可以轉(zhuǎn)化為推廣費(fèi)和短視頻平臺激勵(lì)金時(shí),如此分享也由“自我價(jià)值實(shí)現(xiàn)”來到了第二個(gè)階段——盈利變現(xiàn)。以兒童“吃播”短視頻現(xiàn)象為例,父母對孩子的“養(yǎng)成式”教育在短視頻中變成了利用萌娃形象吸粉盈利的手段,部分父母不惜以犧牲孩子健康為代價(jià),如年僅三歲的“吃播”博主佩琪被其父母喂到了70斤。最終,“吃播”博主佩琪在短視頻平臺的賬號和視頻被網(wǎng)友舉報(bào)并遭封禁。“曬娃”變“啃娃”,且兒童對自我身體的控制權(quán)被父母剝奪,成為媒介景觀中的消費(fèi)符號,“養(yǎng)成失格”也隨即產(chǎn)生。
二、文獻(xiàn)綜述及研究問題的提出
(一)吃播
對“吃播”最直觀的定義即“吃東西直播”。隨著短視頻的興起,“吃播”的內(nèi)容呈現(xiàn)也不再局限于直播這一種形式,更多博主會(huì)選擇錄播這一方式將視頻投放在各大社交平臺,錄制與剪輯的結(jié)合有利于“吃播”群體選取精彩片段再組合;內(nèi)容創(chuàng)作上,美食測評與美食制作是兩種主要形式。為博取用戶關(guān)注度,拉近與用戶的距離,“吃播”還會(huì)選擇新奇的美食代償,或貼上地域標(biāo)簽,吸引觀看者前往打卡。
(二)吃播類視頻的倫理問題
1.商品屬性
基于學(xué)者金美拉的研究,受眾觀看“吃播”主要是為了實(shí)現(xiàn)替代性的滿足、娛樂,尋求信息和消遣時(shí)間。[2]這些泛娛樂化的內(nèi)容構(gòu)成了“吃播”消費(fèi)經(jīng)濟(jì)的新模式,即從分享到引領(lǐng)消費(fèi),用戶不自覺中完成了消費(fèi)。由此,學(xué)者周昕認(rèn)為大眾文化的商品屬性使網(wǎng)絡(luò)“吃播”以快感提供為手段,利用人們的盲目追求和自我滿足,將大眾文化異化為以經(jīng)濟(jì)利益為目標(biāo)的產(chǎn)物。[3]商品的生成離不開營銷。從營銷角度出發(fā),學(xué)者秦琰以李子柒為例,進(jìn)一步分析了美食短視頻自媒體內(nèi)容營銷創(chuàng)新的三大特征:人設(shè)的個(gè)性化塑造、場景交流功能的增強(qiáng)、符號化的表演。[4]這也揭示了短視頻作為商品是如何取得成功的。
2.身體成為消費(fèi)符號
美國學(xué)者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提出“身體美學(xué)”的概念,即“將身體作為感性審美欣賞與創(chuàng)造性自我塑造的核心場所”。[5]學(xué)者秦勇認(rèn)為“吃播”是對傳統(tǒng)審美觀念的突破,其中基于身體欲望的“吃播”打破了“非欲望”的審美局限。[6]尤其當(dāng)身體成為審美客體時(shí),女性則成了審美活動(dòng)中的實(shí)踐客體和審美客體。學(xué)者謝巧認(rèn)為男權(quán)文化建構(gòu)了當(dāng)下的女性美學(xué),女性是在操縱下被塑造和規(guī)訓(xùn)的。[7]而將視角轉(zhuǎn)移到“吃播”的興起時(shí),一部分原因正是為了迎合性別失衡下的“宅男經(jīng)濟(jì)”,穿著暴露的女性“吃播”更容易在各大平臺贏得關(guān)注度和流量。自此,身體成為消費(fèi)視覺符號,迎合著消費(fèi)社會(huì)的審美。
3.暴食、浪費(fèi)
細(xì)分“吃播”的類型,“大胃王”可以占據(jù)其中一類。其主要的特點(diǎn)包含短時(shí)間內(nèi)吃掉大量食物、食物以刺激性內(nèi)容為主、身材的纖細(xì)與進(jìn)食量之間形成反差與對比。對此,學(xué)者苑夢月認(rèn)為“一切為了娛樂,流于庸俗和淺薄的內(nèi)容降低了大眾品味”[8],而學(xué)者潘麗華則認(rèn)為“吃播”中包含的暴食現(xiàn)象如果長期任其發(fā)展下去,會(huì)導(dǎo)致暴食行為的推廣,對觀看“吃播”的用戶形成一種暗示,進(jìn)一步誤導(dǎo)和誘惑暴食。[9]
綜上,進(jìn)一步提出如下思考:第一,反建構(gòu)主義認(rèn)為,身體在傳播中具有一定作用,且具備主體性。站在兒童“吃播”自身角度,成人“吃播”將現(xiàn)實(shí)生活和身體作為鏡頭前展演的一部分,具有控制自己身體的權(quán)利,那兒童“吃播”是否擁有對自己身體的控制權(quán)?短視頻創(chuàng)作的背后更多反映了父母意志,是否有悖傳播倫理?第二,站在拍攝兒童“吃播”的父母角度,短視頻為用戶提供了創(chuàng)作和社交空間,也開通了流量變現(xiàn)的通道,那“云養(yǎng)娃”模式的商業(yè)消費(fèi)邏輯是怎么樣的?第三,站在兒童“吃播”短視頻觀看者角度,視頻中兒童的進(jìn)食內(nèi)容、成長軌跡等是否會(huì)影響其對自己孩子的移情與規(guī)訓(xùn)?第四,針對如上兒童“吃播”目前所面臨的生存現(xiàn)象,后續(xù)兒童“吃播”的生存之路是什么?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深度訪談法,考慮到訪談進(jìn)程中的標(biāo)準(zhǔn)化程度,以及如何更好地引導(dǎo)受訪者談?wù)搩和俺圆ァ彼媾R的倫理失范問題,主要以半結(jié)構(gòu)式訪談為主,訪談之前事先選擇兒童“吃播”佩琪(目前各平臺視頻賬號已注銷)、@希希不挑食、@石頭、@薛小胖澤等視頻賬號分享給受訪者觀看,以便受訪者更好了解兒童“吃播”概念和短視頻平臺中的傳播內(nèi)容。本文訪談中涉及的訪談對象以微博平臺對兒童吃播現(xiàn)象作出批評的用戶、訪談?wù)呱磉呌泻⒆拥母改笧橹鳎?5名。訪談對象及其基本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訪談對象基本信息匯總
四、失格的“養(yǎng)成”:短視頻傳播中兒童“吃播”的生存?zhèn)惱碛懻?/h2>(一)絕對控制:兒童“吃播”身體歸屬權(quán)的再討論
現(xiàn)階段短視頻平臺中的兒童“吃播”主要分為兩類:一是以被父母投喂、每日更新“今天吃什么”為視頻內(nèi)容的兒童“吃播”;二是扮演“大廚”形象,利用兒童自身實(shí)現(xiàn)烹飪美食、進(jìn)食的兒童“吃播”。不論是上述哪種類型,都脫離不開小小身型與進(jìn)食量、廚藝水平等因素之間的反差感討論。尤其是當(dāng)視頻拍攝者(其中大多為兒童父母)選擇用“什么熱拍什么、什么獵奇能吸引人”的方式在競爭中盤活粉絲量時(shí),作為元媒介存在著的身體,就會(huì)更進(jìn)一步化身為商業(yè)化的消費(fèi)符號,刺激著人們的消費(fèi)需求,成為承載多種內(nèi)涵的、最為“美麗”的消費(fèi)品。[10]與成年“吃播”不同,兒童“吃播”往往不具備對自己身體的控制權(quán),這就導(dǎo)致部分父母出于獵奇心理,為追求流量而惡意增加兒童每日的進(jìn)食量。此外,兒童“吃播”中父母對于兒童身體的控制也不僅表現(xiàn)在暴食,還包括兒童“吃播”作為社交平臺上展演對象的穿著、為與父母互動(dòng)特意設(shè)計(jì)的開場白、對白等。
作為一個(gè)合格的父母,我是不會(huì)忍受這樣的行為的。佩琪的相關(guān)視頻我也有看過,一個(gè)年僅三歲的孩子被喂養(yǎng)到了70斤,肥胖帶來的更多是對身體的一種傷害。我覺得對他們的父母來說,應(yīng)該好好反省下這種行為,畢竟當(dāng)小孩的身體出現(xiàn)出題時(shí),再后悔也來不及了。(訪談?dòng)涗洠篘o.4,女,45歲,本科,育有一女)
(二)認(rèn)同建構(gòu):“云養(yǎng)娃”背后的商業(yè)消費(fèi)邏輯
點(diǎn)擊量是判斷短視頻發(fā)布者是否為頭部主播、發(fā)布視頻是否為熱門的重要指標(biāo),這就形成了社交媒體短視頻和短視頻聚合平臺以注意力經(jīng)濟(jì)為導(dǎo)向的發(fā)展形態(tài)。[11]隨著網(wǎng)絡(luò)帶貨主播行業(yè)的興起,品牌為服務(wù)自身而設(shè)置的帶貨主播已不再是唯一,越來越多的品牌方選擇為熱門主播“投流”,通過主播自身熱度提升產(chǎn)品影響力,更進(jìn)一步帶動(dòng)產(chǎn)品的銷售量。以兒童“吃播”為例,雖然“萌娃”賬號背后的實(shí)際操縱者更多是其父母,但“萌娃”天真爛漫的媒介形象會(huì)使消費(fèi)者放下戒備,具備鼓勵(lì)消費(fèi)者下單帶貨產(chǎn)品的能力。為此,不少兒童“吃播”賬號打出了“云養(yǎng)娃”的標(biāo)簽,通過嘗試與用戶一同創(chuàng)造“云養(yǎng)娃”的共在模式,留住粉絲,獲取流量。其中,認(rèn)同建構(gòu)是“云養(yǎng)娃”的關(guān)鍵所在。尤其當(dāng)喂食兒童成為年輕父母的負(fù)擔(dān)與難題時(shí),兒童“吃播”賬號的存在給予了年輕父母有關(guān)喂食、兒童飲食的“參考答案”,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陪伴的作用,并使其得到短暫的替代性滿足。但部分兒童“吃播”賬號的內(nèi)容創(chuàng)作者將“曬娃”上升為了“啃娃”,塑造兒童“吃播”人設(shè)的同時(shí),利用兒童“吃播”人設(shè)進(jìn)行的帶貨行為發(fā)生了“翻車”現(xiàn)象,最終使兒童在社交平臺的媒介形象、聲譽(yù)等面臨負(fù)面影響。
平時(shí)都是孩子?jì)寢寧蓿讼掳嗪蠼o予一定的關(guān)心和陪伴外,我也會(huì)在短視頻平臺關(guān)注兒童“吃播”,看看他們的父母是怎么給孩子做輔食的,方便我和孩子?jì)寢寣W(xué)習(xí)。(訪談?dòng)涗洠篘0.15,男,33歲,本科,育有一子)
(三)隱形規(guī)訓(xùn):以在場束縛對抗養(yǎng)娃的孤立無援感
根據(jù)福柯所言,現(xiàn)代社會(huì)是一種規(guī)訓(xùn)社會(huì),規(guī)訓(xùn)的對象往往指向身體。[12]在觀看兒童“吃播”類短視頻時(shí),父母群體會(huì)格外關(guān)注兒童“吃播”每日所吃的食物、進(jìn)食量,甚至是穿著打扮,并通過評論、私信等方式與兒童“吃播”賬號的所有者產(chǎn)生互動(dòng)行為。由此,觀看視頻的父母與兒童“吃播”本人、兒童“吃播”父母之間形成了一種無形的情感連接,一是用來對抗現(xiàn)實(shí)生活中“養(yǎng)娃”的孤立無援感,二是用以營造“云養(yǎng)娃”的參與共在模式。此為觀看兒童“吃播”的初級階段。進(jìn)入到用戶觀看兒童“吃播”的下一階段,以作為觀看者存在的父母會(huì)將屏幕內(nèi)的兒童“吃播”行為對照自己的孩子,以對標(biāo)孩子的每日進(jìn)食狀態(tài)及生活質(zhì)量。當(dāng)模仿產(chǎn)生并持續(xù)發(fā)展時(shí),部分父母會(huì)將模仿轉(zhuǎn)化為期待,進(jìn)而完成對自己孩子身體、行為習(xí)慣等多方面的規(guī)訓(xùn)。這種以“他者話語”展開的規(guī)訓(xùn)背后包含了隱形的父母在場束縛,使兒童成長背負(fù)“自我規(guī)訓(xùn)”,充斥被解讀與被塑造。[13]
我覺得兒童“吃播”更多扮演了一個(gè)“陪伴式”的角色,用戶可以在觀看吃播的過程中得到一種無聲的陪伴,還可以鼓勵(lì)我們將自己的孩子也變成那樣乖乖吃飯、健康成長的人。(訪談?dòng)涗洠篘o.9,男,32歲,本科,育有一女)
五、“養(yǎng)成”何處歸:短視頻傳播中兒童“吃播”的生存之道
(一)適應(yīng)性成長:內(nèi)容轉(zhuǎn)型成生存關(guān)鍵
短視頻本質(zhì)上屬于內(nèi)容驅(qū)動(dòng)型行業(yè),優(yōu)質(zhì)、持續(xù)、差異化的內(nèi)容供給是平臺制勝的關(guān)鍵。回歸到兒童“吃播”的話題上,伴隨賬號粉絲攀升的還有兒童“吃播”的成長,尤其是身體的長大。當(dāng)兒童“吃播”難以在餐桌上扮演被觀看的對象,并開始對自身隱私投入以足夠重視時(shí),父母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對兒童主播做“吃播”的控制權(quán)。因此,越來越多的兒童“吃播”賬號開始嘗試轉(zhuǎn)型,比如@石頭在抖音平臺更新的視頻中就展示了小朋友日常學(xué)習(xí)、彈鋼琴等的生活點(diǎn)滴。以成長來對抗“長大”,兒童“吃播”后續(xù)多在短視頻平臺更新如何育兒、如何為兒童搭配每天的營養(yǎng)餐等優(yōu)質(zhì)內(nèi)容。
兒童“吃播”亂象的出現(xiàn)已經(jīng)不是一時(shí)的問題了,如果能真正杜絕“啃娃”這個(gè)問題,那我覺得自己以后觀看萌娃吃飯、成長的心情也會(huì)更加愉悅,沒有那么多不適感。(訪談?dòng)涗洠篘o.8,男,22歲,碩士,無子女)
(二)自我穩(wěn)定化:與其求生存,不如真正去生活
針對目前短視頻傳播中一些家長“曬娃”模式的逐漸畸形化現(xiàn)象,文化和旅游部也在2021年末發(fā)布了《關(guān)于加強(qiáng)網(wǎng)絡(luò)文化市場未成年人保護(hù)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為《意見》)。《意見》站在近年來網(wǎng)絡(luò)音樂、網(wǎng)絡(luò)動(dòng)漫、網(wǎng)絡(luò)演出劇等網(wǎng)絡(luò)文化市場快速發(fā)展,豐富了群眾文化生活,拉動(dòng)了數(shù)字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基礎(chǔ)上,細(xì)化到部分網(wǎng)絡(luò)文化平臺存在“兒童邪典”內(nèi)容、利用“網(wǎng)紅兒童”牟利等不良現(xiàn)象和問題,旨在堅(jiān)決阻斷有害內(nèi)容、嚴(yán)禁借“網(wǎng)紅兒童”牟利、有效規(guī)范“金錢打賞”等,真正讓法規(guī)建設(shè)落到實(shí)處,成為短視頻長久發(fā)展的核心。
縱觀近年來火爆一時(shí)的兒童“吃播”,他們更多并不是因?yàn)槠脚_的規(guī)則設(shè)定淡出大眾視線,而是自行選擇了“自我穩(wěn)定化”的生活方式,即不再更新賬號內(nèi)容,或直接將兒童“吃播”賬號先前的內(nèi)容做刪除處理。以“自我穩(wěn)定化”來降低內(nèi)容創(chuàng)作中的不穩(wěn)定性,也是回歸生活,還孩子一個(gè)沒有拍攝、沒有隱私權(quán)讓渡給公共空間的童年。
六、結(jié)語
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與寬帶的普及和智能手機(jī)的發(fā)展作為移動(dòng)短視頻發(fā)展的外部動(dòng)因,視聽場景社交化、碎片化、分眾化等作為短視頻內(nèi)容的內(nèi)部發(fā)展邏輯,內(nèi)外因聯(lián)動(dòng)成就了今天的移動(dòng)短視頻興起。未來還會(huì)出現(xiàn)更多新的媒介形式,但不可否認(rèn)的是,每一種媒介形式都是因人而產(chǎn)、為人所用。面對兒童“吃播”在短視頻傳播中出現(xiàn)的倫理問題,要做到不讓養(yǎng)成“失格”,不讓分享只為流量。未來,垂直化、優(yōu)質(zhì)化的方向無疑是使短視頻保持常青的一大方向。但與此同時(shí),放棄短視頻中的角色扮演,讓孩子真正回歸生活也是一種長久的“養(yǎng)成”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