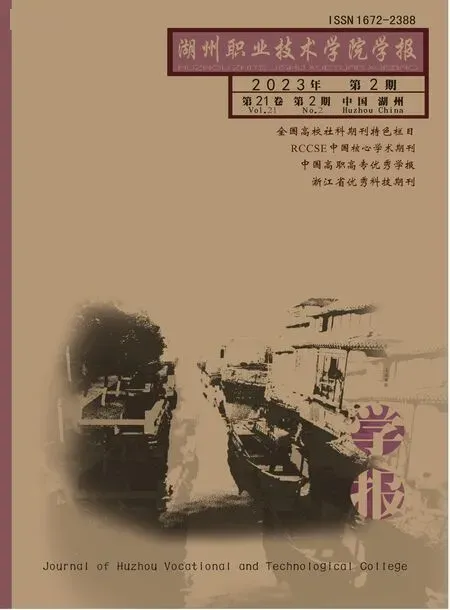欲望心理的裂變
——論施蟄存的愛情小說*
錢 瀅
(上海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 上海 200234)
施蟄存的小說有較多的男女曖昧關(guān)系的愛情書寫,以《上元燈》(1929年)、《將軍底頭》(1932年)、《梅雨之夕》(1933年)、《善女人行品》(1933年)等短篇小說集為代表。施蟄存充分借鑒西方文藝思想和方法,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和顯尼志勒心理分析小說,并將其成功運用到自己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創(chuàng)作了許多反映社會現(xiàn)實的作品。施蟄存通過心理分析的方法,將小說中人物的欲望和壓抑突顯出來,進而表現(xiàn)出他們的心理扭曲和精神裂變。楊迎平認為,同為新感覺派代表作家,“劉吶鷗多寫都市的五光十色、風馳電掣的社交場所,是上海的表面。施蟄存則是深入到都市人的心靈世界,了解的是都市人的情緒心態(tài)。”[1]8施蟄存的小說采用古典與現(xiàn)代相結(jié)合的創(chuàng)作方法,浸透著深厚的傳統(tǒng)文化素養(yǎng),展現(xiàn)出人物深刻的心理狀態(tài)和社會現(xiàn)實。
一、欲望心理的裂變
施蟄存小說通過敘說都市或城鎮(zhèn)男女的曖昧關(guān)系,展現(xiàn)了當時人們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狀態(tài)。有學者認為,施蟄存的心理分析小說可分為兩個方面:“第一,是歷史題材和現(xiàn)代題材的心理分析小說,側(cè)重于表現(xiàn)變態(tài)性心理和精神缺損型的焦慮恐怖心理。這種表現(xiàn)病態(tài)人格的描寫,往往帶有瘋狂,怪誕和神秘的傾向。第二,是以家庭、夫婦生活為主體的‘私人生活瑣事’的描寫,比較集中于對女性心理的細致分析。”[2]110事實上,這兩個方面都是以愛情為主題展開的,作者在表現(xiàn)都市人因欲望受到壓抑而產(chǎn)生病態(tài)人格的同時,也表現(xiàn)了日常家庭生活中夫婦因物質(zhì)欲望難以滿足而產(chǎn)生的細微心理變化。
1.施蟄存的小說涉及許多超出倫常的男女感情糾葛 如:《娟子》寫了教授和表妹的婚外戀,《梅雨之夕》寫了已婚男士和借傘姑娘的曖昧,《蝴蝶夫人》寫了妻子和朋友的約會,《春陽》寫了富太太對銀行職員的誤會,《周夫人》寫了寂寞的寡婦和小男孩之間的曖昧,等等。再如關(guān)于周夫人的描寫,周夫人是一個被欲望和封建觀念壓抑的寡婦,內(nèi)心的寂寞和欲望無處排遣。比如她抱著年幼的“我”,說“我”很像已經(jīng)死去的周先生這一描寫,就說明,她難以擺脫失去丈夫的孤獨和痛苦,只能從一個孩子那里獲取一點溫暖。小說通過敘說超出倫常的人物感情生活來揭露和諷刺社會現(xiàn)實,反映出主人公的情感和欲望受到壓抑而無處宣泄的苦悶心理。
2.施蟄存擅長描繪人在欲望籠罩下的心理裂變和心理扭曲 正如弗洛伊德所強調(diào)的性本能,小說中的人物因性本能無法釋放而產(chǎn)生壓抑甚至變態(tài)的心理狀態(tài)。《鳩摩羅什》中想念亡妻的僧人國師鳩摩羅什,因抵擋不了誘惑,重新娶了宮女,并有十余個妓女侍候他。鳩摩羅什本是得道高僧,但他沒有守住自己的欲望底線,做出了違背戒律的事。《石秀》同樣塑造了一個欲望化的主體,主人公石秀雖然迫于兄弟關(guān)系或道德束縛,拒絕了朋友之妻潘巧云的勾引,但他心中是愛潘巧云的。可是,潘巧云的冷淡和離間使得石秀萌生了對她的殺心,尤其是在殺了和尚之后。“現(xiàn)在的石秀卻猛烈地升起了‘因為愛她,所以要殺她’這種奇妙的思想了。這就是因為石秀覺得最愉快的是殺人,所以睡一個女人,在石秀是以為決不及殺一個女人那樣的愉快了。”[3]119由此可見,石秀因無法滿足自身的欲望,產(chǎn)生了扭曲甚至變態(tài)的心理。《將軍底頭》中不近女色的花驚定將軍,在一次戰(zhàn)役之前愛上了一個少女,但因軍營紀律不得不壓抑戀愛的欲望,因此產(chǎn)生了變態(tài)心理:在他的頭顱被敵人砍下時卻依然為少女的嘲笑而流淚。可見,人物內(nèi)心的欲望壓抑到何種地步。施蟄存把歷史人物的崇高消解了,使得他們成為欲望的奴隸。弗洛伊德認為:“里比多若受壓抑,便轉(zhuǎn)變而成焦慮,或以焦慮的方式而求得發(fā)泄,這是里比多的直接命運。”[4]329正是因為本能欲望受到壓抑,小說中的人物才產(chǎn)生了焦慮甚至扭曲變態(tài)的心理。如在書寫都市生活的《在巴黎大戲院》中,一個已婚男子和一個女人在影院一起看電影,男子在用女人手帕的時候,竟然生發(fā)出想要舔手帕的心思。舔了之后,竟然幻想出抱著她裸體的感覺。由此可見,小說中男主人公的猥瑣和變態(tài)的心理。他是被欲望壓抑的人,因而在內(nèi)心深處顯露出病態(tài)心理。但作為有婦之夫,他不能違背道德去追求另一個女人,因而陷入了道德和欲望的雙重矛盾之中。施蟄存正是通過這些內(nèi)心欲望的大膽書寫,展現(xiàn)了當時社會的人性和現(xiàn)實。
3.在施蟄存的小說中,男女之間的感情因物欲而產(chǎn)生壓抑和怪誕 在施蟄存的小說中,男女之間的感情總是受到諸多現(xiàn)實因素的限制,他們的戀愛不是正常男女之間的戀愛,而是摻雜著利益的交換關(guān)系,表現(xiàn)出人物因物欲產(chǎn)生的內(nèi)心深處的壓抑和怪誕。《李師師》描寫了愛情與權(quán)力的矛盾,李師師在心上人周邦彥和擁有權(quán)力的皇上之間產(chǎn)生了糾結(jié)。《薄暮的舞女》描寫了舞女素雯的愛情與利益的糾結(jié),當她得知自己本可以依賴的對象子平生意失敗后,很快便將目標轉(zhuǎn)移到另外的男人身上。可見,她與自己的“客人”之間是以利益為轉(zhuǎn)移的交易關(guān)系。《花夢》中發(fā)生一夜情的陌生男女,同樣是出于這樣的社會規(guī)則,女人同意赴男人的約完全是看在男人付賬的面上。當男人還渴望著戀愛的感覺時,女人卻這樣想著:“你把錢包裝得滿些,我決不因為不歡喜你而失約的。”[3]420男人最后雖然反應(yīng)了過來,卻還是以買了一個高價的經(jīng)驗來寬慰自己。
施蟄存還擅長書寫家庭生活中的愛情與現(xiàn)實之間的矛盾糾葛。他的小說描寫了許多女性婚后的幽微心理,展現(xiàn)出現(xiàn)實面前復(fù)雜的人性考驗。《漁人何長慶》寫到菊貞因愛慕虛榮從丈夫長慶家中逃走,后來到城市做了妓女。幾年之后,長慶才知道菊貞做了妓女,但他依舊不顧流言將菊貞領(lǐng)了回來,二人又過上了漁家的生活。與傳統(tǒng)觀念不同,這里的女性更容易受到外界的誘惑,男性對此的忍耐也突破了傳統(tǒng)的男尊女卑觀念。《阿秀》中的阿秀,從富商家里逃出來嫁給汽車夫做正式妻子,卻發(fā)現(xiàn)汽車夫炳生也是愛嫖愛賭的人,因此設(shè)計報復(fù)兩任丈夫。最終,阿秀被現(xiàn)實逼成瘋子。《獅子座流星》也是如此,卓佩珊夫人結(jié)婚3年還沒有孩子,她迫切想要一個孩子。可是,肥胖的丈夫并不能為她解決煩憂,她只得在夢中求得一點寬慰。由此,小說表現(xiàn)出這些女性婚后遭遇的苦難,以及對男性的失望。
二、古典與現(xiàn)代結(jié)合的藝術(shù)手法
施蟄存小說在藝術(shù)手法上的顯著特點是將古典與現(xiàn)代相結(jié)合。他擅長運用意識流、精神分析等現(xiàn)代手法,同時將古典園林、庭院作為小說背景,采用詩意化的語言,對古代小說、民間故事等進行改編。施蟄存十分擅長對人物進行心理分析和精神分析,以此把握人物的心理情感,尤其善于運用弗洛伊德的理論,將性沖動隱藏在人物心理之中,從而構(gòu)成小說獨特的戲劇沖突。“施蟄存對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學的接受,主要是通過顯尼志勒小說這一中間環(huán)節(jié);而施蟄存在創(chuàng)作思維技巧與風格上,所受顯尼志勒小說的影響與啟示,無疑是他以后從事心理分析小說創(chuàng)作的最重要的藝術(shù)準備。”[5]288-289奧地利作家顯尼志勒成功地將精神分析理論運用到小說創(chuàng)作中,對施蟄存的小說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在巴黎大戲院》幾乎全篇貫穿著男主人公的心理活動,人物隱秘幽暗的內(nèi)心世界構(gòu)成了小說的主要內(nèi)容。“我覺得她在看著我,不是剛才那樣的只是斜著眼看了,現(xiàn)在她索性回過頭來看了。這是什么意思?我要不要也斜過去接觸著她的眼光?……不必吧?或許這會使她覺得羞窘的。”[3]155小說中的男主人公迫于已婚身份,不得不將自己內(nèi)心的愛隱藏起來。正是這種對內(nèi)心欲望的壓抑,使得他做出吸吮對方手帕的“變態(tài)”行為。施蟄存正是通過大膽的心理描寫來帶動故事情節(jié),從而形成小說的內(nèi)在沖突。
在充分運用西方現(xiàn)代藝術(shù)手法的同時,施蟄存也努力嘗試將中國傳統(tǒng)文學的元素融入小說創(chuàng)作。他在《關(guān)于〈黃心大師〉》一文中提到:“我曾有意地試驗著想創(chuàng)造一種純中國式的白話文。說是‘創(chuàng)造’,其實不免大言夸口,嚴格地說來,或者可以說是評話、傳奇和演義諸種文體的融合。”[3]626《黃心大師》是作者以《比丘尼傳》《洪都雅致》等史料中關(guān)于黃心大師的記載為基礎(chǔ)創(chuàng)作的小說。施蟄存的小說創(chuàng)作試圖實現(xiàn)古典與現(xiàn)代的結(jié)合,如,描繪青春浪漫故事的小說《扇》和《上元燈》都發(fā)生在小城鎮(zhèn),都將古典的園林景觀作為小說的敘事背景。《扇》的男主人公由一把舊團扇想到了自己的初戀,回憶起他去女朋友家的花園的情形。小說中美麗優(yōu)雅的小城鎮(zhèn)園林景色,襯托出人與人之間純粹、美好的感情。《上元燈》也是一篇關(guān)于純愛的小說,一個精致的花燈,成為兩人的定情信物。小說充滿著中國傳統(tǒng)節(jié)日的氛圍,作為信物的花燈顯示出傳統(tǒng)文化的典雅特征。小說中人物之間的情感似乎也被淡化在濃濃的傳統(tǒng)節(jié)日氛圍之中了。作者對古典文化的珍視和運用由此可見一斑。
施蟄存在《我的創(chuàng)作生活之歷程》中提到,他最先接觸的文藝作品是詩,不管是唐詩宋詞的舊體詩,還是海涅的西洋詩,都對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影響。他在許多小說中采用了詩意化的語言,以此來營構(gòu)優(yōu)雅的語言意境。如《上元燈》中寫道:“我約略將這許多燈都看了一遍,實在我以為都是扎得非常精巧,沒奈何,指定了她手中的那一座樓式紗燈。……她這般說,臉上現(xiàn)出一派天真的愉快的驕矜。”[3]9-10這種詩意化語言的運用,使得小說讀來精致典雅,同時易于理解,這也正是作者想要創(chuàng)造的中國式白話文。在根據(jù)古代小說、歷史和民間故事改編的如《石秀》《李師師》《鳩摩羅什》和《將軍底頭》等作品中,施蟄存更是創(chuàng)新性地實現(xiàn)了古典與現(xiàn)代藝術(shù)方式的結(jié)合。這些作品通過對人物的精神分析和藝術(shù)加工,將人物內(nèi)心的欲望和糾結(jié)展露無遺,顛覆了人們對這些英雄或者歷史人物的傳統(tǒng)想象,將他們描繪成個人欲望的化身,刻畫了他們某些人的變態(tài)心理。同時,施蟄存的作品立足古典故事的框架,使用精神分析手法,對人性進行揭露。如彰顯個人欲望的石秀,顛覆了《水滸傳》中“拼命三郎”的英雄形象,被描繪成受欲望束縛的失控而殘忍的殺手。20世紀30年代,施蟄存在擔任《現(xiàn)代》雜志主編時,引進了西方文學和思潮,推進了中國現(xiàn)代派文學的發(fā)展,實現(xiàn)了文學的兼容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有學者認為,這樣的創(chuàng)作反映了一種矛盾的心態(tài):“理性中的趨新與情感的念舊正是施蟄存自身無法擺脫的矛盾,曾經(jīng)有人用‘急火燒制的紅燒肉’外熟內(nèi)生的特征來形容他這種以現(xiàn)代的形式來表述并不現(xiàn)代的思想的矛盾形態(tài)。”[6]28但是,這也正反映出施蟄存在創(chuàng)作現(xiàn)代小說的同時,不忘吸收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優(yōu)秀資源,沒有完全沉溺于西方文學的影響之中。
三、愛情書寫的現(xiàn)實意義
施蟄存的愛情小說書寫,將人物心理置于社會背景之下進行分析,反映出諸多現(xiàn)實問題。伴隨著社會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的變動,傳統(tǒng)的倫理道德觀、貞操觀面臨著被代替和更迭,女性的社會地位也隨之改變。施蟄存的小說則開啟了對當時都市文化浸染的社會現(xiàn)實進行揭露和反思的向度。
1.施蟄存的愛情小說反映了在五四啟蒙文化影響下中國民眾性觀念的開放 施蟄存的許多小說書寫了人物的性心理,將人物的欲望暴露出來,通過深入的精神分析,揭示出當時社會環(huán)境下的諸多社會現(xiàn)實問題。在施蟄存的許多小說中,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他們都是因欲望得不到滿足而產(chǎn)生種種壓抑乃至扭曲心理的個體。如:生活孤寂,身體和精神都沒有依托的周夫人;被好友妻子勾引,內(nèi)心欲望得不到滿足的石秀;以及在欲望和功德之間糾結(jié)徘徊的鳩摩羅什等。作者通過對人物性心理的大膽揭露和剖析,揭示出開放的性觀念影響下的性沖動的釋放。弗洛伊德認為,性變態(tài)是因為羞恥感、厭惡感、恐懼感、痛苦感等各種阻力沒能在性沖動羽翼豐滿之前順利到位導(dǎo)致的。性沖動和性阻礙的雙重壓迫,誘發(fā)了患者的精神疾病[7]26-31。小說中的人物正是在欲望和現(xiàn)實的矛盾之中走向崩潰和扭曲,他們無法控制自己的性沖動,并受到現(xiàn)實道德因素的壓迫,成為被欲望囚困的對象,最終走向了心理裂變。
小說中女性地位的變化也是一個值得關(guān)注的問題。施蟄存在小說中塑造了許多負面的女性形象,如勾引石秀反被石秀殺害的潘巧云,《花夢》中通過一夜情獲利的都會女人等。這些女性形象反映了女性在當時社會面臨的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女性的地位在某種程度上得到提升,女性的欲望在某種程度上得到釋放,但是,女性在某種程度上仍受到傳統(tǒng)倫理的壓制。(1)女性雖然擁有行為的自主性和伴侶的選擇權(quán),但也成為了男性眼中欲望化的標志。《花夢》中的男主人公這樣認識都會的女人:“雖‘愛’這個字,還不曾在這個時代里死滅,但至少中世紀浪漫時代的男女所懂得的愛決不能再存在于現(xiàn)代的都會里了,或者是,再退一步說,決不會存在于都會的女人胸中了。”[3]415施蟄存的許多小說都寫出了男性對都市女性的恐懼心理,但他們又難以抵擋都市女人的誘惑,由此陷入痛苦和糾結(jié)之中。比如《魔道》和《夜叉》這兩部小說,就表現(xiàn)了男性對女性復(fù)雜而矛盾的心理。《魔道》寫男主人公對女人既渴望又害怕,他眼中的女子已經(jīng)成為魔女。她們對他有著致命的吸引,卻又讓他感到神秘而難以接近。《夜叉》中的男性,因愛而不得,對愛情產(chǎn)生了恐懼心理,甚至失手殺掉了一個女子。這些都市男性因得不到女性的賞識和愛而失落,因而產(chǎn)生了恐懼、扭曲的心理。實際上,這些男性都是因為性壓抑而產(chǎn)生了心理疾病。這也展現(xiàn)出女性地位的變化,尤其是都市女性,能夠大膽地沖破傳統(tǒng)觀念的規(guī)約和束縛。(2)女性只是一種欲望的化身。她們在獲得愛情的選擇權(quán)和行為的自主性的同時,某種程度上也受到傳統(tǒng)倫理觀念的壓抑,表現(xiàn)出一種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觀念之間矛盾、搖擺的狀態(tài)。
第二個問題是,女性難以實現(xiàn)經(jīng)濟獨立。很多女性正是因為缺少經(jīng)濟支持而走上了歧途。李大釗認為,婦女和無產(chǎn)階級都處在被壓迫地位,她們的命運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婦女要實現(xiàn)根本的解放,就需要一個“根本的解決”,即經(jīng)濟問題的解決[8]107。根據(jù)女性無法實現(xiàn)經(jīng)濟獨立這一現(xiàn)象,作者塑造了很多追求實際利益的女性形象。這些女性往往因無法實現(xiàn)經(jīng)濟獨立,而難以在愛情中找到自我,常常會失去婚姻的自主權(quán)。如《漁人何慶長》中的菊貞,她想要逃離家庭安排的婚姻,但到了城市卻發(fā)現(xiàn)自己難以立足,又不得不回到漁人身邊。在愛情書寫中,這些女性總是被置于被觀看的缺少自我認知的他者化的位置,而難以實現(xiàn)自我性別身份的有效認同。
2.施蟄存的愛情小說反映了在都市文明影響下,人們因物欲膨脹而產(chǎn)生的虛榮、利己的異化心理,呈現(xiàn)出現(xiàn)代性反思的思想傾向 正如魯迅在《傷逝》中對現(xiàn)代愛情的質(zhì)疑和反思,在現(xiàn)代都市文明之中,愛情早已變得不純粹了。施蟄存擅長通過書寫男女的幽微心理,揭示男女之間情感的不純粹。如《春陽》講了一個繼承亡夫家產(chǎn)的寡婦,她在小心翼翼地保管自己財富的同時,還渴望著新的愛情。但是,銀行男職員的一句“太太”,徹底打消了她的幻想。她的欲望同財富一起被鎖在了保險柜里。小說表現(xiàn)出都市環(huán)境之下,愛情的功利化和虛無化。在人物關(guān)系之中,愛情似乎被消解了,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利益關(guān)系。正如弗洛姆所說:“在一個商業(yè)化占統(tǒng)治地位以及把物質(zhì)成功看得高于一切的文化中,事實上是沒有理由對下列事實抱有吃驚的態(tài)度:人與人之間的愛情關(guān)系也遵循同控制商品和勞動力巿場一樣的基本原則。”[9]3在表現(xiàn)小人物的生活時,小說還對因物欲控制而導(dǎo)致的人性異化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諷刺。如《栗芋》寫到一位乳娘在成為太太后,對撫養(yǎng)著的孩子的態(tài)度都發(fā)生了變化。這種變化表現(xiàn)出人的情感會隨著身份地位的變化而變化,人性也會因追求自身利益而異化。
四、結(jié) 語
從《現(xiàn)代》雜志的創(chuàng)辦理念來看,施蟄存倡導(dǎo)保持政治中立立場,追求文學作品本身的價值。“施蟄存反復(fù)說明‘不是同人雜志’,無非是想把《現(xiàn)代》與‘圈子化’同人刊物區(qū)別開來,在一個多向度的平臺上與作家、讀者對話,容納更多的文學流派和團體,在競爭激烈的上海出版界打開市場。”[10]2正是《現(xiàn)代》雜志自由、開放的中間立場引發(fā)了各種觀點之間的爭論,從而引起了讀者的廣泛關(guān)注。伴隨著《現(xiàn)代》雜志的創(chuàng)辦,施蟄存逐漸形成了現(xiàn)代主義的創(chuàng)作風格,成為新文學運動中的第一批現(xiàn)代派代表作家。“其小說創(chuàng)作出色地運用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論和諸種潛意識的心理形式,來表現(xiàn)三十年代以上海為代表的現(xiàn)代都市文明危機和心理危機,表現(xiàn)在中國社會急劇殖民地化的大滑坡中,青年知識分子如何陷身于愛情失落、靈魂扭曲以及諸種理想與現(xiàn)實、靈魂與肉體的矛盾之中無以自拔,并以此而奠定中國現(xiàn)代派小說的基本敘事模式。”[11]131對欲望心理的大膽書寫是施蟄存小說吸引讀者的重要手段,同時作者有意回避對當時熱點政治事件的討論,為市民階層提供了消遣的通道。
施蟄存追求的反映社會現(xiàn)象且具有創(chuàng)新性的短篇小說,不能被簡單地看成供讀者娛樂的消遣之作。他的作品能夠生動地反映當時的社會生活,尤其是都市人面對現(xiàn)實生活表現(xiàn)出的迷茫、不適的心理狀態(tài)以及人性的幽微,這些現(xiàn)代性內(nèi)容在當今依然引人深思、發(fā)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