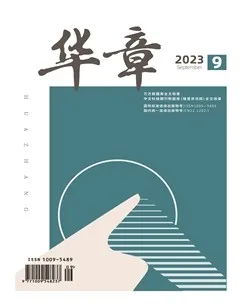時代巨變下的人生抉擇
[摘 要]人生每一個轉折點的選擇都十分重要,它不僅會影響你人生的一段時期,還會影響你的整個人生。路遙的《人生》中塑造了幾個生活在改革開放初期的經典人物形象,通過對人物性格、心理等的細節刻畫使得每個人物活靈活現。對于時代的描述,其字里行間都散發出厚重的歷史感與沉重感。在那樣一個歷史轉折期,計劃經濟開始動搖,社會充滿了不確定性,一群農村知識青年開始覺醒,每個人都感覺到自己的命運有可能被改變,個人發展意識自此出現。高加林是那個時代的悲劇產物之一,在每一個關鍵之處他都做出了選擇,并且為每一個選擇付出了代價。正如時間無法逆流,人生是不能從頭再來的,在階層流動中,高加林如眾多知識青年一樣用自己的方法積極努力向上爬,往外走,從逃離土地,進入城市,再到回歸土地,繞了一圈又回到最初的起點,結局始終不如人意。本文以《人生》為例,以當時的時代環境為背景,探究農村知識青年的價值觀念與精神追求;細品人物刻畫,以高加林為例探討其在社會階層流動中悲劇的可能及個人奮斗者在階層跨越中的悲劇共性。
[關鍵詞]城鄉沖突;愛情選擇;個人發展意識
“人生的道路雖漫長,但緊要處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在小說《人生》的扉頁上印著這句話,出自作家柳青的《創業史》。喜歡路遙筆下那片樸實的黃土地,喜歡那真實的人心。路遙對于日常生活的描寫是細致的,且文字具有濃厚的歷史感和畫面感,他善于用雞毛蒜皮的小事和城鄉習俗的差異凸顯城鄉差距及人的差距。他將一幅長長的畫卷鋪開,底色是孕育萬物的黃土地,黃土地上生活著一群平凡而又不平凡的農民。隨著人物命運的起伏,讀者似是親歷了他們的一生,親見他們對生存、對愛情、對理想的抉擇,再從中感受到路遙之于奮斗者的人文關懷,賦予選擇之于人生的重要意義,領會傳統美德之于文化傳承的必要性。“他試圖在長篇巨制中,通過對日常生活的精心描繪,刻畫出在傳統和現代之間的舊鄉土兒女身上所特有的感覺樣態和精神氣質。路遙關注的現代性的來臨不僅僅是社會組織的轉變、環境的更新,更根本上是人的轉變、是人的身體、心靈和精神體驗的
轉變”[1]。
《人生》主要寫了農民的兒子高加林被迫下崗回到農村、又離開農村去縣城工作、又一無所有回到農村的故事,在幾個重要的轉折點中,他彷徨猶豫,最終做出了幾個影響一生的抉擇,其間有走進城市的新奇,有愛情陪伴的甜蜜,也有南柯一夢、繞了一圈卻又回到原點的悲傷與懊悔。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一定會遇到很多岔路口,而在每一個關鍵點做出的選擇也許會影響人生的一段時期,也許會影響整個人生。自然,每個人的選擇除了受到自身性格的影響,周遭環境及人物的影響,時代背景也是不容忽視的一大因素。所以,本文重點圍繞高加林的人生抉擇進行探究,探討階層流動中造成人物悲劇的可能。
一、個人奮斗者高加林的農民觀
在《人生》中,主人公高加林生活在人民公社體制逐漸解體的歷史轉折期,而在這樣一個改革開放的初期,城鄉開始分裂,階層區分日益明顯。在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的沖突之間,城鄉不僅物質差距愈發明顯,精神上的差別也顯露無遺。因此,農村知識青年的奮斗之路變得格外艱難。
在農民知識青年眼中,勞動算不上是一種工作,在民辦教師職位的高加林因權力關系下崗后,他被迫變回了農民身份,但一個有文化的農民在得到過體面的工作后必然不甘回到土地。若說城市交叉地帶是路遙選擇的知識青年困苦掙扎之地,那高加林一類受過知識熏陶的、斗志昂揚的個人奮斗者則是介于黑白之間的交叉色彩。在傳統農民心中,勞動的本質都相同,辛勤耕耘是刻在骨子里的信仰。但在農村知識青年眼中,體力勞動比不上腦力勞動,在黃土地上刨食的人比不上有正式工作的人。高加林是一個與時代有著矛盾的人物,他的人生觀、事業觀都預示著他不會甘心留在那片黃土地上。他來自農村,從不認為自己的父母、德順爺爺及其他村民低賤,他尊重每一位農民,但內心卻不愿意做農民,不愿“像他父親一樣一輩子當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種說法是奴隸”[2]。
高加林熱愛文學,而民辦教師的身份正是他接觸文學,或是說靠近城市、實現夢想的方式,他幻想逐漸換成更好的工作,離開土地,走進城市,所以下崗這樣的突如其來的鏈條斷裂對他及他一家都是沉重的打擊。他內心對權力充滿了恨意,立志要超過那些換掉他工作的人,去大城市謀求更好的發展。對于知識分子來說,當農民會有些抬不起頭,對于傳統農民來說,一個不會勞動的農民也是會被人瞧不起的。所以下崗后,即使痛苦,他也逼迫自己很快認清當前的處境,他拼命投身于勞動中,但因內心認定了那是上不了臺面的,所以整個過程痛苦無比,像是一種情感發泄,又像是故意懲罰自己,他以自虐式的勞動融入這個集體,所以拼命地揮動镢頭,他努力扮演農民,以此得到短暫的身份歸屬感[3]。而對于走進城市之后的經歷,在高加林眼中則是值得驕傲的。他本身是有才能的,所以他進入縣城后,很快就大放異彩,從外表到內心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進城帶給高加林的滿足感,不僅僅是空間意義上的,更大的是精神層面上的進步和滿足,面對自己喜歡的事,他每天辛苦奔波也不覺得累,去災害現場一待就是五天,每天聽到廣播站播報自己撰寫的報道,他的自尊心就會得到極大的滿足。
傳統農民認同自己的農民身份,在他們心中憑自己的能力生存并不低人一等。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提到“與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相比,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4]。而城市的人們排斥厭惡農民,有知識有文化在“農村戶口”四個字面前不值一提,在時代巨變造成的城鄉差異巨大的當下,“最干凈的工人農民”變成臭死了的社會底層[5]。而高加林,若說他在農村時對于農民身份是在認同與否定之間徘徊,那進城之后的高加林則是堅定地選擇了與傳統文明疏離,他是十分有野心的,他的終點絕不止于眼前的縣城,他還想要去更大的城市完成自己的夢想,而對更大城市的渴望其實就是他對現代文明的渴望。
二、高加林的愛情觀
在《人生》中,塑造了女追男的兩種愛情模式與選擇,一種是與劉巧珍的莊稼地里的勞動加愛情,一種是與黃亞萍的城市里的工作加愛情。有學者稱,這是“癡心女子負心漢”的愛情敘事模式,兩位女子都癡心,都為這個負心漢而悲傷[6]。
提到劉巧珍,第一印象就是德順爺爺的評價:這是一位有金子般的心的姑娘。關于巧珍的外貌,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漂亮,在高加林的眼中也是如此。巧珍雖一直喜歡高加林,但只是將這份情思暗藏于心底,在高加林下崗前從未出現在他面前,因為在她心中,那時的高加林高不可攀,他不會接受一個沒文化的農村女子。她選擇在高加林人生最低迷的時候出現,因為同為農民,身份終于趨向平等。而高加林對巧珍的感情存在頗多顧慮,因為一旦和眼前這個村婦在一起,就離他的城市更遠了一步。這樣被動盲目的接受只會迎來事后的懊悔,這樣不經思索的感情自然也會走向悲傷的感情結局。但巧珍的美麗純真和恰逢其時的陪伴讓他無法抗拒,她懂得如何去保護他的自尊心,她敢于追求自己的心中所愛,即使這些行為在如今來說算是芝麻小事。巧珍是一位喜歡現代文明的農民,她將勞動視為勛章與療傷的圣藥[7],這一點與高加林的認知不同,但她依然對高加林心生情愫,可以說她對高加林的愛慕起源于現代文明的吸引,她喜歡高加林能在報紙上發表文章,也喜歡他的衣服無論新舊都能穿得干凈的樣子,她喜歡的不僅是高加林這個人,更是他身上現代文明的氣質。在被高加林拋棄后,她沒有哭鬧,而是在傷心之后重新堅強起來,選擇了自己的新生活,她嫁給了一直喜歡她的馬栓,以此來療愈高加林及現代文明給她帶來的創傷。在高加林失去一切回到農村時,她沒有選擇去奚落他,甚至去幫他尋找新的工作,可見她對高加林依然存留愛意,但因為選擇了新的生活,所以不違背道德倫理,在這一點上,她又是守舊的。大度、善良、高尚此類美好詞匯集合于巧珍身上,滲透著中華傳統美德的美好,可見路遙對這個人物的偏愛。巧珍是高加林心之所愛,但并非心之所向,被改造后的巧珍才是他的心頭好。盡管最終巧珍與高加林的愛情以錯過告終,但她注定成為高加林一輩子忘不掉的遺憾,注定是他心里的“白月光”。
在“走后門”進入縣城工作之后,高加林和黃亞萍走到了一起,“白月光”變成了“飯粘子”。黃亞萍時髦熱情,是如同紅玫瑰般的存在,她與高加林、劉巧珍的身份大不相同,她是在城市里長大的孩子,她的父親是縣委常委、武裝部部長,她是一位博學多才的女子,在縣城的廣播站任職,優秀的出身加上自身的博學和體面的工作,無一不吸引高加林向其靠近。對于高加林來說,這個新時代女性可以帶他體驗很多他從未體驗過的新鮮事,也可以讓他活得如想象中的體面,同樣,能帶他走出縣城,去到更大的城市。在紅與白的天平上,高加林選擇了他認為與自己更加相配的那抹火紅。黃亞萍對高加林的情感萌芽于高中時期,但一直因為高加林的“農民”身份,黃亞萍也從未想過表達自己的情愫。在她心里是瞧不上農民的,即使她認可高加林的文學素養,但絕不可能與一位農民在一起,所以在她得知高加林與劉巧珍在一起時,說出了“與不識字的人結合簡直是自我毀滅”的話。而高加林因緣際會來到了縣城工作,他突然的身份改變打亂了黃亞萍應家里要求選擇的“平淡生活”,農民身份不再,她重新燃起了對高加林的喜歡,并很快不顧家人反對和張克南的陪伴,堅決地向高加林表白。她能和高加林談論文學理想,也能告訴高加林不了解的國際形勢、能源問題等。每次談論到這些,高加林都是興奮并享受其中的,相比巧珍每次說的土地莊稼、母豬下崽,他自然更喜歡和黃亞萍交談。而當黃亞萍向他表白愛意時又許諾帶高加林去南京,最終黃亞萍以這份“許諾”贏了巧珍,或者說是她所代表的現代文明贏了鄉村文明。這段拋棄良心得來的感情也很快隨著“走后門”的事被揭發而結束,高加林回歸了農民身份,黃亞萍對他是喜歡的,雖然一時沖動說出了愿意和他去農村的話,但細想之下就能發現這一定是不可能的,她不會放下城市的生活,去做一個農民。她對于高加林的感情,逃不出身份的阻隔,她愛的是記者高加林,是在城市里光鮮亮麗的高加林,而不是農民高加林,她的愛是真摯的,但真摯有前提條件,始終會隨著高加林的身份變化而改變。
盡管小說最后說明他意識到了自己依然愛著巧珍,但或許是因為他的身份又重新變回了農民罷了,似乎他的愛與他是什么人有最直接的關系。又或許他希望的是一個如村婦巧珍般崇拜他,又如城市女子亞萍般見多識廣的人。如果小說走向另一種結局,他與亞萍去了南京,巧珍也許就只是記憶中一個對他很好的女孩罷了,只是不管哪種結局,他都失去了一顆真誠對他的金子般的心。有人認為,高加林是那個時代的悲劇產物,這些過錯不能歸咎于他的性格,但如果他早些認清“人就是要扎根土里”的事實,就算他漂去更大的城市闖蕩,也不會因為配不上的觀念,就算毀了聲譽也要丟棄那個每天等著自己的女子。所以他的性格也是造成他最終結局的原因,而巧珍嫁給愛她的馬栓未嘗不是一種幸福。
在高加林的人生觀里,愛情是要讓位的,理想走在前方,這樣的觀念是功利的,所以在劉巧珍與黃亞萍之間,高加林狠心地選擇了能讓他更接近理想——去大城市的黃亞萍,這是基于現實基礎上權衡利弊后做出的選擇,感情的選擇就由“純粹的”變為了“物化的”。他是典型的個人奮斗者,憑借自身才華及靠自己能拿到的扶持——愛情的選擇,來實現自己的進步,在他的人生中,愛情是最渺小的,是不值得他付出什么去換取鞏固的。他是一個有理想、有目標同時兼具能力的人,只因身份是一個農民,沒有權力、地位,所以他恨那些權力者,因為在那個時代,能力并不能使你出人頭地,權力卻可以,所以他選擇依靠勢力來助力自己的奮斗之路。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出勇敢、努力等一切好的奮斗詞匯,從選擇逃離土地,到覺醒,再到回歸,其間充滿個人奮斗者的豪情壯志,也滲透著農村知識青年在那個時代的無奈、迷茫、痛苦。
結束語
小說最溫暖的莫過于結尾高加林回到農村,不知是“生活開了他一個玩笑,還是他開了生活一個玩笑”,原以為會被村民嘲笑,但迎來的卻是大家伸出自己粗壯的手來幫扶他。只能說怪不得時代和命運,只怪那幾個關鍵的抉擇,使得他余生都要活在失去巧珍的惋惜與遠離亞萍——遠離夢想的遺憾里。
參考文獻
[1]遲令剛.立足現代文明的鄉土守望:路遙小說鄉土呈現的一種審美解讀[D].杭州:浙江大學,2013:60.
[2]路遙.人生[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1-255.
[3]王俊虎,王晶.認同·疏離·拒斥:論路遙《人生》中的農民觀[J].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43(6):5.
[4]毛澤東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808.
[5]吳浩.時代巨變下的人生躁動:論路遙的人生[D].長春:吉林大學,2014:37.
[6]倪慶玲.路遙《人生》中人物的愛情選擇[J].今古文創,2022(22):3.
[7]劉曉慧.立足于陸,無畏四海沉浮:論路遙《人生》中高加林的愛情選擇與起伏人生[J].現代交際,2019(9):119,118.
作者簡介:黎旖旎(1998— ),女,土家族,貴州銅仁人,貴陽學院,助教,碩士。
研究方向:中國語言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