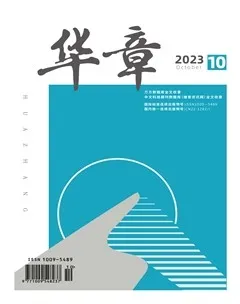論高空拋物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分
[摘 要]司法實踐中高空拋物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難以界分的原因主要在于對“危險方法”的評判標準有所偏頗,應回歸至刑法解釋論予以解決,對“危險方法”的解釋結論是厘清兩罪的重要依據。而通過形式解釋無法進行精準涵射得出可靠結論,故本文通過對“危險方法”進行實質解釋,從而明確“危險方法”的評判標準,解決司法實踐中兩罪難以區分的困境。
[關鍵詞]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高空拋物罪;實質解釋;危險方法
我國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第二款規定,從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拋擲物品,情節嚴重的,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有前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1]。同時,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也對高空拋物行為進行了明確規定,但在司法實踐中,對于何種高空拋物行為屬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危險方法”的標準存在理解分歧,故導致同案不同判等現象出現。鑒于此,本文通過探尋如何合理解釋“危險方法”的路徑,從而解決兩罪罪名適用混亂現象,以維護司法
權威。
一、解釋方法的基本構造與選擇
目前刑法解釋的分類大致分為論理解釋和文義解釋兩種,如何使解釋結論更好地體現公平正義、維護社會秩序,成為學界備受關注的問題[2]。為了使不同的解釋方法得以協調,理論界有學者提出了位階的概念,即認為不同的解釋方法之間應有位階優先適用,但也有學者否定解釋方法之間的位階順序,即不認為解釋方法之間存在位階高低和適用排斥的情況。
(一)位階肯定說:解釋方法位階分為順序位階和效力位階
1.刑法解釋方法的順序位階
主張以文義解釋出發到體系解釋再到目的解釋的學者認為,首先我國是成文法國家,刑法條文通過其文字表達立法目的與精神,文字本身也具有客觀的含義,應作為解釋者最優先適用的解釋方法。其次是體系解釋,將體系解釋位列第二,是出自從簡到繁的邏輯思維的考量。最后將目的解釋置于體系解釋之后,出于對人們由內到外,從外在形式到內在實質的認識邏輯的考量。
如德國的耶賽克認為刑法解釋方法的位階順序應該是以文義解釋為出發點,先適用文義解釋,進而再經過歷史解釋或體系解釋,如果還未實現解釋目標的話,最后再適用目的解釋[3]。程紅教授也認為首先應當進行文理解釋即文義解釋,盡可能的尊重形式解釋規則,客觀地理解刑法條文的字面含義,其次進行體系解釋,將刑法條文著眼于整個刑法中的地位,聯系相關法條的含義來考慮刑法條文的意義[4]。最后在經過上述解釋之后仍無法得到唯一結論的,才可以進行目的解釋,但目的解釋的結論也始終不能脫離條文文義的涵射范圍。
從解釋方法的順序位階來看,學術界通說都是從文義解釋出發,最終至目的解釋,對此并無太大爭議。但筆者認為與其將之確定為順序位階,不如說是法律證成過程中的思維活動,各種解釋方法是通往解釋結論的不同路徑,而怎樣選擇是一種思維方式,有人選擇從A到B,有人選擇從A到C。并未按照某種路徑得出的結論就一定是正確,或者一定是最合理的,解釋結論還應從各種角度去驗證它,解釋方法也可能倒推,刑法解釋不是單一的路徑思維,而是不斷穿梭在刑法條文、案件事實與刑法解釋之中,最終得出合理又合法的解釋結論的思維活動。
2.刑法解釋方法的效力位階
(1)可能文義界限上,文義解釋絕對優先
主張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這是以優先實現刑法安定性的價值目標對刑法解釋效力位階的要求,為了實現刑法的安定性,強化文義解釋的邊界作用,即一切解釋無論出于何種考量都不能超出刑法條文用語可能含義的范圍。當目的解釋、體系解釋或者歷史解釋超過文義解釋可能涵蓋的范圍時,該解釋是無效的。這種觀點看似邏輯自洽,但并未真正解決實踐中各種解釋方法沖突時的
矛盾。
如刑法第二百六三條第六項的規定:“冒充軍警人員搶劫的,應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對于真正的軍警搶劫該如何量刑,不同的解釋方法將會得出矛盾的結論。
通過文義解釋可得,冒充意為假冒,所以冒充軍警人員搶劫是絕對排除真正軍警人員搶劫的,如果將冒充軍警人員搶劫涵蓋真正軍警人員搶劫將違背罪刑法定原則,對于真正軍警人員搶劫的只能適用一般搶劫,雖其性質惡劣,但屬于刑事立法上的缺陷,只能通過立法途徑解決;而從目的解釋來看,冒充軍警人員搶劫強調的并非身份本身,而是利用該身份去搶劫的行為,即與行為人職業本身無關,而強調在搶劫行為實施時,是否向被害人顯示其為軍警人員,即使真正的軍警人員,在搶劫時沒有亮明身份,也不應以冒充軍警人員搶劫量刑。
筆者認為文義解釋的結論雖具合法性但欠缺合理性。真正軍警人員搶劫性質應該是更加惡劣,更具有升格量刑的理由,僅以立法缺陷為由,將真正軍警人員搶劫按一般搶劫論處實在不妥,有學者還認為強調文義解釋優先,是追求刑法的安定性價值,同時也是對法官權利的限制,如果賦予法官更多的解釋權,則可能出現法官造法的情形,不利于刑法的安定性。筆者對此持不同觀點,刑法解釋的作用就是為了彌補法律的漏洞,賦予法官更多的解釋權,促進刑法的安定性,法律的滯后性決定了如果任何問題都依賴立法層面解決,那么可能會出現朝令夕改、頻繁立法的情形。故將文義解釋列為優先地位有時并不能很好地解決解釋活動中出現的問題。
(2)可能文義范圍內目的解釋為冠
這種目的解釋優先說,強調刑法解釋與其他部門法解釋具有相同的性質,主張通過探尋刑法條文的立法宗旨,要實現的目的來對其進行合理解釋。但是對刑法解釋的擴張也需要一定的界限,不能對其無限擴張,同時這種觀點也認為不應完全禁止類推解釋,而應以刑法條文的立法目的與宗旨這樣的實質合理性來對刑法解釋進行限制,即追求一種刑法解釋的實質機能化。
過度強調目的解釋,將會忽視刑法的規制性,將其變成單純的價值考量。所以有學者認為,只有將賦予刑法明確的公式,才能準確描述何種行為在何種情況下為犯罪。
如刑法中對“信用卡”的解釋,刑法上的信用卡是指由商業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發行的具有消費支付、信用貸款、轉賬結算、存取現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電子支付卡。有學者主張將螞蟻花唄等信用支付產品都納入信用卡的涵射范疇。那這種解釋是否合理,筆者認為有待商榷。單從目的解釋的角度來看,利用這種新型支付方式實施的犯罪行為,不僅侵犯了他人的財產權益,也會侵犯金融秩序,將其納入“信用卡”的解釋范疇具有合理性。但這種解釋可能會超出信用卡的語義外延,所以并不被立法者所認可。因此,目的解釋是在可能文義的范圍內具有優先性。
(二)位階否定說:形式與實質相融的解釋規則
位階肯定說認為不同解釋方法具有位階性,在效力上,可能文義界限上,文義解釋絕對優先、可能文義范圍內目的解釋為冠。在理論上看似涵蓋了所有情況,但在實踐中可能不是特別理想,首先,如何把握可能文義的界限就是一個極具主觀,且不易統一標準的問題。其次,所謂優先性如何體現,當解釋方法之間出現矛盾時才會有如何適用的解釋方法優先性之說。文義解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具體案件事實能否被包攝到刑法概念之下并不清楚,需要對法條用語的含義進行闡釋,解釋無論如何不能逾越法條用語的可能含
義[5]。所以有學者認為在可能文義范圍內文義解釋具有優先性。看似邏輯合理,但并不能解決實踐中的真正問題。因為在實踐中,真正成為問題的情形是通過文義解釋得出了多個解釋結論,難以判斷哪種解釋更為合理。
所以本文認為不同的解釋方法之間并不具有位階性,而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約,根據具體案情可做出不同的價值判斷,選擇不同的解釋方法。沒有一勞永逸的適用規則,且適用先后應為一種邏輯思維活動,也不代表一定存在位階,不同的人可以選擇不同的先后順序,只要解釋結論合法合情合理即可。
二、實質解釋下“其他危險方法”的內涵解讀
(一)通過文義解釋可得拋物行為應具危害相當性
1.拋擲場所應具有公開性
高空拋物行為要想被納入其他危險方法范疇之內,其拋擲場所應具有符合足以危害不特定多數人生命財產的可能性,故其拋擲場所應具有公開性。因此在密閉空間或根本沒有行人走動的空間的高空拋物行為一定不構成其他危險方法。例如“賴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刑事二審刑事裁定書”一案。凌晨6時左右,賴某酒后先后將3個編織袋裝的23顆計53斤的柚子、玻璃泡酒瓶、拖把、椅子等物品,從客廳陽臺扔到小區道路上、道路邊停車位及綠化帶。法院認為其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本案爭議焦點在于賴某的行為是否具有危害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財產安全,首先賴某拋擲物品的時間為凌晨6時,當時小區中并未有行人走動,所以該行為其實并不能導致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財產安全遭到侵犯,故賴某的拋物行為并不具有其他危險方法相當的危害性,故在判斷拋擲場所是否具有公開性時,除了考慮地點外還應考慮時間,綜合認定是否具有公開性。
2.所拋擲物品應具有嚴重的危害性
將高空拋物行為規定為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時,應對所拋擲物品的范疇進行限縮,即并非所有被拋擲的物品都能危害公共安全[6]。高空拋物若要危及公共安全,在評價時就需要考慮“物”本身的特征以及物體在下落過程中所能轉化的動能能否對公共安全造成威脅。例如,從高空拋擲衣服、羽毛、紙屑等,并不能危及到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財產安全。同時從2樓與20樓分別拋擲相同的物品也會帶來不同的危害性,高空拋物若要危及公共安全,所拋擲的物品除本身應具有嚴重的危害性之外,還應考慮空氣阻力、物品本身重力的關系。如果在下落中空氣阻力過大,或產生的重力加速度過小,轉化成的動能非常有限,難以危及公共安全。如“盧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一審刑事判決書”。盧某因家庭糾紛先后將塑料花瓶、一把木柄斧子和一包紙質材料從9樓拋擲樓下,法院認為其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本案中,盧某所拋擲的斧子本身具有嚴重的殺傷力,又從9樓拋出,其行為已具有危害不特定多數人法益的現實條件。因此在判斷所拋擲物品是否具有嚴重危害性時,除考慮物品本身的物理屬性之外,還應考慮拋擲高度等因素。
(二)通過目的解釋可得拋物行為具有法益相當性
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高空拋物行為所侵害的法益應為公共安全,即有可能侵犯不特定或多數人的法益。因此有學者認為,如果地面上人員密集,一次性從高空拋出許多危險物,則有可能侵犯多數人的法益,從而應被定性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是張明楷教授對此有不同觀點,他認為,即使在人員密集的場所一次性拋出許多危險性物品,也不能成立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7]。張明楷教授將“公共安全”解釋為“不特定人的安全”側重點在不特定上,而非多數人,所以張明楷教授認為,即使是多次高空拋物,也只是具有導致多數人傷亡的具體危險,行為所造成的危害結果的范圍不會擴大,不可能像放火或爆炸行為那樣導致不特定多數人傷亡的具體危險。所以不能將其認定為危險方法。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太過絕對,公共安全所要求的對象的不特定并非被侵害對象的隨機性和偶然性,公共安全側重保護的法益應該是公共,即應該強調侵害對象是同時威脅“多數人”,或者隨時向“多數人”發展的可能性。比如在特定人群中引爆炸彈,此時就侵犯了公共安全而不能說因為是特定的多數人,所以侵犯的法益不能歸為公共安全,其二者的法益是具有明顯差異的。
結束語
高空拋物罪保護的法益是“公共場所秩序”,雖限定在秩序范疇,但不意味著凡是突破公共秩序、造成人身安全或公私財產安全后果的高空拋物行為一律按照以危罪處罰。如果高空拋物行為造成其他具體損害的,根據具體情形分別認定為故意殺人、故意傷害、重大責任事故等罪。而高空拋物犯罪司法實踐中存在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界限不清的問題,原因在于:未正確衡量高空拋物行為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而盲目適用。以危罪作為一項兜底性條款,在實踐中應該準確認定,不能盲目適用。為了保持刑法的穩定性與謙抑性,必須對其進行嚴格周密的解釋,從而助推司法適用。
參考文獻
[1]舒登維.刑法修正案(十一)關于高空拋物罪的理解與適用[J].廣東開放大學學報,2021,30(5):54-60.
[2]葛洪義.法律方法講義[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3]李斯特,徐久生.李斯特德國刑法教科書[J].政法論壇,2021,39(5):2.
[4]程紅.論刑法解釋方法的位階[J].法學,2011(1):40-49.
[5]周光權.刑法解釋方法位階性的質疑[J].法學研究,2014,36(5):159-174.
[6]俞小海.高空拋物犯罪的實踐反思與司法判斷規則[J].法學,2021(12):81-103.
[7]張明楷.高空拋物案的刑法學分析[J].法學評論,2020,38(3):12-26.
作者簡介:秦心心(1997— ),女,漢族,河北邯鄲人,河北農業大學,在讀碩士。
研究方向: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