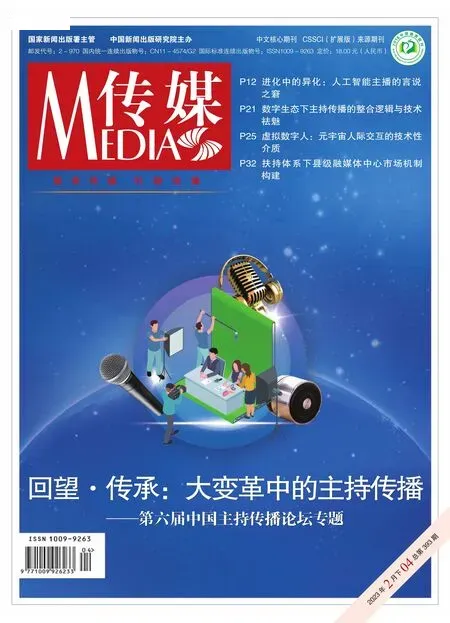中國主持傳播研究二十年:知識圖譜、熱點研判與認知地圖
——基于2002—2022年間的文獻計量分析
文/于佳卉 王志揚 張夢琦
隨著數字媒介在世界范圍內強勢崛起,我國的媒介生態呈現出新舊媒體相互區分又逐漸融合的特征。在新媒體強社交屬性的生產邏輯下,主持傳播實踐開始從大眾傳播向人際傳播方向流變。加之學科融合、學術理論研究深化等因素,使學者們對中國播音學的研究視角從語言學、藝術學轉向傳播學,主持傳播的研究視域就此出現。現階段學者們已完成對于主持傳播的理論初探,形成了與當前媒介融合趨勢下的傳播特征相適應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并形成了多個方向的研究熱點。
為了總結階段性研究成果,本研究立足于傳播學視角,以“主題”為檢索項、以“主持傳播”為檢索詞,在中國知網(CNKI)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數據庫中檢索,使用Cite Space軟件對樣本論文進行分析,通過共現、關聯圖譜等形式展現2002至2022年間我國主持傳播的研究脈絡及發展規律,進而透析出我國主持傳播研究的學術研究動態,為后續的研究者提供參考。
一、中國主持傳播研究的知識圖譜
1.主持傳播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中國主持傳播領域的相關研究自2002年開始出現,其發文量總體呈上升趨勢(如圖1)。為梳理其演進脈絡,本文通過對年度發文量趨勢圖中的關鍵時間節點進行分析,將中國主持傳播的研究分為以下三個研究階段。

圖1 年發文量趨勢圖(N=357)
一是基礎探索階段(2002—2011),中國播音學與傳播學相結合的研究思路剛被提出,總體發文量較少。其原因是該時期受眾接受信息的渠道較為單一,主持人及其傳播活動的傳受關系還未發生明顯改變。廣播電視節目、主持風格、傳播效果、傳播策略等議題是這一時期的研究重點。
二是創新融合階段(2012—2016),互聯網技術帶來的新媒體熱潮使主持傳播的研究熱度呈直線上升趨勢。傳受關系轉變、“去主持人化”現象、傳播主體泛化等因素使其研究視角正式向傳播學轉變。主持傳播中主體身份擴展、傳播平臺重構、傳播內容演化等議題成為這一時期的研究熱點。
三是解構突破階段(2017—2022),“新文科”建設的提出使研究者們對主持傳播的研究熱情持續高漲。除深化中國播音學理論構建、拓展學科疆界、重塑教育理念、完善人才培養體系等議題外,與智媒傳播空間相關的議題也是學者們的研究重點。
2.學術共同體建設情況。通過對中國知網樣本論文的考查,筆者發現研究者與研究機構主要來自國內高校的播音與主持藝術學與新聞傳播學兩個學科,少部分研究者為行業內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傳統媒體從業者。
其一,從研究者合作情況來看(如圖2),主持傳播領域的研究者之間雖有合作但較為分散,兩個學科的研究者合作研究的關系不強,尚未形成密切的合作關系與學術團隊。且學界研究者更重視理論拓展與人才培養,業界研究者則更傾向于經驗分析,二者尚未形成合作研究關系。此外,還缺少語言學、社會學、心理學以及藝術學等其他學科的相關學者的加入,視域更為廣闊、維度更為深化的研究團隊尚未形成。

圖2 研究作者合作情況(N=357)
其二,從研究機構合作情況來看(如圖3),研究以中國傳媒大學與中國人民大學為核心陣地,另有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各級地方媒體等傳統媒體機構。可見傳統媒體機構在新舊媒體融合中對于其自身身份轉化的關注。以研究機構的構成狀況來看,學界與業界暫未形成深度合作的研究態勢。另外,學界與業界對于短視頻創作、社交媒體直播等領域中的主持傳播形態研究熱度較高,但研究對象中卻少見該領域中的頭部從業者與MCN機構。
對常規單一層面切片HE染色的患者,非前哨淋巴結行多層切片HE染色檢測,發現有微小轉移灶;對多層切片HE染色的患者進行多層連續切片及免疫組化,發現淋巴結存在微轉移;對前哨淋巴結無微轉移患者的非前哨淋巴結行多層連續切片及免疫組化研究,尚未發現淋巴結有微轉移灶。

圖3 研究機構合作情況(N=357)
綜上可見,我國主持傳播研究中尚未形成顯著的合作研究聯系,學者與媒體從業者、學術機構與行業機構四者間合作關系較弱,學術共同體尚未形成。
二、主持傳播研究熱點及其研判
在主持傳播關鍵詞共現圖譜中,“播音主持”“主持傳播”“主持人”具有較強的中心度(如圖4),處于整個知識網絡的核心位置,不僅再次佐證了我國主持傳播研究較強的實踐性特征,同時也起到了連接不同研究主題的作用。

圖4 關鍵詞共現圖譜(N=357)
“廣播電視”“新媒體”“融媒體”“短視頻”“全媒體”“媒介融合”“人工智能”等關鍵詞見證了我國主持傳播20年的學術研究動態中媒介環境的變化,可以說主持傳播是媒介技術發展下的產物,使大眾傳播主體“人格化”;“主持風格”“主持藝術”“傳播能力”“口語傳播”等關鍵詞則體現了學術研究中對于人才能力要求與培養方向的變化,實現了從局限于演播室的單一主持方式的藝術探索,到形成多態化的主持傳播方式;“人際傳播”“多維傳播”“文化傳播”等關鍵詞表明了主持傳播研究隨著社會發展逐漸出現的新研究維度,同時也體現了學界對于主持傳播社會功能的動態思考。但是在關鍵詞共現圖譜中,關鍵節點數量較少、節點之間的聯系也較為松散,對于可能會突破現有媒介生態的前沿性的技術研究較為少見。可見我國主持傳播領域的多維度、深層次、高創新力的研究體系還未形成。
經過對關鍵詞共現圖譜的考查,可推斷出當下主持傳播的研究熱點大致有三類。
1.主持傳播重視實踐性研究,其主體呈多元化發展狀態。在主持傳播主體性研究方面,主持傳播不再被認定為是廣播電視行業內獨有的、僅由廣電主持人進行傳播的傳播方式。在數智技術驅動的媒介空間下,主持傳播的主體經歷了從專業化到精英化,再到泛眾化、智能化的轉變。人人都可以成為網絡媒體中主持傳播的主體,同時人工智能主播的廣泛應用更是豐富了其傳播樣態。在此背景之下,原有的主持傳播主體圈層被打破,對傳播者的主體性研究成為研究者們較為關注的議題。
在人文傳播領域,隨著信息流動扁平化、傳播陣地多屏化、傳播內容多樣化的媒介環境轉變,傳統媒體主持人面臨著更高的專業要求。學者們認為提升個性、激活情感、強化責任將成為傳統媒體主持人在當下媒介環境中提高競爭力的關鍵。在人機交互領域,學者們基于目前人工智能技術的行業應用現狀,提出人機協作將是未來主持傳播內容的主要生產方式,強化自身人格化特質是適應人機共存的最好方式。另外,學者們對人工智能主播的負面傳播效果也進行了研究,構建人工智能主播的外部人格將有助于這一問題的解決。
2.主持傳播強化功能性研究。在主持傳播功能性研究方面,媒介技術經歷了從物理媒介到關系媒介再至算法媒介的轉化,不僅使主持傳播的傳播主體范疇不斷被拓寬,同時隨著媒介在文化活動與社會運作中的功能凸顯,大量學者將研究目光聚焦于媒體生態變遷下出現的新現象、新變化并對此作出解釋和回應,因此社會互動中的媒介化研究也成為近年來主持傳播研究領域的熱點議題。
新興媒體帶來的碎片化、口語化、簡單生活化傳播特征更加直觀地迎合了當前受眾需求,卻也引發了研究者們對于我國文化空間建設的憂慮。用價值觀傳播樹立文化自信、用文化與跨文化傳播兼顧文化滋養、用話語傳播引導社會話語,發揮主持傳播在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中的價值觀導向作用。對于當前媒介環境下出現的社會問題也可以通過深耕內容管理、培養權威型意見領袖、開展“甄別、批判、參與、賦權”的媒介素養教育等方式建立新時代的傳播秩序。
3.主持傳播推進學理性研究,其人才培養與理論挖掘呈多維化發展狀態。在主持傳播學理性研究方面,隨著媒介環境的變化與研究的深入,為主持傳播的人才培養模式探索和理論研究注入了新的內核。加之建設“新文科”浪潮的推動,突破中國播音學學科發展瓶頸、完善理論體系成為學者們頗為關注的議題。
在人才培養角度,在新的技術條件下可以通過明確學科定位、更新人才培養體系、優化教學方法、重塑教育理念、實現產教融合等方式對中國播音學的人才培養模式進行升級。在學術研究的角度,應聚焦于學科的本源研究、史學研究和學科的交叉研究,將近親學科“口語傳播學”“修辭學”等納入理論研究范疇之中,打破中國播音學有“術”無“學”的發展桎梏。
三、主持傳播研究的地圖與方向
回顧我國主持傳播領域的20年的學術研究脈絡后發現,主持傳播領域的研究發展態勢與媒介環境變遷、學科發展需求以及我國所處的國內外政治文化環境息息相關,這也揭示了該領域未來的研究趨勢。
1.注重理論建構,補充研究完整性。當前學界對于主持傳播學的理論研究相對深入,研究者們在新技術條件下拓寬了對主持傳播主體的研究范疇。對于不同傳播渠道中的“文化身份”“身體性”“場域”“傳播流”等要素進行了探索。針對信息傳播內容的生產與分發差異而產生的多元傳播內容形態進行了分析,但對于傳播鏈條中其他要素的研究并不完整,研究范式也較為單一。
受眾與傳播效果是主持傳播活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受眾早已從內容的消費者變為內容的生產者,而傳播效果則是檢驗主持傳播活動合理性與社會傳播影響力的關鍵所在。在未來的主持傳播研究中,不妨把受眾需求或傳播效果作為切入點,選擇合理的理論視角與傳播模型,從而提升主持傳播領域的研究完整度。
此外,當前主持傳播的研究還沒有形成規范的研究范式,多以經驗梳理方式提出建議性對策。既缺乏對于多重傳播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的考察,也沒有對于傳播系統與社會系統之間相互作用的反思。因此,在研究方法的探索中應予以重視并加以補充,可以適當引入傳播學中實證研究范式與批判研究范式,采用中微觀視域以及宏觀視域解決社會中實際問題以提升研究的嚴謹性和社會性,用更廣闊的研究維度探索問題的本質。
2.注重生態建設,重視研究社會性。學者們對于網絡傳播擬態環境中出現的社會問題進行了深刻的思辨,針對青年亞文化、消費主義、數字勞工、數字鴻溝等網絡傳播中出現的復雜問題提出了合理的解決方案。根據媒介環境學的核心思想,主持傳播作為媒介生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其中的人、社會、媒介三者之間的良性發展關系討論仍不夠充分。
媒介融合已成為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核心技術與控制文化形成了信息偏見與話語壟斷;扁平化、碎片化、層級化的傳播主體為謠言噪音導致意見極化提供了土壤。對于不具備媒介素養的傳播者和受眾來說,實則是弊大于利。如何利用現有傳播媒介發揮主持傳播主觀優勢、提升傳受雙方的媒介素養、打造健康發展的媒介環境是實現主持傳播社會功能的關鍵所在。
面對技術變革,以及后疫情時代國內外的輿情壓力,如何利用現有傳播媒介發揮主持傳播在人際傳播與大眾傳播中的優勢、重塑公眾認知安全屏障、通過圈層合作促進不同傳播主體之間形成共識、打造健康發展的媒介環境是當下主持傳播的研究中應重點思考的問題。
3.注重技術賦能,強調研究前瞻性。當前主持傳播研究主要聚焦于媒介融合背景下出現的各類問題的思考以及傳播策略的提出,傳播場域也主要集中在現實物理世界與數字虛擬世界,研究能根據社會環境與媒介環境的變化而發現新的研究方向,具有一定的創新能力但暫時缺乏前瞻性視角。
人類的傳播方式會受媒介形態的影響而發生改變,元宇宙和賽博格分別指出了人類未來“社會”與“身體”的演化方向。技術升維邏輯下的媒介發展將會突破現實的物質世界與已存的數字虛擬世界,從復刻到延伸,形成源于現實而又超脫于現實的跨物理時空;同時,技術推動下的傳受邊界消弭,將促使人類產生對于未來內容生產的無限“想象”。屆時,“場景”“身體性”“創作者經濟層”“受眾體驗層”等元素都將會出現新的變化。
面對未來全新的社會與媒介形態,主持傳播主體如何在去中心化的結構樣態中完成自身角色調試,適應從大眾傳播到大眾人際傳播的模式轉變;研究者們如何以技術為基點,構建話語體系與傳播范式;又將如何促進媒介代際演進下的媒介素養教育的迭代發展,這一系列的前瞻性探索是研究者們未來需要進一步關注的問題。
四、結語
主持傳播研究是一項具有深層社會屬性與傳播意涵的議題,從萌芽初生時期較為單一的議題到如今全方位、多維度、強交互的研究生態,媒介技術的不斷發展為主持傳播研究的演進提供了可能。對主持傳播研究20年來的學術發展動態進行梳理,不僅是對其主題理論體系與實踐形態的歷史性總結,更是激活中國播音學持久學術活力、更新主持傳播主體創作內涵、構建中國特色話語體系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