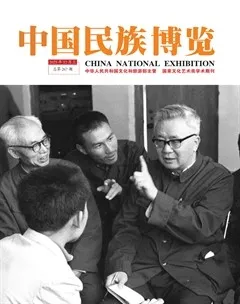《遂初堂書目》史部分類探析
【摘 要】南宋藏書家尤袤編纂的《遂初堂書目》為現存南宋三家私人藏書目錄之一,其史部類目的設置既承襲前代目錄的分類思想,又依據學術的發展變遷,于史部中創設本朝史、史學類,對后世書目史部分類產生深遠影響。雖有一定的創新,但也存在其不足之處。
【關鍵詞】尤袤;《遂初堂書目》;史部;目錄分類
【中圖分類號】G25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3)23—027—03
《遂初堂書目》(以下簡稱《遂初目》)是南宋著名詩人、藏書家尤袤編撰的一部私家目錄。《遂初目》雖無解題,記載也較為簡略,但在目錄分類上卻有所突破,該目首次為“本朝”史書設立類目,還創設了“譜錄”“章奏”“樂曲”等門類,對后世書目體例產生了深遠影響。學界目前就《遂初目》的研究多集中于該書的目錄學價值及相關問題的考辨,對其史部分類的研究則不夠深入。本文首先概述尤袤之前史部類目的演變,從而分析《遂初目》史部分類對傳統類目的突破及其分類上的不足。
一、《遂初目》之前的史部分類概述
我國古代圖書的分類起源于西漢劉向、劉歆父子編撰的《七略》,《七略》以輯略總敘諸書之旨要,又分為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六類,依類著錄圖書。漢代經學興盛,史籍數量較少,《七略》及之后的《漢書·藝文志》均未給史書單獨設類,諸如《史記》《戰國策》等史書則多附于春秋類下。首先給史籍創立類目的,是西晉秘書監荀勖編撰的《中經新簿》(又名《晉中新簿》)。《隋書· 經籍志序》稱:“魏秘書郎鄭默,始自《中經》,秘書監荀勖,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群書。一曰甲部,記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1]《中經新簿》設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項,專收史類書籍,史籍書目至此才有了歸宿。至東晉李充編撰《晉元帝四部書目》(以下稱《四部書目》)在《中經新簿》又重分四部,改乙部收錄史記,丙部收錄諸子,確立了經、史、子、集的次序。對史部編類的形成產生重要影響的還有梁朝阮孝緒編撰的《七錄》,該目設“紀傳錄”一項,下分國史、注歷等十二個小類,收史部書籍,對后世史部類目的設置具有重要意義。
唐魏徵編撰《隋書·經籍志》(以下稱《隋志》)在李充《四部書目》的基礎上改甲、乙、丙、丁為經、史、子、集之名,從而正式確立了經、史、子、集四部分類體系。《隋志》史部分十三類,“雜傳”“舊事”“職官”“簿錄”四類直接依照《七錄》的分類。又增加“雜史”類,收錄一些體制不經、真虛莫測的委巷之說,將“國史”分為“正史”“古史”兩類。另對《七錄》中的一些類目做了適當的更名,將“注歷”“儀典”“法制”“偽史”“土地”“譜狀”易名為“起居注”“儀注”“刑法”“霸史”“地理”“譜系”。《隋志》史部分類標志著史部格局的基本定型,此后,其分類編目一直為歷代沿用。《舊唐書·經籍志》(以下稱《舊唐志》)的類目設置多采用《隋志》的分類,僅略作更名,如改“古史”為“編年”,改“簿錄”為“目錄”等。《新唐書·藝文志》(以下稱《新唐志》)史部類目幾同于《舊唐志》,僅改“雜傳”為“雜傳記”。至北宋王堯臣等編撰《崇文總目》,才又新增了“歲時”類,著錄相關時令類書籍,又改“起居注”為“實錄”,改“譜牒”為“氏族”,改“雜傳”為“傳記”。《郡志》在史部類目設置上的貢獻主要是創制了“史評”類,收錄史學批評著作,取消“歲時”,改“目錄”為“書目”,其余類目則依照《崇文總目》的分類。《遂初目》之前的史部類目,除創設了“歲時”“史評”類,其余類目基本不出《隋志》的框架。由于時代的發展變化,各類別書籍數量的增多減少,圖書的編目分類亦隨之發生變化。而史部類目的演變,一方面反映出各時代史部圖書種類及其數量的變遷,另一方面也是一時代之史學思想的映襯。
二、《遂初目》史部類目的突破
雕版印刷術的廣泛普及、活字印刷術的發明,使宋代的目錄學發展十分繁盛。北宋、南宋時曾多次整理宮廷官府的國家藏書,編制了《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中興館閣續書目》等書目。與此同時,私人藏書家編撰目錄的風氣亦蔚然成風。據《中國私人藏書史》統計,“宋代私家藏書達萬卷以上的大藏書家共計二百一十四人”[2],這些藏書家大多編有書目,且在目錄的編類上也有諸多創新。《遂初目》作為南宋僅存的三家私人藏書目錄之一,尤袤在吸收前代目錄學成果的基礎上,對一些類目作了調整,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宋代的圖書狀況。宋代史學發達,統治者十分重視對當代史書的編修,宋代史書在數量、體裁、內容上較之前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有的書目編類也難以全面揭示宋代史學的發展變遷。尤袤為順應時代及學術的需要,大膽增創類目以適應這一變化。下面筆者就《遂初目》史部分類上的變化展開論述,以分析其分類之突破。
(一)調整“國史類”“正史類”的收書范圍
“國史”類,為“朝廷敕編當代史”,始于南朝梁阮孝緒編撰的《七錄》。《七錄》首列“國史”于“紀傳錄”之下,該目設立的“國史”是相對于“偽史”而言,并非專收當代史書。《七錄》未有“正史類”,故阮氏之“國史”大致相當于之后的“正史”之意。其后,《隋志》將“國史”析為“正史”和“古史”。其史部序云:“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并有解釋……《史記》傳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編制,以備正史。”[3]《隋志》所指“正史”,當是《史記》《漢書》一類的紀傳體史書,而為這類“正史”書籍作集注、集解、音釋、音訓、駁議等的相關書籍同樣為“正史”的范圍。《隋志》確立了“正史類”收錄書籍的體例和標準,對后世影響深遠。此后,諸家書目多設“正史”而不設“國史”。尤袤于史部同時設立“正史類”和“國史類”兩項,從《遂初目》著錄的“正史類”“國史類”書籍可以窺知:①尤袤調整了“正史”的范疇,僅列宋以前的紀傳體正史著作,不列相關注疏、集解等書籍;②“國史類”俱錄宋代官方敕修的當代史書,內容包含官修正史、編年、寶訓、圣政圣語、御筆、典故、時政記等。尤袤“國史類”的設立對后世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明楊士奇等編《文淵閣書目》效仿《遂初目》設“國朝”類,主要著錄御制文集、御制詩集、當朝編撰的律法、禮法、實錄、寶訓等書籍,其收錄范圍較《遂初目》更廣,并首次將御制文集、詩集載入史書。明末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則直接沿用“國史”之類名,置于“正史”之前,書籍僅收當代實錄、寶訓、圣政紀三類。“國史”類目的設立,凸顯出當代史書的重要性,為研究一代之歷史提供便利。
(二)創制“本朝史類”
“雜史”一類源出《隋志》,雜史類小序云:“自秦撥去古文,篇籍遺散……又自后漢已來,學者多鈔撮舊史,自為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又有委巷之說,迂怪亡誕,真虛莫測。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廣覽,以酌其要,故備而存之,謂之雜史。”[4]指出“雜史類”主要收錄一些“體制不經”的史部書籍。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以下稱《通考》)也稱“雜史”有“體制不純,事多異聞,言或過實”[5]的特點。雜史雜傳皆為野史之流,又都出于正史之外,故歷代在其歸類上較為混亂。鄭樵《通志·校讎略》亦云:“古今編書所不能分者五:一曰傳記,二曰雜家,三曰小說,四曰雜史,五曰故事。凡此五類之書,足相紊亂。”[6]《隋志》設“雜傳類”,其序載:“因其事類,相繼而作者甚眾,名目轉廣,而又雜以虛誕怪妄之說。推其本源,蓋亦史官之末事也。”[7]明確“雜傳”所記為虛誕怪妄之說。馬端臨《通考》指出雜史與傳的區別:“蓋雜史,紀、志、編年之屬也,所紀者,一代或一時之事。雜傳者,列傳之屬也,所紀者一人之事。然固有名為一人之事,而實關系一代一時之事者,又有參錯互見者。”[8]據此知雜史以編年、紀傳為體,多記國家及君王事;雜傳多以列傳為體,記一人之事。《遂初目》“本朝雜史”“本朝雜傳”收錄書籍的標準同“雜史”“雜傳”類一樣,除僅著錄宋代部分外,無實質性差別。“舊事”又稱“故事”,《七錄》最早設立。《隋志》設“舊事”類,著錄書籍多為舊時典章制度。《舊唐志》亦設“舊事”類,其小序稱“以紀朝廷政令”[9],除典章制度外,還將“詔令”之書收入該類。《新唐志》始更名為“故事”,在承襲《舊唐志》“舊事”類收書標準外,又納入名臣名人事跡,比如《張九齡事跡》《彭城公故事》等。《遂初目》設“故事類”和“本朝故事”兩類。“故事類”收錄書籍15部,多為唐人唐事,而這些書籍又被后世的目錄書多歸類為傳記類。“本朝故事”類著錄書籍58部,包含有關朝政、軍事、財政、茶馬鹽等相關書籍,相較于“故事類”,“本朝故事”的收書范圍更大,記載當朝社會政治經濟等內容甚為豐富。
(三)首設“史學類”
《遂初目》之前已有“史抄”“史評”類。南宋陳骙《中興館閣書目》設“史抄”類,僅著錄《兩漢博聞》《重編史雋》二書。晁公武《郡志》在《中興館閣書目》的基礎上創制了“史評類”,是類著錄《劉氏史通》,其解題云:“前世史部中有史鈔類而集部中有文史類,今世鈔節之學不行而論說者為多。教自文史類內,摘出論史者為史評,附史部,而廢史鈔云。”[10]宋代“論史”之風頗盛,史評著作增多,晁氏應時而設“史評類”。其后,《遂初目》首設“史學類”,其收錄范圍較之《郡志》“史評類”已發生了一些改變。《郡志》將蘇轍《古史》入“史評類”,《遂初目》入“雜史類”,《古史》為紀傳體史書,入“雜史類”更為妥當。除著錄史抄、史評、論史著作外,尤袤還從諸目中首次析出《史記正義》《史記音義》《唐書糾謬》等正史相關書籍置于“史學類”。馬端臨《通考》沿襲其歸類,將《史記正義》《史記音義》等歸入“史評史鈔類”。《千頃堂書目》設“史學類”,又設“史鈔類”,其“史學類”略同于“史評”,只是名稱不一樣。
三、《遂初目》分類之不足
《遂初目》在分類上有所創新,但也存在其不足之處。在類目的設置上,《遂初目》主要有以下兩點缺陷。
(一)未有三級類目的設置
新舊《唐志》已有三級類目的設置,經、史、子、集四大類為一級類目,大類下又有若干小類為二級類目,其中一些小類又設有一些子目為三級類目。如《新唐志》“正史類”下分“集注”,“起居注”下分“實錄”“詔令”,“雜傳記”下分“女訓”等。鄭樵《通志·藝文略》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更為完善的三級分類體系,是目將著錄的一萬多部圖書分類分為十二類,類下又分若干家,家下分若干種,類例分明,層次清晰。《遂初目》經部“論語類”下標有“孝經孟子附”,史部“偽史類”下標“夷狄附各國史后”,子部“數術家類”下標“一天文,二歷議,三五行,四陰陽,五卜筮,六形勢”,但只在類目名稱下標注,未在所著錄書籍中進行區分,這種標注更象是類目的說明,而非三級類目的設置。針對一些收書眾多、內容復雜的類目,設置三級類目能正確反映圖書的內容,使錯綜復雜的書籍以類相從、嚴整有序。《遂初目》史部書目眾多,分類又繁,由于未設置三級目錄,其二級目錄下圖書的著錄仍顯得混雜。
(二)有些書籍分類不安,訛誤多見
《遂初目》在書籍歸類上稍嫌輕心草率。《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稱《總目》)亦指出:“《元經》本史而入儒家,《錦帶》本類書而入農家,《瑟琶錄》本雜藝而入樂之類。亦有一書偶然復見者,如《大歷浙東聯句》一入別集,一入總集之類。又有姓名訛異者,如《玉瀾集》本朱橰作,而稱朱喬年之類。”[11]《遂初目》歸類上主要存在四種失誤。一是分類不安者,如《總目》所指《元經》應入史部,《錦帶》應入類書,《瑟琶錄》應入“樂曲類”,《蕃爾雅》《蜀爾雅》本“小學”而入“地理類”。二是一書兩入者,如《汲冢周書》一入“尚書類”,一入“春秋類”;《皇祐平蠻記》一入“本朝故事”,一入“地理類”;《文苑英華》一入“總集類”,一入“類書類”。三是重復著錄者,如“儀注類”《郊祀錄》著錄兩次;“別集類”《崔顥集》《吳均集》均著錄兩次;另有一書二名分入兩類者,如“雜史類”有《大業拾遺記》,“小說類”又著錄《南部煙花錄》,二者實為一書。四是書名訛誤者,如“別集類”《李泰伯旴江集》應作《李泰伯盱江集》,《晁伯封邱詩集》應為《晁伯宇封邱詩集》。凡此種種,都表現了《遂初目》書籍歸類的輕率、訛誤多見。
四、結語
宋代史學著作發展繁盛,史部不少類目中的當代書籍數量已然超過前代。尤袤不泥守舊有的史部分類體系,更易類名或調整收錄范圍以正確反映著錄書籍的內容、性質,又依據學術思想的發展變化,增設“國史類”“本朝雜史”“本朝故事”“本朝雜傳”四類,專收當代史書,展現出其在書籍分類上的遠見卓識,為后世史部類目的設置產生了深遠影響。《遂初目》雖有諸多創新,亦存在著分類不安、訛誤多見等問題,但大醇小疵,瑕不掩瑜,這些問題都不能掩蓋其價值。
參考文獻:
[1][3][4][7]魏徵.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2]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M].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
[5][8]馬端臨.文獻通考[M].北京:中華書局,2011.
[6]鄭樵.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華書局,1995.
[9]劉昫,等.舊唐書·藝文志[M].北京:中華書局,1975.
[10]晁公武.郡齋讀書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1]永瑢.四庫全書總目[M].北京:中華書局,1965.
作者簡介:曹麗(1990—),女,漢族,四川內江人,研究生,西華大學,研究方向為中國語言文學(古典文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