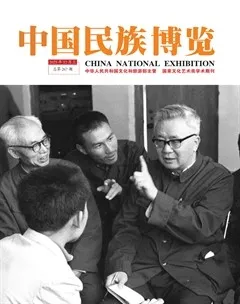前衛中的“傳統”


【摘 要】在“85美術”接受西方觀念藝術的過程中,觀念的內涵主要來自與“達達”相關的對藝術本體的質詢,其中字象藝術利用漢字言、義、象獨特的整一形式表達一種“反觀念”的觀點。通過分析以徐冰、吳山專與谷文達為代表的字象藝術家作品中“去主體性”“元一性”“轉型性”這三組內在的本質概念,可見出東方對西方當代藝術的回應及本土自我的創新實驗。
【關鍵詞】字象藝術;85美術;形態意向
【中圖分類號】J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3)23—205—03
吳山專在《字象的誕生》中將中文作為媒介的當代藝術稱作“字象”,它們既是文字,也是圖像藝術。從廣義的藝術本體的角度上看,中國字象藝術旨在指出藝術作品的價值不在于能指和所指之間的對稱,從而最終得到清晰的意義,相反,恰恰在于作品散發的“無”“非”“空”的意味。
一、去主體性:反觀念的本土邏輯
“85美術”從專注人道主義情懷的藝術,投向具有人文熱情的“新觀念”。而這種轉變催生藝術進入以往被視為非藝術甚至反藝術的領域,哲學和文化相關的概念性詞語充斥其間。這與西方觀念藝術對藝術本質的探求一致——藝術實踐中概念與圖像的作用及二者間的關系。可以說,85中的字象藝術家試圖將藝術形式與觀念傳達、文化啟蒙緊密結合,不再有“為藝術而藝術”。它從直接的政治指向性進入了更為廣闊的文化現代性,并且以整一的現代性視角審閱藝術的發展。
但由于藝術家接受西方藝術的途徑較為匱乏,為此對相關內容的理解相對膚淺,造成了與西方60年代以來的觀念藝術不可忽視的區別。西方觀念藝術是對先前現代美學自律的逆反,意圖徹底顛覆對藝術的傳統認知(如杜尚的《泉》以非藝術品代替藝術品),挑戰“何為藝術”的觀念。而“85美術”中的觀念行為可以定義為一種“大藝術”的文化觀。藝術家重視觀念和圖像的平衡,試圖將物品、環境和藝術家自身融為一體,重在對這種整體的在場性的體會。“反藝術”在此并非反美學,而是使藝術創作具有“非物質性生產”的日常化行為特性,反對暴力主體性(主體觀念)干預藝術,同時反對與文化功能無關的形式自娛。字象藝術恰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徐冰早期作品雖受西方哲學思想的影響,但作品中更多表現出東方意味。比如他的畢業作品《五個復數系列》(1986),選取非常平常的農村景色,重復地在同一塊板上刻制不同的畫面,并將修正的畫面轉印在同一橫幅上。在“重復”(重復即空)的藝術觀念和方法論中,徐冰不斷解構作品的創作痕跡,達到“去主體”的目的,及消解保持作者“唯一性”原初痕跡的復制性途徑。同時展示創作思維的過程,借此改變傳統作者與讀者間的關系。顯然,完全不同于西方觀念藝術中完全忽視制作和工藝效果的方法。而這種意識預示著日后《天書》等字象作品所含有的某種特定精神。
所以,從屬觀念行為藝術的字象藝術在本質上是反觀念的。比如,廣告俚語被吳山專運用到他的藝術中,《紅色幽默》系列鋪天蓋地的文字,是與“現實”一樣真實可辨的語言陷阱等等。這并非是西方達達主義和觀念藝術試圖從媒介革命的角度將藝術與生活在本體論的概念中進行整合,相反,它是一種東方風格的“日常冥想”和“行動實踐”,強調某種勞動性、常規性、重復性及連續性。西方達達和觀念藝術將語詞和圖像對立分離,意圖走向觀念至上,主張通過思辨性或反邏輯的破壞性對舊觀念進行完全的覆地,所以,語詞在藝術作品中占絕對話語權,概念先于形象。而“85美術”的作品更像是常規性的沉思和體驗,且包含藝術家同媒介(物)交往過程中產生的非理性意識——來自樸素的、沒有觀念干擾的日常行為。觀念、形象和體驗之間沒有任何界限。西方觀念藝術受20世紀哲學乃至語言學轉向的影響,這種趨勢此后發展為后現代以來的當代藝術占主導的文化政治語言學現象。為此,字象藝術與同代的廈門達達、“理性繪畫”是相通的,與西方當代藝術的抽象、觀念和寫實的分離性、獨立性和極端性不同,藝術敘事具有包容性,其特點既非抽象,也非觀念,更非寫實,而是綜合性的,并且“比興”敘事和日常性兩種語言因素的運用則強調隱喻和過程。
二、元一性:本體價值的當代轉換
漢字作為東方美學的典型符號,自身蘊含圖形美感、文化性等基本屬性,可以完全獨立于任何主觀詮釋。80年代藝術家對西方觀念藝術——概念和圖像的二元性做出回應時,必然想到使用中國符號,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形態置換為當代藝術形式,成為符合現代語境的藝術方式。
漢字歷經漫長且復雜的演變過程。漢代許慎的“六書”對古代文字學中象形、指事、會意等因素之間的互相混成的構成原理進行系統理論。漢字以象形為基礎,后發展成“形、義、音”三體合一的符號系統。中國古代藝術理論中則有“理、識、形”之說。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卷一的“敘畫之源流”中指出,“顏光祿云,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圖載”從字面意義解釋便是圖以載道,與文以載道相似。現今,“圖載”(圖以載道)變成了視覺文化,因為視覺文化也是通過圖像文字等媒介表現某種文化政治觀念。圖載的三種方式——圖理、圖識、圖形與先期資料,如先秦兩漢文獻中有關文字、書畫起源的“文、書、圖”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此外,《易經》中有關“象”也有辭象、形象的說法。因此,形象、概念和書寫混成合一的特點都離不開中國文字的起源,也正是這個特點使中國的象形文字得以保留到今天。20世紀末,古代與文字有關的優秀傳統文化因素成為中國藝術家探索當代藝術的重要參照資源。
但中文的概念、圖像兩種元素密切相關不可分割的特點導致了語義的模糊性和復雜性。所以,中文完全可以作為藝術的“元一性”元素整體保留,無需添加意義或者給予意義。這正是中文和其他表音語言系統的根本區別,也是中國的“文、書、圖”與西方符號學之間的根本區別。符號的對立面是形象,但形象一旦被理念化也可以稱為符號。這個圖像符號的二元性正是觀念藝術的基礎。然而,中文本身既是符號,也是形象,比如,“森”是3個“木”集合而成的森林的符號,同時也是森林的形象。為此,吳山專通過“文、書、圖”的這種自足性或者元一性強調藝術的“非觀念性表達”的本質。
西方觀念藝術家用圖像,或圖像和圖像(或文本)的并置去說明一個明確的文字意義(觀念或概念),中國的字象藝術家則試圖突出中國文字的“無意義”的一面,比如吳山專曾明確地指出,他的紅色幽默的字象藝術的核心就是表現“赤”和“虧空”。漢字自身帶著數千年的豐富含義,讓它失去意義并非易事。即便運用后現代主義的拆解方式,仍然會生出新的語義,因為漢字的偏旁本身便具有獨立意義。所以,我們看到,徐冰、吳山專、谷文達等都努力通過對文字的拆解獲得某種視覺和概念互相隱喻的模糊性力量,相反,西方當代觀念藝術則試圖帶給觀眾更多的邏輯思考和明確的觀念批判。
可以說,80年代的字象藝術利用與優秀傳統文化最密切相關的文字進行藝術創作,以一種懷疑、調侃的態度挖掘某種當代價值。看似與西方觀念藝術之后的語言學傾向一致,然而,受到解構主義語言學影響的西方后現代主義主要通過圖像拼貼并置所產生的語義沖突去表達其當代顛覆性意義。中國90年代出現的政治波譜更符合這樣的后現代圖像學現象。相反,80年代的字象藝術并不具有顛覆性取向,它借用“文、書、圖”整一的藝術形式從事反觀念化的創作,文字和圖像可互為對方,但不相從屬。
三、轉型性:基本元素的文化策略
當代藝術“文化母土”所帶來的固有思維模式,禁錮了藝術家在西方語境下的創作靈感和動力,如果不能超越本土文化,那么跨文化行為就無法實現。事實上,當藝術家在作品中表達對民族性的渴望時,所表現的東西在意識中便自然而然流露出來,并不是被西方簡單地同化和征服。藝術作品從全人類、全世界的角度來詮釋文化問題時,自身的“他者身份”便從挑戰變成了機遇。從中國的歷史背景出發,歷史淵源及文化深厚使他們很難充分且全面的認識到其他民族的價值觀。在機遇與挑戰面前,即使藝術文化步入現代化進程,仍堅持著自身獨特的思維方式和審美觀念。不同的文化態勢與思維模式之間的沖突碰撞,藝術家自我身份的選擇成為難題。

字象藝術的“反觀念”在80年代后現代主義和西方觀念藝術運動中具有獨特的當代價值。但80年代末,隨著徐冰、谷文達和吳山專相繼移居歐美,即便他們的創作仍以文字為媒介,但更多地圍繞西方熱點意識形態問題展開——文化身份等。從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以及與當代藝術本體間的哲學關聯,轉向文字如何為當下的文化策略服務。80年代的思考和實踐基于中國的文化現代性戰略層面,是本體的實踐,而90年代以后的文字運用則是具體的文化策略。
徐冰《天書》字型變異、印刷模式和文本形態三者的互動價值,體現出中國漢字文、書、圖合一具有的當代性轉換。而后,跨文化的文字嫁接(新英文)和流行符號的文本化實驗(地書),則針對不同文化及思維模式進行轉譯與有機結合的嘗試,意圖通過文字上某種形式的轉變以實現不同環境的“融會貫通”。吳山專以意義模糊性、錯位和語義虧空作為文本圖像創作的基本出發點,對“能指——所指——符號”為基本元素解構的當代語言學的進行呼應和質疑。但90年代移居歐洲后,他把這種對字象本體的思考轉向為身份性(性別)等相關的、用作文化驗證的圖符思考。而谷文達在80年代進行有關“篡改”文字的美學化和圖像化實驗,更多地著眼于中文語言本身的語言學特征,以審美取代利用文字把握世界真理或內在真實的妄念,無需深究文字的邏輯意義。后,在國外則多立足當下生存環境、文化傳承和人類未來,以特定的媒材選擇代表特定的時代與社會的進步,其中頭發為媒介創作的《聯合國》甚至走向極端宏大敘事和極端形式化的兩極分化。盡管他在作品中也不斷傳達用西方當代藝術批判中國固有文化,用中國自身歷史考量西方當代文化的觀念,但最終并沒有完成徹底轉向。一定程度上,80年代文化戰略意義上的“字象”實踐在90年代異國環境的影響下并沒有成為一個更加成熟的當代圖像系統之一。
此外,本土一些藝術家在90年代仍以文字為形式進行創作,但通常只是觀念的表達,文字是工具,而非作為本體的“字象”。即使有延續徐冰“重復即空”修行方式的作品,如宋冬的《水寫日記》和邱志杰的《重復書寫一千蘭亭序》,但他們的文字書寫并不是為了表達,而更多地是為了自我日常性的“功課”。高名潞將這種書寫稱為“極多主義”,它通常發生在極端私密的情境中,比如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2005年期間出現的“公寓藝術”之中。書寫本身和日常性、勞動性融為一體,它是反觀念、反理性和反功能主義的藝術,是90年代市場化和全球化的新語境中的特定的藝術行為。這里的“字象”不是為了向公眾展示的文字結晶,而是印在自己的心靈中的別人看不到的記憶,即隱秘的字象。
四、結語
80年代中期,字象藝術家一定程度上并沒有充分地探討和分析相關理論性問題,創作卻有意或無意地涉及到文化性、元一性等概念。這是對文化的批判,力圖建樹某種文化圖像的文字學多元邏輯,反對觀念對立圖像的二元邏輯。
然而,如何從形態背后的深層方法論的角度去審視中國當代藝術的特點,在借鑒和批判西方當代藝術的雙向層面創造出中國當代藝術的獨特體系才是關鍵,其目的并非要讓中國當代藝術有別于其他區域的當代藝術那么簡單,而是說,中國當代藝術的哲學應當對全球未來當代藝術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語言學和方法論貢獻。
參考文獻:
[1]蔣薇薇.論谷文達的藝術創作及其批評研究[D].南京:南京藝術學院,2020.
[2]郭亞麗.20世紀80—90年代文字媒介藝術研究[D].天津:天津美術學院,2020.
[3]孟星星.當代文字媒介藝術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6.
[4]高名潞.“八五美術運動”的“玄想”敘事——基于個人批評實踐的反思[J].文藝研究,2015(10).
[5]張慧.文字何以成為圖像[D].北京:中央美術學院,2014.
作者簡介:牛芳草(2000—),女,漢族,江蘇徐州人,碩士研究生在讀,吉林藝術學院,研究方向為美術學(當代美學與藝術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