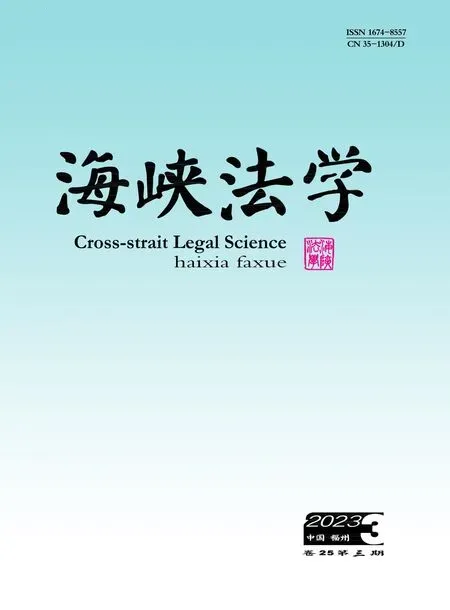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政策的“德性論”論證和重構
駱正言
一、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中的意見分歧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面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我們應該“提高重大疫情早發現能力,加強重大疫情防控救治體系和應急能力建設”。如今緊張的三年疫情防控已經過去,撫今追昔現在是我們應該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的時候了。因為未來我們還可能遇見同類事件,做到這一點我們才能更有效地應對。回想新冠疫情防控最困難的時期,社會上出現了兩種針對疫情防控的意見分歧,涉及不同的法理和倫理觀念,值得我們深入剖析和反思。
一部分觀點認為,為保護人民生命健康,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應堅持常態化的、嚴格的疫情防控,比如強制隔離。①任穎、常廷彬:《中國公共衛生立法路徑研究——黨領導立法的制度優勢與法治保障》,載《法治論壇》2022 年第1 期,第22~32 頁。有學者以新加坡為例,說明采取強制的隔離手段具有一定的正當性,新加坡奉行一種軟法的治理,通過宣傳“新加坡團結”的精神,強調社會責任,期望民眾遵守居家隔離的措施。②張樂樂、徐兆涵、王知:《新加坡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治理體系及其評價》,載《醫學與法學》2022 年第2 期,第1~5 頁。在這些學者看來,在處置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重要關頭,我們不應該過分強調私權利,只要“疾病業已發生或有迫在眉睫的威脅,……且很可能導致大量死亡、嚴重或長期殘疾,……政府就應當宣布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啟動公共衛生應急處置工作。”①申衛星:《公共衛生法治建設:意義、價值與機制》,載《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1 期,第13~28 頁。
但另一部分觀點認為,嚴格的疫情防控措施違反了法治的理念,過分限制了個人的自由。比如在新冠疫情爆發早期,某地方城管隊員(鎮聯合整治疫情專班)為制止商鋪營業,搬走店內多宗商品。事件被網民拍攝后上傳到網絡,引起許多網友的批評,當地政府也公開向商鋪業主賠禮道歉,并退還扣押物品。對此有學者認為,“該鎮聯合整治專班完全沒有必要對該商鋪的物品采取扣押措施。”②王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時期的城市管理與行政執法》,載《城鄉建設》2020 年第5 期,第8~11 頁。針對疫情防控的其他批評還有:沒有根據法律,遵循程序,對于相關人員和場所進行封控,具體說只有甲類傳染病病人、疑似病人,才能采取隔離措施,密切接觸者不能采取隔離措施,更不能交由村委會、居委會的人員來執行,不能戴了個紅袖章就來執法;③蔣盼:《重大疫情防控中的強制隔離制度及其法律控制》,載《行政法論叢》2021 年第1 期,第35~52 頁。村委會無權以自己名義采取行政強制措施實施,限制村民的人身自由和財產權。④史全增:《論村委會在重大公共衛生風險防控中的法治化參與路徑》,載《行政法學研究》2021 年第3 期,第37~48 頁。在公共衛生治理中必須遵循比例原則,根據必要性、有效性和科學性的原則評估是否需要采取強制性措施,⑤陳云良:《促進公共衛生法律體系向公共衛生法治體系轉化》,載《法學》2021 年第9 期,第17~37 頁。有些防控人員因為工作量巨大、心理負擔重,情緒失控等原因,⑥莊曉燕:《疫情防控中行政管理權與人格權的協調》,載《行政與法》2022 年第5 期,第61~68 頁。實施了一些不必要的、過度的“暴力執法”“過激執法”的措施,⑦比如認為防控人員公布個人行動軌跡,侵犯了個人的隱私權,不符合比例原則。李憣、王丹蕊:《新冠疫情防控中公眾知情權與患者隱私權的平衡》,載《醫學與法學》2022 年第4 期,第19~25 頁。以及沒有對實施隔離措施的人,規定相應的行政補償。⑧李雯雯:《重大疫情防控中國家安全利益與公民權利的協調》,載《上海法學研究》2022 年第6 卷,第41~46 頁。
通過以上的列舉我們可以看出,針對新冠疫情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輿論界和學術界的意見存在很大分歧。問題是產生這些差別的原因為何?怎樣看待這種分歧?這些問題的解答非常重要,因為其背后潛藏著大相徑庭的倫理觀點,只有澄清了這些分歧的原因,才能讓我們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不同應對措施有充分的理解,讓決策機關能夠在權衡利弊得失的基礎上,制定出更為合理的防控政策。
針對這一問題,本文將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分析:一是質疑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政策的觀點基于什么樣的法理和倫理主張?二是支持采取嚴格的防控措施的觀點基于什么樣的法理和倫理主張?三是我們應該根據什么樣的倫理主張,如何設置更為公正、科學的應對政策?
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政策的道義論審視
我們先來看看質疑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政策的觀點(以下簡稱為懷疑論)及其法理和倫理依據。懷疑論認為疫情防控要依法進行,要尊重人權,不能采取超越法律之外的防控手段,給個人帶來不必要的約束和損失。比如不能隨意讓企業停產停工,讓商店停止營業,甚至直接“封門落鎖”,即便迫不得已實施嚴格的管控措施,給人們帶來損失,也必須予以補償。那么這種觀點是基于什么樣的法理或倫理主張的呢?
(一)懷疑論從“常態法”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
筆者認為,懷疑論的法理依據是“常態法”。所謂“常態法”是相對于后文的“緊急法”而言的。從“常態法”思維來看,要封鎖疫情區,隔離感染者,必須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和條件進行。如謝暉教授主張,即便緊急狀態法也應“與日常狀態的法一樣,是法治的常態,而不是法治之例外”。①謝暉:《論緊急狀態中的國家治理》,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20 年第5 期,第31~48 頁。另參見謝暉:《例外狀態令尊于法——世界各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令”的法哲學省思》,載《學術論壇》2021 年第3 期,第25~43 頁。那么關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有哪些法律呢?主要是《傳染病防治法》《突發事件應對法》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等。
關于人員隔離,《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第33 條和第44 條規定,突發事件應急處理指揮部認為“必要時”,有權對人員進行疏散或者隔離,對傳染病疫區實行封鎖。根據這些條款,只有傳染病人、疑似病人和密切接觸者,才需要接受衛生行政主管部門或者有關機構的隔離治療和醫學觀察。②《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2003 年制定、2011 年修訂)第33 條規定:“根據突發事件應急處理的需要,突發事件應急處理指揮部有權緊急調集人員、儲備的物資、交通工具以及相關設施、設備;必要時,對人員進行疏散或者隔離,并可以依法對傳染病疫區實行封鎖。”第44 條規定:“在突發事件中需要接受隔離治療、醫學觀察措施的病人、疑似病人和傳染病病人密切接觸者在衛生行政主管部門或者有關機構采取醫學措施時應當予以配合;拒絕配合的,由公安機關依法協助強制執行。”關于疫情區封控,《傳染病防治法》第42 條和《突發事件應對法》第49 條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必要時報經上一級人民政府決定,可以采取限制或者停止集市、影劇院演出或者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動,以及停工、停業、停課和封閉可能造成傳染病擴散的場所。③《傳染病防治法》(2004 年制定,2013 修訂)第42 條規定:“傳染病暴發、流行時,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立即組織力量,按照預防、控制預案進行防治,切斷傳染病的傳播途徑,必要時,報經上一級人民政府決定,可以采取下列緊急措施并予以公告:(一)限制或者停止集市、影劇院演出或者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動;(二)停工、停業、停課;……(五)封閉可能造成傳染病擴散的場所。”需要注意的是,兩部法律都規定只有在“必要”的時候,才能采取隔離和封控的措施。
此外更為重要的是,如果被隔離和封控的人員不予配合,執法人員可以采取什么方法,敦促其遵守法律呢?這就要說到行政法上的行政強制措施。行政強制措施是與行政處罰相對的一種行政行為,其手段是約束個人的人身和財產,目的是制止違法行為、防止證據損毀、避免危害發生、控制危險擴大。(《行政強制法》第2 條)在法學理論上,行政強制分可為直接強制(Unmittelbare Rechtsdurchsetzung)和間接強制(Mittelbare Rechtsdurchsetzung)。④Bernhard Raschauer,Alleigmeines Verwaltugsrecht,Springer-Verlag,1998,S.483.直接強制是指對人身和財產的直接限制,比如將隨意停放、阻礙交通的機動車拖走,或將可能咬人的烈犬捕殺;間接強制是以警告和罰款等方式,迫使行為人改變行為,遵守法律。比如通過罰款,迫使行為人騎電動車時戴上頭盔,開汽車時系上安全帶。
關于強制手段的選擇,學術界一般認為應多使用間接強制,少使用直接強制。只有在行為人極有可能造成生命和財產損害時,才可以直接使用警力消除危險。比如胡建淼教授認為,直接影響被執行人的人身自由權的即時強制措施(直接強制)限于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方可使用:(1)瘋狂或酗酒泥醉,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身體之危險,及預防他人生命、身體之危險者;(2)意圖自殺,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者;(3)暴行或斗毆,非管束不能預防其傷害者;(4)其他認為必須救護或有害公共安全之虞,非管束不能救護或不能預防危害者。⑤胡建淼:《論中國臺灣地區的行政執行制度及理論》,載《法學論壇》2003 年第5 期,第75~87 頁。
如此嚴格要求的原因是,直接強制過于嚴苛,與尊重人權、保障自由的精神不符。①比如余凌云教授指出,韓國行政法理論認為,直接強制過于苛酷而與尊重人權、保障自由之新憲法精神不符”,直接強制只能作為最后的行政手段,不宜廣泛適用。甚至有一段時間,受日本理論的影響,韓國基本上廢除了直接強制。余凌云、陳鐘華:《韓國行政強制上的諸問題——對中國草擬之中的行政強制法的借鑒意義》,載《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2003 年第3 期,第59~64 頁。類似的觀點還有向燕:《從隱私權角度論人身強制處分》,載《北方法學》2011 年第3 期,第100~108 頁;李升、莊田園:《德國行政強制執行的方式與程序介紹》,載《行政法學研究》2011 年第4 期,第129~138 頁;孫遠:《不強迫自證其罪條款之實質解釋論綱》,載《政法論壇》2016 年第2 期,第59~69 頁;洪家殷:《論行政調查中之行政強制行為》,載《行政法學研究》2015 年第3 期,第90~109 頁;劉磊:《強制拆除法律屬性二元論——以正在進行的違法建設切入》,載《東方法學》2014 年第5 期,第96~104 頁;史艷麗:《論行政即時強制的權力界限》,載《法學評論》2015 年第5 期,第42~49 頁。從法治的立場來看,“無損害亦無責任”,執法人員不能僅僅以有可能造成危害為由,限制個人自由,只有可能造成嚴重且即刻的危險的情況下,才能夠采取直接強制措施。②張明楷著:《刑法學(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 年版,第4~9 頁。下面要探討的是這種“無損害亦無責任”的觀點,它的倫理基礎是什么?
(二)三種倫理觀:德性論、道義論和功利主義
要談“無損害亦無責任”的倫理基礎,我們得先介紹三種典型的倫理觀:德性論(virtue ethics)、道義論(deontology)和結果主義(consequentialism)。
德性論是一種從個人主觀的善惡(德性)出發判斷其行為的對錯的倫理觀。動機是善良的,其行為就是對的,動機是邪惡的,其行為就是錯的。德性倫理學不僅是倫理學或道德哲學的術語,也應用在法學的領域。③Lawrence Solum、王凌皞:《美德法理學、新形式主義與法治——Lawrence Solum 教授訪談》,載《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10 年第1 期,第335~343 頁;吳冠軍:《認真對待德性:自由心證的法理學再探討》,載《探索與爭鳴》2015 年第5 期,第36~41 頁;童建軍:《當代西方德性法理學及其中國意義》,載《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4 期,第15~21 頁;謝小瑤、張城璐:《德性法理學視角下的法官義務》,載《法治社會》2021 年第4 期,第103~115 頁。道義論和結果主義與德性論不同,它們從客觀行為是否符合行為規則來確定行為的對錯,二者合稱“規范倫理學”。
分別來說,道義論源自康德哲學,也稱“義務論”,它以行為人是否遵循一定的義務來衡量其行為的對錯,這些義務可概括為三大原則,一是要符合“普遍化標準”,也即如果一個行為每個人都可以做,該行為就可以成為普遍的行為規則;二是要符合“目的公式”,也就是永遠將他人視為目的、而不僅僅是手段;三是遵循“自主原則”,就是尊重每個人的自主權或自由權。
結果主義最主要的代表是功利主義,典型學者是約翰·密爾(John Mill),它是根據某一行為可能產生的結果來判斷該行為的對錯的一種倫理理論。除了功利主義之外,利己主義也是結果主義的表現形式。
我們可以用美國政治哲學家桑德爾的話做一個總結:“迄今為止我們已經探索了三種公正進路:第一種認為公正意味著使功利或福利最大化——為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第二種認為公正意味著尊重人們選擇的自由——或者是人們在自由市場中所作出的實際選擇(如自由至上主義者們的觀點),或者是人們在平等的原初狀態中,所可能做出的假想的選擇(如平等主義者的觀點)。第三種進路認為,公正涉及培養德性和推理共同善。”④[美]邁克爾·桑德爾著:《公正:該如何做是好?》,朱慧玲譯,中信出版社2011 年版,第296 頁。桑德爾這里說的第一種是結果主義,第二種是道義論,第三種是德性論。
(三)懷疑論以道義論作為倫理基礎
說完三種基本的倫理觀,我們來探討懷疑論的倫理基礎。筆者認為懷疑論的倫理基礎是道義論(義務論)——重視普遍的規則、將他人視為目的、尊重他人的自由。更具體地說,道義論是18 世紀之后發展起來的,在此之前德性論是倫理學的主流。道義論尊崇實證的法律規則,嚴格區分法律和道德(美德),如同康德所說,“法律涉及人的意愿的外在表現,道德涉及到人的意愿的內在動機”;耶利內克(也是德國法學家)說得更通俗:法律是最低的道德,不能追求“倫理上的奢華”;①Roscoe Pound,Law and Mora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24,pp.103,107,110.
總之,道義論只要求最低的道德,而不奢望過高的道德。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認為:“法律如果被用作執行整個道德律,其代價是很昂貴的。”②Parsons,Legal Doctrine and Social Progress,1911,19.轉引自[美]羅斯科·龐德著:《法律與道德》,陳林林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 頁。以最低的道德來設定個人義務,個人權利就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所以道義論將“個人”(而不是集體)始終當作目的,而不是僅僅是手段,反對以犧牲個人(不管是生命還是財產),來達到保全他人、集體或者國家的目的。如前所述,突發事件應對懷疑論堅持“法無授權即禁止”,主張一切防控措施必須依據法律來落實,法律沒有規定的,政府就不能作為。很明顯它遵循的就是道義論。
正因如此,有學者主張從道義論推出公民針對疫情防控的容忍義務,是不嚴謹的。王春業教授根據現代法治的原理指出,當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發生沖突時,應該優先保護公共利益:“如果公共利益不存在,受損的不僅是大多數人的利益,也將使得公民個人利益不復存在。”③王春業、張玥:《論重大突發事件處置中公民的容忍義務》,載《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22 年第2 期,第75~84 頁。這種觀點的不當之處在于:
第一,從現代人權理論出發,當個人權利和公共利益發生沖突時,通常會“推定”(prima facie)個人權利優先于公共利益。④李延舜:《個人信息保護中的第三方當事人規則之反思》,載《法商研究》2022 年第4 期,第76~89 頁;[美]德沃金著:《認真對待權利》,信春鷹、吳玉章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年版,第256 頁;[英]約翰·密爾著:《論自由》,許保骙譯,商務印書館1959 年版,第1 頁、第112 頁。這種優先性也有人譯為“初顯優先性”。換句話說,除非存在適當的理由,個人權利不被剝奪,或者說“遇疑問時自由優先”(in dubio pro liberate),⑤[德]羅伯特·阿列克西著:《法、理性、商談》,朱光、雷磊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254 頁。“法無禁止即自由”就是這個道理。
第二,即便為了公共利益可以限制個人權利,在現代法治觀念下,這種限制必須遵循比例原則,特別要遵循必要性原則。如果國家機關能夠找到替代性的方案,能以更輕微的約束個人權利,甚至不約束人權的方式,達到行政管理的目的,就不能約束,或者過度限制個人權利。然而,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出現之后的短時間內,行政機關是很難切實地證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政策應對措施是必要的,也是最少限制個人權利的。因此依據比例原則,也不能直接推導出公共利益一定優于個人權利。
第三,按照行政法的基本原則,行政機關要限制個人權利,還必須遵守正當程序原則,也就是要向行政相對人說明理由,要聽取相對人的意見,要召開聽證會,還要告知相對人獲得救濟的渠道。而這些措施,在公共衛生事件突發的緊急關頭,是無法做到的。所以根據道義論以及基于道義論的現代法治理論,來思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措施,只能得出懷疑論的結論。那么主張公民具有容忍義務的觀點,其立論的基礎是什么呢?
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政策的德性論分析
筆者認為,主張嚴格防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學者的立論基礎是“應急法”原理,其倫理基礎是“德性論”。
(一)從“應急法”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
所謂“應急法”也稱緊急狀態法,它與“常態法”相對,是指社會整體面臨突如其來的攻擊或不確定和急劇擴張之風險時,為維護公共秩序和利益而采取的各種緊急措施。①鄭玉雙:《緊急狀態下的法治與社會正義》,載《中國法學》2021 年第2 期,第107~126 頁。“應急法”出現的原因主要是“現代風險社會的不確定性,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緊急狀態出現的頻率。”②金曉偉:《論我國緊急狀態法制的實現條件與路徑選擇——從反思“應急法”律體系切入》,載《政治與法律》2021 年第5 期,第123~135 頁。“應急法”的特征就是在應對緊急情況時,常常會采取一些非正常的手段,比如疫情防控中的強制隔離,關門閉戶,甚至全面封城等。
“應急法”的例證很多,如《突發事件應對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等。《突發事件應對法》第69 條第1 款規定:“發生特別重大突發事件,對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環境安全或者社會秩序構成重大威脅,采取本法和其他有關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應急處置措施不能消除或者有效控制、減輕其嚴重社會危害,需要進入緊急狀態的,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或者國務院依照憲法和其他有關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決定。”
“應急法”所采取的措施雖然激烈,但并不一定導致公權力的過度擴張。一方面,就像有學者指出的:“世界各國的經驗顯示,緊急狀態是相對而不是絕對的,其取決于每一個國家的緊急狀態法制實踐模式。如果緊急狀態能夠在短時間內成功地解決危機事件,一般不會導致緊急權力的過度膨脹。”③金曉偉:《論我國緊急狀態法制的實現條件與路徑選擇——從反思“應急法”律體系切入》,載《政治與法律》2021 年第5 期,第123~135 頁。另一方面,“應急法”強調社會控制和社會責任,對有危險的事物和人員予以事先的控制。④張明楷著:《刑法學(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 年版,第4~9 頁。它主張“社會本位”,社會利益優于個人利益,其更深層次的倫理基礎是德性論。
(二)“應急法”的倫理基礎——德性論
德性論是從個人品德(德性)和動機的好壞,來判斷其行為的對錯,而不是從行為的危害大小來判斷。德性論是古代社會的倫理學主流,比如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推崇的慷慨、勇敢、節制等德性,主張要符合中道,“過和不及”都不好。⑤魏奕昕:《亞里士多德論實踐智慧的統一和道德德性的統一》,載《哲學動態》2021 年第12 期,第96~104 頁。中國古代的孔子也類似,強調要愛人(仁者愛人),要幫助他人和寬容他人(“忠恕”),要“溫良恭儉讓”“仁義禮智信”。在德性論看來,善待他人、約束自己、利他主義就是美德,與此相悖的剝奪他人生命、健康、財產、名譽就是惡行。⑥Lon L.Fuller,The Morality of Law,New Haven,Connecticut,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pp.6-11.需要注意的是,根據美國學者布倫科特的分析,美德倫理學不僅是古代哲學和中世紀宗教社會所堅持的倫理學,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倫理基礎,馬克思反對剝削,譴責自私,批判資本主義將個人變為商品,把個人培養的技藝用金錢來標價,都是主張德性倫理學的體現。布倫科特還引用美國法學家富勒的觀點——道義論(或義務論)是一種資本主義的倫理,用以說明馬克思反對道義論,而主張德性論。George G.Brenkert,Marx’s Ethics of Freedom,Routledge&Kegan Paul,1983.p.263.
進入近代社會以后,德性論在18、19 世紀經歷過一段時間的衰微,這時候道義論和功利主義異軍突起。但從20 世紀中期開始,德性論又出現了復興的跡象,目前比較重要的學者有麥金泰爾、桑德爾等。⑦[美]邁克爾·桑德爾著:《民主的不滿》,曾紀茂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263 頁;杜宇鵬、李含陽:《道德的基礎何以可能——兼論麥金泰爾德性倫理思想》,載《黑龍江社會科學》2021 年第6 期,第21~29 頁。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作為規范倫理學的道義論和功利主義,只要求人們遵守最低的或最基礎的行為規范,不對個人的道德品行做評價,不給個人提更高的做人、做事標準。這導致社會責任缺失、道德水平下降、貧富分化嚴重、黃賭毒流行等問題。⑧[美]邁克爾·桑德爾著:《公正:該如何做是好?》,朱慧玲譯,中信出版社2011 年版,第301 頁。而德性論強調通過提升個人品德,增進人與人之間的團結,重新獲得了人們的關注。
在談及防疫政策時,有一些觀點主張發揚犧牲精神,希望人們迎難而上,沖鋒在前,這就是德性倫理學的典型表現。如果某人在疫情防控中,處處斤斤計較,一點不能吃虧,不服管理,四處閑逛,就會遭到人們的批評,被說成“利己主義者”。和道義論以制度和法律約束人不一樣,德性論希望靠批評反省、表揚嘉獎、激發責任感和歸屬感等形式,以名譽、責任、信任等機制,培養人們自我反省、追求完美、主動擔當的品德。①Irene Van Staveren, Beyond Utilitarianism and Deontology: Ethics in Economics,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9, 2007,p.21–35.
由此可見,以上人們針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政策的認識分歧,不僅源自法律理論的不同,也源自倫理基礎的差別,我們在制定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政策時需要審慎選擇。
四、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政策的德性論重構
關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政策的價值選擇,筆者認為我們應該回歸德性論,以德性論重構常態法,尊重國家的緊急權(“應急法”),兼顧公民個人的生命、健康和財產權。
(一)重拾德性論,賦予個人容忍義務
首先我們要探討為何要回歸德性論。關于德性論的重要性,有人提出它是中國的舊傳統,已被歷史證明沒有實際效果。②吳經熊著:《法律哲學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74 頁、第75 頁;孫笑俠、馮建鵬:《監督,能否與法治兼容——從法治立場來反思監督制度》,載《中國法學》2005 年第4 期,第13~24 頁。但是,倡導保持或回歸傳統的聲音也非常強烈。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國外。
在西方,在大部分歷史時期,德性論都占據著重要的位置。按照美國法理學家龐德的總結,西方法律史經歷了五個階段:原始法階段、嚴格法階段、衡平法和自然法階段、成熟法階段和法的社會化階段。原始法階段是指法律規范尚未分化,法律規范和其他社會規范(如道德教化)統合在一起,法律執行機構也沒有完全獨立的時期,這一時期當然是德性論的時代。嚴格法階段是形式化的法律規范和專門化的法律機構出現的時期,大致相當于公元前4 世紀的羅馬,12 世紀的歐洲和13 世紀英國。這一時期個人主義思想出現,法律更注重形式化,和道德嚴格區分。這是一種道義論的萌芽。
衡平法和自然法階段相當于公元3 世紀的羅馬,17、18 世紀的歐洲和英國。此時法律和道德又被等而視之,立法者努力將道德義務轉化為法律義務,執法者也依據理性而不是嚴格的規則裁判案件。這是德性論的復歸。成熟法階段則開始于19 世紀時期的歐美各國,法律更注重保護財產權和自由權(特別是契約自由),“努力從私法的每一項義務背后發現了相關聯的權利,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復到嚴格法所信奉的那些觀念上去了”。道義論又開始盛行。
最后是開始于20 世紀的法律社會化階段,該階段通過吸納各門社會科學的思想,揚棄了抽象財產權和契約自由,“從個人利益的方面轉到了社會利益”,將人人絕對平等的稅收,修改為按收入多少計算、比例逐級提高的累進稅。③[美]羅斯科·龐德著:《法理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年版,第370 頁。這又是德性論的體現。龐德寫作此書的時間是20 世紀初,20 世紀70 年代西方經濟自由化思潮再次勃興,注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觀念又開始主導了經濟、政治和法律領域,法律再次進入道義論和功利論為主流的階段。④[英]埃米利奧·卡內瓦利、安德烈·彼得森·伊斯特赫德、張金曦、劉明明:《社會主義的歸來?——關于當代經濟學的文獻綜述》,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2 年第5 期,第96~108 頁。
進入21 世紀之際,西方也有很大一批學者提倡反思現代,回歸傳統。比如前述的美國哲學家桑德爾。至于其原因,桑德爾在《公正:該如何做事好》一書中說:“隨著不平等的逐步加深,富人和窮人的生活會進一步分離。富人們將孩子送往私立學校(或者是在富裕郊區的公立學校),而將城市里的公立學校留給那些沒有其他選擇的家庭的孩子。類似的趨勢導致了那些由于其他公共制度和設施的特權而產生的分離。私人健康俱樂部代替了市政娛樂中心和游泳館;高檔住宅區雇傭私人保安,因而較少地依賴于公共警察的保護;人們所擁有的第二輛或第三輛車,消除了人們對公共交通工具的依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①[美]邁克爾·桑德爾著:《公正:該如何做是好?》,朱慧玲譯,中信出版社2011 年版,第301 頁。
以上是西方的情況。在中國,關于傳統的價值,歷史學家陳寅恪的觀點不斷被人引用,他認為無論外來思想如何強大,中國社會的思想主流仍將保持不變。②陳寅恪先生說:“竊遺中國自今日以來,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于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于歇絕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載陳寅恪著:《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寅恪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282~285 頁。最新研究可參見孟慶延:《思想、風俗與制度:陳寅恪史學研究的社會學意涵》,載《社會》2020 年第5 期,第34~62 頁。法學家蘇亦工最近也提出,西方法律關注“抽象個人”,把人看成“單純追求利益的動物”,而中國法律與中國文化關注的是“合乎最基本的倫理要求之人”。③蘇亦工:《辨正地認識“法治”的地位和作用》,載《山東社會科學》2015 年第12 期,第80~90 頁。當今中國面臨的社會危機,也為學者們批評道義論和功利主義提供了依據,比如貧富差距的加大,弱勢群體的邊緣化,社會上升通道的堵塞,以金錢來衡量一切的、精致的利己主義的思潮的泛濫,它們或多或少與市場經濟、功利主義或道義論有關。④王姝:《資本的精神向度追問——從<21 世紀資本論>談起》,載《學海》2015 年第4 期,第16~23 頁。方淩波:《糗文化與時代的精神隱疾》,載《探索與爭鳴》2014 年第12 期,第120~122 頁。
因此,從人類歷史來看,德性論已有幾千年(有文明記錄)的歷史,而道義論和功利論的盛行也不過幾百年,雙方并沒有絕對的上下尊卑。從道德直覺和事物本質來看,只有關心他人,約束自己,才能成為好的德性,僅僅為了個人利益采取行動,絕對算不上高尚。總之,強調道德修養、重視人與人之間團結的德性論,應該作為中國社會的立身之本。不過以上只是理念上的思考,具體的做法如何,下文再繼續展開。
(二)個人應該尊重國家的緊急權
具體說到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如果奉行德性論,我們要做的是當危機、不確定、非常狀態出現時,尊重國家根據“應急法”原理行使的緊急權,國家可以宣布某地區從常態法切換到緊急法,進入緊急狀態,實行封城、封戶、關閉工廠、暫停營業的措施。
關于這一點,有學者從權利限制的角度提出,公民應該“放長眼光,自我克減權利和自由”。⑤謝暉:《例外狀態令尊于法——世界各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令”的法哲學省思》,載《學術論壇》2021 年第3 期,第25~43 頁。也有學者認為由于信息不全、時間緊迫,我們不能苛求國家做出絕對正確的決定。⑥賓凱:《系統論觀察下的緊急權:例行化與決斷》,載《法學家》2021 年第4 期,第1~15 頁。還有學者盡管承認國家采取這些行為在法律上是有依據的,但對國家沒能根據法律規定,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提出批評。⑦劉小冰:《以緊急狀態法為重心的中國“應急法”制體系的整體重構》,載《行政法學研究》2021 年第2 期,第32~42 頁。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第43 條規定;“可以預警的自然災害、事故災難或者公共衛生事件即將發生或者發生的可能性增大時,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根據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規定的權限和程序,發布相應級別的警報,決定并宣布有關地區進入預警期……”。
以上這些觀點,是從法治的角度為國家緊急權提出的論證,在筆者看來,這么做還是不夠的,因為它仍然從個人權利的視角來考慮問題。筆者主張從個人德性論的立場考慮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政策。德性論主張關愛他人(仁者愛人),主張約束自己(懲忿窒欲),多一點付出,少一點索取(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以這一觀點看國家的法律和政策,就能滋生更多的敬畏之心、容忍之心。甚至在防控形勢緊張的時期,公民也有義務積極參與其中。對此《突發事件應對法》第49 條規定:“自然災害、事故災難或者公共衛生事件發生后,履行統一領導職責的人民政府可以采取下列一項或者多項應急處置措施:……(六)組織公民參加應急救援和處置工作,要求具有特定專長的人員提供服務”。參與防控的人多了,就不會出現食品短缺、物價飛漲的情形。
(三)國家應給公民提供盡可能的保障和補償
不過反過來,作為國家,在制定和執行疫情防控政策時,根據德性倫理學的要求,也應該盡力保護個人的生命、尊嚴和財產。
首先,在封控區要保證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在公民遭遇生命危險(比如遭遇嚴重疾病、生命垂危)時,應該盡力安排救助。德性論的經典《中庸》對治國提出如下要求:“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大意是大凡治理天下國家有九條常規:努力提高自身的品德修養,尊重賢人,愛護自己的親人,敬重大臣,體恤眾臣,像愛自己的兒子那樣去愛人民,招集各種工匠以資國用,優待遠方的來客,安撫四方的諸侯。“像對待家人一樣愛護人民”,國家就應該為人民群眾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不讓人民群眾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忍饑挨餓。
其次,盡管每個公民面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具有容忍義務,在遇到公民個人(非傳染病人)不遵守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措施的情況時,即便在封控區,也應該采取說服、教育、警告、罰款等間接強制措施,敦促其遵守法律規定,而不該直接采取扣押財物、“封門落鎖”,甚至羈押等直接強制措施。
最后,我們對在疫情中犧牲生命、損失財產的人,應該盡量給予補償。這不僅是法律規范的要求,也是德性倫理的期待。從法律規范來看,《突發事件應對法》第61 條規定:“受突發事件影響地區的人民政府應當根據本地區遭受損失的情況,制定救助、補償、撫慰、撫恤、安置等善后工作計劃并組織實施,妥善解決因處置突發事件引發的矛盾和糾紛。”從德性倫理來看,濟弱扶傾是值得贊揚的美德,所以對于那些遭受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沖擊,生活窘迫的家庭,我們當然應該給予補貼,幫他們度過難關。
以上本文談到了針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的兩種迥異的態度。這兩種態度可以歸結為常態法和應急法,其背后的倫理基礎是道義論和德性論。前者主張個人利益優先,國家、集體應該為個人服務,后者主張集體利益、國家利益更高,個人要為共同體做犧牲。鑒于中國獨特的歷史傳統和西方國家治理的弊病,我們應該秉持德性論,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嚴重威脅大多數人的安全時,作為個人應該尊重國家行使緊急權,采取隔離封城等嚴格的防控措施。作為國家也應該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盡力保障公民的生命、尊嚴和財產,盡量使用說服、教育、警告、罰款等間接強制措施,而少用扣押財物、“封門落鎖”等直接強制措施。此外國家還可以依法征調公民參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緩解防控人手不足的問題,并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中犧牲或受損失的人給予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