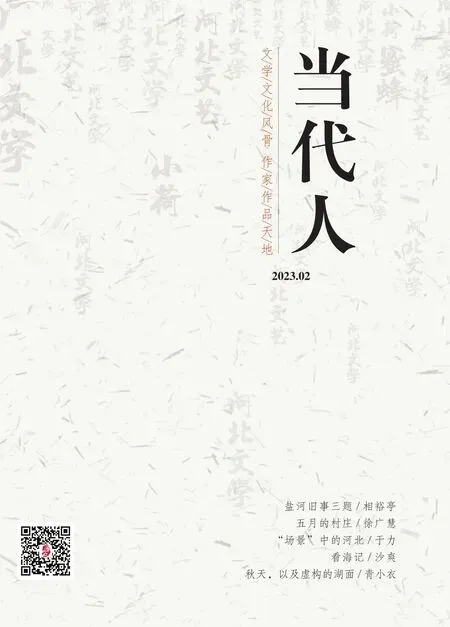鹽河舊事三題
◇相裕亭
壓臺
也是朋友介紹來的,說是鹽業行里有位小業主畫畫得不錯,手頭已經畫了一些了,想請郝逸之郝先生費費神,幫忙給指點指點。
郝先生礙于朋友的情面,說:“行呀,行呀!”
過了幾天,那位朋友真的就領上那位小業主來了。進門,對方提了煙酒糖茶四色禮盒,儼然一副拜師學藝的樣子。同時,對方也帶來了一些他前期的畫作。郝先生展開來看了兩幅,點頭說:“不錯,不錯!”
其實,對方那些草畫在郝先生眼里,哪能稱得上是不錯,頂上天,也就是個人喜好,涂鴉罷了。
不過,那人倒是挺虔誠的,一口一個郝老師地叫著。他站在郝先生跟前,一直是手足無措的樣子,臉上還不時地堆著拘謹的微笑。
郝先生從那人的穿戴與長相上看,對方經銷鹽的買賣應該是做得不錯的,左手中指上的那枚“黃箍子”(金戒指),足有女人家的頂針那樣寬大。再者,那男人才三十幾歲,衣衫下的“鍋肚”都已經吃出來了。想必,他近幾年的生意,做得風生水起。
初次相見,因為中間“搭橋”的朋友急著要去辦理別的什么事情,學畫的那人與郝先生沒說上幾句話,也就一起告辭了。
事后,那人主動邀請郝先生到附近一家酒樓去坐坐。
郝先生說:“不用,不用,你好好畫畫就行了!”
在郝先生看來,但凡找上門來跟他學畫的人,都是奔著畫畫來的,無需多余的客套。他們只要把筆下的畫畫好了,比請他吃猴頭、燕窩都令他高興。
郝先生的名頭擺在那兒,見天想請他吃飯、謀他畫作的人不是一個兩個,他能推辭的,盡量都婉言推辭了。
郝先生是鹽區這邊土生土長的畫家。年輕的時候,他想天想地的做過許多事情。有一段時間,他也曾跟著人家,依托本地的鹽田,倒騰過一陣鹽的買賣。后來受小學同窗沈達霖的影響,想往仕途上靠,最終還是沉下心來畫畫了。當然,這其中,那位在京城為官的同窗沈達霖幫了他一把,協助他在天津衛開了一家頗具規模的畫店。那段時期,津門一帶,包括京城里的達官顯貴,知道郵傳部的侍郎沈達霖喜歡他郝逸之的畫,都不惜重金,前來購買。后來,沈達霖客死于天津衛的法租界,郝逸之也就知趣地回到鹽區來了。
鹽區人包容著郝先生,同時也認可他筆下那些“鹽河小漁船”的畫。曾有那么一段時期,鹽區這邊許多官宦人家,包括鹽河兩岸的茶肆,酒樓,以及鹽區的沈家、謝家、吳家等幾家高門大戶,都掛著他郝先生的畫。鹽業行里的那位小業主,就是選在那個時候,登門拜見郝先生的。
怎么說郝先生還是個文人,他身上的文雅之氣沒有丟。即便后來他答應了對方的邀約,也沒有忘記讓人家節省一點,一再提醒對方:“你找個小地方,我們坐下來說說話就可以了。”目的,還是不想讓對方過于破費了。
可真到了郝先生前去赴約的那天傍晚,他想到前幾日那人登門時所帶的禮物過于厚重,隨手在畫案上摸過一盒印泥,想在酒桌上當作禮物回敬給對方。
那印泥,是郝先生自己用陳年的蓖麻油、松子、艾草絨、朱砂等糅合碾制的,比那人扣在宣紙上的“紅印子”強多了。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講,對方想學畫,郝先生回敬他一盒印泥,這也是對他的鞭策與鼓勵。郝先生甚至想到,酒桌上他還可以向對方傳授一些畫畫方面的技巧。譬如構圖中的留白,以及筆墨濃淡的應用。所以,郝先生在對方為他安排酒局時,順口示意了一句,說:“酒桌上的人不要太多。”
郝先生想利用酒桌上的時機,與對方好好說說畫畫的事兒,也不枉人家專門請了他一場。酒場嘛,兩三個人,可以談事兒,上至八九個人,那就是喝酒、鬧酒了。
可對方覺得郝先生的身份不一般,應該找一個有身份的人來與他對等作陪。否則,對郝先生也顯得不夠尊重。
那么,請誰呢?請什么人來能壓得住當晚酒宴的臺面兒呢?思來想去,那位“高徒”想到了鹽政司的潘向余潘課長(科長)。
潘課長是鹽區鹽業行里的老大,他手中掌管著銷鹽走鹽的“鹽引”(鹽票)。學畫的那位小業主,每過一段時間,都要從他手中討得一些“鹽引”,方能購得官方白花花的海鹽。此番,請潘課長來作陪,一則是他的身份在那兒,可以與郝先生平起平坐;再者,還可以通過酒場,加深一下他與潘課長業務上的情感。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請他來支撐門面,給郝先生臉上好看的同時,也可以讓郝先生了解一下他與鹽政司里上層長官的關系。另外,那位小業主還邀約了幾位鹽業界的同行,也都是平時圍候在潘向余身邊討“鹽引”的大小業主們。這里面,無非是他平時吃了人家的酒席,借這個機會再返請人家一場。當然,這樣的場合,還可以抬升他自己在同行當中的地位,長長自己的臉面呢。
郝先生不知道對方是怎樣安排的,他只是掐著相約的日期,踩著點兒趕到對方說給他的那家酒樓。
進門一看,一屋子人正圍在酒桌旁邊的一張小方桌上打牌。學畫的那位業主見到郝先生推門進來了,下意識地把手中的牌舉起來,連聲叫著:“郝老師,郝老師,你過來打把牌!”
郝先生連連擺手,一面解釋說:“你們打,我不擅長那個。”
對方見郝先生不入牌局,便把手中的牌轉給旁邊一位相眼的(觀牌者),就手推開跟前兩三把擋著他道兒的座椅,走到郝先生跟前,說:“潘課長馬上過來!”并說,等潘課長一到就開席。
郝先生嘴上說好好好,心里邊卻在思量,今天這飯局,怎么還請到了潘課長呢?敢情對方不是為著畫畫來的。郝先生甚至想,早知道這樣,他可能就改變主意了。當然,那種想法,只是在郝先生的心中一閃,很快也就過去了。飯局嘛,什么人做東,請到什么人,那都是東家的事情。這個道理,郝先生還是懂得的。
還好,時候不大,潘課長來了。潘課長事先可能知道當晚要請的貴賓是畫家郝逸之。一見面,打老遠就把手伸過來了。郝先生之前與潘課長打過交道,準確地說,是潘課長向郝先生討過畫。所以,此番兩個人見面,顯得可親熱呢。
潘課長一面與郝先生寒暄,一面介紹他身邊帶過來的兩位隨從,說:“這是我們課里的兩位筆桿子!”言下之意,他們與郝逸之一樣,都是文化人,甚至可以理解為,那兩位文化人正好與郝逸之有共同語言,可以聊得來。其實,他們是鹽政司里寫公文、記賬本的,與他一個畫畫的,風馬牛不相及呢。
但郝逸之還是滿臉堆笑,與大伙兒一一握手言歡。
回頭,酒桌上落座時,潘課長很自然地站在主陪的位置上,他拉開了座椅,并沒有立刻坐下,而是禮節性地示意郝逸之,說:“老郝,你過來呀!”
郝先生連連拱手,說:“豈敢!豈敢!”他示意潘課長:“你請!你請!”
潘課長也就沒有再推辭。
酒宴開始以后,大家相互介紹,郝先生還真是被大伙兒捧為當天晚上的座上賓,尤其是說到郝先生是大畫家時,大家都投來敬仰的目光,再聯系到他們業界內的那位同行,也就是當晚請酒的那位“高徒”,將要跟著郝先生學畫,都說他遇上高人了。
那一刻,郝先生的臉上,真像是貼了金一樣,笑容可掬,閃閃發光。
然而,兩杯酒下肚以后,大家的話題,或者說是注意力,不經意間都轉向了那位掌管“鹽引”的潘向余潘課長身上。一個個爭先恐后地向潘課長敬酒。以至于飯局中場時,郝先生起身去了趟廁所,離席有大半天,大伙兒竟然沒有察覺到他不在酒桌上。
是夜,曲終人散,郝先生獨自走到家門口的水塘那兒,忽而摸到衣兜里裝有一個硬物兒,那是準備送給他那位“高徒”的印泥。略帶醉態的郝先生捏在手上把玩片刻,忽而,胳膊一抬,當作石子瓦片一樣,“唰”的一下,給“嘣嘣嘣”地撇進月光盈盈的水塘里了。
斷情
富貴是個養路工。他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他分管的那一段沿著海岸線延伸過來的沙塘路養護好。海邊的人拉大柴、拖海貝、運石料,稍不留神就會把車上的貨物散落到路面上。那樣的時候,富貴就要及時清除掉;再者,海潮異常涌來時沖垮了路基,或是暴雨過后路面上汪了水,他要弄些石料與黃沙土來修整。天氣晴好時,他還會舞弄一把橡膠皮鑲牙口的木爬犁,把滑到馬路邊沿上的黃沙,“稀唰稀唰”地推到馬路中間的跑車道上去。

富貴彎下腰來,舞弄他手中那把“豬八戒式”的橡膠皮爬犁時,如同人們在打谷場上翻弄稻谷、麥粒一樣。看到有顆粒大一些的石子兒,他要撿起來扔到路邊水溝里去,或是直接用那爬犁角“剜”起來,甩到一邊。
公路邊上,每隔一段距離,就會有一小堆黃沙土,尖尖圓圓地堆在那兒,都是富貴平時預備好了,專門用來鋪墊路面的。
富貴養護的那段路面,前后有三四公里長。他每天要在那段路上來回走三四趟。往往是,去的時候走馬路那邊,回來的時候走馬路這邊。看到哪個地方不平整,他就會停下來,鏟一些黃沙土來鋪墊一下,以備后面的車輛過來了,能夠平穩地通過。
這條公路,是汾水(今日嵐山)到新浦的。其實,更應該說它是從青島延伸過來的,或者說路的兩端還延伸到很遙遠的地方呢。但富貴不知道那些。富貴只知道,每天清晨會有一輛綠頭白腚的破舊客車,從汾水那邊“哈啦哈啦”地開過來,開到鹽區小碼頭停一下,然后,鳴一聲喇叭,揚起一片塵土,便很高傲的樣子,頭都不回地奔新浦方向去了。
早年間,這條公路是小日本用來跑車的。日本投降以后,地方上沿用了日本人用過的公路,并在沿路各村招募養路工。富貴就是在那個時候被招去做養路工的。
當時,村里的干部找到富貴時,并沒有直接跟他說叫他去做養路工,而是拐了一個彎子,問他:“富貴,你想不想去住瓦房?”
富貴嚇了一跳,認為要送他去“坐局子”呢。
剛解放那會兒,鹽區這邊草房子多、瓦房少,誰做了什么違法的事情,被送去“坐局”了,人們往往會變相地說某某某去住瓦房了。富貴呢,想了想自己沒做什么違法的事情呀,他瞪大了眼睛,疑惑地望著村里干部,問:“嘛?”
村里的干部知道富貴想到了“坐局子”那一層,這才笑了一下,跟他說養護公路的事情。
富貴一下子就明白了,人家要派他去養護公路呢。當年,每隔一段距離,小日本就在路邊蓋兩間青磚紅瓦的小房子,專門提供給那些看管公路的人居住。眼下,那房子還在。富貴去養護公路的同時,自然也要把那房屋接管過來。
現在想來,富貴當初去養護公路的時間,大致應該是在1948年前后。
當時,蘇北、魯東南一帶已經解放了。上級正在招募各類有專長、有文化的人才。其中就有養路工。當然,養路工算不上什么人才,只要身體好,懂得愛護公共財產。具體一點說,能夠把自己分管的那段公路養護好就行。
當時的養路工不是什么好職業。甚至有人認為那是個吃灰塵的行當。每天守在馬路邊,車輛“嗚”的一聲開過去,揚起一團灰塵,如同漁夫們在河溝里捕捉魚蝦時撒開的旋網子,瞬間就把路兩邊的行人給罩住了,可臟的!
再者,富貴剛被派去做養路工時,村上只給他一點有限的生活補貼,僅夠他一個人開銷。好在富貴是個光棍漢,他不在乎那些。只要他一個人吃飽了,全家都不餓了。可后來,養路工被上面收編了,統一吃上了國家的統銷糧,富貴他們那個職業,變成了人們羨慕的行當。只可惜,那個時候,富貴快五十歲了,他已經過了大姑娘小媳婦愛慕的年紀。
其間,有人跟他開玩笑,說:“這下,富貴可以娶個老婆嘍!”
富貴笑,富貴覺得眼前的好事兒來得太晚了。若是早二十年,或者說早十年,他或許真的能娶個黃花大姑娘呢。眼下,黃土都埋到脖子了,他哪里還有那樣花花道道的心思。富貴倒是覺得,以后,他每月領到工資后,該接濟一下二弟他們一家子了。
富貴的二弟身體不是太好。他闖過東北,在東北那白山黑水的地方折騰了幾年,把自個兒的身體給糟蹋壞了。
早年間,鹽區這邊好多男人在家吃不上飯,或者是討不上老婆時,就到東北去闖蕩幾年。趕到某一年春節前回來時,頭上戴頂三面狍子皮的坦克帽,肩上披一件雙排扣的毛領子短大衣,便會撩得前后村里的大姑娘們心里毛毛的。
富貴的二弟就是那樣討上老婆的。只可惜,富貴的二弟沒有與他媳婦過上幾年好日月。
富貴的二弟是個病秧子,整天就像只小瘟雞似的蔫頭搭腦的沒有精神。現在想來,他那毛病應該是糖尿病。你想嘛,他一個大男人,不頭疼,也不發燒,就是渾身上下沒有力氣。就那,他還折騰了十幾年,直至把他女人拖累到沒有姿色了,他也撒手西去了。
好在,那時候他兒子大毛子已經長大。
在那期間,也就是富貴的二弟死了以后,村里有好心人想撮合富貴與他弟媳婦到一起去。
那樣的事情——兄弟媳婦改嫁給自己的小叔子,或是大伯子與弟媳婦另起鍋灶過日月,至今都不算什么丟人的事情。甚至還會有人說,那是肥水沒流外人田呢!
富貴呢,剛開始他沒有往那方面想,總覺得自己的兄弟走了,他要把自家的侄子拉扯成人。可經旁人一蠱惑,他還真是動了心思。晚間睡覺時,他望著窗外的月亮在那兒胡思亂想:若真是讓他和弟媳婦拾掇到一起去,除了他年齡上與弟媳婦懸殊一些,其他方面都沒有什么。富貴甚至覺得,若是弟媳婦愿意,他們倆人還能生個一男半女呢。那樣的話,他富貴也可以留下自己的后人啦。
話再說回來,如果富貴不把他弟媳婦娶過來,萬一哪一天,弟媳婦再另嫁他人呢?到那時,他富貴豈不是傻了眼!與其讓別人把弟媳婦娶了去,還不如他這個做大伯子的把弟媳婦攬到懷里。有了這樣的想法,富貴去弟媳婦家的次數就勤了。
“缸里的水夠不夠多?”
“南園上的蘿卜是不是該澆些尿水了?”
“三奎家二玲子有了日子(要結婚了),大毛子去送喜禮時,也給我帶上一份子吧。”富貴說那話時,往往連弟媳婦家的喜禮錢也給墊上了。
那一陣子,富貴的鞋子擦亮了,衣服也穿得整潔了,頭發上好像還抿了些滑溜溜的水花呢。弟媳婦看到了,心里自然也就明白了大伯子的心思。
但是,富貴沒有料到,他心里企盼的事情,卻遭到了大侄子的反對。
那天傍晚,富貴委托西街的二大娘上門去說合時,被大毛子聽到了。確切地說,在這之前,大毛子已經在外面聽到了一些風言風雨,心里正憋著一股火呢!他很難接受大伯與他媽媽睡在同一張床上。所以,當二大娘在小院里與大毛子媽說起那件事情時,大毛子先是把小里間的木門摜得“咣當”一聲山響。隨后,他飛起一腳,把門口正在地上尋食吃的小花狗給踢到門外去,還連聲喝斥那只無辜的小花狗:“滾,你給我滾!”
大毛子那話,顯然不是在罵狗,他就是罵那個多嘴的二大娘呢。
二大娘賺了個無趣,回過頭來與富貴回話時,說到大毛子罵她時的那個場景,委屈得眼淚都快落下來了。
富貴當著二大娘的面兒,牙根兒咬得吱吱響,他罵大毛子是個王八蛋、白眼狼!富貴覺得,這些年來,他對大毛子真是白疼了,那小王八犢子,一點都不懂事兒。
大毛子媽看兒子不高興,心里剛剛燃起的那點微弱的欲火,很快也就熄滅了。尤其是想到,兒子馬上也到了提親的年齡,她咬咬牙,也就不往那方面想了。
但,富貴的心里好像還在想著那件事兒。他曾幾次想與大毛子單獨談一談,可大毛子始終躲著他。
這期間,富貴到弟媳婦家又去了幾趟。不是大毛子不搭理他,就是弟媳婦看他來了,趕忙借故說到鄰居家有個事情——不待見他。弄得富貴很尷尬,也很沒有臉面。
自那以后,富貴就不好再到弟媳婦家去了。但富貴心中的欲火還在燃燒。況且,欲火燃燒得越旺,他越忌恨大毛子那個狗東西。
某一天,大毛子如同往常那樣,在公路邊的樹叢里割青草,富貴尋查路面時,看到大毛子的草筐放在路邊上,他不但沒有停下來幫大侄子薅青草,反而拿出他守護公路的派頭來,揚起手中的鐵锨,一下子就把大毛子那草筐給挑到路邊水溝里了,口中還惡狠狠地罵道:“去你媽的!”
大毛子當然知道大伯那是罵他的。但他沒有吭聲。
在鹽區,小叔罵哥嫂家的侄子,不算什么事情。可做大伯的,可謂是長兄如父,萬萬不能罵弟弟家的子女。這在鹽區是幾十年、上百年不變的理兒。一旦大伯罵了弟弟家的孩子,那就是切骨之痛,或者說會結下深仇大恨。
可當天,富貴偏偏就不顧后果那樣罵了大毛子。
大毛子沒有回話,他起身揚起手中的鐮刀,“喳”的一下,削斷一棵拇指粗的小樹,連那草筐也不要了,鼓著嘴兒,轉身走了。
自此,大毛子與他大伯不相來往了。后來,大毛子娶親,都沒有給他大伯送一支喜煙、一塊喜糖。
一晃,又是幾年的光景過去了。
富貴一天天老了,身體也一天不如一天。先前,富貴手頭有了錢就去買燒餅、下館子。而今,他手中握著錢,卻盡往藥鋪里去尋摸吃什么藥物呢。
大毛子知道他大伯生病了,可他裝作什么都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有人來告訴大毛子,說他大伯在那小屋里吊死了,大毛子這才不得不去料理富貴的后事。
有人告訴大毛子,說他大伯養護公路那么多年,每個月上級都給他發工資,他手頭應該是有一些余錢的,讓大毛子在大伯那小屋里各處翻翻找找。
可就在大毛子床上床下左右翻找時,院子里忽而有人喊他,說:“別找啦,你大伯的錢都在這里呢!”
喊話的那人,撥弄著當院里一堆沒有燃盡的紙灰錢角,對大毛子說:“你看看,這些都是錢,都是沒有燃盡的錢。”
原來,富貴在臨死前,把他這些年所積攢下的錢,一把火都燒了。
老湯
王緒德是個廚子。
早年間,他在地主張康家做飯,跟后廚一個淘米、擇菜的俏婆子好上了。他屋里的婆娘知道以后,一氣之下,上吊死了。這件事,應該說把王緒德的名聲弄得很不好。等他想續弦,好多女人都覺得他是那樣的人,不去挨他。
不過,王緒德那人做飯還是挺好的。他在張康家做廚子時,能把張康家那么一大家子人的口味都給調當好。老爺、太太喜吃軟的、清淡的,少奶奶、大公子要吃油頭足的肉塊兒、魚段兒,王緒德都有辦法讓他們吃出歡喜來。張康家的小少爺不吃辣椒。可海邊人做魚時,必須用紅辣椒來熗鍋,外加蔥、姜、蒜、花椒、大料所爆開的熱油汆湯方可除去魚腥味兒。小少爺眼睛尖,一看到燒好的魚段中放了紅丟丟的辣椒,他立馬就會把小手中的筷子給扔到桌子上,嘟囔起喇叭花一樣的小嘴巴,連聲嚷嚷:“有辣椒,有辣椒。我不吃!我不吃!”
王緒德考慮到張家老少幾代人的口味,再做魚時,干脆就在紅辣椒上扎上密密麻麻的針眼兒,將其放進咕嘟嘟的魚鍋中,待它的辣味在魚湯中完全釋放出來以后,就手把那蒸煮得紅塌塌的辣椒皮從魚鍋里撈出來扔掉。
那樣,小少爺看不到盤中有辣椒,他也就不再叫喚那魚是辣的了。小孩子嘛,眼睛看不到,他就認為不存在的。
這件事,王緒德當漢書(教科書)一樣,掛在嘴邊講了不少年。
后來,鹽區這邊解放了。王緒德便在鄉間紅白事上掌大勺——做大廚。
吃過王緒德做的飯菜的人,都說他燒出來的飯菜味道好。跟在他身邊剁肉、洗菜、打下手的人,都知道王緒德燒菜,離不開一勺老湯。
其實,王緒德那是糊弄人的。王緒德到人家里去做事(掌大勺)時,每回都要自帶一個狗頭大的小瓷罐。那小瓷罐上方,有一個烏釉發亮、四眼相通的小蓋兒。王緒德說那里面裝著他自己調制好的老湯。每道菜要出鍋時,他都要從那小瓷罐里舀一點老湯澆在菜里來提鮮。
外人不懂他那老湯是怎么配制的,可與他搭檔的支客,心里跟明鏡似的。
支客,就是戶主家找來掂量買菜、待客的司儀。他與大廚是互相協作的關系。支客在分配主人家煙卷時,往往會多塞一包給大廚。大廚呢,等晚間客人們都打發走了,會切一點拱嘴(豬嘴唇),留一點海蜇皮與支客圍在鍋臺邊喝兩盅,招惹得附近幾條街上的狗,都嗅著味道跑到他們倆跟前打轉兒。
鹽區這邊,一般人家辦喪事或婚事,大都要提前一天或兩三天,把支客和掌勺的大廚叫去商量購菜、待客的事。同時,還要掂量著在戶主家的院子里,支起一溜兒鍋臺——搭起一個簡易的臨時廚房。
支鍋臺時,當地人講究一個單數。可以支一口鍋、三口鍋或五口鍋。不能支兩口鍋、四口鍋。這道理源于夫妻間“一個鍋里摸勺子”。大概的意思,是講究一家人團團圓圓地生活在一起。若是支兩口鍋、四口鍋,那樣將意味著各吃各的,不吉利。可有的小戶人家辦喪事或婚事,支兩口鍋(一個鍋里蒸飯,一個鍋里熬菜)也就湊合啦,沒有必要真去拉開架勢,支上三口鍋或五口鍋。遇到那樣的人家,王緒德往往會把他自家的一口小耳鍋拎來,在頭鍋和二鍋的煙道口那兒,挖一個臉盆大的“煙灶”,將那口小耳鍋支在那兒,里面可以溫菜,也可以用來燒水,最為關鍵的是,那樣可以表示主人家起用了三口鍋呢。
一般在支鍋臺的時候,支客先要問一下主家有多少客人,需要辦一個什么樣的場子——魚肉到碗底兒,還是用白菜、豆腐來待客。王緒德聽支客與主家談論那些時,他心里盤算的卻是那肉魚該剁成多大的塊兒,才能均勻地盛到每一只碗里。時而,他也會咂摸一下嘴兒,似乎是說,主家報出那么多的客人,卻計劃買來那么一點肉魚,只怕是碗里盛不著呀!
但那話,王緒德一般不會說出口。他知道,但凡是碗里盛不上多少葷菜的人家,都是家里很窮困的。那樣的時候,他心里就會幫助主家思量,是用白菜、蘿卜墊碗底兒,還是用肉湯滾過的粉條子來墊碗底兒。
末了,等支客與戶主把待客的葷菜、素菜都商定好了以后,王緒德總是會跟支客說:“再稱兩斤小白蝦吧!”
王緒德所說的“小白蝦”,鹽區四季都有。
那種蝦,個頭不大,頭尾對接著圈成一團,也不過就是成年人的指甲蓋那樣大。但它的味道非常鮮美,尤其是它的湯汁,奇鮮。
王緒德要買它,是想用它來調制老湯。他把那小白蝦搗爛,稍加清水,煮出清香的鮮湯后,再用大油(豬油)熗鍋,蔥、姜、蒜爆香熱油以后,倒入之前篳出來的蝦湯,加鹽,調制成鮮香的鹽鹵。然后,小心翼翼地將那鮮香的鹽鹵,裝進他那個小瓷罐里,等熱菜出鍋前,澆上一點,那菜的味道瞬間就不一樣了。
有人說王緒德那瓷罐里裝的是老湯,這也是有道理的。譬如他頭一天在一戶人家做事,想到第二天或是第三天,還要到另外一戶相對較為窮困的人家去做事,他在調制湯鹵時,干脆就多熬制一些,帶到下一家去,為那戶人家節省一點開銷。不過,那樣的時候,他那瓷罐中也會藏一些肉塊、魚段兒帶回家自己享用呢。
王緒德作為掌勺的大廚子,他以老湯的名義,帶來那個小瓷罐和帶走那個小瓷罐,又有誰會去跟他計較呢。大家只覺得他裝老湯的那個小瓷罐還有他手中那兩把亮閃閃的刀具怪神秘的。
王緒德使用的刀具,包括他手中帶眼的勺子(漏勺),以及他叉肉、挑雞時所用的那把鴨嘴樣寬的小鐵叉子,都是他自己帶來的。他的刀具很快,向來都是東街喬鎖匠幫他磨的。
鹽區這地方,殺豬、宰羊的屠戶,大都會劁小豬、摘羊凹腰;扎紙把子(紙人紙馬)的篾匠,個個都會幫著吹鼓手們打大鼓、敲小鑼子。而東街的喬鎖匠,原本就是個修鎖配鑰匙、鼓弄手電筒的,可他偏偏還會戧剪子、磨菜刀。
王緒德每回去找喬鎖匠磨菜刀,他都要揣兩包上好的香煙給喬鎖匠。喬鎖匠從不當著王緒德的面兒給他磨刀。有時,王緒德來磨刀,恰逢喬鎖匠閑著沒事,倆人便扯一些閑話,直等到王緒德起身走了以后,喬鎖匠再把那磨刀石翻過來,給王緒德磨他那兩把硬度極高的刀。這里面的道理,說破了也很簡單,如果用磨刀石的正面(帶“馬鞍腰”)來磨王緒德那兩把寬大的刀,磨著磨著,刀口的刃子就磨卷了。只有放平了磨刀石,才能磨好。這也是喬鎖匠自個兒摸索出來的經驗。
可這一天,王緒德又來磨刀,他好像要等著喬鎖匠給他當面磨好呢,與喬鎖匠閑扯了半天也不肯離去。末了,王緒德好像忽然間想起什么事似的,問喬鎖匠:“大得子媽呢?”
喬鎖匠略頓一下,說:“去西巷三華家了。”
大得子,是喬鎖匠的兒子。人們稱呼喬鎖匠的婆娘,都是稱呼“大得子媽”。
王緒德問:“她多會兒能回來?”
喬鎖匠“嘛”了一聲,問王緒德:“你有事呀?”
王緒德磨嘰了一下,說他前些天,在西莊一戶人家做事,看到那戶人家的男人死后,撇下個俊巴巴的小媳婦,他想托大得子媽去幫他說合一下看看。
在這之前,王緒德早已經打聽到大得子媽的娘家是西莊的。
喬鎖匠疑疑惑惑地問王緒德:“你覺得行嗎?”
王緒德說:“叫大得子媽去跟人家好好說說。”
說那話的時候,王緒德又從懷里掏出三五包上好的香煙塞給喬鎖匠。
喬鎖匠嘴上說有啦有啦,可他看到王緒德這回掏出來的香煙,都是帶牌子的好煙,便說:“回頭,大得子媽回來,我讓她去給你好好說說看。”
王緒德滿心歡喜地回去了。
過了兩天,王緒德來取刀具時問喬鎖匠結果。
沒料想,大得子媽給他的回話是,人家那小寡婦不愿意跟他一個做飯的廚子。當然,大得子媽的原話不是那樣說的,可意思就是那個意思,弄得王緒德碰了一鼻子灰。
時隔不久,王緒德不知從哪里打聽來實情,說是大得子媽當初去幫他撮合那件事情時,不但沒有說他王緒德半句好話,反而把他過去的一些老底都給翻弄出來了——壞了王緒德的好事。
原因是,大得子媽自個兒的作風不是太好,她擔心娘家那邊的那個小寡婦若是嫁給了王緒德,以后她在這邊一些不好的傳聞,沒準兒就會傳到她娘家那邊去。
但大得子媽沒有料到的是,王緒德那人是個小心眼子,人家沒有把他想的那件事情給辦成,他竟然連刀具也不找喬鎖匠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