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美林:用古文字釋放中國文化能量
張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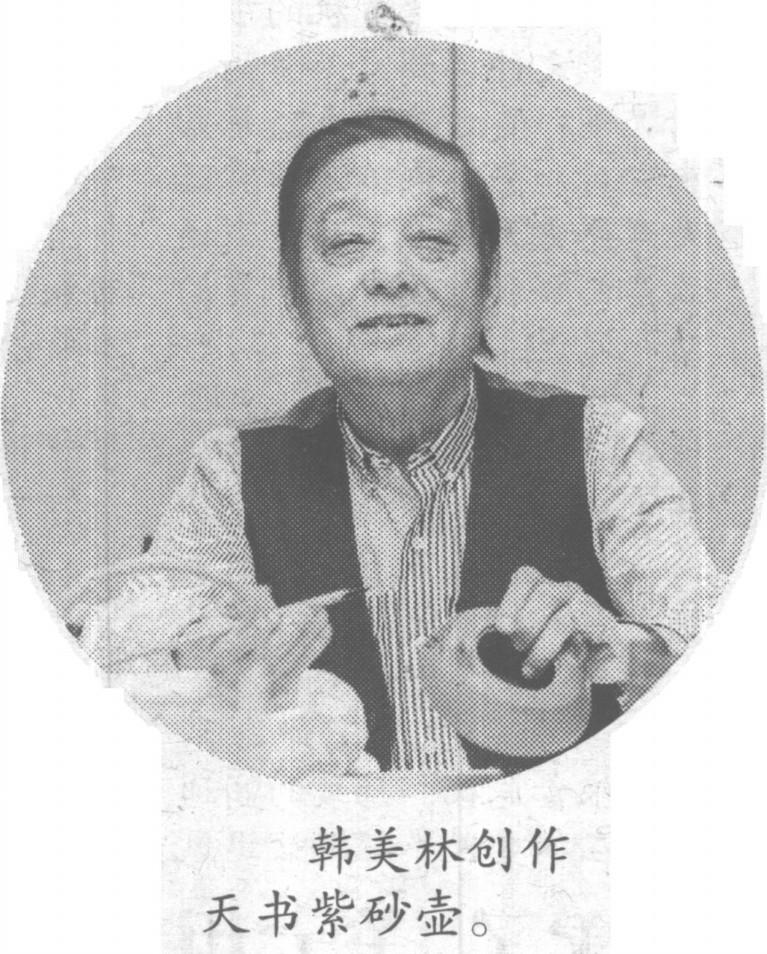

似乎是一種來自遠古的宇宙原始能量,在混沌中生發(fā),慢慢生長出蜿蜒的線條,萬物由此而生。它們時而享受生命的恬淡美好,時而與命運的苦厄激烈抗爭,很多聲音出現(xiàn)又消失,來去無蹤,神秘莫測……前不久,這首特殊的管弦交響樂《遠渡》在國家大劇院舉行首演,引發(fā)文化界關注。其特殊之處不僅在于神秘、原始的意境,還在于,它的創(chuàng)作靈感來自著名藝術家韓美林的書法作品《天書》。首演的最后一個音符落下后,作曲家姚晨與韓美林攜手登上舞臺。他們的合作成為又一令人矚目的“藝術融通”文化事件。去年,將傳世繪畫《千里江山圖》化身舞蹈的《只此青綠》以“舞繪融通”的全新方式重現(xiàn)中華傳統(tǒng)美學。“不同的藝術再不聯(lián)合就跟不上這個時代了”。韓美林在接受《環(huán)球時報》記者專訪時感慨道。事實上,不止藝術跨界,對古文字長達半個世紀的追尋探索,讓韓美林完成了對中國文化理解的四個跨越。
跨領域:藝術再不聯(lián)合就跟不上這個時代了
韓美林的家,大氣整潔又充滿童趣:墻上的大型書畫作品透著他耄耋之年的蒼勁恢宏,沙發(fā)旁萌萌的小擺件則讓人想起他設計的北京奧運“福娃”。桌案上是他剛寫好的幾張“天書”手稿-—以古文字、符號為原型創(chuàng)作的書法或形象。“天書”的名字其實是國學家季羨林起的,“既然人類不知道它是什么,只有上天知道,就叫'天書吧”。
談及那首跨界交響樂,韓美林仍難掩激動之情。“宇宙是無限的,音樂也是無限的。這首樂曲為藝術融合開辟了一個新的切口。音樂和書法、繪畫的內(nèi)核一樣,只是表現(xiàn)形式不同。繪畫是寫實的,音樂是抽象的。”在他看來,藝術的基本規(guī)律都一樣,繪畫中的結(jié)構(gòu)、字形、頓挫,音樂中的旋律線、輕重、轉(zhuǎn)折、斷連,舞蹈中的形體、動作、收放等,都是相通的。“天書跟音樂五線譜上那些小蝌蚪有什么區(qū)別?你看這些線條是不是旋律?”韓美林說著,在紙上隨手畫了一筆線條。
由此,古文字給韓美林帶來了第一個跨越:藝術領域的跨界。“現(xiàn)在到了不同藝術必須揉在一起的時候。如果藝術再不聯(lián)合就跟不上這個時代了。”韓美林解釋道,現(xiàn)在不是農(nóng)業(yè)時代、工業(yè)時代,而是各領域全面發(fā)展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做藝術家很難。“為什么現(xiàn)在世界上彳艮少有大藝術家、大音樂家、大畫家?就是因為很多藝術蒙杲能適應這個時代的要求。這個時代不僅全面發(fā)展,而且加速發(fā)展,要求藝術家也要全面發(fā)展。頭頂音樂,腳踩文學,假如不具備這兩個基本條件,就稱不上是這個時代的藝術家。音樂家如果沒有文學修養(yǎng),沒有對形象理解的深度,只能稱為匠人,加上個'家是不行的。”
跨規(guī)則:擺脫“藝術教條主義”
古文字帶來的第二個跨越,是對規(guī)則束縛的跨越。文字歷,來被視為中國文明探究追溯的源頭和根基。“文字之始,莫不生于象形。”象形不僅是中國文字的淵藪和特征,更賦予文字自然的靈性。隨著中國歷史的變遷,文字在積累知識、傳承文化、促進交流中的意義與價值得以發(fā)展,但對中國文字的圖形表現(xiàn)、審美認識與挖掘應用尚未充分展開。2007年,韓美林的首部《天書》橫空出世。2021年“天書”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迎來首次整體亮相。現(xiàn)在韓美林的第三本、第四本《天書》已交付出版。第五本、第六本正在創(chuàng)作中。
韓美林告訴《環(huán)球時報》記者,他與古文字結(jié)緣從幼年就開始了。六七歲時,他家的巷子口有個藥店,.后院全是藥材,一些大圓簸箕上鋪著黃表紙,上面放著骨頭和龜甲,店員說這是“龍骨”,能治病,上面那些文字他講不出來。“龍骨我不懂,但那些文字在我的腦子里慢慢生根開花,當時我根本不知道這就是甲骨文。好奇的我把它們當成圖畫臨摹下來。沒想到,長大后,一收集就是半個世紀。”
50年來,韓美林從甲骨、石刻、巖畫、古陶、青銅、石鼓等歷史遺存中記錄了幾萬個古文字或符號。足跡遍布深山老林、黃土沙海,甚至海拔4300米的青藏高原。著名書法家啟功笑稱,韓美林是在辦古文字收容所,并鼓勵他把天書寫下去。“古文字都是描下來的,只能說是資料,不能說是藝術。你能寫出來就好了,你是畫家,又有書法底子,別人還,真寫不了……啟功如此鼓勵韓美林。
“我必須以藝術生涯中對美理解的深度,將古人創(chuàng)造的文化以現(xiàn)代審美意識去理解、創(chuàng)造,但在文字的結(jié)構(gòu)上、字形上不傷害它。”韓美林說,“大家都說天書是新朋友,但實際上是老朋友、老祖宗,只不過我把它當小孩兒一樣重新培養(yǎng)。”除創(chuàng)作《天書》,韓美林還將古文字的神韻融入水墨、陶瓷、紫砂、印染、木雕、鐵藝等多個藝術領域。
對韓美林來說,古文字的“自由散'漫”具有巨大吸引力。它的一字多義、一義多字、一字多形、多字一形,對于畫家是極強的誘惑。“它們形象上的多變官啟發(fā)我造型和結(jié)構(gòu)的多樣性。小篆以后中國文字逐漸統(tǒng)一,但從藝術角度看,太板,沒個性。我更喜歡2000年前小篆以前的文字。”
韓美林認為,現(xiàn)在中國的藝術創(chuàng)作大都是指定性的。古文字和巖畫對他產(chǎn)生的直接影響,就是讓他擺脫了學院派“藝術教條主義”的束縛。“藝術沒有'維﹂,沒有所謂七十二法,這一點我們祖先已經(jīng)開了先河。我畫畫不要維',不要'三面五調(diào)'。'感覺世界是人類對客觀世界頓悟的另一個境界,是人類文化的升華。”韓美林說,古文字給他提供了這種感覺條件,得到了學院派得不到的東西,也決定了他藝術作品的個性。
跨時代、跨民族:既傳統(tǒng)又現(xiàn)代的大文化
韓美林說,自己率先寫“天書”是為了給美術界的人參考,看著幾千年的文化里竟蘊涵著如此豐富的形象。“它絕對不會啟發(fā)你去做那些鐵片子一擰,繩子一繞,不銹鋼球當頭照的雕塑!它教我們兩個字——概括”。
在韓美林眼中,古文字是極度的“概括”,能啟發(fā)人的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這些古文字絕對有本事把你領到概括'的大藝術、大手筆、大氣派里。它就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看到它,還用得著到外面去拾人牙慧拿回中國當教師爺嗎?”韓美林說,現(xiàn)在,中國繪畫中所說的“形象感”很多都是洋教學的標準,但其實,中國古文字在這方面絕不遜色西方,它是既傳統(tǒng)又現(xiàn)代的大藝術、大文化。《天書》出版后,西方奢侈品牌與韓美林合作,推出以天書為設計元素的限量版腕表、服裝、汽車等。韓美林感慨,“古文字不僅是中國,也是世界公認的瑰寶和遺產(chǎn),幾千年還永葆青春,時尚而前衛(wèi)。21世紀更是它展現(xiàn)風采的時代。”至此,古文字給藝術家?guī)砹锁Q越時代和民族的新啟示。
在研究古文字的過程中,韓美林還得出一個結(jié)論:“有人說古文字有3000年歷史,但我認為,中國古文字的源頭是無限源,你丕知道它從什么時候并始,也不知道未來會向何處去。”韓美林認為自己是將被遺忘的古文字由負變正的那個“零”。
不止古文字,未來的藝術該走向何方?人智能是否會改變藝術創(chuàng)作的未來?“人工智能絕對不會取代藝術家。區(qū)別在于,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本質(zhì)上是用技術手段控制的藝術創(chuàng)作,而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是通過人的本能感受刺激出來的藝術形象和作品。”韓美林認為,藝術創(chuàng)作不能脫離人的本性和本質(zhì)。就像在工業(yè)化時代,人們更感覺手工制作可貴一樣。因為那里有人的本能和溫暖。
“未來,我們必須跟著時代走,而不能跟著潮流,潮再大也會退下去。”韓美林說,很多人都不會想到,如今數(shù)學、量子通信能覆蓋生活中這么多領域。老教授以前學的數(shù)理化也得跟著時代進步。不知道什么叫費米子、光量子,怎么教現(xiàn)在的學生?科學家證實,利用核聚變,1升海水能釋放出相當于300升汽油燃燒的能量,將來人類也許就不需要挖地球上的煤、油了。“藝術也如此。未來,古文字、古文明也將給藝術釋放巨大能量。”韓美林說,“一個中國的藝術家,若想走向世界,這條路應該是必經(jīng)之路——古老的、民族的、現(xiàn)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