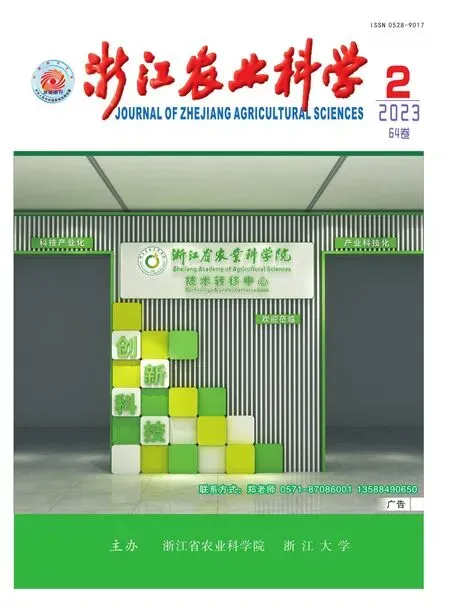香椿離體再生技術研究進展
李玲, 黃榕, 艾薇, 王友如
(湖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特色野菜良種繁育與綜合利用技術湖北省工程研究中心 食用野生植物保育與利用湖北省重點實驗室,湖北 黃石 435002)
香椿是楝科香椿屬落葉喬木[1],是我國傳統藥食同源木本植物。其樹干通直,樹體龐大,色澤花紋清晰,芳香耐腐,被譽為“中國桃花心木”[2]。香椿地理位置分布廣泛,北至遼陽錦州一線,西至陜西延安市,南至廣西廣東一帶,東至我國臺灣省[3],喜溫帶和亞熱帶氣候[4]。香椿也是唯一一個被我國命名“樹上蔬菜”的植物,它富含豐富的維生素、胡蘿卜素、香椿素和鈣鎂等營養元素,具有超高的營養價值,深受消費者的喜愛[5]。香椿藥用歷史悠久,早在古代就已知其具有清熱利濕、利尿解毒等功效。《本草綱目》中記載:香椿葉、芽、根、皮和果實均可入藥[6]。
基于以上香椿的材用、食用和藥用價值特點,我國部分地區將香椿產業作為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農業現代化產業項目。四川大竹縣被譽為“中國香椿第一縣”,據相關數據記載,2020年該縣的香椿芽銷售1.1萬t,產值達3億元;四川簡陽市香椿的種植面積近3 500 hm2;太和香椿近些年種植面積近235 hm2,香椿芽年產量達500 t[7]。香椿產業在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香椿產業發展迅速,但種苗參差不齊、品系良莠不分和優質苗木供不應求等問題嚴重制約著產業的健康快速發展。植物組織培養技術的最大優點是能夠快速大量地獲得保持優良母本性狀的再生個體,不受環境季節等因素影響,快速繁殖優良香椿種苗[8]。
本綜述從微繁途徑再生技術和組織培養再生技術2個方面總結香椿離體再生技術的最新研究進展及存在的問題,為構建高效香椿再生技術體系提供借鑒。
1 基于微繁途徑的再生技術研究進展
微繁技術是指以植物莖段、腋芽和頂芽等為外植體,通過消毒和無菌操作等一系列方式快速獲得大量的能穩定遺傳的叢生芽的一項技術。目前國內的香椿離體再生技術研究,大多采用的是芽微繁途徑獲得再生苗。
1.1 外植體選擇
大部分學者在進行香椿芽微繁研究時,均是選取香椿(含腋芽的)的莖段、腋芽、頂芽或叢生芽作為外植體,這主要是由于香椿含芽處增殖系數相較于其他外植體較高。
覃蘭英等[9]最早開展香椿微繁研究,以莖段為外植體發現,在基本培養基(MS)+0.1 mg·L-1吲哚乙酸(IAA)+0.1/0.5 mg·L-16-芐基腺嘌呤(6-BA)叢生芽誘導可達4~5個,從此開啟了離體再生技術研究的序幕;康明等[10]以遷西香椿45 d無菌苗莖段(帶側芽)為外植體,在MS+1.0 mg·L-16-BA+0.1 mg·L-1吲哚丁酸(IBA)中發現有叢芽形成;謝文申等[11]發現,以香椿莖段為外植體時,在培養基MS+0.1 mg·L-16-BA+0.5 mg·L-1激動素(KT)+0.1 mg·L-1萘乙酸(NAA)中發現大約30 d后可形成叢芽;吳麗君[12]發現,選取福建香椿0.5~0.8 cm莖段時,在MS+0.5 mg·L-16-BA+0.5 mg·L-1NAA培養基中,20 d后小芽能長至1.5~2.0 cm;馬勤[13]研究發現,香椿品系T4的莖段在MS+0.2 mg·L-16-BA+2.0 mg·L-1赤霉素(GA3)中芽的增殖系數可達3.38;許麗瓊等[14]研究發現,3月采取孝感紅香椿莖段(帶1個芽)接種至增殖培養基MS+1.0 mg·L-16-BA+1.5 mg·L-1GA3+0.5 mg·L-1KT中,增殖倍數可高達4.7;周玉玲[15]研究紅香椿一號的莖段發現,在MS+1.0 mg·L-16-BA+0.1 mg·L-1NAA+0.1 mg·L-1IBA+0.1 mg·L-1玉米素(ZT)培養基中芽的增殖倍數在6.0以上;張曉申等[16]發現,以鄭州香椿3 cm長莖段為外植體時,在培養基MS+0.6 mg·L-16-BA+0.2 mg·L-1NAA,莖段的芽誘導率為66.7%;高鷃銘[17]以帶小芽的莖段為外植體時發現,在培養基MS+1.0 mg·L-16-BA+0.1 mg·L-1NAA+0.1 mg·L-1GA3中,芽的增殖倍數為3.63;楊超臣等[18]發現,香椿莖段在MS+1.0 mg·L-16-BA+0.1 mg·L-1NAA+1.0 mg·L-1GA3培養基中,芽增殖倍數為4.82。由上可知,香椿莖段芽微繁效果較好,能在短時間內獲得大量叢生芽。
王春林等[19]最早以太和香椿腋芽為外植體進行芽增殖試驗,在培養基B5+1.0 mg·L-16-BA+1.0 mg·L-1GA3中發現,1個月后繁殖系數可達6~7倍;陳彥生等[20]以腋芽莖段為外植體時發現,在培養基MS+0.2 mg·L-16-BA中3~5 d后腋芽就開始萌發,15 d后成苗率達73%;曹娟等[21]在研究紅香椿腋芽時發現,在培養基MS+0.2 mg·L-1GA3+0.02 mg·L-1NAA中,增殖系數達3.8。
陳實[22]在研究南京香椿子葉、下胚軸(含頂芽)時,發現在B5+1.0 mg·L-16-BA+0.5 mg·L-1NAA培養基中生芽率達61.5%;袁應菊[23]采用太和香椿頂芽為外植體研究發現,接種在增殖培養基MS+0.3~0.8 mg·L-16-BA+0.1~0.2 NAA mg·L-1中,叢生芽平均每個可再生3個左右。
張曉申等[16]發現,以鄭州香椿莖段誘導的叢芽為外植體時,在培養基MS+1.0 mg·L-16-BA+0.5 mg·L-1NAA中,叢芽的增殖系數3.7。馬宗新等[24]以太和香椿的叢芽為外植體時發現,在培養基MS+1.5 mg·L-16-BA+0.08 mg·L-1NAA+0.01 mg·L-1GA3中,芽的增殖系數為2~3倍;梁明勤等[25]以菜用香椿的叢芽為外植體,在1/2 MS+0.5 mg·L-16-BA+0.5 mg·L-1GA3培養基中發現增殖倍數可達6.95;馮姍姍[26]在研究太和香椿的叢芽時發現,在培養基MS+1.0 mg·L-16-BA+0.1 mg·L-1NAA+0.5 mg·L-1GA3中,芽的增殖倍數達5.9。
經比較發現,腋芽莖段的萌發時間較短于莖段,且叢芽的誘導率也高于莖段,有可能是莖段木質化程度高于腋芽,在消毒過程中莖段較容易褐化死亡;或者又由于腋芽的幼嫩程度高于莖段,所以較易誘導萌發。
1.2 基本培養基
基本培養基是香椿微繁再生中的主要能量來源。目前微繁中常用到的培養基有MS、1/2MS、WPM、B5、1/2DCR、無離子水或是改良的培養基等。
香椿芽微繁途徑研究進展表明,大多數采用的是MS基本培養基。王春林等[19]首次采用B5培養基對太和香椿莖尖和幼苗莖部進行誘導,發現均有成苗和生根出現;許麗瓊等[14]發現,B5與1/2MS培養基對莖段培養的效果差異不大,分析可能與培養基本身的營養物質有關,但二者都不如MS培養基的營養全面;陳實等[22]經成分對比發現,MS比B5培養基的硝酸鹽含量更高,表明MS的銨含量高于B5,銨對香椿外植體的生長發育有一定影響,認為B5培養基的效果較好于MS[14]。1/2MS培養基適用于香椿芽苗的生根試驗,能在短時間內有效促進芽苗底部形成發達根系,便于后續移栽。
1.3 植物生長調節劑
植物生長調節劑是微繁技術中的關鍵因素。一般認為,當細胞分裂素濃度相對高于生長素濃度時,有助于促進芽的生長;當細胞分裂素濃度相對低于生長素濃度時,有助于促進根的生長和愈傷組織的形成[27]。
香椿在芽微繁中主要使用的細胞分裂素是6-BA,其次便是ZT和KT;最常用的生長素是NAA。6-BA是最常用的一種細胞分裂素。梁明勤等[25,28]認為,6-BA對香椿芽的增殖有顯著影響,在誘導香椿芽快繁過程中6-BA濃度常控制在0.2~1.5 mg·L-1,尤其是低濃度的6-BA增殖效果最佳[29],當濃度越接近0.5~1.0 mg·L-1的時候,增殖系數較高,最高可達6.95[25]。6-BA還可以抑制植物的頂端優勢,但濃度過高會導致外植體出現玻璃化和輕微白化狀態[30]。陳彥生等[20]研究發現,在培養基中加入GA3,不僅可以促進腋芽增殖還可以有效降低玻璃化苗產生,也能降低試管苗木質化程度[24]。GA3的含量會在香椿休眠芽到萌發這一階段內急劇升高[31],是影響香椿芽萌發的重要影響因素。周玉玲等[15]在研究紅香椿芽增殖中發現,激素的影響效果由大到小依次為ZT、6-BA、NAA、IBA。
從近30 a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在香椿芽微繁的過程中,單一的植物生長調節劑是無法獲得較高增殖系數的叢芽,一般情況下,細胞分裂素、生長素或者赤霉素等按照合適比例添加,才能獲得較好的微繁效果。以香椿莖段、腋芽或頂芽為外植體的芽微繁技術相對成熟,可獲得較高增殖系數的香椿無菌苗,為工廠化生產優質香椿苗木提供了技術支撐。一般使用的基本培養基是MS,細胞分裂素是6-BA,生長素是NAA,濃度在0.1~1.0 mg·L-1,1個帶腋芽的莖段誘導的叢芽一般可達3~6個。目前關于香椿離體再生技術的報道大多還是以芽微繁的方式進行,僅有極少數是基于愈傷組織的再生技術,大多停留在愈傷誘導階段,愈傷分化仍未有實質性的技術突破。
2 基于組織培養的離體再生技術研究進展
傳統意義上的植物組織培養技術是指先誘導外植體脫分化形成愈傷組織,然后再使愈傷組織再分化形成不定芽,最后誘導再生植株生根成為完整植株的過程。
2.1 外植體選擇
目前香椿植物組織培養主要在以無菌苗葉片、幼葉或是在室外取幼嫩香椿葉片為外植體。最早進行香椿組織培養的是王春林等[19],以太和香椿的幼葉為外植體,在液體培養基B5+2.5 mg·L-16-BA+2.5 mg·L-1NAA 中發現在黑暗條件下培養可以10 d快速誘導愈傷形成,40 d分化成葉芽,且愈傷誘導率及不定芽再生率均不高。隨后,許麗瓊等[32]選取以孝感紅香椿葉片為外植體,發現在培養基MS+1.0 mg·L-16-BA+0.1 mg·L-1KT+0.5 mg·L-1NAA中,6 d愈傷誘導率為100%,也有不定芽出現(培養基未記錄)。之后,曹娟等[21]采用紅香椿葉片為外植體,在培養基MS+0.15 mg·L-1噻二唑苯基脲(TDZ)+0.3 mg·L-1NAA+1.0 mg·L-1KT中發現愈傷誘導率為92.8%,且葉片愈傷組織在培養基MS+0.1 mg·L-16-BA+0.5 mg·L-1KT+0.1 mg·L-1NAA有不定芽產生;梁明勤等[25]以太和香椿嫩葉為外植體時,在培養基MS+0.3~0.8 mg·L-16-BA+0.1~0.3 mg·L-1NAA中有愈傷形成,但無不定芽形成;馮姍姍[26]以太和香椿葉片為外植體時,在培養基MS+1.5 mg·L-12, 4-二氯苯氧乙酸(2, 4-D)中愈傷組織誘導率為100%,葉片細胞團在MS+1.0 mg·L-1KT+0.1 mg·L-1NAA中有側根出現。
在組織培養過程中,外植體的選取能夠很大程度影響植物再生,不同植物的不同外植體建立起再生技術體系的難易不同[33]。目前,以無菌苗葉片、幼葉和室外取材葉片為外植體時,愈傷組織誘導相對容易,但仍存在愈傷組織分化的難題未取得實質性突破,其原因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2.2 基本培養基
目前香椿組織培養中所用培養基來看,主要培養基是以MS為主,也用到了B5培養基。
2.3 植物生長調節劑
葉片愈傷組織的誘導和分化,主要采用的細胞分裂素是6-BA,生長素是NAA,其次搭配KT、2, 4-D和TDZ。添加不同種類的植物生長調節劑至基本培養基中能夠較大程度影響外植體誘導分化。適當濃度的NAA能有效促進芽的萌發,也能夠誘導較多愈傷組織的形成[25]。2, 4-D對外植體愈傷組織誘導效率高[26],但是濃度過高會對外植體材料有一定的毒害作用[34]。在葉片愈傷誘導過程中,TDZ、NAA和KT或是6-BA、KT、NAA組合中,愈傷組織的誘導率均能夠達到90%以上,因此KT和NAA對香椿葉片愈傷誘導有較大的促進作用。目前出現不定芽的培養基中均用NAA和6-BA處理,因此一定比例的NAA和6-BA可以誘導不定芽生成,但是兩者濃度的比例還需進行適當調節。
總之,目前香椿組織培養的再生技術研究主要以香椿幼葉和葉片為外植體,在細胞分裂素BA、KT、TDZ和生長素NAA、2, 4-D組合下進行的愈傷誘導分化,一般細胞分裂素同生長素濃度比例在2~5 mg·L-1。總體效果呈愈傷組織誘導相對容易,效率較高,但愈傷組織分化十分困難。
3 離體再生技術中存在的問題
目前香椿離體再生技術大部分是以頂芽或腋芽為基礎的微繁技術,基于愈傷組織誘導分化的香椿組織培養研究中,愈傷組織成功誘導案例比較普遍,但愈傷組織的分化幾乎沒有成功。
3.1 微繁效率問題
目前香椿微繁技術存在的最大問題是繁殖效率不夠高。影響微繁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外植體的年齡。在選取含腋芽或頂芽的外植體的過程中,未能選取最佳年齡階段的莖段。年齡階段的選取十分重要,如果選取外植體較為幼嫩,則會在消毒的過程中容易消毒過度,導致材料褐化死亡;如果選取外植體莖段較成熟,則會導致消毒不徹底,莖段染菌或是莖段不易誘導芽的萌發[35]。第二,最佳植物生長調節劑類型及其濃度配比。未篩選出最佳的細胞分裂素和生長素組合及其濃度配比。植物生長調節劑濃度及其比例對芽微繁再生技術產生較大影響。細胞分裂素使用比較多的是6-BA和KT;生長素使用比較多的是IBA、NAA和IAA,赤霉素GA3有一定的使用。6-BA使用濃度一般是0.1~1.5 mg·L-1,KT使用濃度是0.5 mg·L-1,IBA、NAA和IAA的使用濃度分別是0.1、0.02~0.5和0.1 mg·L-1,GA3的使用濃度是0.01~1.00 mg·L-1。細胞分裂素和生長素濃度一般控制在1~10 mg·L-1,增殖系數為3~6。目前香椿微繁途徑中細胞分裂素TDZ和生長素2, 4-D的使用極少,TDZ具有很強的細胞分裂素的效果,活性是普通細胞分裂素的幾十倍[36],2, 4-D可以誘導外植體表現出胚胎發生能力[37]。
3.2 組織培養再生技術中存在的問題
在香椿組織培養過程中,外植體類型及其年齡選擇上,多局限于消毒葉片、莖段,而且這些葉片和莖段的年齡階段并未明確說明。
在香椿愈傷組織誘導與分化的研究中,細胞分裂素使用較多的是6-BA和NAA,細胞分裂素與生長素的質量百分比在愈傷誘導過程中的比例為1~3;在愈傷組織分化中,細胞分裂素與生長素的質量百分比的比例更高達6~10。TDZ和2, 4-D在愈傷組織誘導分化中有初步應用,但目前這2種植物生長調節劑并未組合應用。另外香椿體細胞胚胎途徑的誘導與分化研究幾乎是空白[38]。
4 香椿離體再生技術研究的建議
4.1 微繁途徑的再生技術
可選擇不同基因型或不同種源地的香椿頂芽或腋芽為材料,探索微繁中的外植體恰當年齡段以及合適的植物生長調節劑的類型及其濃度配比,建立高效微繁再生技術體系。
4.2 組織培養再生技術
外植體的選擇上,可選用合適年齡階段幼嫩種子苗的子葉、下胚軸或無菌苗的幼嫩組織或器官,如將葉柄、葉柄節或頂芽、腋芽作為外植體;也可選擇發育未成熟的胚或者幼嫩生長活躍的具有能力細胞的組織或器官(如頂芽或腋芽或者器官間交接處的組織)作為外植體研究體細胞胚胎發生途徑再生技術體系。在繼代方式上也可考慮葉片近軸端或是遠軸端接觸培養基等[39],優化各種條件培養。對于基于組織培養的再生技術體系,選擇恰當幼嫩年齡階段的外植體尤為重要。無論是基于愈傷組織誘導分化的再生技術還是基于體細胞胚胎誘導分化的再生技術,筆者建議重點考慮細胞分裂素TDZ和生長素2, 4-D與其他細胞分裂素和生長素的聯合使用,以期望達到較好的再生效果。
目前TDZ已經在很多植物組織培養中添加應用,如油菜、蘋果、樸樹、紅花槭等,均發現它具有很高的細胞分裂素活性,可以有效促進芽增殖,對再生較困難的木本植物的離體芽增殖也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40]。張小紅等[41]曾在香椿愈傷組織誘導和芽增殖中添加了TDZ,發現當濃度高于0.02 mg·L-1時會抑制香椿生長,且容易出現較多變態苗;當濃度在小于0.02 mg·L-1時,能夠有效地促進香椿芽的生長。該研究中只開展了TDZ和NAA組合的研究,未和其他植物生長調節劑組合。因此,在后續香椿組織培養研究過程中,可以用其他植物生長調節劑與TDZ組合,研究出最佳香椿愈傷誘導及愈傷分化的試驗組合,早日建立起高效再生的香椿再生體系。為后續香椿分子育種與功能基因的研究提供理論基礎和技術支撐。
有學者在研究灰堇菜時發現,在添加2, 4-D的MS培養基上,利用葉片愈傷組織開展的體細胞胚胎發生途徑成功地獲得再生植株[42]。李文靜等[43]在研究野生薺菜中發現,2, 4-D濃度過高會抑制愈傷組織再生植株。2, 4-D目前在很多植物體細胞胚胎途徑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建議在香椿體細胞胚胎誘導研究中添加適量2, 4-D。
綜上所述,香椿再生技術研究大多以微繁技術為主,基于組織培養的再生技術未見實質性突破,研究結果大多局限于外植體愈傷組織的成功誘導,愈傷組織分化鮮見報道。香椿的組織培養體系還需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與探討,需要在恰當的基本培養基、合適外植體選擇、合適植物生長調節劑類型及其配比上做出恰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