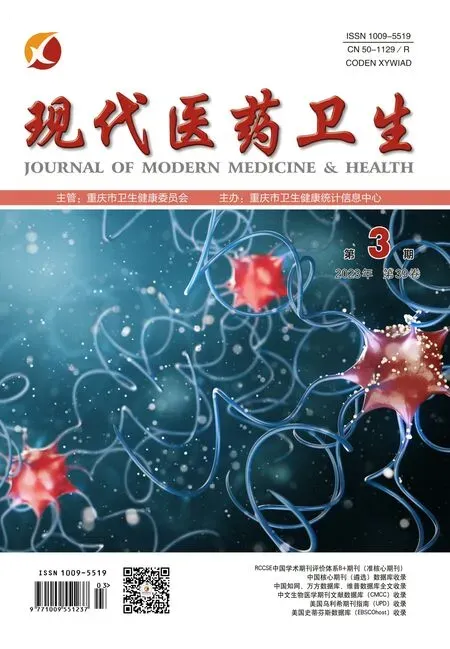神經源性腸道功能障礙便秘癥狀的非藥物干預研究進展*
黃齡漪 綜述,郭聲敏 審校,王劍雄,黃厚強,廖如榆,周星辰,鄧 雅,蒲霞敏
(1.西南醫科大學護理學院,四川 瀘州 646000;2.西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護理部,四川 瀘州 646000;3.西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康復科,四川 瀘州 646000)
全球預估有超過250萬人因脊髓損傷(SCI)而發病,國內發病人數為23.7人/百萬~60.0人/百萬人口[1-2]。脊髓損傷伴神經源性腸道功能障礙(NBD)是一類脊髓受到創傷或非創傷等原因引起的結腸運動和(或)感覺失去神經控制或徹底喪失功能的嚴重并發癥,而NBD便秘作為該并發癥中常見的臨床表現,在治療方面仍較為棘手,正常排便功能恢復緩慢。據調查問卷發現,58%的SCI患者會導致很嚴重的便秘,甚至有95%的患者需要大于或等于1種刺激方法來促進排便[3]。患者不僅喪失排便自控力還會伴隨便血、肛裂、痔瘡、直腸出血、脫垂、尿路感染、腹痛、自主神經反射障礙等問題出現。由于藥物治療在慢性神經源性腸道功能中會出現劑量依賴和加重排便困難等問題,因此,尋求非藥物腸道管理干預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能彌補其治療的有限性,幫助患者改善排便困難現狀,重返社會活動。
1 NBD便秘發生的相關機制
NBD患者腸功能失調后,一方面,結腸慢性擴張,結腸張力逐漸下降,容積擴增,蠕動變慢,糞便停滯,毒素堆積,糞便干結;另一方面,直腸內壓力隨著排便逐漸增加,肛門括約肌緊張,排便時間延長,共同導致便秘發生[4]。其中頸髓完全性受損患者,因受損平面位置較高,結腸傳輸時間較慢;第一腰椎(L1)以下平面排便反射弧被破壞,直腸順應性下降,都較易發生便秘[3]。隨著病理生理學機制的深入研究,SCI患者便秘可能與年齡相關的腸神經退行性變有關[5]。除此之外,其可能還與血管活性腸肽(VIP)、結腸肌層內P物質含量的改變和腸道微生態失衡對腦-腸軸的異常調節等有關[6-7]。
2 NBD便秘診斷與評估
目前,針對NBD的診斷主要依據羅馬Ⅲ診斷標準和國際胃腸組織的OMGE指南相關內容[8]。NBD針對性評估依據包括國際脊髓損傷腸功能基礎數據集及擴展數據集、NBD評分;便秘指南有:中國成人慢性便秘評估與外科處理臨床實踐指南(2022版)、中國慢性便秘診治指南、便秘外科診治指南、便秘臨床實踐指南;臨床運用較多的便秘評估量表有:Wexner便秘評分、Cleveland便秘評分系統、便秘評估量表(CAS)、布里斯托大便分型法、功能獨立性量表(FIM)中直腸相關內容、Barthel指數(BI)腸道部分、便秘相關生活質量評分(CRQOL)、漢化版便秘患者癥狀自評量表(PAC-SYM)、漢化版便秘患者生存質量量表(PAC-QOL)、便秘嚴重程度評估量表(CSI)[9-10]。
當前,便秘的臨床指南和評估量表雖有很多,但未細分到具體疾病中,對特殊人群如小兒的評估方法也較少,尚缺少針對性的NBD便秘評估量表;部分量表僅采用其腸道部分進行評估,多數量表只關注于評估便秘癥狀本身,而忽視對便秘長期伴隨者的心理狀態及生存質量的評估;不同醫院量表的選擇不統一,評分標準存在差異,多量表的評估和記錄給醫務工作者增加了額外的工作負擔。STUDSGAARD等[11]研究的一種通過臨床路徑確定病情進展的監測工具“MENTOR”,填補了院外評估空缺,更好地提高了出院后患者居家護理的能力,有望成為非醫院環境下評估NBD治療的工具。
3 NBD便秘的非藥物干預治療
脊髓損傷在急性和慢性期都會發生不同程度的便秘,臥床、活動減少、食欲減退、精神壓力過大、藥物不良反應、知識缺乏等綜合因素使得便秘問題更加突出[12]。非藥物干預治療將從飲食及飲水管理、腹部按摩、直腸刺激(DRS)、肛門灌洗(TAI)、生物反饋與電刺激、中醫干預、心理管理、護理及健康教育、其他治療等方面展開闡述。
3.1飲食及飲水管理 合理膳食與飲水是非藥物腸道管理中最常見、易干預的措施。基于快速康復理念,對SCI患者進行全周期的營養干預,能降低患者并發癥的發生[13]。但FARKAS等[14]研究發現,在SCI個體中,全水果、蔬菜和全谷物的日攝入量卻低于指南推薦膳食量。因此,建立規律飲食,每天攝取大于或等于15 g膳食纖維,減少攝入不溶性纖維谷物,謹慎咖啡因、酒精、山梨醇等食物對脊髓損傷后神經源性腸道管理有益[15-16]。在飲水方面,每天飲水1.5~2.0 L能增加排便次數[10],指導患者準確記錄飲水日記,根據24 h出入量來科學飲水可改善便秘癥狀。
3.2腹部按摩 腹部按摩和熱敷能緩解腹部緊張,加快腸道蠕動[17]。金娟等[18]使用醫用振動排痰機,振動頻率設置為20~30 HZ,按壓深度2~5 cm,每天20 min,定時(排便前15 min)進行1次腹部定向多頻振動按摩后,大便外表光滑易排出,不僅避免了護理人員體能消耗,還提高了臨床工作效率。FEKRI等[19]發現腹部“ILOVU ”按摩手法和“YounIChoi” 自動腹部裝置的配合使用,可改善便秘與腹脹。MCCLURG等[20]研究發現,使用“MOWOOT”自動提供間歇結腸外蠕動治療,每天20 min,持續4周顯著增加了每周排便次數,減輕了慢性便秘癥狀,對于慢性疾病和老年居家及行動受限的患者,具有安全性和有效性。
3.3DRS 清醒、餐后或熱飲后,腸道收縮最強,定時進行DRS能促進左側結腸蠕動,增加直腸反射性運動,放松長期處于緊張狀態的肛門外括約肌,協助排氣、排便[21]。文獻系統回顧表明,DRS最優的刺激時間是1 min,停止刺激后的3~5 min還會增加腸道蠕動,且不會對腸道黏膜造成損傷[22]。蘇穎等[23]研究發明的可定位式DRS器,通過定位氣囊可替代徒手指力進行DRS,使DRS部位更精準 。研究統計表明,38%~42%的SCI患者能從DRS中獲益,在短期治療時可使用DRS[24]。在干預性研究中,因DRS總是與其他干預措施共同使用,使得很難確定其單獨使用的利弊,故在長期使用的安全性及并發癥的預防、患者和護理人員最佳的刺激姿勢及刺激手指數量等問題還值得進一步研究[25]。
3.4肛門灌洗(TAI) TAI通過特定的系統裝置輔助灌洗,定時對腸道排空,能幫助患者逐步重獲排便自控力[26]。研究證據支持TAI能成功治療40%~63%的便秘[27]。FAABORG等[28]發現,TAI對自主神經功能反射障礙(AD)的刺激程度比DRS較輕,故可作為嚴重AD患者排便時的替代治療,同時也可作為兒童治療的首選方案。Peristeen灌洗系統(使用泵而不是重力對結腸進行沖洗)是TAI常用的一種裝置[29]。VAN RENTERGHEM等[30]比較了比利時2種灌洗系統coltip?和Peristeen?在兒童灌洗中的差異,發現與前者相比,Peristeen?的使用可以使兒童在便秘問題上具有更好的自制力。目前,TAI在國內的應用不如國外廣泛,臨床上缺乏有關TAI在NBD患者應用中的高質量臨床研究和現有灌洗系統裝置的對比研究。改良和開發新的、價格便宜的灌洗裝置,值得研究者思考。
3.5生物反饋與電刺激 生物反饋與電刺激通過調節骶神經、局部皮膚神經及腸周圍神經等來促進對結腸傳輸時間的調控,從而提高腸道敏感性。目前,刺激方式包括脛神經刺激、骶神經根刺激、圓錐刺激、腹部肌肉電刺激、骶骨切開術伴骶前刺激、磁刺激、生殖器背側神經刺激、經皮干擾電刺激[31]。盧萍丹等[32]研究發現,生物反饋與電刺激具有協同作用,聯合使用優于單獨的生物反饋,可降低直腸肌及肛門外括約肌張力,緩解便秘。陳其強等[33]研究表明,將針灸和生物反饋電刺激相結合并聯合康復運動訓練,患者NBD評分和Wexner便秘評分降低情況均優于單純使用生物反饋電刺激組,從經濟學角度來說也更為便宜。KREYDIN等[34]開發實施了一種新型脊髓神經非侵入性刺激方式,使用專有的SCONETM設備,通過高頻電流進行脊髓神經調節可以改變肛門直腸和感覺功能,減少腸道護理時間,因所納入樣本量小,具體機制不詳,有效性還待驗證。總的來說,目前臨床生物反饋電刺激對脊髓損傷患者腸道功能障礙的研究多為小樣本且隨訪時間較短,下一步應擴大樣本量和增加隨訪時間,選擇最佳閾值進行干預,減少電刺激給SCI患者帶來的如性行為障礙等一系列不良反應。
3.6中醫干預 中醫通過針灸、推拿、艾灸、穴位貼、循經刮痧等干預方式能疏通經絡,調和陰陽,激活中樞,調節結腸平滑肌的內在神經支配從而改善便秘[35]。LI等[1]研究發現,將杵針療法與推拿、功能鍛煉三法并舉,能使患者每周自發排便次數增加,不僅克服了傳統針灸穿刺皮膚的缺點,避免了患者的恐懼和感染風險,還大大提高了患者的依從性。 以八髎為主穴外加配穴治療便秘,能增強肛管收縮,改善盆底和肛門括約肌的功能[36],總有效率可達80.0%~93.3%[37]。
3.7心理管理 NBD便秘除影響患者的日常生活及社會交往,還會引發焦慮、悲傷、恐懼、自卑等負性情緒。54%的患者自述腸功能障礙是引起抑郁的原因之一[3]。曾雪琴等[38]運用認知行為療法(包括認知和行為干預2個部分)對患者進行正向引導并鼓勵家屬參與,促進脊髓損傷患者身心康復。此外,運用團體心理聯合同伴教育能夠有效改善SCI患者焦慮和抑郁等情緒[39]。吳承杰等[40]研究認為,對NBD患者進行多中心、大規模的生活質量和心理狀況調查研究,著手于具體問題出發,能更好地做到個體化心理管理。
3.8護理與健康教育 給NBD患者提供個體化的護理,能提高患者治療依從性,幫助患者重建對腸道管理的信心。在護理方面,基于臨床護理路徑應用[4]、綜合護理干預管理[41]及多學科協同護理模式[42]可廣泛在神經源性腸道個體化管理臨床實踐中推廣和使用[41-42]。同時健康教育在院外個體化腸道管理中十分重要,采用多樣化、互聯網、智能化的延續性健康教育指導途徑,制訂健康宣教畫報和手冊、開展“思維導圖”講座培訓、微信或醫院官網定期推送相關知識及視頻、操作技術現場指導、排便日記記錄等方式充分調動患者及家屬的積極性,定期“線上+線下”相結合模式對健康教育效果進行反饋與強化[43]。此外,護理人員應利用好醫院所在的信息化管理平臺,構建NBD的智慧化決策信息系統,提高護理質量和腸道管理效能。
3.9其他治療 醫護人員可指導患者開展如橋式、提肛、腰部前屈、盆底肌力運動等康復治療[44],一定程度上起到鍛煉腸道功能的作用。鄧艷紅等[45]將直腸球囊擴張術結合直腸功能訓練,利用含導絲導尿管球囊的彈性阻力重復刺激NBD患者腸道,訓練排便,有利于促進腸道恢復。TAMBURELLA等[46]研究發現,整骨手法治療(OMT)可以恢復內臟的生理彈性和運動性,對NBD腸功能的改善和患者的生活質量有積極影響,但研究結果受疫情的影響和樣本量小的限制,還需進一步研究。LIU等[47-48]研究表明,高壓氧治療可能通過特定信號通路對NBD產生抗氧化作用來改善腸通透性,從而保護大鼠脊髓損傷后的腸屏障功能,但是否能夠改善患者的便秘癥狀還尚待研究。
4 小結與展望
NBD具有發病率高、危害性大、治療效果反復的特點,盡管臨床上對于NBD的研究干預種類多樣,但具體到NBD便秘癥狀的臨床研究卻較少,目前多中心、大樣本、前瞻性、高質量研究遠遠不夠。雖然NBD便秘非藥物干預方式種類多樣,但面對不同患者個體差異時,應做到精細化評估,根據便秘患者的現狀,結合其意愿、經濟、家庭照顧者等條件,確定幾種可能干預方案實施的優先順序,從中選擇最佳干預方式。
未來,糞便微生物群移植對腸道結構和功能的影響將是NBD便秘治療的研究熱點。NBD便秘評估量表的研發與信效度的檢驗,以及相關主題國外量表的漢化,創建以患者為中心的工具進行便秘治療后的效果評價即患者自我報告結局的NBD便秘生存質量研究工具的開發,不同損傷平面的便秘嚴重程度與康復治療與護理的探索,個人-家庭-社區三方聯動的腸道管理圈的構建,排便的體位和姿勢的研究,輔助排便器具的開發與應用,實現個性化目標的路徑管理,NBD便秘預測模型的構建與應用等一系列問題都需要臨床研究者繼續拓展。相信隨著該領域的不斷演進,NBD便秘問題的治療能提高患者滿意度,患者能重獲腸道的自控能力,進行正常的社會生活,其他疾病所引起的患者便秘也能從此研究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