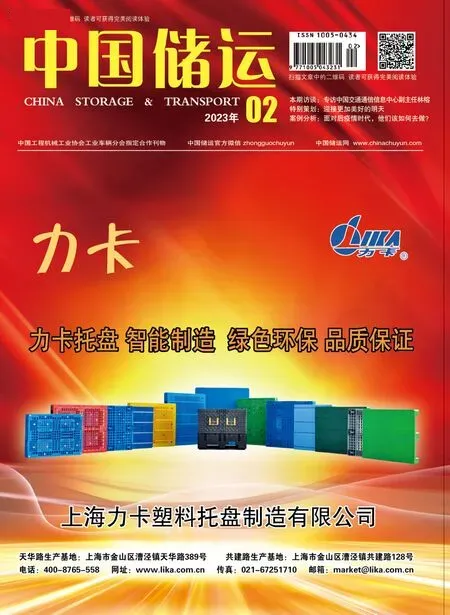論我國物流法律體系的建構
文/樸銀玥
隨著我國物流業的快速發展和全面依法治國進程的深入推進,理論和實踐界關于加快我國物流法律體系建構的呼聲日益高漲。然而,我國物流立法的步伐一直較為緩慢,現有法律體系尚不能滿足物流業發展的制度保障需求,也無法有效應對物流業發展的潛在法律風險。可以說,“現代物流法律規范的零散無力和制度體系的缺漏空泛,仍處于自發盲目、無序推進狀態。”[1]因此,對我國物流立法問題進行重點關注和重新審視,加強我國物流法律體系建構的現實意義、制度設計和基本思路的研究,對于推進物流業的法治化建設具有重要價值。
一、我國物流法律體系建構的現實意義
1.克服現有物流法律規范分散的弊端。我國物流法律規范的主要問題在于相關規定過于分散,法律、法規、規章之間缺乏統一性和協調性,尚未對物流各環節進行系統整合,對物流功能的發揮難以起到引導、促進和保障作用。截至目前,我國關于物流業的法律規定仍然尚未走出這一困境。一方面,中央層面缺乏集中專門的物流立法,相關規定散見于《民法典》《郵政法》《電子商務法》《反恐怖主義法》《鄉村振興促進法》等法律之中;另一方面,地方層面的相關立法較為零散,分布在優化營商環境、數字經濟發展、大數據發展、平安社會建設、社會信用建設等法規、規章之中。因此,為克服物流法律規范分散的弊端,必須建構現代物流法律體系,以體現現代物流的時代特色和適應新興技術的發展要求,為全面依法治國夯實立法基礎。2.實現傳統物流行業轉型升級的需要。近10年來,我國物流行業呈現出突飛猛進的發展態勢,其主要原因在于積極打造了“物流+數字經濟”的發展模式,發揮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的優勢予以助推,加快從傳統物流向現代物流的轉型升級。這從另一個層面折射出,我國物流行業發展面臨著法律體系不健全問題,無法為物流行業轉型升級的“高質量、提質效、反內卷”目標提供立法層面的強有力制度保障。正如有學者所言,我國物流行業的發展緩慢態勢表明其面臨法律體系內在阻礙,需制定針對性立法進行疏解。[2]為此,我國需要綜合考慮物流行業轉型升級在管理體制、經濟條件、市場環境和人文因素等方面的法律需求,加快物流法律體系的建構,為物流行業轉型升級提供制度供給。3.統籌物流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要求。物流立法作為物流業規制的最有效手段,能夠進一步鞏固對內發展和對外貿易的基礎,實現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的結合。[3]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義之一,是我國全面依法治國的基本經驗和根本遵循,這對于我國物流法律體系的建構同樣具有重要的引領意義。一方面,從國內法治來看,現有物流法律規范尚未涵蓋物流領域的重要事項,也未能從技術上對物流行為進行普遍調整,導致宏觀層面的調控能力和微觀層面的約束能力均存在不足。另一方面,從涉外法治來看,我國加入WTO后,國外大型物流企業的進入對本土物流企業造成了強烈沖擊,但現有物流法律規范還沒有與先進的國際立法理念相匹配,也未能與國際貿易相關法律機制相接軌。因此,加快建構我國物流法律體系,貫徹落實統籌物流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重要部署,使物流立法既立足國情又與國際接軌,提高我國物流企業的綜合競爭力,并為我國物流企業進駐國際市場從法律制度層面保駕護航。
二、我國物流法律體系建構的制度設計
1.物流主體法律制度。“物流主體法指確立物流主體資格、明確物流主體權利義務和物流產業進入退出機制的法律規范。”[4]一方面,流主體是指從事物流行為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既包括作為個人形態的自然人,也包括作為組織形態的政府監管部門、物流企業、中介組織、物流協會商會等。物流主體法律制度即是對這些主體的權利義務、職權職責進行明確,從而實現對他們的規則控制和引導,保障物流活動在法治軌道上有序開展。另一方面,關于物流主體的法律制度還必須以明確其主體資格作為前提,即無論是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都必須滿足一定的條件才能具有從事物流活動的資格,這包括資格的取得、變更和消滅三個方面內容。2.物流行為法律制度。物流行為法律制度主要涉及物流主體在整個物流環節中的各種行為的法律規范,包括儲存、包裝、裝卸、搬運、運輸、配送、加工、信息處理、售后服務等等。由此可以看出,物流行為并不僅指貨物運輸過程中的行為,其已經延伸到發貨之前和收貨之后,貫穿于整個物流環節。但總體上來看,這些行為大多體現為民商事行為,主要體現為物流企業和物流服務對象之間。事實上,如果將政府的物流管理服務行為納入,物流行為的類型則會隨之增加行政行為,包括登記、報告、查驗、安檢、糾錯、整改等等。為此,物流行為法律制度應當分為兩個層面:一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關系的民商事行為,突出經營法律關系;二是調整不平等主體之間關系的行政行為,突出管理服務法律關系。3.物流管理法律制度。由于我國物流管理方面的法律規范并不多見,而且缺乏前瞻性和系統性,導致物流領域出現的新業務、新問題在管理層面上出現法律漏洞。如物流中轉后疊加運費的問題,就讓不少消費者苦不堪言。如果僅靠行業自律而不發揮政府監管的作用,那么對物流行為難以起到有效的規制,物流市場也會出現混亂的局面。這就要求,在尊重物流行為意思自治的基礎上,將公權力介入進行調適,發揮人民政府及其發改、金融、稅收、海關、郵政、檢驗檢疫、交通運輸、市場監管等主管部門的作用,在物流業組織管理上作出明確的規定。4.物流糾紛解決法律制度。有學者指出,我國物流法律規范的效力等級較低,且存在相互抵觸的情形,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比例較低,難以發揮有效解決物流糾紛的作用。[5]事實上,物流糾紛解決法律制度既包括實體性法律規范,以明確權利義務和法律責任,也需要程序性法律規范,以明確糾紛處理的方法步驟。對于前者而言,上述關于物流主體、行為和管理的法律制度已經予以解決;對于后者而言,目前的主要方式在于訴訟和仲裁兩種途徑。遺憾的是,由于物流領域的糾紛具有廣泛性和復雜性,爭議的處理機構和處理程序既可以依照法律規定,也可以根據雙方約定,因此物流仲裁具有明顯的優勢。因此,需要在我國法律體系建構過程中,對物流糾紛的類型進行細化分類的基礎上,再進行訴訟和仲裁的分流。
三、我國物流法律體系建構的基本思路
1.明確行政法的基本類型。物流法律體系建構的本質在于通過立法為物流業的各項活動提供法律依據,從而形成體系化的物流法律制度。物流本身是市場活動,因此針對物流的立法在法律基本類型上應定位為行政法,即主要從行政管理的角度明確各類物流主體的各種權利、義務以及職權、職責和法律責任。如日本先后制定的《物流法》《大店布局法》《貨物運輸事業法》《倉庫業法》等法律法規都是行政法,對該國物流業發展起到了極大推動作用。[6]作為行政法,我國物流法律體系的大部分規范內容應當納入行政法部門,充分發揮政府及其相關主管部門在物流業發展的作用,在堅持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優先的原則下,依法維護各類物流主體在物流活動中的合法權益。同時,作為行政法,在中央和地方進行物流立法時應當突出法律責任的威懾作用,以行政處罰和行政處分作為主要法律責任類型,輔之以必要的民事責任、治安管理處罰責任和刑事責任。2.選擇促進型立法定位。在確定行政法基本類型的前提下,我國物流立法接下來需要選擇立法定位。目前,理論上關于物流立法的定位存在管理型立法、監督性立法和促進型立法三種觀點。從實踐中來看,我國現有地方物流立法都是主要采用管理型和促進型兩種立法模式,前者如《烏魯木齊市寄遞物流安全管理條例》《佛山市寄遞物流安全管理辦法》,后者如《鄂州市現代物流業發展促進條例》《福建省促進現代物流業發展條例》。筆者主張物流立法應當選擇促進型立法或者以促進型為主的立法,以倡導性條款為主,以強制性條款為輔,打造以人為本、政府主導、多元參與、社會共治、統籌推進的物流發展大格局。這一立法定位要求針對政府的物流管理義務明確為強制性義務,并與法律責任對應起來;針對物流企業的發展義務明確為倡導性義務,以鼓勵、引導和支持為目標,不規定相應的法律責任。3.堅持立改廢釋多措并舉。我國物流立法是一項系統工程,在既有分散型法律規范體系以及缺乏物流基本法律的前提下,編纂物流法典的時機并不成熟。因此,從立法權能來看,建構物流法律體系的思路應當堅持立改廢釋多措并舉,不能急于制定中央層面的“物流法”,而是通過專項立法的形式進行規范補充,并對現有物流法律規范進行系統整合。具體包括:一是研究制定中央層面的“物流運輸法”和地方層面的“物流業發展促進條例”“快遞業促進條例”;二是對《郵政法》和“物流園區管理辦法”等中央現有立法進行修改;三是廢止《商品代理配送制行業管理若干規定》《商品條碼管理辦法》等陳舊的部門規章;四是對《民法典》《電子商務法》等新法中關于物流的內容進行立法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