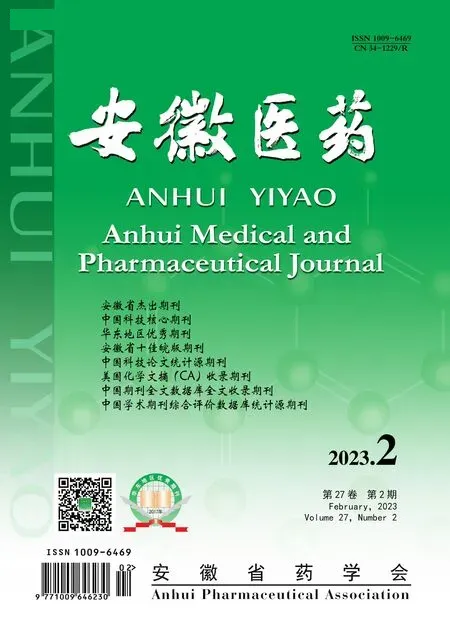乙酰膽堿受體抗體及蘭尼堿受體抗體雙陽性新生兒短暫性重癥肌無力1例
吳燕輝,張美玉,袁迎第,殷其改
新生兒短暫性重癥肌無力(transient neonatal myasthenia gravis,TNMG)是一種神經肌肉接頭疾病,由母體抗體經胎盤傳播引起,常見的抗體為乙酰膽堿受體(acetylcholine receptor,AChR)抗體、骨骼肌受體酪氨酸激酶(muscle—specific kinase,MuSK)抗體、脂蛋白受體相關蛋白4(lowdensity lipo-protein receptor-related protein 4,LRP4)抗體、蘭尼堿受體((ryanodine receptors antibody,RyR)抗體[1]。雙抗體陽性的重癥肌無力(myasthenia gravis,MG)很少發生,AChR及Musk雙抗體陽性的MG病例曾有少數報道,而關于AChR及RyR雙抗體陽性的TNMG則更為罕見。現報道南京醫科大學附屬連云港醫院2021年3月收治的1例AChR抗體與RyR抗體雙陽性的TNMG,并復習文獻資料,以提高臨床醫生對TNMG的認識。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男,30 min,因“氣促、呻吟30 min”收入新生兒重癥監護病房(NICU)。病兒系第2胎第1產,胎齡37+4周,因“母重癥肌無力、妊娠合并甲狀腺功能減退、妊娠期糖尿病、胎兒宮內窘迫”剖宮產娩出于南京醫科大學附屬連云港醫院產科,Apgar評分1 min 9分、5 min10分,羊水糞染,出生體質量2 750 g,病兒生后不久出現氣促、呻吟,以“新生兒濕肺、新生兒肺炎可能”收入院。其母親有3年重癥肌無力病史,孕早期及中期未服藥控制,孕后期出現眼瞼下垂,我院神經內科門診予溴吡斯的明片口服治療,外院查OGTT檢查提示妊娠期糖尿病,予飲食控制,孕期檢查提示妊娠合并甲狀腺功能減退,予甲狀腺素片口服治療。
體格檢查:足月兒貌,反應一般,哭聲響,呼吸稍促,伴呻吟,皮膚無青紫,前囟平軟,未見鼻扇,口唇紅,頸軟,可見輕度吸凹,雙肺呼吸音粗,未聞及明顯啰音,心率150次/分,律齊有力,未聞及病理性雜音。腹軟,臍無滲出,肝脾不大,未及包塊。肛門及外生殖器無畸形,四肢肌張力正常,原始反射減弱。
實驗室檢查:白細胞15.50×109/L,中性粒細胞比率 68.4 %,淋巴細胞百分比 21.5 %,血紅蛋白146 g/L,紅細胞4.04×1012/L,紅細胞壓積42.1 %,血小板277×109/L,C反應蛋白(CRP)0.14 mg/L;降鈣素原(PCT)0.06 μg/L;尿常規、血氣分析、肝腎功能、電解質等未見明顯異常。全胸正位片:兩肺紋理增多。
1.2 診療經過入院后予鼻導管吸氧,吸氧濃度為35%,流量1 L/min,頭孢唑肟抗感染、補液支持,維持內環境穩定等治療,入院第2天病兒開奶,表現為自行進奶差,吸吮能力弱,偶有吐奶,哭聲低,呼吸困難逐漸加重,表現為氣促加重,提高吸入氧濃度氧飽和度不能維持在正常范圍,予氣管插管機械通氣治療,改為鼻飼奶喂養,復查胸片未見明顯異常,動態檢測血常規及CRP、PCT等感染指標未見異常.血培養陰性,心超未見心內結構異常。結合母親有重癥肌無力的病史,予新斯的明試驗提示陽性,血清神經肌肉疾病檢測提示血RyR抗體(+),AchR抗體(+)。結合病兒臨床表現及實驗室檢查,病兒TNMG診斷明確,予溴吡斯的明片口服1毫升/次,2次/天,靜脈營養補液等對癥支持治療。
2 結果
病兒呼吸困難逐漸減輕,生后1周撤機并逐漸停氧氣,病兒自行進奶逐漸好轉,吸吮有力,于生后第15天治愈出院。出院后繼續口服溴吡斯的明片2周停藥,出院后門診隨訪至3月,病兒吃奶好,智力及體格發育在正常范圍。
3 討論
TNMG是患有自身免疫性MG的母親將抗體被動轉移給新生兒所致,發病率約為MG母親分娩嬰兒的 10%~20%[1-2]。TNMG 可發生在具有 AChR、MuSK、LRP4或RyR自身抗體的所有MG亞群中,該病主要表現為短暫性的呼吸困難、吸吮能力差、進食困難、哭聲弱、上瞼下垂、肌張力減弱等癥狀,該病兒在生后第2天出現呼吸困難,吃奶吸吮力差,其出生前胎兒宮內窘迫,出生時羊水糞染,容易被誤診為“新生兒肺炎、新生兒敗血癥、新生兒缺氧缺血性腦病、宮內感染”等疾病,但病兒血常規、降鈣素原等感染指標未見異常,Torch檢查及血培養陰性,不支持宮內感染及敗血癥的診斷,病兒胸片未見明顯吸入性肺炎表現,頭顱B超未見異常,可以排除新生兒肺炎、新生兒缺氧缺血性腦病的診斷。結合其母親病史及臨床表現,新斯的明試驗陽性,后續完善血清神經肌肉疾病檢測RyR抗體(+)、AchR抗體(+),故考慮病兒TNMG。
TNMG多為暫時性,且在臨床容易被忽視。新生兒多在出生后3~72 h出現癥狀,且臨床表現往往不典型[3]。對于TNMG的診斷主要根據臨床表現,結合母親病史,完善相關的實驗室檢查(包括抗體檢測、神經電生理和膽堿酯酶抑制劑試驗給藥),并排除其他疾病可診斷[4]。該病兒生后主要表現為氣促、自行進奶差、吞咽困難、吸吮力弱,后呼吸困難加重,結合母親存在重癥肌無力,新斯的明試驗陽性,抗體檢測提示AChR及RyR抗體陽性,故TNMG可診斷。該病兒血清學檢測特點為AChR及RyR雙抗體陽性,雙抗體陽性的MG較少見,筆者檢索了1990年至2021年9月國內外的文獻,報道的重癥肌無力雙抗體陽性的文章共16篇,其中2篇報道了AChR和LRP4抗體均陽性的MG,其余均為AChR及MuSK雙抗體陽性的MG,但AChR與RyR雙抗體均陽性的MG病暫未發現相關報道,且在新生兒中暫未見雙抗體陽性的MG報道。劉舉等[5]發現AChR和MuSK抗體雙陽性MG病人病情可能更嚴重,更易出現肌無力危象及胸腺增生性病變。也有研究發現AChR和LRP4雙抗體陽性的MG病人病情比單抗體陽性的MG嚴重[6]。目前關于AChR與RyR雙抗體陽性的相關文獻較少,研究發現各種胸腺異常,如胸腺增生、胸腺瘤等常見于AChR-MG[7],抗AChR抗體可抗胎兒型和成人型AChR。TNMG通常是一種短暫的疾病,如果母親有選擇性地抑制胎兒型AChR功能的抗體,其所生的嬰兒可能會導致嚴重和持久的肌病特征,通常伴有胎兒關節攣縮,這被稱為胎兒AChR失活綜合征[8]。Oxkoui等[9]報道了1例33歲AChR抗體陽性的母親所生的三個孩子都因罹患TNMG入住新生兒重癥監護病房(NICU),并經治療肌無力癥狀改善,長期的隨訪發現三個孩子在后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語言障礙和聽力損失。也有研究發現并發胸腺瘤的MG病人RyR抗體存在高表達,并且當RyR抗體陽性的晚發型MG病情更嚴重[10],但是RyR抗體陽性的病例在TNMG中比較罕見。該病兒臨床癥狀雖然較重,治療過程中給予呼吸機輔助呼吸,但治療過程順利,病情恢復快,病情危重程度與其血清AChR及RyR抗體雙陽性無明顯相關性,因此在這兩種抗體均陽性的病例中病情是否也重于單獨抗體陽性,以及是否更易合并胸腺瘤等,仍需未來長期的隨訪及研究。
治療方面,癥狀較輕的病兒主要為支持治療,包括留置胃管喂養及輔助通氣。新生兒MG的發生與母親MG嚴重程度和抗體濃度之間尚未發現密切的相關性,因此根據母親MG的情況很難預測新生兒MG的發生和嚴重程度[11],且因病兒呼吸困難和吞咽困難多在生后48~72 h內出現[12],故建議MG母親所生新生兒均轉入NICU密切監護至少3 d。在喂養方面應鼓勵MG母親母乳喂養[13]。藥物治療方面主要包括膽堿酯酶抑制劑、免疫調節和免疫抑制藥物。免疫調節和免疫抑制是較有效的藥物治療方法,但是免疫調節和免疫抑制通常有更大的副作用,輕度病兒可酌情使用膽堿酯酶抑制劑,重癥病兒可行靜脈注射免疫球蛋白和血漿置換治療[14]。新生兒Fc受體(FcRn)靶向劑是一種新的治療MG的方法,通過拮抗新生兒Fc 受體導致循環 IgG 和特異性自身抗體的快速減少,FcRn靶向劑的治療潛力已經在MuSK-MG小鼠模型中得到證實[15]。該病兒住院期間給予小劑量的溴吡斯的明片口服1毫克/次,2次/天,并予機械通氣、鼻飼管喂養、靜脈營養補液支持等治療,病情逐漸好轉,生后1周撤機,并逐漸過渡至全胃腸喂養,出院后繼續口服溴吡斯的明片2周后停藥。停藥的時間與其母親抗體在病兒體內的消失速度有關系,研究顯示,母體的抗體降解時間大約在2周,部分可持續數月[12]。
綜上所述,盡管TNMG發病率低,90%TNMG的病兒在兩個月內完全康復,無后遺癥,但該病嚴重時可引起呼吸衰竭甚至死亡,少數新生兒會發展成幼兒MG[16]。臨床上雙抗體陽性的MG較為罕見,尤其是AChR及RyR抗體均陽性的目前暫未見報道,雙抗體陽性MG病情往往重于單抗體陽性的MG,不同的自身抗體可能對新生兒MG有不同的作用,故特異性自身抗體的檢測對于孕產婦、胎兒和新生兒MG的診斷和處理尤為重要。少部分TNMG會出現AChR失活綜合征,導致永久的殘疾,因此對于有TNMG病史的病兒應長期隨訪肌病體征及有無構音障礙或聽力障礙的[17],以給予早期治療,改善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