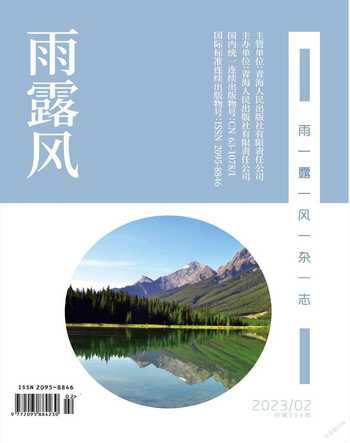“美是生活”視域下的《羅生門》研究

羅生門原指日本平安時期京都城的南門“羅城門”,在十世紀(jì)末因頻發(fā)災(zāi)害而荒廢。最早關(guān)于羅生門的藝術(shù)作品是芥川龍之介取材于平安時期民間傳說故事集《今昔物語集》中佛教徒用來勸告世人的一個寓言,隨后于1915年在《帝國文學(xué)》發(fā)表了短篇小說《羅生門》。20世紀(jì)50年代,黑澤明融合芥川龍之介小說《竹林中》的故事情節(jié)和小說《羅生門》的環(huán)境和人性結(jié)構(gòu),翻拍出電影《羅生門》。通過電影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獲得的贊譽,“羅生門”作為日本現(xiàn)代文學(xué)的代表符號,開始愈發(fā)頻繁地出現(xiàn)在人們的視線之中。現(xiàn)今,“羅生門”已經(jīng)突破了藝術(shù)的界限,成為當(dāng)代社會中“人性復(fù)雜”反思的文化規(guī)約符號,大量藝術(shù)活動均借“羅生門”之口宣泄內(nèi)在的情緒。但關(guān)于“羅生門”的研究多從其文學(xué)藝術(shù)本身所傳達出的人性反思角度進行,或?qū)⑵湟曌魈囟ōh(huán)境下的“日式”藝術(shù)風(fēng)格,少有將其視作客觀環(huán)境與主觀內(nèi)在共同造就的典型藝術(shù)形式。而車爾尼雪夫斯基(以下簡稱“車氏”)的“美是生活”的美學(xué)理論,或許能用來更好地解讀《羅生門》所反映的藝術(shù)內(nèi)涵。
一、基于生活美學(xué)的研究方法
車氏在其著作《生活與美學(xué)》中提出的“美是生活”理論,主張“任何事物,凡是顯示出生活或使我們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肯定美是“使我們想起人及人類生活的那種生活”,而美的意義在于自然界中美的事物對“作為人的一種暗示”。關(guān)于“美”的定義,車氏說道,“美的事物在人心中所喚起的感覺,是類似我們當(dāng)著親愛的人面前時洋溢于我們心中的那種愉悅。” [1]6認(rèn)為美是人對現(xiàn)實生活的主觀感知,同時認(rèn)可了美是現(xiàn)實生活與人主觀精神的共同產(chǎn)物,完善了傳統(tǒng)美學(xué)或現(xiàn)實主義或浪漫主義的片面論斷。這就意味著美的價值在于人對生活態(tài)度的反思,也在唯物主義立場上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觀能動性,認(rèn)為“生活中的各種事件雖然不由人來決定,這些事件的精神卻是由人的性格來決定的。” [1]46因此從生活美學(xué)的研究方法來看《羅生門》,主要分為兩個方向的交互論證——現(xiàn)實與觀念。現(xiàn)實方面,體現(xiàn)為不以個人的意識為轉(zhuǎn)移的客觀美;觀念方面體現(xiàn)為由人的認(rèn)知所把握的主觀美。
車氏主張“真正的最高的美正是人在現(xiàn)實世界中所遇到的美,而不是藝術(shù)所創(chuàng)造的美”,[1]11現(xiàn)實美是第一性的存在。芥川龍之介也同樣注重現(xiàn)實環(huán)境對藝術(shù)品的指涉作用。在《侏儒的話》一文中,龍之介認(rèn)為“為了能夠看上去最美,(藝術(shù))必須被整個時代的精神氛圍和流行所包圍。”而在車氏眼中,藝術(shù)只是現(xiàn)實無法得到滿足而不得已選擇的替代品。如不在海邊的人同樣可以通過一幅描繪大海的畫來感受大海的波瀾壯闊,只是不如看海本身感受強烈。但不在海邊的人可以欣賞畫作的原因在于他真實的感受過大海本身。一件藝術(shù)品之所以能夠引起藝術(shù)觀者的強烈共鳴,卻是藝術(shù)家與讀者對于現(xiàn)實共同的奔赴:一方面是由于藝術(shù)家從現(xiàn)實抽象而來的藝術(shù)表達,另一方面是由于觀者在藝術(shù)品中讀到了過去實在的發(fā)生。因為兩者共處一個文化語言之中,所以藝術(shù)家的個人化言語才能夠被觀者所捕捉并識別。如果剔除了共性的現(xiàn)實因素,就像對牛彈琴,牛是無法理解《羅生門》的復(fù)雜人性的。
在觀念方面,芥川龍之介同樣重視人性本身對于藝術(shù)的浪漫建構(gòu)。他在《侏儒的話》中提到,如果完全的依附于現(xiàn)實,所產(chǎn)生的詩歌如“‘地球旋轉(zhuǎn)幾度幾分,總不如‘日落西方來得優(yōu)美。”他同樣認(rèn)為,烏托邦之所以不存在,就在于烏托邦的成立必須剔除人的本性,而剔除本性的烏托邦就變成了不完美的虛假所在。這一點與車氏的美學(xué)理論幾乎吻合。雖然車氏認(rèn)為現(xiàn)實是美的終極源泉,但不等于主觀價值在審美活動中毫無意義。生活終歸為人的生命活動,美是主觀對現(xiàn)實生活的感知,“美是生活”是人的生活,是人類社會所規(guī)定的生活。所以“自然界的美的事物,只有作為人的一種暗示才有美的意義。” [1]10因此藝術(shù)作為審美活動的集中性表達,因其更具目的性,即直面人內(nèi)心復(fù)雜的情感而比現(xiàn)實更容易感動人本身。
而關(guān)于客觀與主觀研究的結(jié)合,還存在“孰高孰低”的偏好傾向。如部分學(xué)者研究認(rèn)為《羅生門》偏好主觀觀念的表達,將其視為人內(nèi)心矛盾的悲劇式對立;部分學(xué)者則將該作品視作特定社會環(huán)境下的反映,著重探討作品背后的必然性傾向。而車氏雖然是個徹底的現(xiàn)實主義傾向美學(xué)家,但也從未否定過浪漫的人性的意義,只是將其視作第二性的存在。同樣,作為藝術(shù)研究手法的生活美學(xué),也不應(yīng)該片面地注重或主觀或客觀一點,生活是人性的人在現(xiàn)實世界的活動,二者缺一不可。《羅生門》所反映的藝術(shù)內(nèi)涵,當(dāng)為社會語言指涉下的言語表達,悲劇式的社會背景由諸多悲劇的個體所組成,而單一個體雖有其獨特性,卻依舊以社會為依托。
二、“羅生門”的發(fā)生
雖然電影《羅生門》自小說《羅生門》和《竹林中》改編而來,但由于藝術(shù)發(fā)生的年代不同,結(jié)尾處所體現(xiàn)的“人性本質(zhì)”也是天差地別。“每一代的美都是而且也應(yīng)該是為那一代而存在:它毫不破壞和諧,毫不違反那一代的美的要求。” [1]48人性的差異皆因藝術(shù)家所處的不同年代,小說以眾人趨惡為結(jié)果,電影卻在眾惡之間保有善的火苗,因而產(chǎn)生了兩種截然相反的藝術(shù)體驗。
(一)芥川龍之介:人性本惡
小說《羅生門》講述了一位被主人解雇的家將到羅城門下避雨時,目睹了一位老太婆為生計而做出與道德相違背的“惡”事,進而促使家將向現(xiàn)實的“惡”低頭的悲哀故事。作為惡行的悲劇,其中傾盆大雨、破敗的城門化為“俄狄浦斯王的神諭”,無一不透露出社會現(xiàn)實“推著人走向墮落”的無奈,更加深化了“善”的難得。
車氏認(rèn)為,現(xiàn)實作為第一性而存在,是藝術(shù)的唯一源泉,不同藝術(shù)的發(fā)生緣由當(dāng)以社會背景為準(zhǔn)。芥川龍之介出生于十九世紀(jì)末,生活于二十世紀(jì)初,正處于日本作為一戰(zhàn)戰(zhàn)勝國,民間思想激變,而自由民主與明治權(quán)威并存的大正年代。社會范圍內(nèi),衰落的傳統(tǒng)武士精神與新匯的自由民主精神交織。如原文所說“在京都,地震啦,旋風(fēng)啦,失火啦,饑餓啦,一樁樁災(zāi)難接連發(fā)生”。時代的發(fā)展并未改變民間的破敗,反而使民眾生活的困苦不斷加劇。同時在“人性覺醒”下,民眾不再麻木不仁,對于痛苦的認(rèn)知也愈發(fā)深刻。于龍之介個人而言,相傳他初戀因養(yǎng)父的極力反對而失敗。自此感受到人性的丑陋與自私,認(rèn)為愛情中交織著利己主義。最終在社會背景的重壓下因生存的痛苦而倒向了虛無主義。在這種頗具批判和諷刺意義的認(rèn)知中,龍之介的人生觀轉(zhuǎn)為極端消極之下的利己主義“性惡觀”,并誕生了偉大的小說《羅生門》。
但不少學(xué)者主張“羅生門”是老太婆與家將內(nèi)心的外在符號,反映出悲觀意識下“人心向惡”的本質(zhì)。這種觀點無疑僅停留于符號的外在形式敘述上,造成了因果關(guān)系的顛倒。所謂“一切美術(shù)作品毫無例外的一個作用,就是再現(xiàn)自然和生活”,[1]91小說中昏暗壓抑的背景無疑就是龍之介在其獨特時代下個人與社會現(xiàn)實的縮影。羅生門由曾經(jīng)“繁華”向“破敗”的發(fā)展也映照著“善”轉(zhuǎn)“惡”的動態(tài)變化,成為了當(dāng)下“社會惡”的符號。“羅生門”在此處即獲得了兩個方向的所指,水面之上的部分體現(xiàn)為人物行為在道德屬性層面的轉(zhuǎn)變,即外在形式的敘述;水面之下所指為時代背景下的觀念縮影,羅生門的破敗是由消極的社會發(fā)展所致而非人物的主觀活動。根據(jù)文本內(nèi)容可知,在羅生門破敗以前,家將是一位堅守“餓死是小,失節(jié)是大”理念的道德先生。其從惡則是因被趕出美好舒適的環(huán)境后,生計受到了威脅,自此感悟到“當(dāng)全社會都處于一個惡的時代中,只有成為惡本身才能夠得以生存”的消極觀念,老太婆只是一個導(dǎo)火索罷了。所以家將的從惡并非僅僅個人的道德喜好,其本身所映射的是作為故事的當(dāng)下的社會語言,是主觀之于現(xiàn)實的不可抗力的具體顯現(xiàn)。故而當(dāng)感嘆“羅生門外,是黑漆漆的夜幕”時,不應(yīng)停留在對具體人物的道德批評上,忽略現(xiàn)實因素去謾罵家將的“棄義”行為也缺乏深層的反思價值。悲劇所帶來的“破壞式”演繹目的在于對“善”的向往以及強化對能夠引領(lǐng)“善”發(fā)展的良性社會現(xiàn)實的追求欲望。
(二)黑澤明:向善而生
拍攝于上世紀(jì)五十年代的電影《羅生門》由黑澤明同時改編自芥川龍之介《竹林中》和《羅生門》兩篇小說。電影首先沿用了《羅生門》的名字,并將電影情節(jié)同樣置于破敗的羅生門之下,由對話三人的言語描述而產(chǎn)生。結(jié)果與內(nèi)容方面則更多地源自《竹林中》一文。該文講述了武士金澤武弘攜妻真砂返鄉(xiāng),途中遇到大盜多襄丸,本欲同行卻反遭多襄丸迫害。武弘死后,多襄丸和真砂各奔東西。但二者被官府捉拿對質(zhì)公堂時,對于武弘的死因卻產(chǎn)生了三種截然不同的故事(武弘的魂魄被巫女喚醒)。這篇小說以獨特的文學(xué)性描述了人在面臨諸多選擇的時候,最終都倒向了利于自身的選擇,并以此為基礎(chǔ)編織謊言,扭曲現(xiàn)實甚至蒙騙自己,從而讓自身生活在一個利己謊言所建構(gòu)的“自我舒適環(huán)境”中。《竹林中》與小說《羅生門》不同,雖然同樣表現(xiàn)為“惡”的形式,但有著不同的追求。《羅生門》以破壞“善”來珍惜“善”,而《竹林中》不論武弘、多襄丸還是真砂都希望給自身樹立一個“善”的形象,通過對“惡”的掩蓋來體現(xiàn)對“善”的追求。
而電影創(chuàng)造性地將直接的文學(xué)敘事發(fā)展為樵夫,雜役,僧人三人對話的轉(zhuǎn)述,從而把《竹林中》這一文學(xué)故事以事件在場者和藝術(shù)觀者的身份進行了初步的反思。在三重敘事中,大盜多襄丸自認(rèn)兇手,但是由于真砂的挑撥離間所致;真砂聲稱受到多襄丸強暴,后被丈夫鄙視不潔,失手之下誤殺丈夫;武弘(女巫)則聲稱真砂與多襄丸通奸,真砂教唆多襄丸弒夫后遭到鄙視,故多襄丸將武弘釋放,但武弘自認(rèn)違背武士精神,自殺而亡。但黑澤明通過轉(zhuǎn)述手段,額外增添了一個角色——樵夫。樵夫雖然像前三人一樣為了掩蓋自己因偷竊武弘財產(chǎn)的事實而撒謊,但最終仍選擇了善的一面,收養(yǎng)了武士夫妻的遺嬰。自此,黑澤明的《羅生門》雖然在敘事過程上與芥川龍之介保持一致,但就結(jié)果而言電影反而透露出在惡的世界中善念猶存的傾向。
從黑澤明所處時代來看,“善”的萌芽卻是其原境下的人性發(fā)展。二十世紀(jì)五十年代,二戰(zhàn)結(jié)束,與芥川龍之介時期相反,該時期的日本作為戰(zhàn)敗國被美國駐兵占領(lǐng),取消了國內(nèi)的法西斯條例,更為注重戰(zhàn)后經(jīng)濟的恢復(fù)。因此此時的日本經(jīng)由窮兵黷武之下的高壓反倒使得封建思想的影響力有所衰減,美國的全方位介入也讓民主思想更加全面深入。即使此時國內(nèi)環(huán)境依舊千瘡百孔,但積極的經(jīng)濟建設(shè)活動讓此時的日本社會充滿對未來的希冀。從文化哲學(xué)的角度看,歷史是當(dāng)下認(rèn)知中的歷史,原境化的理解得以讓今人能夠以符合當(dāng)下實踐的眼光重新審視歷史上的事件。因此“黑澤明認(rèn)為人即使是在貧困的處境中也能戰(zhàn)勝內(nèi)心的自私和卑鄙,使人墮落的并不是環(huán)境,而是人內(nèi)心的軟弱和欲望”。[2]電影的思想始終站在社會人道反思基礎(chǔ)上,表達了對封建倫理的嘲諷及人性自私的無奈。藝術(shù)品指導(dǎo)思想的轉(zhuǎn)變,實為社會現(xiàn)實的變化所致。樵夫的善也終于突破惡的重壓,讓行腳僧“終于能夠相信人了”。
三、“羅生門”的悲劇
即使電影以樵夫的善而結(jié)尾,但整體而言與小說一樣傳達出罪惡社會中人性的復(fù)雜,是一種悲劇式的演說。“無論悲劇人的苦難和死亡的原因是偶然還是必然,苦難和死亡反正總是可怕的。” [1]33車氏將悲劇的概念置于“美是生活”理論的統(tǒng)籌之下,認(rèn)為美的感受類似于人見到親人的愉悅,而非痛苦的回憶,悲劇則作為“美的反面”而存在,是生活中不美的體現(xiàn)。如果以此為基礎(chǔ)來看《羅生門》,拔頭發(fā)的老太婆、做強盜的家將以及掩蓋事實的多襄丸、武弘、真砂都是迫害美好生活的“惡”,是“丑陋的畸形人”,而非真實人性的體現(xiàn)。固然社會的惡需要避免和抵制,但辯證來看,美的確定需要反面的襯托,悲劇的本質(zhì)如魯迅先生所言,是通過將美毀滅給人看而得到實現(xiàn)的。一味的反感家將從惡的結(jié)局沒有意義,單純的研究爭辯武弘之死的真相更沒有任何價值。累積成“羅生門外一片漆黑”的惡固然需要道德的反思,但文學(xué)藝術(shù)真正的價值是在悲劇中的反思而不是回避。
從古典美學(xué)來看,悲劇多與命運的概念相關(guān)聯(lián),悲劇人物的行為選擇以及悲劇事件的發(fā)生都是因為與命運發(fā)生沖突而產(chǎn)生的結(jié)果。黑格爾認(rèn)為,當(dāng)沖突發(fā)生時,“每一方拿來作為自己所堅持的那種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內(nèi)容的卻只能是把同樣有辯護理由的對方否定掉或破壞掉。因此,雙方都在維護倫理理想之中而且就通過實現(xiàn)這種倫理理想而陷入罪過中。”[3]在《羅生門》的演繹中,所有“人性的復(fù)雜”都源于以自身利益為中心的考量。多襄丸掩飾暴行的原因是貪戀真砂美貌,維護威武大盜的形象,聲稱受到真砂的教唆挑撥而殺死武弘;真砂為維護貞潔的名聲,聲稱受到多襄丸的強暴和武弘的鄙視而失手殺死武弘;武弘(女巫)為了維護武士精神,聲稱在受到侮辱后自殺而亡;樵夫為了掩蓋自身盜竊的行為,主張真砂的不潔。正因為如此,在真相被掩蓋的事實中,樵夫受到了道德倫理的譴責(zé),讓“這世上,無法再相信別人”。但唯心觀念指導(dǎo)下的黑格爾美學(xué)認(rèn)為悲劇沖突的誕生及毀滅的必然是由于絕對理念所規(guī)定的宿命,并非悲劇人物所致。將悲劇的發(fā)生歸結(jié)于絕對的精神力量,由于宿命的不可抵抗性而忽視了悲劇對于現(xiàn)實的抽象反思和指導(dǎo)價值。車氏在唯物立場的反思中,強調(diào)命運一說為野蠻人的妄想,而忽略了歷史發(fā)展以及社會環(huán)境的必然。從而將悲劇的價值從個體引以為戒的內(nèi)省上升到社會發(fā)展的反思的高度,開始從外部條件尋找悲劇的內(nèi)因,為馬克思主義美學(xué)奠定了基礎(chǔ)。
辯證來看,藝術(shù)典型的悲劇是社會悲劇的縮影。芥川龍之介認(rèn)為“人性的,太人性的東西”都是動物性的內(nèi)因所釀造。人首先作為動物屬性的生命個體,生存是其生命活動的基礎(chǔ)和最初動因。老太婆選擇拔私人的頭發(fā)是出于生計的需要,家將作強盜也是為了謀生,否則將會餓死。社會性的語言則賦予了“惡-活”與“善-死”的對立,進一步推動了悲劇事件的發(fā)生。但文明的發(fā)展和文化的規(guī)約為動物性的人賦予了社會性的道德意義。所以社會的人會因為與道德的相背而產(chǎn)生內(nèi)在的譴責(zé)。同樣,從藝術(shù)觀者的角度來看,如龍之介所說“悲劇就是,對自己的羞恥行為敢于擔(dān)當(dāng)。因此,很多人共通的悲劇起著排泄作用”。正因為觀眾在《羅生門》中看到了自身的影子及過去歷史的現(xiàn)實,方才強化悲劇的認(rèn)知,進一步反思“復(fù)雜人性”的惡。相比之下,武弘之死的真相反倒不那么重要了。
四、結(jié)語
當(dāng)今社會,人們的生活愈發(fā)藝術(shù)化,日常瑣碎的生活越來越受到關(guān)注;藝術(shù)愈發(fā)生活化,平常的人性愈發(fā)頻繁地通過藝術(shù)的形式得到審美性的顯現(xiàn)。通過對生活美學(xué)的探討,更能審視《羅生門》對于社會環(huán)境的抽象總結(jié),從而充分發(fā)揮主觀能動性來反思內(nèi)化的道德認(rèn)知和道德行為選擇,從而引導(dǎo)“當(dāng)下善”的發(fā)展,而不是停留在劇情真假的形式爭辯當(dāng)中。
作者簡介:高浩軒(1997—),男,陜西榆林人,蘭州交通大學(xué)藝術(shù)設(shè)計學(xué)院2020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藝術(shù)設(shè)計專業(yè)數(shù)字媒體藝術(shù)。
注釋:
〔1〕車爾尼雪夫斯基.生活與美學(xué)[M].周揚,譯.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57.
〔2〕范妮.開啟日本電影現(xiàn)代意識的人道主義者黑澤明——解析《羅生門》的導(dǎo)演表現(xiàn)藝術(shù)[J].電影評介, 2012(8):18-19,21.
〔3〕黑格爾.美學(xué):第3卷下冊[M].朱光潛,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1: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