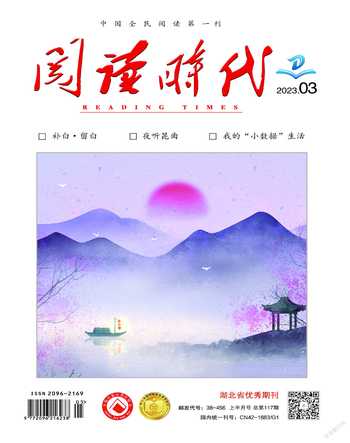補(bǔ)白·留白
陳洪波

曾有一位畫家在自己的畫作上題款:“非經(jīng)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涂鴉怒梅數(shù)枝,以為某某賢契補(bǔ)白。”所謂“補(bǔ)白”就是填補(bǔ)空白,放在這個畫家的具體語境來分析,他所說的“補(bǔ)白”其實(shí)是在款識上對自己作品的自謙之辭,意思是說自己的作品只能供人填補(bǔ)墻壁上的空白。
我對“補(bǔ)白”的理解領(lǐng)悟得遲,也因此,對未能“補(bǔ)白”的遺憾至今記憶尤深。我還記得1973年冬天,那年我15歲,農(nóng)閑時的鄉(xiāng)親們善意起哄要我寫春聯(lián)。我會寫毛筆字,但不是書法家。或者說我不是書法家,但會寫毛筆字。我的字寫得不好,可當(dāng)年村里沒有人比我的字寫得更好,正應(yīng)了那句俗話:“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寫毛筆字的那一天,陽光普照,惠風(fēng)和暢。眾人在露天場地擺放一張八仙桌,德高望重的長老金旺爺親自磨墨鋪紙,幾十個大人小孩圍觀捧場。我初生牛犢不怕虎,一上午寫了16副對聯(lián),每家送一副,寫完一副就贏得一陣喝彩。鄉(xiāng)親鄉(xiāng)情,感人至深,我真想唱一句家鄉(xiāng)的黃梅戲《女附馬》:“手提羊毫喜洋洋。”這也成為我印象里最溫馨、最難忘的寫毛筆字經(jīng)歷。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dāng)時已惘然。”后來,我寫毛筆字就不那么怯場了,而那些美好的事和真摯的情至今仍留在我的記憶之中。只是回想起來,在當(dāng)時我對立志和力行卻并不敏感,甚至連“補(bǔ)白”之類的謙辭都不會用。如果我能趁熱打鐵,持之以恒,勤學(xué)苦練,也許會在書法上有所成就。遺憾的是,人生沒有如果,也沒有“補(bǔ)白”。
我的字寫得不好,但向我求字的不少,我通常都委婉拒絕,打算“敝帚自珍”。回想起來,近二三十年間,收藏我字者不超過10人,主要是我的家人和親戚,因?yàn)椤凹页蟛豢赏鈸P(yáng)”,但“內(nèi)揚(yáng)”似乎能被人容忍。即便是“內(nèi)揚(yáng)”,我也覺得寫之有愧,卻之無情。與其卻之無情,不如寫之有愧。或者說寧可寫之有愧,不可卻之無情。總之,寧丟面子,勿傷感情。親人索字,有求必應(yīng)。只不過,寫來寫去就那么幾個字,諸如“業(yè)精于勤”“天道酬勤”“澹泊明志”“寧靜致遠(yuǎn)”“厚德載物”“上善若水”“家和萬事興”等等。
漢代揚(yáng)雄的《法言·問神》云:“言,心聲也;書,心畫也。”明代唐順之的《跋自書康節(jié)詩送王龍溪后》云:“詩,心聲也;字,心畫也。”可見,寫字送人從本質(zhì)上講是表達(dá)心情、心意、心愿。親人說是討我的“墨寶”,我說是供親人家中墻壁“補(bǔ)白”。我寫字既“不為稻粱謀,不作名利求”,也不為修身養(yǎng)性,延年益壽,個中寄托,唯有情義。無巧不成書,我在校對拙著《漣漪漸消》清樣時,發(fā)現(xiàn)“情義無價”版塊有點(diǎn)空白,心想既然主題吻合,不妨以此文“補(bǔ)白”。不料,編輯說那點(diǎn)空白是有意“留白”,不補(bǔ)為好。
何謂“留白”?“留白”就是留下空白。一般是指書畫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為使整個作品畫面、章法更為協(xié)調(diào)精美而有意留下相應(yīng)的空白,留有想象的空間。從藝術(shù)角度而言,留白就是以“空白”為載體,進(jìn)而營造出美的意境。例如,南宋馬遠(yuǎn)的《寒江獨(dú)釣圖》,只見一葉扁舟,一位漁翁在垂釣,整幅畫僅施淡墨,寥寥數(shù)筆勾出水紋,卻讓人感到煙波浩渺,一望無際。如此以無勝有的留白藝術(shù),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正所謂“此處無物勝有物”。現(xiàn)在,圖書版式裝幀設(shè)計(jì)也時興運(yùn)用適當(dāng)大小的留白,頁面上的元素之間有足夠的空隙,因而平添了遐想的美感。
“補(bǔ)白”是填補(bǔ)空白,“留白”是留下空白,虛實(shí)相生相伴,變幻無窮無盡,兩者都是博大精深的藝術(shù)手法。是補(bǔ)是留?各有其理,當(dāng)以自圓其說為佳。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先秦時期韓非的《韓非子·難一》記載:“楚人有鬻盾與矛者,譽(yù)之曰:‘吾盾之堅(jiān),物莫能陷也。又譽(yù)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yīng)也。”“補(bǔ)白”與“留白”之爭,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似有異曲同工之處。
從書畫說開去,文章也是如此。“補(bǔ)白”這個詞條也可指書籍、報紙、刊物上用來填補(bǔ)空白的短小文章。例如,寫作本文的初衷即擬作補(bǔ)白。我并非美學(xué)內(nèi)行,但也附庸風(fēng)雅,妄議“補(bǔ)白”與“留白”,深感人生不易,矛盾無時不在,無處不有。所以要崇尚哲學(xué),研修辯證法,參悟并享受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的奧妙與樂趣,順其自然,隨遇而安。
(作者系本刊特約撰稿人)
責(zé)編: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