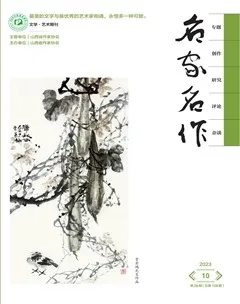論唐詩中“牧童”意象的形成與意蘊
李悅誠
詩歌與鄉土一樣,都是人的精神寄托。牧童(也叫“牧豎”)是農業文明的產物。唐朝,牧童這一看似不起眼的形象走進文人的詩歌之中:漂泊無依之時,“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1]1248的畫面樸率真切又溫暖慰藉;興廢征戰之時,“御路疊民冢,臺基聚牧童”[1]8061的場景不動聲色卻凄惻感傷;閑臥松云之時,“道心及牧童,世事問樵客”[1]1247的意境可謂一時興會,理在言外;身不由己時,“青山青草里,一笛一蓑衣”[1]9610的詩句寫盡了無拘無束、瀟灑自得的神趣。總體來看,詩中的牧童形象既寄托著中國文人對于安寧、自由的向往和對淳樸人性的追求,也是時代變遷、傳統影響和作家藝術建構的產物。
一、牧童形象的興起與入詩
(一)先秦文學作品中牧童形象溯源
農事與田園在中國詩歌中登場很早,然而牧童成為詩歌中的意象卻經歷了漫長的過程。通過梳理相關文獻,我們認為先秦文學作品中,除《莊子》以外罕有引人注目的“牧童”形象,即便是在被稱為“先秦生活百科全書”的《詩經》中,也只有對底層牧者境況的簡單描寫。通過閱讀《莊子》《詩經》相關部分可以發現,兩部作品預示了唐代詩人對于牧童形象的不同寫作思路。
《莊子》中的牧童是具有“象征性”的牧童形象。《莊子·徐無鬼》中記載了“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2]677的故事。黃帝到達襄城的原野,隨行的“七圣”都迷路了。此時一牧馬小童現身,自稱知曉“大隗”的所在,并宣示治國之道。《莊子》中的牧童“微言大義”,本質上是“道”的代言者,是想象力非凡的文人“建構”出來的形象。作者無意于作品的“真實性”,但這種借牧童之口表達出的“無為”思想,以及假托一物抒發思想的“寓言”手法,卻深深影響了后世。到了唐代,大部分詩歌中的“牧童”形象都是文人理想化的“符號”,其實質是作家的個人寄托,少部分仍是《莊子》中“巖穴從來出帝師”[1]7403精神的延續。
與之相對,《詩經》中的“牧人”形象則偏向“現實性”。文學起源于勞動,作為農業大國,牛、羊一直是重要的祭祀和生活用品。《小雅·無羊》就有對于牧羊者的描寫:“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糇,三十維物。”[3]589雖然詩人只是進行了單純的描寫,并未以審美的眼光進行觀察,但這種以現實之眼觀照底層人物的傾向,卻為后世樂府詩人所繼承。
總體來看,唐代詩人的牧童書寫繼承了以《莊子》為源頭的浪漫主義傳統和魏晉山水詩的創作方法。他們取景的視野更加寬廣,創作方法上又常常“以我觀物”,具體體現在:第一,牧童形象更加豐富,唐人常描繪牧童之“歸”、牧童之“游”、牧童之“唱”等,這些動作實際上延續了《莊子》對于牧童的“象征性”處理,背后是期盼自由、安穩生活的心愿。第二,以“牧童”為主角的詩歌也從無到有,甚至出現了專詠牧童的作品。
此外,唐代詩人對牧童的書寫也秉承《詩經》的風雅精神,其“觀風俗,知薄厚”“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文學傳統與唐王朝中后期的社會現實相結合,詩人將目光投向田野,以文筆揭露弊政,由此誕生了新的文學作品,代表作如張籍的《牧童詞》。
(二)隱逸與漫游的風氣
梁海燕認為,“‘牧童’形象的被發掘與確立,是唐詩人于詩歌史的一個貢獻”[4]53。《全唐詩》中涉及“牧童”的詩篇共計59 篇,其形象之豐富、描寫之多樣遠超前代。唐詩中之所以出現如此多的牧童形象,筆者以為,除了文學傳統上的原因之外,唐代文人隱逸與漫游的經歷也功不可沒。袁行霈在《中國文學史》中講道:“漫游、讀書山林、入幕與貶謫生活,從不同的層面豐富了唐文學的內涵,構成了唐文學多彩的情思格調。”[5]171總體來看,一方面這些隱逸與漫游開拓了詩人的眼界,拓寬了詩歌的表現范圍。在涉及“牧童”的詩篇中,有9 首詩題目即明確為“途中所作”或“游覽時作”,7 首可確證為詩人隱居或流離時所作。另一方面,處于漫游、歸隱時的作家心態千差萬別,眼中的景象自然也各不相同。總體來看,詩人們懷著不同的心境走進自然,對詩境的營造及物象的選擇讓讀者得以品味古人獨特的心態秉性,也為“牧童”形象增添了多樣的光彩。
二、唐詩中牧童的形象特征
(一)弄笛引歌天地間,未見其人先聞聲
笛樂器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在唐代,笛已有廣泛受眾。唐詩中也因此多了牧童且行且歌的瀟灑身影。據筆者統計,涉及牧童的59 首唐詩中,描寫到“吹笛”的共有11首,描寫到“歌唱”的共有5首。漫步于山水茫茫之間,忽聽一曲笛聲(歌聲),恰如潯陽江頭那無名的琵琶,雖不知源頭方位,心潮卻隨那模糊的感覺而起伏。這種“未見其人先聞其聲”的暗示寫法常見于詩中。徐鉉深諳此道,其“谿橋樹映行人渡,村徑風飄牧豎歌”[1]8602兩句,沒有渡河的嘈雜,也不見行進的塵煙。一個舒緩的“飄”字即寫出了風的輕柔,歌的悠揚。讀者雖不見人,卻能想象出遠處牧童且行且吟的身影。再如“遠岸牧童吹短笛,蓼花深處信牛行”[1]8690兩句,作者不寫遠處的牧童形貌如何,只寫對岸歌聲陣陣、花叢輕曳,那牧童“信牛由韁”、吹笛而行的自在情態便躍然紙上。詩人們欽慕他們“時復往來吹一曲,何愁南北不知音”[1]6386的自在。最終,“牧童”的身份隱去了,只有那一曲啟程、一曲歸家的笛聲飄蕩南北,天地皆是其知音,為其嘆賞。
(二)披蓑伴牛輕裝去,自由自在獨自行
與笛子相比,蓑衣與牛似乎才是牧童的必備之物。于濆在《山村曉思》中云:“牧童披短蓑,腰笛期煙渚。不問水邊人,騎牛傍山去。”[1]6925詩歌上一聯突出牧童“短蓑”“腰笛”的干練,緊接著順承下一聯的動態,意在顯示其自由自在的風采。簡約的形象描繪往往能誘發讀者豐富的想象。也正由于這種描寫方式的流行,牧童恰如江雪之上的笠翁一般,只留得一片“神氣”,可望而不可即,其符號屬性也因此大大增強了。
與簡約的外在裝束描寫相對應的,是他們行蹤的自由與神秘。面對陌生的來人,習慣了自由的他們時常帶有一份“騎牛不顧人,吹笛尋山去”[1]8626的自在散漫。看著牧童“牛得自由騎,春風細雨飛”[1]9610,大多數習慣了“聞見道理”的詩人們常常陷入少陵野老一般呼而不得的尷尬情態,讀者也在愕然之中觸動了那“絕假純真”的最初本心。
三、唐詩中牧童形象的文化內涵
(一)安寧和諧的象征
中國山水詩中的景物與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由生命安頓而來的欣慰感、幸福感所凝成的意象”[6]20。這種欣慰與幸福來源于身體的安頓與社會的和諧,既是靖節先生倍加珍惜的方宅草屋、巴山歸客數次夢回的燭邊燈前;也是黃發垂髫的各得其所,天下大同的治世之景。重讀唐詩,我們時常能在牧歸之圖中感受到心靈安頓,在田翁與牧童的嬉戲中體會到歌舞升平。
自《君子于役》將夕陽與歸禽并置,從而展示出帶有“原型”意味的歸來圖景以來,多少詩人皆于黃昏日暮之時升起鄉關之思,見荷鋤下山之人而屢動歸家之意。詩人善于將對于時序的敏感與對于漂泊的孤寂進行詩意的呈現,進而呈現出無數動人的景象:王維在《渭川田家》中云:“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1]1248自然時律與人情溫暖相映照。另一首詩《淇上田園即事》云:“日隱桑柘外,河明閭井間。牧童望村去,獵犬隨人還。”[1]1278則凸顯了心境的空明。他此刻沒有了上一首詩中“念”與“候”的意向性動作。詩中,一切情緒都在照相般的自然圖景中消失了。讀者亦如靜立的桑柘,伴著、看著亙古不變的“日落而息”的人們走向家園。對于志在隱居之人而言,“背琴鶴客歸松徑,橫笛牛童臥蓼灘”[1]8691是永遠的理想,松徑深處,蓼花叢中是他們的家,他們與牧童一齊而“臥”,宣告著心靈的安頓。
唐詩中,除了有著詩意色彩的“牧歸圖”之外,還有許多帶有凡俗氣息的恬靜畫面。譬如,很多涉及牧童的詩篇都會將“牧童”與“野老”(或野翁)對舉,營造出老幼同樂的理想田園風景。許渾落第歸鄉,所見“牧豎還呼犢,鄰翁亦抱孫”[1]607治愈了他的失意之苦。杜荀鶴乘興出游,目睹了“漁父晚船分浦釣,牧童寒笛倚牛吹”[1]7974。而早在先秦時期,孟子便以推己及人的態度與仁民愛物的情懷提出了老有所終、幼有所長的理想社會畫卷。因此,“老”與“幼”的對舉不僅是詩歌文體上的“對偶”條律使然,更是作者對社會理想的投射。每一個離鄉遠去的人都曾經屬于那片土地。游子深知,此刻的離去不是永別,因為總有那滄桑的身影在為之守候。為此,他們也樂于提起筆,在凝練的語句中寄托老幼和諧的永恒理想。
(二)時代變遷的見證
人世代謝,古今變遷,峴首山上羊公的勝跡等來了孟浩然慷慨的回音,而廣陵城內隋宮的廢殿卻招致李義山尖銳的詰問。然而永在的江山不只會留下感傷心靈的淚痕,“黍離離兮城坡坨,牛羊踐兮牧豎歌”[1]1576可能才是那古跡的常態。曾經的王城名宅如今已是荒草叢生,成為牛羊與牧童的樂園。劉滄《鄴都懷古》中“芳草自生宮殿處,牧童誰識帝王城”[1]6788,一個“誰識”透露出懷念的意味。王貞白則在《金陵懷古》中以“御路疊民冢,臺基聚牧童”[1]8061不動聲色地表達諷刺。最終則是“朝見牧豎集,夕聞棲鳥喧。蕭條灞亭岸,寂寞杜陵原”[1]8798,千言萬語化成了無言的蕭條與寂寞。與其感嘆惆悵、譏諷、寂寞,不如為如今黎庶的安樂而欣慰。曾經,這片土地是牧童的樂園;現在,悠遠的牧歌仍將洗刷歷史的傷痕。
實際上,除了詩歌的記錄之外,牧童也不止一次“闖入”史書記錄的現場。在先唐史籍涉及的牧童故事中,最有名的當屬發生在驪山的“牧豎之禍”。秦始皇雖力建陵墓,極盡奢侈,卻最終“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7]901。宏大的帝陵卻毀于小小的牧羊兒之手,此事雖未經考證,卻隨即成為典故。杜牧寫有“牧童火入九泉底,燒作灰時猶未枯”[1]5946,李白則直言:“君不見驪山茂陵盡灰滅,牧羊之子來攀登。”[1]207無論是否實有此事,文學家都在如斧鑿錚錚的言語中繼續著自己的審判。由牧童引燃的那終結一個時代的火焰,仍在文學家心中熊熊燃燒。
(三)社會民生的縮影
前文已述,唐代詩歌出現了很多偏于正面的牧童形象。牧童之“歌”、牧童之“游”、牧童之“歸”大多被賦予了理想化的色彩。這一現象背后的主要原因還在于唐代的社會總體較為穩定。李世民在征戰之余不忘創作,其《重幸武功》中“駐蹕撫田畯,回輿訪牧童”[1]1既透露出自我表彰之意,亦有步入盛世的雍容氣度。安史之亂后,以“元白”和“張王”為代表的詩人的創作逐步遠離了興象玲瓏的傳統審美模式,體現了寫實尚俗的新特征。其中,張籍的樂府詩往往由小的事件切入更廣泛的社會現象,代表之作就是《牧童詞》:“遠牧牛,繞村四面禾黍稠。陂中饑烏啄牛背,令我不得戲壟頭。……隔堤吹葉應同伴,還鼓長鞭三四聲。‘牛牛食草莫相觸,官家截爾頭上角!’”[1]4281此詩雖短,卻展現了豐富的社會信息,尤其結尾處官家截取牛角的典故暗示著晚唐時期的社會動蕩。此詩中的牧童真正走出了文人描繪的理想田園,并以自身獨特的生活方式展現了社會現實殘酷的一角。但可惜的是,其他作家大都沒有張籍一般深入社會的眼力,《全唐詩》中也再無其他現實性較強且專詠牧童的作品。這些詩句提醒著我們,文學既可以作為承載個人情志的清麗之“詩”,也可以作為觀風俗厚薄的現實之“風”。牧童可以作為觀照現實的一個入口,讓人們看到相對真切的民生細節。
四、結語
通過細讀《全唐詩》中涉及“牧童”的詩歌,我們仿佛也和他們一起走進了深林山澤之中,聆聽牧歌聲聲。牧童形象雖然在唐代詩歌中得到了更為充分、更“多維”的展現,但其內容的底色仍非“草野”的,而是文人化的。文人借用“牧童”展現了他們對于安寧的向往、對于歷史的沉思、對于現實的思考。盡管屬于牧童的時代已經遠去,但他們仍然是經典的精神符號,成為人們田園牧歌式理想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