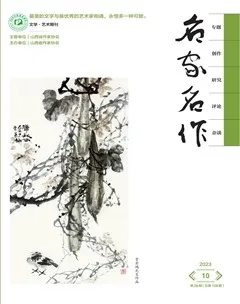當 歸
高夢瑤
漆團的墨云沉沉壓下遙北之際,嗚咽的風浮掠大地,嘶啞地吼著悲涼的腔調(diào)。黃沙被猛地揚起又落下,壓折貧瘠土地上殘存的干枯野草。幽黑色城門兀自直直地立著,斑駁的墻上布滿枯藤,脆弱地蓋住深紅的猙獰刀痕。
“噗通”,膝蓋的護甲重重摔在黃土上,長槍如林,撐起一座座鮮血浸染的碑……
“哥哥什么時候回來?”
一條跛腳的老黃狗路過城門,對著城門上一大一小的兩個身影干吠兩聲。只只皺了皺被凍得通紅的小鼻子,城門上縈繞著從北方蔓延而來的血腥味。他不安地扯了扯姐姐的大紅袖子,遠方除了若隱若現(xiàn)的火光,直撲面門的只有——無盡的大霧。他努力地用灰撲撲的小手揉了揉眼睛,卻什么也看不清。他只好轉(zhuǎn)頭望去,北方的小城夜里卻燈火通明,星星點點的光簇擁著中心的高樓,朱紅的柱,漆黑的瓦,聳立的檐角攀著青色的獸,風傳來檐下泠泠的輕響。金色的燈火下,艷麗的輕紗飛舞往復,青瓷的酒盞叮咣交錯,官貴人們的笑聲一路向南方傳去。
姐姐沒有說話,只只也不惱,他靜靜地把腦袋埋在姐姐的懷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她看。姐姐今天并沒有梳頭,鴉青的發(fā)絲散垂身后,金色的龍鳳攀上暗花的領(lǐng)口。腳邊的木燈發(fā)出淡淡的橘色光暈,朦朧地映著團簇的石榴。風拂過擺,石榴皺了,露出一截白色的衣角。她大紅的廣袖翻飛,像在黑漆的城門上盛開的虞美人。
“姐姐今天真好看!”
只只笑著,將小手向姐姐面前揮了揮,然后被騰空抱起,坐在了城墻邊。他將腳向外伸,沾著泥土的小腳興奮地在空中畫了一個圈。只只伸著脖子小心地向下望去,堅硬的石板上坑坑洼洼,似乎還回蕩著馬蹄的鏗鏘聲響。只只看得有些暈眩,他不安地把腳收回來,不敢再向下望。老黃狗蹲了一會兒,抬頭看了看城門上的兩個孤單身影,緩緩起身,耷拉著尾巴,一瘸一拐地消失在黑夜中。
只只看著那條行動不便的黃狗,腦袋中想起了家里僅有的財富——白馬。那是阿父留下的唯一物品,一匹年邁的白馬。姐姐說,當年就是那匹白馬將血痕遍體的阿父從戰(zhàn)場載回城門。可那時候只只還在娘親的肚子里,嘗到了娘親咽下肚的血淚,卻看不到寒窗外聳立的白幡。哭聲終在凜冽的寒風中,被黃沙沉沉掩埋。只只的記憶里從沒有過娘親和阿父。
“娘親和阿父一起去了很遠的地方。”
只只只記得姐姐對他說的話,繁星滿天時,他總是偷偷地跑去馬棚。他喜歡這匹白馬,他能從那濕轆的白色睫毛下看到自己小小的身影,看到阿父。
三更時,哥哥騎著白馬隨軍隊一起沖出這道漆黑的門,從那時起,只只就被姐姐拉著,趁亂登上城門頂,目送戰(zhàn)旗下黑點一般的人們呼喊著向北方遠去。
“砰啪”,突然,急促的長鳴在天邊響起,打斷了只只的思緒,伴隨著一點火光升空,有什么劃破大霧,猛然在耳邊炸響,北部的天空驀地被點亮,隨后,越來越多的火光升上天空,如流星般照亮整個黃沙飛揚的極北邊境大地。只只并不明白那是什么,只興奮地用小手指著天空。
“姐姐快看,煙花好漂亮。”
金色的火光讓只只想起了五天前的夜晚,那日只是個尋常的日子,卻比過年還熱鬧。金色的華蓋駛過街道,像星火組成的長龍。只只從沒見過那樣漂亮精致的馬車:棚頂四角上掛著紅色的流蘇和五顏六色的燈,一顆顆閃著光芒的珠子鑲嵌在架上。高大的馬用堅硬的鐵蹄將黃沙卷起,街邊未來得及收的攤鋪被踏碎。只只在俯身叩拜的人群中伸出頭去,想看清車里人的樣子,卻只有模糊的影。不一會兒,浩浩蕩蕩的車隊就快速消失在南方,他們跑得那樣急。只只望著南方,咯咯地笑起來,他想起了家門口沙狼追逐小蛇的樣子。
沉重的號角聲從前方傳來,漸漸地,天空的火光燃盡后緩緩落下,天地間一片死寂。
天亮了。
“嗒嗒”,一道雪白的身影搖搖晃晃地出現(xiàn)在北方。此時東側(cè)黑暗的天幕終于被撕裂出一個缺口,金光從中瀉下,照亮白馬柔軟的鬢毛。它慢慢地走向城門,濕轆的睫毛閃著皎潔的星光,深棕的馬蹄沉悶地敲在石板上,幾道鮮紅的血順著馬背而下,浸濕身下大片雪白的毛發(fā)。只只看見姐姐向白馬伸出手——蒼白的顫抖的手。
雪白的馬背上只掛著一條殘破的、染紅的白袍。
只只感受到姐姐緊握的手驀地松開,她緩緩站起來,解開精致的大紅排扣,揮手——卻是縞素。火紅的袍從城門下凄惶地落下,落到冰冷的石板上,晶瑩的淚從年輕的臉上無聲地落下,染紅蒼白的領(lǐng)口。
白馬走進城門后,漆黑的門又沉重地合上了。
“哥哥怎么沒回來?他也像娘親和阿父一樣去了遠方?”
刺骨的北風又開始肆虐黃沙滿地、寸草不生的北方孤境,新生的朝陽將粼粼金光灑向這座被遺棄的漠北小城。